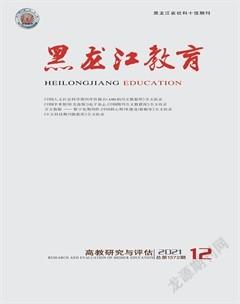脫域與再嵌入:后疫情時期高校愛國主義教育新范式
摘 ? ?要:重大疫情的爆發對教育生態場域產生了深刻影響,高校愛國主義教育在教育主客體之間、教育情感情緒、教育邊界等方面出現了脫域現象。根據互聯網的發展、大學生目前的生存狀態,重新審視和研判網絡環境嵌入的可能性及方式是后疫情時期高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文章從多元化知識體系的構建、儀式化傳播策略的運用和信任型虛擬場域的建構方面提出后疫情時期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新范式。
關鍵詞:脫域;后疫情;愛國主義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1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1002-4107(2021)12-0087-03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教育系統全面實施網絡教學,教育生態場域中的社會關系從原有的地域性關聯中“脫離出來”,出現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提出的“脫域”現象。面對后疫情常態化管理,高校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面臨前所未有的時空挑戰:教育主客體脫域后的教育活動是否能發揮原有作用,大學生在現存場域教育效果的實現是否真實,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應如何優化才能更好地適應疫情常態化管理后的發展,這一系列問題的提出都值得學界深入探索。
一、脫域:重大疫情對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
愛國主義教育不是單向的灌輸,它所營造的生態場域包括以社會環境為主體的宏觀生態場域、以學校環境為主體的中觀生態場域和以學生具體活動環境為主體的微觀生態場域。而重大疫情的爆發對教育生態場域產生了深刻影響,愛國主義教育生態場域出現脫域現象,表現在教育主客體之間、教育情緒情感、教育邊界等方面。
(一)教育主客體關系的脫域
1.支配關系虛擬化。疫情期間,愛國主義教育生態場域的宏觀、中觀、微觀場域幾乎全部集中到虛擬場域。網絡虛擬展廳的開設,數字化教育、學習方式的開展,教育主客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及過程,從原有的同一時間、共同空間中脫離出來,呈現虛擬化,基于實體空間所形成的愛國主義教育生態場域邏輯、文化習慣與制度規約在網絡場域中消解。
2.雙主體性顯著化。疫情使大學生從社會、學校等地方性空間中抽離出來,嵌入無限延伸的再造時空中,網絡空間成為學生與社會互動的無形載體和重要場域,而互聯網自由、開放的技術特質與去中心化、扁平化結構屬性,決定了教育雙方在網絡場域中的雙主體性更為凸顯。教育者不再擁有把握信息資源的優勢,受教育者在興趣和需求的指引下逐漸掌握更多的信息資本,教育生態場域中的“位置—權力關系”發生變化,雙主體性特征更為明顯。
3.教育引導式微化。網絡教學生態場域一方面改變了以往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的習慣和規則,對思政教育工作者把握網絡場域、評估學生網絡心理特征、采用新媒體技術開展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教育雙方互動關系的脫域使思政教育工作者對學生的學習效果、反饋無法及時把握,對教育活動反饋的情緒情感的真實性無法準確把握和判斷,致使疫情期間愛國主義教育引導力式微。
(二)教育情緒情感的脫域
互聯網教育活動使愛國主義教育的主客體雙方關系出現了實體場域的脫域現象,也讓雙方的教育情緒情感出現了脫域現象。
1.情緒情感脫域的原因。在學校實體場域中,教育主客體雙方的情緒情感在同一個場域發生,即便是偶爾采用網絡教學場域,所在場域也是公共的,比如教師在辦公場所,學生在圖書館、自習室等公共場所。而疫情后的網絡教育場域卻將教育主客體雙方從公共實體場域中脫離出來,置身于私人實體場域之中。
2.情緒情感脫域的影響。公共教學環境的脫域導致愛國主義教育主客體雙方的情緒情感脫域,愛國主義教育活動過程缺失了現場感和公共感,同時也消解了嚴肅性。思政教育工作要發揮作用,必須通過人來實施和轉化,這就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在開展教育活動過程中要具有飽滿的感染力、足夠的說服力,才能實現教育的影響力。但在私人實體場域中,由于公共場域氛圍的缺失,思政教育工作者的情緒情感無法做到沉浸,致使教育缺乏感染力,并且由傳統教育方式的習慣規則被打破所帶來的不適應也會影響教育方式的表達和傳播。另一方面學生在家庭場域中參與教育活動,脫離了公共教育場域的氛圍,現場實體場域的掌聲、互動被互聯網整整齊齊排列的表情符號替代,缺乏情緒渲染、情感共鳴,教育的實效性受到影響。
(三)教育邊界的脫域
1.信息優勢逐漸喪失。互聯網信息的市場化、商業化,易與高校教育信息資源產生勢差,學生與教師平等獲得各種教學資源和信息,學生易受互聯網信息影響,從而影響其價值觀的形成,比如學生受疫情前期網絡上流傳的許多負面信息或謠言的影響等。
2.學校資源實現共享。在線教育的發展促使高校各種教育資源在互聯網上共享、發展,學生能跨校獲得教育資源,比如疫情期間各高校通過互聯網開設了網絡講座、公益活動,開設線上校史館、博物館等,極大滿足了全國學生多元化教育資源的需求。
3.自我教育得到拓展。互聯網去中心化、去年齡化的特征,使信息資本被認同者獲得并加以自主傳播,高校學生自媒體的發達正是學生自主傳播的本能得以激發的表現。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利用特長對互聯網資源進行加工,并以更符合大學生需求的表現方式進行傳播,不僅滿足了大學生的個性化需求,也豐富了教育資源。比如疫情期間大學生自發創作的抗疫文化作品、電腦模擬仿真疫情趨勢等都成為高校愛國主義教育資源的重要素材。
二、再嵌入:后疫情時期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挑戰與機遇
后疫情時期高校愛國主義教育需要根據互聯網的發展、大學生目前的生存狀態,研判高校愛國主義教育主客體之間、教育情緒情感及教育邊界重新嵌入網絡環境的可能性及方式,對嵌入的困難作充分的評估和準備。
(一)嵌入的挑戰性
1.網絡“語言”的蒼白。高校近年來重視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在網絡“語言”把握方面較社會媒體依舊處于弱勢。一來教育主體表達方式上較多采用生硬的“灌輸式”,缺乏對網絡語言表達、網絡空間傳播規律的有效運用,將愛國主義教育內容與網絡載體的“沉浸式”把握方面存在欠缺,致使網絡教育內容帶有明顯的“說教”痕跡,相比社會媒體的傳播內容缺少親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二來在內容選擇上,疫情期間的愛國主義教育內容“校本”特征明顯,但疏于對內容的邏輯梳理,在同疫情期間愛國主義事跡相結合的基礎上缺乏充分論證和說理,欠缺多角度多人群的論證模式,致使高校間愛國主義教育內容“雷同”度較高,內容淺顯,新意不足,與高校的實際教育能力和水平尚有距離。
2.網絡發展的“洼地”。長期以來互聯網在技術水平、文化傳播力等方面高度發展,較校園網絡文化發展技術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同時互聯網文化價值觀的多樣性對大學生多元化興趣愛好有更強的吸引力,是影響大學生價值觀形成的重要因素。疫情期間網絡文化的高度發展進一步加快大學生對高校網絡的離心率,影響了高校教育主體對教育客體的把握。另一方面社會主流媒體在疫情期間通過其掌握的信息優勢較早承擔起媒體教育責任,對大學生產生重要教育影響,在營造全社會愛國主義氛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致使高校教育主體既處于網絡信息弱勢,也缺乏網絡“先手”優勢。
3.網絡“信任”的短板。社會關系的嵌入依賴信任,而大學生是否信任網絡環境中的高校教育主體,取決于網絡信息優勢和網絡教育管理能力方面的完善程度。在天然缺乏網絡信息優勢的前提下,長期以來高校網絡輿情處理能力不足,系統的網絡教育管理機制構建尚待時日,致使教育主客體間在互聯網教育關系中缺乏網絡“信任”基礎。疫情期間由于網絡成為唯一的教學場域,教育主客體關系的脫域,使雙方因時空錯位產生誤解且不易被察覺。教育情緒情感的脫域又使教育活動不能完全符合教育設計和達到教育目的,導致大學生共情性減弱,影響教育效果。可見疫情期間的教育場域再次削弱了大學生對高校教育主體的網絡“信任”。
(二)嵌入的可能性
1.愛國主義實踐獲得認同。疫情期間社會各界涌現出來的先進人物事跡、各高校大學生志愿者投身疫情志愿服務的實踐經歷,得到大學生的廣泛高度認同。盡管多數大學生并沒有機會直接參與疫情志愿服務,但是通過互聯網宣傳、教育,大學生對參與疫情志愿服務取得高度自豪感的共識,對“愛國主義本質是愛黨、愛國和愛社會主義三者的統一”建立了更直觀的認知,實踐活動彌補了思政教育工作者在教育過程中的脫域。
2.愛國主義情感得到共鳴。疫情期間社會媒體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抗疫防疫期間涌現的模范人物、先進事跡作了大量宣傳。從網絡輿論來看,大學生高度認可并正面評價,愛國主義情緒情感在互聯網上不斷高漲,這無疑對學生教育情緒情感的脫域給予了一定的彌補。
3.愛國主義形式大大豐富。疫情期間社會媒體加大開發微課、微視頻等教育資源和在線課程的力度,研發體現愛國主義教育要求的音樂、舞蹈、戲劇作品等互聯網產品,豐富了愛國主義教育形式,有效利用了教育邊界的脫域,以潛移默化的方式進一步增強了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實踐:后疫情時期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的新范式
(一)多元化知識體系的構建
傳統的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知識體系構建主要以教師單向灌輸為主,學校、學院制定愛國主義教育方案,思政工作者根據愛國主義教育內容開展教育活動。在這樣的機制下,愛國主義教育知識體系遵循高度的統一化、客觀化、標準化,對學生的主體地位缺乏足夠重視。疫情期間教育主客體關系的脫域影響了雙方的地位變化,學生的主體需求、個性化發展在互聯網土壤中得以充分展示,對促進高校愛國主義多元化知識體系構建提出迫切要求。
一要使教育主體多元化。互聯網技術為教育主體實現在網絡上的數字化,以不同的表現形式為實現自身價值提供了可能性。重點把握幾支關鍵隊伍,凝聚教師、教輔管理隊伍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入第一、二、三課堂,充分運用學生黨員、學生干部隊伍的引領作用,做好輿論引導,充分利用大學生網絡意見領袖隊伍在互聯網上的活躍度,鼓勵自媒體創作,豐富愛國主義教育素材,使愛國主義教育主體多元化。
二要實現需求個性化。將全面覆蓋和突出重點結合起來,充分調研需求,完善效果反饋,分層次、分對象,針對不同年級、不同專業、不同身份的大學生制定不同內容的教育方案。結合學生主體在互聯網上的個性發展需求,豐富愛國主義教育知識體系的認知結構和情感結構,從感性到理性,從全面到具體,從主觀到客觀,滿足不同時期不同知識結構的學生需求。
三要專家權威凸顯化。加強思政專家學者隊伍建設,把愛國主義教育與哲學社會科學相關專業課程有機結合,通過完善高校愛國主義教育網絡建設,充分利用疫情期間涌現的大量愛國主義教育素材,設置理論學習、熱點討論等項目,組織專家學者制作思想性、教育性、生動性強的愛國主義教育課件,彌補互聯網專業學術型知識的缺乏,增強說理性,突出思想內涵,強化教育引導。
(二)儀式化傳播策略的運用
一要提升愛國主義教育實體學習環境感受。根據后疫情時期疫情防控的要求,返校復工后高校應通過知識教育、國情教育、主題實踐、勞動實踐等形式深化愛國主義教育行動實踐,充分利用校史資源開發現場愛國主義教育學習時間場所,彌補疫情期間教育主客體雙方脫域帶來的消極影響。比如通過校內紅色資源場所開設實景微課,打造“家門口”學習教育陣地;舉辦抗疫書畫作品展,通過抗疫藝術作品展現文化感染力,傳達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舉辦校史主題展,通過校史文化展覽、講述高校紅色文化故事,感受學校精神和紅色底蘊等。
二要創新愛國主義教育的儀式化傳播路徑。首先要提升話語符號的網絡重構能力。近年來主流媒體與新媒體不斷融合探索,重大主題報道在儀式化傳播中的影響力劇增。“主流話語、民間話語和新媒體話語之間史無前例地形成合力,主題傳播過程體現出話語共建、參與互動、群體認同的儀式化傳播特點”[1]。高校愛國主義教育應從話語符號、話語模式、話語載體等方面優化愛國主義教育網絡語言,提升符號感染力。其次要提升虛擬技術改善現場體驗感受能力。在5G、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支撐下,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MR(混合現實)和流媒體、超高清等技術手段為構建全息化、可視化的教學流程、建設虛擬仿真教學資源、打造思想政治理論課虛擬仿真體驗教學中心提供可能,有助于為學生提供沉浸式、交互式的學習體驗,營造代入感強烈的儀式氛圍。最后要提升高校學生虛擬社群的儀式傳播能力。虛擬社群促使“儀式化”互動由單向轉為多向,高校學生虛擬社群主要表現為類型豐富的趣緣社群,比如專業學習群、興趣愛好群、學生骨干群等,通過交流溝通、共享資源等互動,“激活人際關系的微弱鏈接,拓展人際關系網絡,深化強連接網絡的情感、信任與互惠關系”[2]。有效把握高校學生虛擬社群,提升學生網絡社交能力,是愛國主義教育儀式化傳播路徑得以實現的重要因素。
(三)信任型虛擬場域的建構
一是革新高校網絡管理結構。后疫情時期,網絡管理已經成為教育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應積極優化網絡管理結構,建設愛國主義網絡教學支撐平臺,實現網絡課程、課件、案例、題庫、媒體素材等與愛國主義教育資源的互通共享,促進愛國主義教學內容更豐富,網絡支撐環境更優化,打好高校虛擬場域建設的機制信任基礎。
二是提高高校網絡管理水平。“對于一個行動持續可見而且思維過程具有透明度的人,或者對于一個完全知曉怎樣運行的系統,不存在對他或它是否信任的問題”[3]。要取得他人的信任,機制本身要做到提供完整的信息。所以高校在完善教育管理機構的同時,更要加強網絡教育管理機制信息的公開,使學生對高校網絡教育管理機制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提高思政工作者的網絡管理水平,及時準確掌握學生思想動態,做好解釋說明,平衡教育主客體之間的信息差,打好高校虛擬場域建設的群眾信任基礎。
三是引導高校虛擬場域生態。高校虛擬場域社交有別于社會虛擬場域的陌生人社交,也有別于熟人社交,它介于兩者之間,主要是在高校中各學生群之間建立的場域。學生通過共同的學習目標、工作主旨或興趣愛好聚攏在虛擬社群,從陌生到比較熟悉,但線下可能并不相識,這種關系很脆弱,但是又有極強的影響力。高校應加強虛擬場域生態的價值觀引導,識別、判斷虛擬社群活動的目的、價值和影響力,及時有效地發現、規避隱患,建設積極健康的高校虛擬場域生態,發揮高校傳播先進社會文化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王軍.新媒體語境下重大主題儀式化傳播的實現路徑及其文化圖景——以愛國主題為例[J].山東社會科學,2020(6).
[2]蔡騏,岳璐.網絡虛擬社區人際關系建構的路徑、模式與價值[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8(9).
[3][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29.
收稿日期:2021-04-10
作者簡介:魏巍(1979—),女,上海人,華東政法大學黨委學生工作部講師,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項目:2020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項目“‘二次元’文化的美育價值研究”(C2-2020043);華東政法大學2019年度科學研究項目“二次元文化對當代大學生價值觀的影響研究”(19HZK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