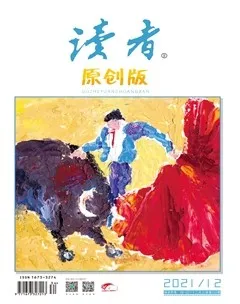瓦三章
古保祥
在鄉下,最讓我哀傷的就是瓦。
風吹日曬,雨雪風霜,最吃虧的是瓦,最不會享受的也是瓦。
瓦高高在上,貌似高冷,但它們罩著你,護著蒼生。如果沒有它們,雨砸下來,落進房子里,你的蝸居很快便會成了澤國。
所以,我們最應該感謝的就是瓦,普普通通卻默不作聲的瓦。
瓦從不悲傷,陽光曬裂了照樣堅持工作,不敢懈怠;瓦從不炒作,它不像蟬那樣站在高處,拼命宣傳自我。我們通常選擇躲在屋檐下看雨,雨從瓦片上有聲有色地流過。一兩片碎裂的瓦跌在地上,碎成一地蒼涼。
瓦通常喜歡與鳥站在一起,鳥是瓦的情人,但鳥通常選擇始亂終棄,它們從瓦的身上跑到樹上,瓦不哀嘆,不惆悵,瓦始終如一,不忘初心。
苔蘚一般喜歡寄居在瓦的身上,在瓦的縫隙里,青苔珠胎暗結,它們與瓦片一起成長。青苔是開在瓦上的花,一開就是百年千年。
瓦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工作,它們在懸崖上展覽千年。瓦從窯爐里便被千度鑄燒,到最后,結局只能是破碎。其實所有生物結局都一樣,包括人類。
父親說,沒有瓦的鄉下不叫鄉下。
我每年回鄉下,下車后就喜歡看鄉下的瓦,古樸典雅,或紅或紫,鑲嵌在時間的維度上,不僅僅是好看,好像歲月產生了錯覺,時光回溯到了幼年。
我更喜歡看在瓦窯里辛苦的農人們,他們每個人都像父親一樣偉大。
他們的皮膚與瓦一樣有光彩,韌性十足,堅硬無比。他們工作起來沒有時間概念,像瓦片,任憑歲月變遷,他們照樣艱苦樸素。
父親手握藍瓦,辛苦勞作。他像瓦,樸素實在,不會賣弄,不投機取巧。瓦片碎了,鉆進肉里,血與瓦融在一起,瓦有了生氣,鮮艷無比。在鄉下,每個父親的手里面都握著若干小瓦片,它們像子彈,永遠長在肉里,到老時依然堅固,像骨骼,清奇、硬朗、有骨氣。
父親給瓦鋪打小工,為煤廠打零工,為磚廠打短工,為全家打長工,不會歇,不敢歇。父親一輩子就喜歡與泥土打交道,而泥土塑造了瓦片,父親與瓦一脈相承,父親的基因里有了瓦的博大,瓦的生命里有了父親的血汗。
遇到一個瓦匠,靈巧的雙手在瓦片上糾纏,瓦聽話、謙恭,一片片瓦被他整齊地堆在土地上,不需多久,哪家的房頂上便會出現它們矯健的身影。
父親喜歡原始的青瓦,他說這種瓦大氣、古典,有一種滄桑美。其實我知道,他是在懷念他的父親,懷念他的先輩。那種瓦在歷史上存在了幾個世紀,它們見證過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忙碌勞作。由生到老,它們的工藝簡單卻成熟,就像他們的愛情,一輩子只愛一個人,一輩子也只夠愛一個人。
江南的瓦,如處在花樣年華的少女,奢華有情調;塞北的瓦,滄桑堅硬,安如磐石,能抗拒世間所有嚴寒;滬上的瓦,博大豐滿,華麗璀璨,像金,像銀,像無垠的江山社稷。
走在蘇州河邊,我居然碰到一個賣瓦片的人,他賣的是關于瓦的藝術品。一地的瓦片,各式各樣,琳瑯滿目,隨便挑,隨便給錢。我看到一片秦朝的瓦,古色古香。我與他溝通,他侃侃而談:“最能代表古代中國的物品就是瓦片,瓦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
我看到凌厲的語言利器在空中飛舞,從春秋到戰國,到兩漢,再到盛唐,最后到了清朝。他的語言像一只貓,縱游在歷史長廊里,將關于瓦的文化講述得豐滿感動、淋漓盡致,讓人醍醐灌頂,禁不住潸然淚下。
我坐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里,看到雨水無情地從瓦片上滴落,我細數著雨的滴數,默想著瓦的承受能力。我又看到密密麻麻的瓦片擠在一起,它們團結有力,一塊碎了,并不會對另一片產生負面影響。一對新人剛剛在院里成婚,成群的喜鵲奔走相告,落在瓦片上,它們在瓦上開會。瓦就是鳥類的會議桌。
在豫北,我看到一群孩子在一塊破碎的瓦片上焙雞翅,香氣四溢,讓人垂涎欲滴。此時的瓦片,感慨于自己作用的偉大,而孩子們驚異于瓦片的堅強。
我認真地端詳過一片瓦,瓦與我對視,我看到瓦的紋路,溝壑叢生,令人不忍卒讀。這就是瓦的路,從生到死的路,瓦的身上有高山,也有低谷。我有些自傲于自己的發現,而瓦從不真情流露。
再大的功勞,也不會讓一片瓦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