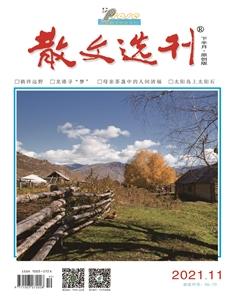徜徉遠野
習習

1
說的是柳田國男的“遠野”。
明治四十二年(1909 年),從初春開始,一個叫佐佐木鏡石的人經常去柳田國男住處,給他講了很多地處幽遠的遠野鄉的故事,柳田國男將佐佐木鏡石講的記錄下來,便有了《遠野物語》這本書。“物語(ものがたり)”即故事、傳說,日本古典文學的一種體裁,是在口頭說唱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學樣式,后來又受了中國六朝、隋唐傳奇文學的影響。
我見到不少國內作家的“物語”,大都遠離故事,只是書寫某些器物,大約沒大明白“物語”本來的意思。
話說回來。柳田國男是日本民俗學的奠基人,也是日本民俗學田野調查第一人。他將日本民俗學視為發現日本國民性的重要途徑。他認為,傳說、昔話、神話的傳承跟民眾的心理、信仰等有密切關系,因此,他將民俗學研究視為理解日本歷史和民族性格的方法之一。
《遠野物語》是柳田國男一系列日本民俗學典籍中的一本。
2
柳田國男1962 年以87 歲高齡去世時,我還沒有出生。
柳田國男的“遠野”是一個鄉村的名字,但我喜歡這本書的一個主要原因確乎是遠野鄉里所呈現的漢語語詞的“遠野”所具有的意義。書里的大部分故事都有澄明開朗的自然背景,這樣,即便很小的事,有了山林、天空、土地、江河,故事再小都顯得要扎實起來了,就像有了土,再小的種子就可以抓著土要生芽了。有了這樣的背景,書里的故事很容易讓人有想象的空間。所以,《遠野物語》盡管是一個個片段式的記述,但讀起來不促狹、不幽澀、不憋悶。
有一天,小國村的一位男子去旱池峰砍竹子時,看見一個大漢睡在一片茂密的地竹中(地竹為深山上生長的一種矮小的竹子——原文注解)。這位大漢仰臥著,鼾聲如雷,旁邊放著他脫掉的地竹編成的草鞋,大小有三尺左右。(《遠野物語·三十》)
是不是能聞見竹子的味道?三尺有多長,想象一下,心里是不是想笑呢?
行至百望山,留宿一晚,便時常可在深夜間看到天空微明的景象。秋天,進山采蘑菇后留宿山中的人經常會遇見這種現象,有時還會聽到山谷那邊傳來歌聲或是大樹砍倒的聲音。這座山深不可測,五月份去割萱草時,從遠處望去,梧桐花漫山遍野,有如紫云繚繞,但人們無法靠近去欣賞。(《遠野物語·三十三》)
多么爛漫的秋天。這段物語讓我想起日本電影《絕唱》,電影里的一首主題歌回環往復,歌聲響起時,鏡頭反復閃回一個陽光明媚、綠意盎然的山谷,鏡頭由遠而近,近至一棵小樹,樹葉被陽光照得透明,憂傷靜緩的《伐木歌》唱到這棵發光的小樹時,總是“嘎”地響起一聲響徹山谷的砍斧聲,每響一次,心都要驚一下……說到日本電影,在氣質和內容上最接近柳田國男的,要屬導演今村昌平了。今村昌平導演的《諸神的欲望》,上映于1968 年,日本學者正深入于國民性的探究。《諸神的欲望》講的是在偏僻孤島上發生的事情,今村昌平努力在片中集人類學、民俗學的要素。電影里勾連著一個看似游離于主要情節之外的富有寓意的鏡頭:一棵茂盛的樹下,一個說唱藝人彈琴說唱,似乎片子里講述的島上發生的一切,正在被他說唱。說唱,正是日本物語文學的雛形。和柳田國男研究民俗學的目的近似,今村昌平想借這部電影揭示日本民眾一種歷史的潛在的意識,包括人與人、人與巫、人與神之間的復雜關系。鏡頭當然離不開遠野、沙灘、大海,在這樣一個未可知的遼遠中,集結在一個孤獨的漁村里的一小群人,生活的境遇顯得更加混沌、艱難和復雜。我深記這個情節,一望無際的大海上,一對兒相愛的兄妹拼命劃著小船想逃離孤島,后面追來一只大船,上面整齊排列著兩行劃槳人,他們奮力劃槳,臉上一律戴著巫師的面具,看不見他們的臉面,他們追上小船,奮力揮動船槳,暗色的血漿濺起,面具不動聲色。無可抗拒的巫神的殺伐,強大與弱小,集體和個人,每每想起這個情節,也總是心驚。作為民俗學的一個符號,面具代表介于神和人之間的一個神秘的身份,這個元素,我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日本的黑白電影里,反復看到。
在深山里搭小屋時,常常會聽見從旁邊的森林里傳出類似巨樹被砍倒的聲響。在這片土地上,你問十個人就會有十個人說自己經歷過這種事。剛開始是斧子“咚——咚——咚”,過了一會兒就變成了“嘎吱——嘎吱——嘎吱”緩緩倒地的聲音,據說人們甚至能感覺到木頭倒下時樹梢攪動空氣帶來的輕風。(《遠野物語拾遺·一百六十四》)
這則故事來自柳田國男《遠野物語》原本的補充拾遺部分,我也放在這里,作為對我引用的上一則故事的補充。
3
遠野的六日町曾發生過火災,當時不曉得從哪里來了個小孩,拿著個笸籮就滅起火來。火被撲滅后,那個孩子不見了。人們都覺得離奇。這時,在下橫町一個叫青柳某的澡堂子里,人們發現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小孩子的泥腳印。循著腳印走,就來到這家的佛堂面前,佛壇里有一個小小的阿彌陀佛像。只見那佛像從頭頂到腳尖兒都糊滿了泥,大汗淋漓。(《遠野物語拾遺·六十二》)
這段物語是《遠野物語》出版后,柳田國男追加的內容之一,收在《遠野物語拾遺》中。其實,與這個溫情生動的故事類似的,在《遠野物語》也有一個。說一家人在插秧,眼看第二天要變天了,可還剩一塊兒地無論如何都插不完了,家人們焦急地低聲議論著,正說著,不知從哪里跑出一個小男孩,一到地里就幫他們干起活來,一家人終于趕在天黑前把秧苗插好了。這家人想邀請這個男孩到家里吃晚飯,可發現他早已不見蹤影。幾個人回到家里,發現緣廊上有很多小小的泥腳印,一點點延伸到了祭祀屋內的神龕前,拉開神龕一看,發現神像的下半身還沾著泥漿。
山口、飯豐、駙馬牛的字荒川東禪寺,以及火渡、青屜字中澤、土淵村字土淵都有一個地方叫壇之塙(即丘陵上蓋有墳冢的地方——原文譯者注),壇之塙附近一定會有一個地方叫蓮臺野。很久以前有把年過六旬的老人趕到蓮臺野的習俗。老人們不能白白等死,白天會到地里干農活,維持生計。因此,直到現在,山口、土淵一帶還把早上到農田干活稱為“出墳”,把傍晚從農田歸來稱為“歸墳”。(《遠野物語·一百一十一》)
這則物語讀起來驚心。最驚心的是,有一次,我竟在蘭州附近臨洮縣的馬家窯遺址,聽到當地人講到類似的事情。自然是從陶器說起的,說馬家窯遺存到今天的陶器,除了當年先民日用的、祭祀陪葬的,還有許多是在偏遠的小山洞里發現的。傳說,那時,部族里的老弱病殘會自覺地或者被族人送到一個個孤立的小山洞里,因為部族的糧食不能再繼續供給這些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了。剛開始,部族的人會拿些飯食添進洞門口的器皿里,漸漸地這些人就被完全遺棄了。這些器形大都是一種小口鼓腹的小甕,盛載的食物只夠不多時日的供給,甕器便于盛裝和貯藏食物。這些器皿頗似倒計時的沙漏。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對于人類,這種約定俗成顯出一種平靜的殘酷。
馬家窯遺址在緊鄰洮河的一片黃土臺地上,而今,依舊能撿拾到很多破碎的陶片。我記得第一次去馬家窯遺址時,前一天剛下過一場大雨,雨水沖刷過松軟的土坡,地上露出一層新的碎陶。我不知道撿拾到的哪一塊兒出自那樣的小甕。
還要說到今村昌平。對我而言,對日本歷史、文化的了解,大都通過書籍和電影。今村昌平1983 年導演了另一部電影,名叫《楢山節考》。《楢山節考》少了《諸神的欲望》里豐沛原始的野性,但依舊承襲了他特有的客觀、冷靜,依舊和人類學、民俗學相關。看他這部電影時,我還是很自然地聯想到了柳田國男。作為將日本“在野的”民俗學學問,變為大學正式科目,并被稱為“民俗學之父”的柳田國男,他的學術對日本的影響,包括對文化藝術的影響,可以想見。而且也有著時間上的承襲和流續,柳田國男出生于1875 年,今村昌平出生于51年后的1926 年。《諸神的欲望》上映時,是柳田國男去世的第四個年頭,在我看來,這部表達日本民俗學內容的老電影就是對柳田國男的致敬之作。
今村昌平的《楢山節考》在中國上映時,有很多負面的評價,比如說它粗鄙、原始、丑陋等等。我想是因為很多觀眾對今村昌平的學術理想及日本民俗學的發展不夠了解的緣故。設若觀眾之前閱讀了柳田國男的書籍,并了解了他對日本學術界的影響,斷然不會對今村昌平的電影貿然進行評價。
《楢山節考》——名字已有民俗學的味道——對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空間的觀察和考證。這部電影講的是這樣的故事,日本某地深山有個村落,村后面有一個綿延不絕的大山,叫楢山,山頂終年積雪。村里人生活非常貧寒,沒有多余的糧食給老人和小孩吃,于是村里有了個世代相傳的習俗:每戶人家,只有大兒子可以娶妻生子,用這樣的方法減少吃飯的人口,此外,70 歲的男人和活到60 歲的女人,由兒子背著他們到村后的楢山上,任其自生自滅。
電影里的老母親馬上60 歲了,但耳聰目明,身體硬朗。怕別人笑她老不死,她背著人偷偷敲掉了幾顆牙齒。眼看離上山的時日不多了,她終于了結了大兒子的續弦之事,又想辦法叫不能娶妻的二兒子初嘗了一次魚水之歡,做完這些,便心無牽絆地由大兒子背著上了楢山。電影里有大段背母上山的鏡頭,母親在兒子背上,兩個人看不到彼此的表情,兒子和母親都懷著復雜難言的情感,但今村昌平不讓他們有任何的傾訴和表達。兒子將母親放置在堆滿骨骸的山上,按規矩不能回頭,一口氣跑下楢山。他身后的楢山,在觀眾的眼前,忽然間,彌漫起漫天大雪,壓抑的情感終于借雪花紛紛揚揚。很明顯,相比15 年前的《諸神的欲望》,《楢山節考》的電影鏡頭更加精工細琢。兩部片子都包藏著很大的民俗學概念,包含著導演想借風俗故事呈現日本人某種性格和精神的強烈意愿。
4
說得有些遠了。
回到“遠野”。夜深人靜時,捧著《遠野物語》這部半個多世紀前的日本民俗學著作,閱讀的目的并不一定要著意于作者的寫作目的。但長久地困縛于城市,在聞不見泥土氣味的高樓上,通過這一段段文字,徜徉于遠野,眺望云天、山巒,嗅聞花木流水,看那些泥土色調的故事和人,這叫身心多么妥帖。
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也就是佐佐木鏡石給柳田國男講過這本書的內容的第二年,柳田國男前往遠野鄉,親眼看到了過盂蘭盆節(中國一般稱為中元節,亦即鬼節)的遠野鄉的種種景象。他在描述了這些景象的序言里,表達了出版《遠野物語》的一些想法:“出版這樣的書,不免會被人指責說是把自己狹隘的趣味強加給別人,但我卻敢說,想必在聽了這樣的故事、見識到這樣的地方后,沒有人會不想講述給其他人聽吧,至少我的朋友中沒有這樣沉默又極為嚴謹的人。”
我不是那樣沉默而又極為嚴謹的人。而且,我舍不得結尾,還想借柳田國男的口吻講一個看上去有些荒誕、有些黑色幽默,但對主人公而言確實有些悲慘的故事:
村里有一戶富庶的世家,主人有一次從城里醉酒而歸,一路上不斷聽到狼叫。他自己便學著叫了幾聲。這時,狼群嚎叫著跟隨而來,他慌忙逃回家,關緊門窗,躲在室內。狼群整夜在窗外嚎叫,直到第二天天明,才盡散去。他出去一看,狼從馬廄下挖地道而入,七匹馬全被咬死。這戶世家從此一蹶不振,傾家蕩產。
這就是一個有錢的醉鬼學了幾聲狼叫的后果。
想到蒲松齡筆下那兩個狡黠的狼了嗎?蒲松齡在結尾處說道:“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 止增笑耳。”這就是蒲松齡的文筆,相比柳田國男的這則物語,蒲松齡笑得何等輕松。
作為收尾,一笑耳。
好了,現在暫且可以合上《遠野物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