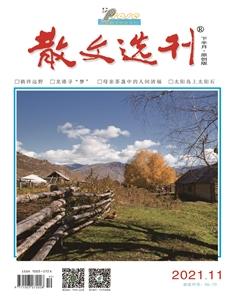久違的笑容
蔣小林

一年前,我考上了縣城的一所中學,當我捧著高中錄取通知書笑吟吟地回家告訴爹娘后,爹娘激動之余便是憂愁滿面,爹望著錄取通知書發出一聲聲沉重的嘆息,娘背著我悄然抹淚。那年月,靠工分吃飯,家里的日子本就捉襟見肘,十六歲的我完全可以在家掙工分,至少可以讓家里的日子過得不再那么艱難,可我偏偏考上了縣城的一所中學。
爹為了供我上學,給我湊學費、生活費,下午生產隊收工之后,在三叔的悄悄帶領下,到遠在十里外的打石場,頂著星星月亮抬石頭上車,抬一塊石頭二角錢,四人平分,一人五分錢。爹和三叔在生產隊收工后摸著黑如奔命一般,有時在家喝兩碗冷苞谷糊糊,有時家里斷糧實在沒有吃的,爹就在水缸里舀一大瓢水灌下肚便和三叔深一腳淺一腳朝石場趕……
那一晚,爹和三叔像往常一樣摸著黑向石場趕,剛到石場,天突降大雨,望著無情的天,嘩嘩而降的暴雨,爹唉聲嘆氣。因為他心里比誰都清楚,明天又是周末,我又要返家,下一個星期的生活費還沒湊齊。看著在一起搭伙兩個抬石頭的伙伴冒著雨回家去了,三叔跟爹商量也準備回家,等天晴了再來。可爹不肯走,無論三叔怎樣勸也拗不過固執的爹,無奈之下三叔只好被迫留了下來,本是四個人一起抬的大石條,走了兩人只剩三叔和爹,爹在小石屋里拿出木杠、大麻繩和三叔抬對肩,爹頭頂舊草帽,冒著雨抬了起來。沉重的石頭壓在了爹的肩頭,爹的臉上分不清是汗水還是雨水。爹和三叔咬著牙,一步一步掙扎在泥濘不堪的道路上,來來回回,一趟又一趟,雨順著爹的背流。為了掙幺兒讀書的學費、生活費,路再難,肩頭的擔子再重,風雨中爹也緊咬牙關任憑幾百斤的石頭壓在肩頭,在泥濘中一步步艱難前行。眼看一拖拉機石頭已抬了一大半,爹腳下膠鞋一滑,一個趔趄,壓在肩頭的木杠瞬間滑落,石頭砸在了地上,幸虧三叔手腳快,一把拉住了爹,爹才沒有栽倒在地。這一個趔趄,重重閃了爹的腰,剎那間,腰疼痛不已,爹被三叔扶回了家。
娘要向隊長請幾天假讓爹在家臥床養病,無論娘怎么勸,要強的爹也不準娘去請假,他讓娘用碗倒了半碗白酒,在他腰上搓,用力揉。第二天忍著疼照樣出工,到生產隊掙工分,挖土、挑糞、犁田,直到一天腰痛得站不起來,爹才被迫躺在床上。娘在房前屋后扯些草藥敷,用酒擦,仍不見好轉,爹的腰一天比一天疼得厲害。
此刻,爹一陣陣痛苦的呻吟聲在小屋里響起,我心如刀絞,站在床前久久不肯離去,本是返校讀書的日子,想到一貧如洗的家,臥病在床的爹,心里矛盾,忐忑不安,有了厭學的情緒。無論爹怎樣催我出去吃早飯,我都不肯走。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天都大亮了,因為從家里到學校至少要走三個小時:“你快出去吃飯,吃完趕快返校讀書,不要守在我床邊!”爹說完又呻吟了起來。我終于鼓起勇氣,大聲地說道:“爹!我不去讀書了,在家掙工分!”話剛出口,爹氣得臉色鐵青,瞪著雙眸,突然想說什么,張開嘴喉嚨卻被什么堵著一樣,一句話也沒說出來。他喘著粗氣抓起床頭的一個空碗朝我擲了過來,大聲罵道:“你這個沒出息的東西,我和你娘忍饑挨餓,供你讀書,你卻說出這樣的混蛋話來,如果你想一輩子背太陽過山,我就成全你,扁擔和鋤頭在門角里,今天你就跟你娘出門上坡掙工分!”我從未見過爹這樣兇,嚇得我大氣也不敢出,望著面前摔碎的碗,破碎的仿佛就是爹那一顆傷心欲絕的心,娘走了過來,把我拉出了爹的房間。
桌上早已舀好了一大碗苞谷粑粑,爹和娘平時舍不得煮苞谷粑粑,一日三餐總是喝稀得能照出人影的苞谷糊糊,只有周末等我回家,一家人才能吃一頓苞谷粑粑,正值青黃不接的時節,農村人說的過荒月,家家日子都難熬,這幾十斤苞谷還是娘翻山越嶺從大舅家背回來的。想到爹的病,我坐在桌前,無言地流著淚,握在手中的筷子仿若千斤。娘一個勁催我快點吃。“你和爹早飯吃啥?”我不安地問。“你別管那么多,我和你爹餓不著。”娘的話說得很輕松。我呆坐在桌前,半口也吃不下,爹臥病在床,一日三餐盡喝苞谷糊糊,我站起身,從碗柜里拿出一個空碗,把桌上的那碗熱氣騰騰的苞谷粑端到了爹的床前。爹側著身子,面朝里面,看樣子怒氣未消。我喊了幾聲,他沒應聲。最后我大聲地說:“爹!我錯了,我不該說那話!不該惹你生氣!”我說完,眼淚滾落在熱氣騰騰的碗里。爹慢慢轉過身,看了我許久,半天沒有吭聲,許久才開口道:“快吃吧,吃完好好讀書。”我無言地點點頭,把那碗苞谷粑粑放在床邊的一個柜子上,從碗里分了一半雙手遞給爹:“爹!這是給你的,你吃點吧!”爹接過碗,偷偷地把臉別了過去。最后爹掙扎著身體下床,把手中的半碗苞谷粑又重新倒回到我的碗里,讓我別擔心他,在鄉下,地里隨便扯一把菜也能過活一頓,說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千萬不要虧著自己。爹說完,非得讓我站在他的面前把那碗苞谷粑粑吃下肚,我端著碗,淚水模糊了雙眼。
學校一周繳五斤大米在伙食團,二塊錢菜錢。那年月,周周五斤大米二塊錢,對我家艱難的日子簡直就是雪上加霜。每周周末我回家,娘看見我,憂愁的臉上又增加了幾道深深的皺紋。正值荒月,家里的日子也是東湊一頓西湊一頓,吃的都是粗糧,饑一頓飽一頓是常事。哪有米讓我拿到學校,娘為了不讓我在學校餓肚皮,總是厚著臉皮與別人強顏歡笑借了東家借西家,方圓幾十里,凡是熟人娘都借遍了。爹身體強壯時,二塊錢還不是問題。可今天,爹腰疼得床都下不來,一貧如洗的家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出五斤大米,娘翻箱倒柜找了許久,一分兩分、一角二角地湊,才湊足一塊五,娘囊中羞澀地把手中的錢遞給了我:“這一周,要不,你給哪個同學借五角錢,借一個星期的飯票。”我默默地從娘手中接過錢點點頭,心事重重地打開門正要走,想不到爹拄著一根竹棍走了出來,大聲地叫住了我。他轉過身對娘說道:“都在過荒月,家家都有難,你讓他跟哪個同學借?”說完,從上衣兜里摸出五角錢塞在我手里:“別的學校,胡豆也可抵大米,你們學校可以嗎?”我輕輕地點點頭。爹回過頭對娘說道:“把壇子里你留的胡豆倒出來,讓他拿到學校抵大米。”娘猶豫了一陣,終于轉身進屋,我心里清楚,娘留那半壇胡豆,是準備給大嫂坐月子吃的,大嫂身懷六甲。在娘的心頭,手心手背都是肉哇!娘難為情地把胡豆倒了出來,遞給我時,我的手,半天都抬不起來,頭低得死死的,我怕抬頭,更不敢看爹,也不敢看娘,我怕爹娘看見我淚眼婆娑的雙眼,爹把胡豆接了過來,鄭重地交到我手上,讓娘送我一程,我的心千頭萬緒,被一陣陣寒風吹亂。
后來,爹的腰好了,又四處找活干,去磚窯挑磚、裝窯、出窯,抬石頭、挑沙、背水泥,只要有錢賺,爹不分臟活累活,活輕活重,統統扛在肩頭。就這樣,爹用他如山的肩膀,一肩一擔挑出了我三年的求學路。雖然我有愧于爹,沒有考取大學,但爹從未責怪過我,經常在我面前說:“莊稼人不求大富大貴,讀書讀不傻人,你是我們家唯一上過高中的人。”爹越是這樣說,我內心越是難安。
漸漸地,我們家的日子變得陽光了起來,我寫的第一篇文章在報上刊載,識字不多的爹手捧著報紙滿院子說,在他的一些莊稼漢的朋友中,有板有眼地讀著、笑著,逢人就說,他幺兒的書,他沒有白供,他的血和汗沒有白流。
爹的熱淚,流淌在久違的笑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