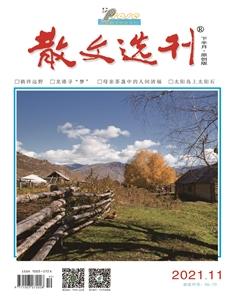多雪的冬天
胡慶魁

那年我得了鼻咽癌。
25歲的我得了癌,讓所有認識的人嚇一大跳:就是那個穿著背心短褲頂著風雪晨跑的小伙子?然后就嘆息,接著的那個冬天荊江大堤上的跑步者潰不成軍。
1978年12月28日,在湖北沙市輕工局任理論教員的我,應邀到特種燈泡廠宣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講了不多一會兒,突然覺得不對勁,舌頭像生了銹,拐不過彎來,邢賁思的“思”字怎么也念不伸。勉強講完,渾身大汗淋漓,衣服沒一些干處。我感到情形不對。有個把月了,總是莫名其妙地來毛病,先是老也治不住的咽炎、扁桃體炎;接下來鼻子短路不通氣;過了幾天,耳朵拉起了風箱,呼啦呼啦的,耳門一關一閉;不知何時,右頸有了顆小豌豆似的小珠珠;到后來,頭疼,好像有個小人揮著柄鐵錘在里面敲啊敲,吃了無數的去痛片、頭痛丸也無濟于事。貓不吃魚——毛病大。當晚我坐沙宜班船到了漢口。
同學譚業平來接船,他摸摸我右頸的“小豌豆”,臉上便有些嚴肅。我們先回學校,動物專業的蔣開友同學已經等在生物系大樓前了。蔣負責“液晶檢查淺層腫瘤”,這是武大生物系當時頗有名氣的一項試驗。蔣在“小豌豆”上涂了液晶,細心地做了三次,這才舒展眉頭,“沒事,老同學,你看——三次都是陰性!”在珞珈山櫻花樹下握別時,一陣頭疼襲來,我不由抓了抓頭皮。業平因此建議到廣燦那里看看。蔣說,也好,液晶檢查有百分之五的誤差。
李廣燦同學在湖北省南湖腫瘤醫院搞基礎研究。他放下手中的試管,帶我們到檢驗科。一個鼻頭有雀斑的護士取根很粗的針管,“哧”的一下扎進“小豌豆”,還用力攪了幾下,把我眼淚都攪出來了。然后坐走廊長凳上等著,三人不說一句話。墻上的時鐘很沉重地走著。過了好久好久,小護士在門口招手,廣燦和業平很快跑過去了。我仍舊坐著,腿綿軟綿軟的。很久,他們也不出來。我走進檢驗室,見兩人正靠在檢驗臺上發愣。我從廣燦攥得緊緊的手里抽出那張化驗單,被汗水濡濕的一行字特寫般定格在眼前:右頸轉移癌!
我頭有些暈,微閉上眼,一個巨大的黑洞朝我張開。
當災難臨頭,我雖然有些慌亂,但絕沒有驚慌失措。我那在松滋河打了一輩子魚的外公常說,是福擦身過,是禍躲不脫。躲不脫的禍既然來了,那就讓它來吧。瞥見醫院花圃里最后一朵石榴花即將凋謝,我想,正在逼近的這個冬天會下很多很多的雪。走過落葉飄零的城市,我躺在了同濟醫院腫瘤科6病室28床。
隔天給單位打電話,聽得一個“癌”字,打字員劉萍嚇得把話筒捂得緊緊的。她以為捂住了話筒就捂住了嘴巴,免得漏出那個恐怖的字眼。
在同濟醫院又做了次切片,從鼻子與咽喉交界處取了肉樣鏡檢,確診為“鼻咽癌丙三期”。原來,鼻塞、耳朵漏氣、頭疼、舌頭不拐彎,全是腫瘤給壓迫的!那顆“小豌豆”不過是癌癥運動的表現。上手術臺做鈷-60照射時,我問大夫“鼻咽癌”治愈的希望多大?大夫回答:“五年生存率30%。”我在心里說,我就是這30%了!
鈷-60射線的力量十倍于火,幾天下來,鼻咽腫脹,口腔潰爛,哪怕喝一口水也會疼得鉆心。我咬緊牙關進食。一點兒不夸張,每次都吃得我死去活來。大弟永魁把摻了生魚鱉肉熬的白粥擱小桌上,我吃一口他記一次數,大約50多口個把小時才能吃完。大弟一邊當啦啦隊員,淚水一邊順臉朝下淌。
我要吃!我必須吃!不吃白細胞朝下掉,挨不過照射早晚要交飯票。對造物主今世只給我一次的生命,豈能輕言放棄!
那時鈷-60還沒先進到自動跟蹤,幾個摩托車頭盔樣的東西照著你脖子和面頰,毫不留情地將好壞細胞一起殺死,就像把洗澡的小孩和洗澡水一塊兒潑出去。同室的兩個病友照射前白細胞挺高,一照直線朝下掉,又吃不下東西,消耗得不到補充,白血球掉到3000以下,紅燈一亮,不停機人就要完蛋,過幾天待白細胞升上去再照,癌細胞也跟著生長,而且長得比正常細胞還快,這么折騰幾次還不玩完?我好歹挺了過來,我放療沒停一次機。
15天后奇跡出現,“小豌豆”變成了火柴棍,腦袋里揮舞鐵錘的小人沒了——頭不疼了!穿過1978年多雪的冬天,我在翌年的陽春三月出院,道旁的桃花開得火一般紅。
很快,一個又一個“五年”過去,我娶妻生子,兒子轉眼上高二了。20年來我正常工作,從未因“癌”請過一天假。連朋友們也大多不知道我曾在死亡的門檻上腿都站軟。前不久同濟醫院函調,我在建議欄里調侃道:“破門的足球,靠氣充著;得了癌的人,得給他精氣神兒掙扎著——氣一跑人玩完!”
有同事打探到我得過那病,卻怎么也不肯相信,“你看你,比我們還來勁兒……”我順竿兒往上爬,“是啰,那會兒醫療水平低,一定是弄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