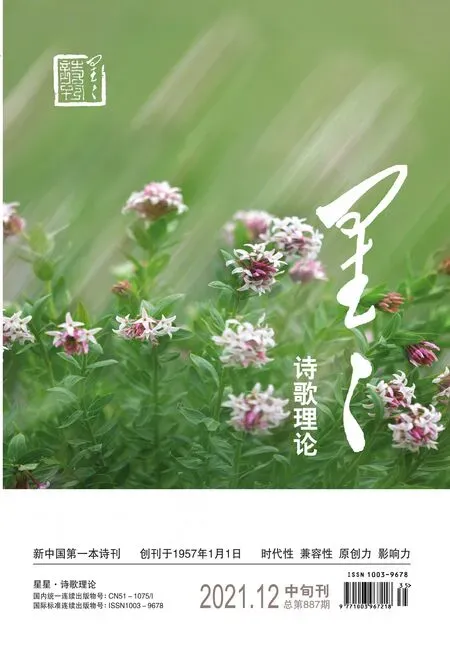故鄉辭
——致我們終將消歿的幼年
>>> 周俊鋒
首屆光中詩歌獎征文活動以“鄉愁”為主題,結合詩人的個體創造和發現來處理這一慣常而熟悉的題材,從技藝層面切實呈現出當代漢語詩歌語言試驗的繁復或精湛;然而,在詩人手藝的背后容易忽略的問題可能在于技藝尺度與價值尺度二者的混淆,單一尺度上的詩學技藝已然很難對當前人們既有的、略嫌僵化和貧瘠的知識結構實現切實有效的更新,甚至有浮泛成為一種懷舊式、小情緒的風險。回顧獲獎作品的鄉愁書寫,或是重新對鄉愁書寫傳統進行一次粗略的檢視,橫亙在繁復炫麗的詩人手藝之外的恰恰不是“寫什么”或“怎么寫”的問題,往往聚焦于“為什么寫”這一關涉文學書寫自身的問題導向:故鄉辭的重復書寫,不斷激活個體與歷史、時代普遍聯結的文化記憶和源頭印跡,然而故鄉和傳統已將注定走向消歿,迎難而上的鄉愁抒寫是否能夠給予我們足夠的“發現底驚異”呢?
青小衣的詩歌《蟲鳴,即鄉音》以細小的切入口來呈現抒情主體內在的心理沖突,前行與回溯、喧騰與寂靜、溫柔與暴烈,類似的表達充滿情感邏輯的悖謬和張力。抒情主體藉由蟲鳴展開對故鄉或鄉音的辨認,然而這段旅途必然面臨一種來自歷史與空間的雙重擠壓,“回家的路途,信封上模糊的地址/名字,戶口本上失蹤的籍貫/宗譜上陌生的血脈”,以反向的方式探詢故鄉的難度,實則從另一方面襯托出“我”想要抵近故鄉的執著追求與堅定信念。此外還應當注意到,該首詩歌對抒情場景的轉換和塑造特別是黑夜、月光、泥土/地下等意象營構仍有繼續細膩打磨的空間,月光的“閃爍不定”與“明晃晃”、泥土里拔出來以及從地下重新長出來等表達,在一首詩歌內部缺乏相應的區隔。
檐瓦,閃現于漢語新詩的意象長廊之中有著特殊的詩學蘊意,時間與空間的疊合使得故鄉老屋的形象呼之欲出,浸潤著故鄉記憶的滄桑、斑駁以及世事浮沉更迭的羈絆。陸健的詩歌《想起一片瓦》情感綿密,以“故鄉是……”的比喻句式串聯起父親的肩背、母親的愛情、奶奶的小腳、爺爺的蹣跚,以及南下外出務工的人們,抒情主體不斷指認“故鄉”的同時也在不斷確證“家”的最初涵義:我的故鄉情結源自于對家的體味和重復辨認。想到一片瓦、想到心里的一根刺,想到我們“在自己的身體里埋葬又新生的自己”,想到清晨距離眼前一億四千萬公里遠的太陽,對生命時間和故土記憶的那份熱望被重新激活。而龍向枚的詩歌《青瓦之上》更為注意“青瓦”意象的引入與銜接,以“遠行的出走——鄉愁呼喚”的情感邏輯勾勒出“你卻沒有回頭”的抒情主體形象和詩歌結構。詩歌首節富于畫面感和聲音表現力,“一條河流能帶走河沙,從不帶走兩岸”,巧妙傳神地抒寫出故鄉承托的那份堅韌與厚重,伴隨著蒼茫奔走的旅途,不斷堆疊起碩大的鄉愁。這首詩歌的立意和辭藻別具匠心,勝在對詩歌細節的處理和情感沖突的設置,“青瓦之上”以及離鄉對遠行意義的探問在某種意義上使得故鄉書寫在詩歌經驗的創造性處理上獲得超拔,離家的選擇則成為一種必然。而區別于這種否定性的情感指向,陸健的詩歌借農民工的選擇和行為來仔細辨認對故鄉的“逃離”——“好像離家越遠反倒離家更近”,以細膩而綿密的方式強化主體對于故鄉的情感羈絆,用正面的方式加深用汗水血肉捂熱的那段現實,實則有著異曲同工的妙處。
詩人田禾的獲獎作品《冬眠》樸素而深沉,以“可能與不能”的關系性話題并置眼前,大地、茱萸、青蛙、烏龜、蝸牛等,開始陸續進入冬眠,開始實現退回根部、實現深土里和石縫中的冬眠,乃至于萬物用全部的身心擁抱這個特殊節季里必然的可能性。“詞語在冬眠”,然而由“但”字所領起的、詩歌所要傾心關注的恰恰是另外一個刺點,從大地上的動植物再到多數的鮮花“假寐式”的休眠,父親以及他所貫注全部心力的鄉土世界,在冬眠時節里猛地迸發出內在的隱力,“爐火不能冬眠,炊煙不能冬眠/它會比平時燃燒得更旺”,淬火的鐮刀以及父親、酒、火爐勾勒出來的鄉村生活圖景,鮮亮而富于生命本身的熱情和生力,借明月的光芒“照亮”更多隱秘的角落和隱微的生存。
邵散燕的詩歌《我與故鄉隔著一首詩的距離》側重于凸現內在情感的厚度和可能抵達的廣度。他青睞于采用一種背離的方式貼近和強化詩意的主旨,“不斷嘗試遠離故土”“我離她越遙遠”,以減法來不斷刪刈關于故鄉分外沉重的情感羈絆,最后只留下“一條江,幾座山,零星地名”,然而愈是被刪減后的故鄉記憶卻不斷延展,甚至像似括號的一邊,無形地勾連起任何一個我可能存在的遙遠地方。
詩人徐俊《故鄉啊,我是活在你光明中的瞎子》更為聚焦的是一種我與故鄉之間展開互動和對話的關系,故鄉為我所饋贈的禮物,“讓我有足夠的力氣,托舉這星辰”,以及我能夠為故鄉所反哺和回饋的愿念,“我會用全部的生命,/為故鄉鋪一條通往太陽的道路”,灶膛里的火焰、門前老樹的枝椏、一籃子鳥鳴,以及與半生運命緊密聯結的造房婚育、莊稼欠收,故鄉緊緊跟隨并且疼愛我、養育我、裹挾我,成為無法訴說的恩情。整首詩歌的內容豐厚,情感較為濃郁,但同時也遺留不少亟待濃縮和提煉的詩意缺憾,有如“讓民間祥瑞”“讓大地光明滿溢”“喂養天空和大地”等類似表達在不少獲獎作品中多有顯露,筆觸上略嫌籠統和宏闊,相反卻忽視掉原本可以細膩展開的有關故鄉的那些潮濕的、引發顫栗的事物,詩歌比擬“自己就是那樹上的一根枝椏”“這疼痛的枝椏/讓大海激蕩不已”,而典型意象和情境營設的過程中詩人似可以展開更為幽微曲折的文學風景。值得注意的是,該首詩歌不同程度上呈露出史詩向度的寫作嘗試,但“祭拜太陽的儀式”“眾神降落,鳥群飛過月亮”等內在的情感線索和整體的詩歌結構,或許在有限的詩歌篇幅中尚不能形成足夠有效的統一。
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嵌入故鄉的文學母題,抵近故鄉在某種意義上即是對主體自身,乃至成為更普遍意義上的一種對文化記憶和原初印跡展開歷史性的叩問。從技藝的維度來看,故鄉辭的重復抒寫和詩學變形不斷激勵和喚醒我們對故鄉、對當下、對自身的本源認識,而故鄉的琉璃瓦盞愈是精微、故鄉的檐瓦青苔愈是蒼翠,反倒襯托出當代漢語藉由詩歌激活一代人故鄉記憶的能力愈發貧弱。從價值層面或另一個敞亮的視野來看,故鄉辭的書寫又能夠在多大限度有效更新、乃至改變同時代人們對個體和社會互動關聯的既有認知呢?文化或能反哺、記憶或許閃現,而我們終將消歿的幼年卻早已經成為定局,緊隨著故鄉的生命消瘦,文字的生命也如燭火微暗的搖晃,難有叩擊人心或靈魂的滌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