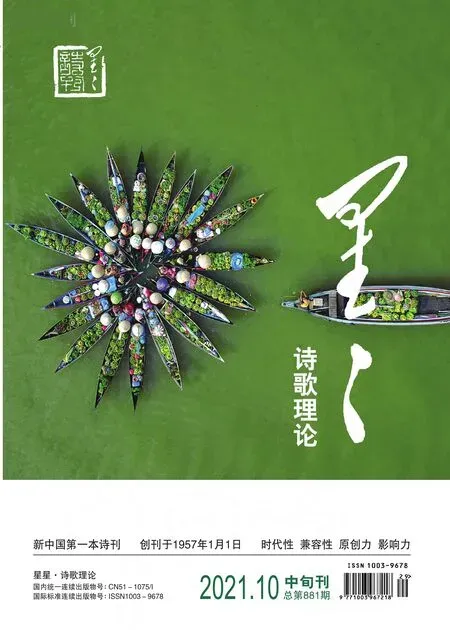“詩片斷”中的“零余”體驗
>>> 孜 繁
梁小斌的組詩“詩片斷”由記錄詩人生活所感、所思的一系列“斷章”組成,看似“碎片感”的形式之下寓有內在的一致性,即對生活的細察與審視,對人生的深刻反思。詩人以敏感的詩歌感官捕捉并寫出極為細微、切膚的感受,詩中尤其呈現出一種郁達夫筆下“零余者”般的處境和體驗。這種“零余”體驗系于詩人的人生際遇,折射出一顆豐富易感之詩心的沖突掙扎,也滲透著詩人對“人生何為”的深沉思考。
隨筆“冥想錄”與“詩片斷”中的詩歌文本有著密切的互文關系,梁小斌在文中提到,“在信息后面,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個生命存在的具體形式,我對這個形式感到有壓抑感。我想逃避,但我不能。”“審美意識與倫理意識形成了巨大的對立。現實生活不能讓人以隱士面目出現,實現對生活的審美。”從中能看出,縈繞于詩人心中的是一組難解的問題:現實/世俗生活與“審美生存”的沖突。他感受到現實生活與審美意識存在著齟齬,但無法從中逃脫。這種內心斗爭與行動層面的掙扎既與詩人的個人經歷緊密相關,又與文學、文化中一種極具原型意義的思考相接通,“出世”與“入世”般的斗爭,“To be,or not to be”的古老命題……這些頗有哈姆雷特、浮士德意味的知識分子之沉思在梁小斌筆下依然激蕩回聲:“對氣息的熱愛,對儀式的反感,對將要行動感到驚慌。”一個獨立而不免惶惑、“零余感”的詩人形象宛然紙上。
因此,“詩片斷”反映的恰是這樣一個主題。具體而言,一方面,當詩人傾心并踐行的具有“超越性”的審美生存面臨世俗生活的巨大壓力之時,詩人開始對之作出反思并嘗試投入現實生活的洪流中,恰如他在“冥想錄”中所言,“在我落魄的時候,我充滿著好奇心,一個懂得這些的人引領著我觀看他生活的程序,使我產生想生活在其間的念頭。”這種轉變也體現在詩歌寫作觀層面對“真實”與“凝練”的追求,落實為組詩對生活細節的把握。而另一方面,知識分子一貫的懷疑精神使詩人對“出世”作出反思的同時也有著對“入世”的疑懼,這使他不可能遽然躍入生活之海而隨流揚波,而是在被迫的“轉變”中始終帶有一脈隱痛:當詩人隱遁在書齋和抒情的“幻境”中,就難免懷疑自己感受的虛假,與真實的生活的隔絕;而當拔足出象牙塔般的“真空”,則在對生活細節的細膩體察中汲取詩意之同時又難免產生被世俗同化的恐懼和“惡心”,內心激蕩著一種不甘和屈服感。詩人的這種心境在“冥想錄”中有明確的剖白:“現在我想到要熱愛我的妻子了,要學會在菜場上討價還價了,要能夠懂得妻子懷孕時的心情了,這是深切的,從一無所知到興趣盎然再到生活的表達。從表面上看,我逐漸懂事的歷程,可以大書特書,實際上這也反映了我在強大現實面前的茍延殘喘。”詩中亦有印證:“一個拎菜籃子的人,我發現他的感受是假的,我對他的感受惡心。”這里作為世俗生活器具的“菜籃”自然難以澆詩人胸中塊壘。懷著這種復雜的感受,詩人的筆觸在蘸取生活細節,開拓日常詩意之時,也常在詩行間展現內心的沖突與掙扎,詩中的“我”迥異于詩人在創作早期對主體意識的張揚,而更近于卡夫卡“地窖中的穴鳥”(吳曉東語)和郁達夫閣樓上的“零余者”形象,體現出現代主體的脆弱與彷徨。邊緣處境帶來的挫敗感與驚悸,在愛情中放大的復雜人生感受,都在詩中充分地呈現出來。
首先,正如詩人在“冥想錄”對詩歌之“真實”和“凝練”的提倡,這組詩的大部分片斷都是對生活細節的“速寫”,即聚焦一個生活場景,一組日常物象,以凝練的詞句將其表現出來,組詩中的兩則“深秋印象”即是代表。在這類描寫中詩人也會不時露出一筆溫暖的底色:“聽診器在她手上焐熱之后,才放到我胸口,這是我最感動的時候。”從中能看到,詩人努力去擁抱另一種生活方式,并從中捕獲新鮮的詩意。這與詩人在隨筆中吐露的感受相呼應:“只是因為我學會了熱愛這些我以前認為是世俗的生活,我終于也理解了常人的情感。”“我只有深切地愛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玩意,我才能更為體察到我與生活的正確關系,永遠熱愛吧!”但是,詩人在體察到“入世”的溫暖的同時也有著警惕和反思,具體表現為,在以日常細節入詩之時,詩人的筆觸往往不止逡巡于表面,而是涉及形而上層面的追索,以及向內心的深入開掘。在組詩的第16個片斷中,詩人處理了“電動剃須刀”“花生殼”“煙灰缸”等日常物象,而具象的描寫以縹緲收尾:“江上的船駛過來,我相信它會駛到我邊上。”這蹈虛的一筆折射了詩人從“形而下”的日常瑣細向“形而上”飛升的夙愿。組詩中也有一些片斷以詩人寫作中一以貫之的“童真”視角展開:“汽車裝人剩下幾個,像剩下幾粒飯。”在這類描寫中,詩人也借兒童視角去觸及人性的深刻體驗:“我穿大鞋子,晚上容易做惡夢。趿著拖鞋的孩子一看就走不遠。”成年人視角對孩子的無理預判產生一種讖言般的恐怖,成為籠罩“零余者”的夢魘。
詩中的“零余”體驗具體表現為邊緣處境、被拋棄感、病痛感受等,尤其是一種驚悸不安之感:“煙灰還沒有燃盡,我就想把煙灰撣掉,心神不安的情緒。”這種情緒由當下觸發,也常與人生際遇和回憶相連,如“麥子總割不到邊,對勞動的絕望。我對門衛需要我出示證件的感想。”詩中的絕望、恐懼以及莫可名狀的不安背后都能看出詩人人生經歷的烙印。而在這種“零余者”處境和驚悸感中依然浸透著一脈反抗意識:“我蜷縮在浴巾里,我在走廊里被迫跑起來,我小心翼翼把煙頭……我剝糖吃,又包上了,我看書避開小甲蟲,我不愿和解,不愿感到被釋放。”詩中對外界“套中人”般“神經質”的防御背后是對“和解”與屈從的恐慌,對徹底融入世俗生活的抗拒。正如在另一個片斷中詩人寫道:“他的胃口很好,還沒有來得及惡心,就被他消化掉了。”這種毫無反省地被同化顯然是為詩人所不取的。
此外,詩中的“零余者”處境、“零余”體驗還通過愛情主題得以凸顯。在愛情和婚姻中,詩人對生活及自己的內心都有著更細膩的認知:“我整理妻子的書,我的妻子喜歡我‘笨’,我買雞蛋,這時,我回憶/我的愛的體驗的方式,不是‘理解’而是我的內心小感受。”在組詩中,詩人也凸顯了世俗愛情與人生道路的沖突,以及自己的選擇:“在一個豪華的地方,我想她,我發現我被剝奪得一干二凈,自我的荒謬,我什么也不知道,好像有一個神秘的臺階通向她/但我不愿意走。”詩人在“冥想錄”中也吐露了自己因邊緣處境和“零余者”般的形象而在情感中遭遇的挫敗體驗,以及由此深切覺知的人生體悟:“我才體察到我生活在她們的外部,我是以一種她們所不需要的方式接近她們。”“走向她,對我來說,是一條陌生的小徑,她期望我踩著紅地毯去看她。”世俗愛情的要求和自己的內心相違,詩人清醒地覺知到了這一沖突,也感受到巨大的痛苦和彷徨。“我的幻想是不真實的,我長時間的磨難,因為我在幻覺中吃盡了苦頭,我面對了真實,但回到幻覺,回到我對她們的認定,我怎么在自己的理性上自圓其說呢?”但詩人依然持以不妥協的態度,對自己的道路九死不悔:“拒絕具有極大的典型意義,我只是在些種境遇里才能明白,清澈地體會我的反叛,我的真實,我的存在。”
梁小斌在“詩片斷”中呈現的“零余”體驗及背后的深刻思考是耐人尋味的。世俗生活與審美生存的關系,“入世”與“高蹈”的斗爭……面對這永恒的內心命題及具體的社會現實處境,詩人何為?回答這個“精神史”意義上的問題顯然是困難的。但明晰的是,這種思考是彌足珍貴的,詩中的“零余”體驗體現了詩人梁小斌內心破繭般的割裂感與掙扎,背后是詩人對反思精神與批判性的堅持。詩人天真敏感的詩心從未被世俗的機心異化,執拗孤絕的姿態下是對“真”的恪守與無盡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