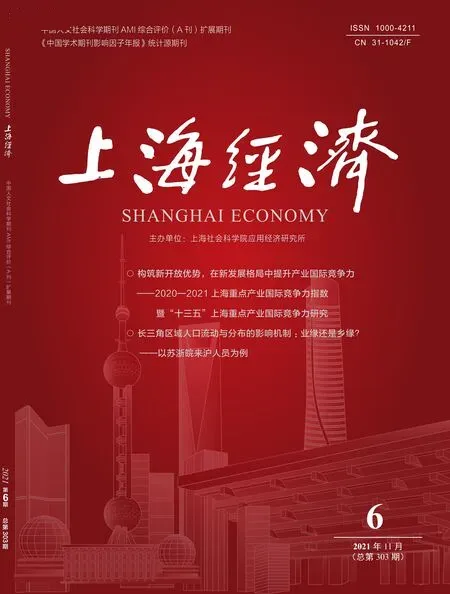“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改善的貿易效應研究
岳中剛,葉茂坤
(1.南京郵電大學統計科學研究基地/經濟學院,南京 210023 2.南京郵電大學經濟學院,南京 210023)
一、引言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三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中強調,要深化互聯互通和貿易暢通,深化基礎設施合作,提高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和聯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優先領域,也是沿線國家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的重要基礎。良好的交通基礎設施能夠通過降低運輸等貿易成本,提高運輸便捷性等貿易效率,不僅可以推動本國貿易增長和產業升級,更有利于沿線國家形成優勢互補、分工協作的全球價值鏈與跨國產能合作體系(劉志彪和吳福象,2018)。自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我國充分發揮交通基礎設施技術和建設優勢,加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中歐班列”“瓜達爾港”等一大批合作項目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應,“六廊六路多國多港”架構基本形成,對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改善和貿易發展帶動作用明顯增強。2020年,我國企業承攬的境外基礎設施類工程項目5500多個,累計新簽合同額超過2000億美元,占當年合同總額的80%。中歐班列通達歐洲城市90多個,涉及20余個國家,開行1.24萬列、發送113.5萬標箱。從2013至2020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04萬億美元增至1.4萬億美元,占我國對外貿易額比重達到29.1%。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一帶一路”交通基礎設施項目為沿線經濟體帶來了3.35%的GDP增長,除去必要的投入之外,還有2.8億元的增長。此外,這些項目還有非常明顯的溢出效應,對非“一帶一路”合作國家也將帶來2.6億元的GDP增長,為全球帶來2.87%的增長。然而,截至2019年,仍有超過半數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條件較弱,直接阻礙這些國家參與全球貿易,貿易額僅達到實際潛力值的70%。那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能在何種程度上促進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額?本文通過對此問題的探討,評估“一帶一路”倡議中“基礎設施建設先行”的實施效果,為沿線國家高水平開放提供決策依據。
與以往文獻相比,本文的可能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本文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水平開放的視角,評估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對貿易的促進效應以及異質性特征,從而得以將“一帶一路”倡議中“基礎設施先行”的討論,從“是什么”推進到“為什么”的深度,是現有文獻中較早對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改善與雙邊貿易全面深入探討的研究,為沿線國家依托“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深化與沿線各國產業的分工協作與錯位發展,進而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政策參考。第二,對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狀況進行了量化測度,并將其與國家層面的宏觀特征數據進行了匹配。以往文獻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測度缺乏量化標準,本文采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交通基礎設施質量的評分數據,該數據可以較為客觀且有效地量化不同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狀況。
本文后續內容包括: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說;第三部分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的特征性事實;第四部分為模型構建、變量界定與描述性統計;第五部分為交通基礎設施改善與雙邊貿易的實證檢驗;第六部分為交通基礎設施改善與雙邊貿易的異質性討論;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
(一)交通基礎設施改善與雙邊貿易
交通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直接提升了現有的交通可達性、打通關鍵交通節點,有助于創造并拓展網絡外部性、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繼而促進雙邊貿易的開展,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Donaldson, 2018;劉生龍和胡鞍鋼,2011)。Donaldson(2018)通過構建李嘉圖模型,提出并檢驗了基礎設施的改善能降低貿易成本和區域價格差,促進出口貿易的開展。Bougheas(1999)等人發現,各國基礎設施的質量參差不齊是導致貿易運輸成本存在差異的重要因素。基礎設施質量的提升能夠有效降低運輸成本,增加了貿易機會,提升貿易流量。Limao和 Venables(2001)的研究結果發現,交通基礎設施的質量和分布密度是影響貿易的決定性因素,非洲整體的貿易額常年低于預期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基礎設施薄弱。Martincus和Blyde(2013)利用智利地震這一自然事件,證明了交通基礎設施的減少對出口貿易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盛丹等(2011)驗證了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對中國企業的出口決策和數量均能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且主要體現在擴展邊際。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觀點,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提升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在不同區域間存在一定差異。以中國為例,如在內陸地區進行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其水平的提高會促進出口貿易,更好幫助內陸企業“走出去”,提高內陸地區的經濟開放程度,但在東部沿海地區進行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卻抑制了出口貿易的開展,促使企業將既有經濟資源投向國內市場,促進國內貿易的發展(劉晴和邵智,2008)。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的質量提升對雙邊貿易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二)不同類型交通基礎設施改善與雙邊貿易
在衡量交通基礎設施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時,具有代表性的海運、航空、公路、鐵路基礎設施通常被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基于此,部分學者針對不同種類基礎設施對于貿易的影響展開相關研究。Feryer(2019)發現,在貿易增長目標的實現過程中,縮短國家間的相對距離是切實可行的途徑之一。在當前貿易開展過程中,海上距離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與此同時空中距離的重要性隨著航空運輸量的快速增長而逐步增加。白重恩等人(2018)通過對中國國道主干線規劃進行研究分析后發現,公路直接途經地區以及距離公路較近地區的貿易額增長速度要遠快于沒有公路開通的地區。章秀琴和余長婧(2020)的研究結果表明,港口、公路和航空基礎設施質量與雙邊貿易額呈現顯著正相關的關系,鐵路基礎設施的貿易促進效應不顯著。其中,對沿線國家雙邊貿易促進效應最大的是港口基礎設施質量的提升。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2: 不同類型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存在差異。
(三)交通基礎設施改善與雙邊貿易的異質性
現有文獻通常會從實施交通基礎設施相關政策國家的經濟狀況、行業差異、距離和空間等角度出發展開異質性研究。Alice(2017)在其研究中對樣本進行了不同地域的劃分,發現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獲得收益較多的國家主要分布在中東、中亞和東亞地區。而在沿線發達經濟體中,德國的收益略高于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呂越(2019)在其研究中,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分為相鄰和不相鄰國家、風險高和風險低國家組進行分樣本回歸后發現,“一帶一路”倡議產生的對外投資促進效應在不同國家和經濟體間存在顯著差異。也有文獻指出,東道國自身的經濟體量、經濟發展水平、地理區位等因素決定了其交通基礎設施水平上升所帶來的貿易促進效應大小(朱博恩等,2019)。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3:交通基礎設施改善的貿易效應,在不同國家、時間維度上可能存在異質性。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的特征性事實
在開展實證研究前,本文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的特征性事實入手,為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對雙邊貿易的影響效應提供初步證據。
首先,本文選取了2009年和2017年沿線國家之間雙邊貿易額的截面數據,其中數據來源為UN Comtrade數據庫和各國海關數據。其中,為便于圖片展示,本文剔除了小于雙邊貿易額中位數的樣本。經過計算,得出2009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的中位數為2150萬美元,而到2017年雙邊貿易的中位數則上漲至3815萬美元。從上述數據結果可以得知,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額增速較快,具有很強的貿易潛力。其次,基于FR算法規則(Fruchterman-Reingold),本文繪制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網絡圖。其中,網絡圖結果由Gephi軟件給出。圖1展示了2009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情況,而圖2展示了2017年的雙邊貿易情況。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該類網絡圖中,每個“節點”代表不同的沿線國家,而作為連線的“邊”則代表兩個沿線國家之間展開了雙邊貿易。節點的大小和顏色深度代表該沿線國家開展雙邊貿易國的數量特征,“節點”半徑越大,顏色越深,代表與該國進行雙邊貿易的國家越多。而連線“邊”的線條粗細和顏色深度代表沿線國家之間雙邊貿易額的大小,連線“邊”的線條越粗,顏色越深,代表兩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額越大。

圖1 2009年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網絡圖

圖2 2017年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網絡圖
通過對比圖1和圖2所展示的結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主要呈現如下三個特征:
第一,在“一帶一路”倡議推出后,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更為頻繁。這一特點可以通過圖1和圖2中展示的沿線國家節點大小來判斷。對比2009年沿線國雙邊貿易的網絡圖,可以發現2017年時部分國家節點的顏色更深,半徑也得到一定程度擴大,說明與其開展貿易的國家數量得到增長,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包括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以色列、沙特等國,而少數沿線國家開展雙邊貿易的對象國數量在下降,如土耳其和阿曼。
第二,沿線國家貿易網絡呈現“多級化、區域一體化”的特點,并且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這種趨勢正在進一步加強。從不同國家節點的分布情況來看,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重要參與者,始終在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中占有最大比重。此外,相比2006年,在2017年時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更為密切。其中,以東南亞和中東地區的沿線國家雙邊貿易增長最為明顯。
第三,從總體來看,各沿線國的出口貿易額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穩步增長。代表各沿線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額的連線“邊”更粗,顏色也更深,說明“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促進了沿線國家之間的設施聯通并帶動貿易暢通,提高了沿線各國的雙邊貿易額。
四、模型構建、變量界定與描述性統計
(一)模型構建
交通基礎設施質量越好的國家,越有可能獲得更高的雙邊貿易額。因此,本文擬采用引力模型進行分析。Anderson和 Wincoop(2003)在引力模型理論基礎上加入貿易壁壘因素構建貿易阻力模型,本文依此為基礎,設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額與相關影響因素的模型如下:

依此,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是“一帶一路”沿線國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為了將兩個沿線國進行雙邊貿易時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同時納入考察范圍,設置兩國綜合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并以雙邊貿易額Tradeijt作為被解釋對象。基于上述研究,設立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對雙邊貿易的基準回歸模型,具體如下:

在式(2)中,Tradeijt表示兩沿線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額,Infraijt表示沿線國交通基礎設施質量,Controlijt為控制變量, 主要包括了兩國之間距離、是否接壤、是否有相同官方語言、非關稅壁壘等因素,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δ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jt為誤差項。
(二)變量界定和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額。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下各國合作水平不斷攀升,分工明晰的區域貿易一體化價值鏈體系逐步建立。本文重點關注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因此選定“一帶一路”中兩個沿線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總額作為被解釋變量,數據來源為UN Comtrade數據庫和各國海關數據。
2.核心解釋變量: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質量。為了更有效地衡量“一帶一路”國家的基礎設施質量,我們除選取總體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指數(Infra)之外,另選取子指標的評分(Feyrer,2019)。分別為航空(Air)、港口(Port)、公路(Road)、鐵路(Rail),得出1~7分的交通基礎設施評分(1分為最低,7分為最高)。其中,數據來源為2006—2017年發布的公開數據《全球競爭力報告》,但由于《全球競爭力報告》的部分國家數據缺失嚴重,因此本文剔除阿富汗、巴勒斯坦、白俄羅斯、伊拉克、馬爾代夫、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七國的樣本數據。進一步剔除缺失值后,本文最終保留58個沿線國家的數據。
3.控制變量:借鑒以往文獻的做法,本文引入諸如沿線國人均GDP等能夠影響兩國雙邊貿易額的控制變量(李兵和顏曉晨,2018;Feyrer,2019)。本文從《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引入非關稅壁壘衡量貿易風險和政策影響,而兩國之間距離、是否接壤、是否有相同官方語言數據來源于CEPII數據庫。
(三)描述性統計
表1給出了本文所使用的主要變量名及描述性統計。其中,各沿線國的雙邊貿易額和人均GDP、距離進行對數變換處理。從數據展現出的特征可以發現,交通基礎設施子指標數據的數值相差較大,在對子指標航空、港口、公路、鐵路分別進行變異系數運算之后,發現鐵路的離散程度為0.86,遠大于公路、港口、航空三種類型交通基礎設施的離散程度。說明相較于其他交通基礎設施,沿線國家鐵路基礎設施水平的差異最大,這可能是由于鐵路建設對自然環境和技術水平的要求更高,興建周期也較長。此外,沿線國家間在鐵軌寬度等現行標準上存在一定差異,發展跨國鐵路方式的國際貿易難度較大。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五、交通基礎設施改善與雙邊貿易的實證檢驗
(一)基準回歸結果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以“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國家為研究對象,以其中兩國的綜合交通基礎設施質量作為出發點,建立沿線國家雙邊貿易額與交通基礎設施質量的面板數據。在對模型進行Hausman初步檢驗的結果后發現,選用固定效應模型優于使用隨機效應模型。此外,本文還從個體和時間兩個層面對標準誤聚類得到穩健標準誤。其中,基準回歸的結果如表2所示,模型(1)和(2)的結果表示,在不加入控制變量的條件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對雙邊貿易額的影響為正向,且回歸結果均能夠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
在表2的模型(3)和(4)中,本文引入了能夠影響出口的相關控制變量,并分別考察有無控制時間效應的情況。控制變量由沿線國家的人均GDP、兩國之間距離、是否接壤、是否有相同官方語言、非關稅壁壘等變量構成。模型(3)和(4)的回歸結果顯示,在加入控制變量后,交通基礎設施對于雙邊貿易額的估計系數相較沒有放入控制變量前有所下降,但結果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顯著,印證了交通基礎設施質量是提升雙邊貿易額的重要因素。而綜合上述兩個模型的控制變量回歸結果看,人均GDP的提高和兩國接壤、具有相同官方語言顯著促進了雙邊貿易。這可能的原因是人均GDP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沿線國家在貿易活動上會更為頻繁和多元化,加之其貿易條件通常比較便利,有利于開展雙邊貿易活動;而兩國的接壤和具有相同官方語言減少了雙方開展貿易的溝通成本、運輸成本等,在同樣的文化背景下,兩國更有可能開展貿易活動。而兩國距離、非關稅壁壘負向顯著影響雙邊貿易。這可能的原因是兩國距離的增加會直接提高貿易雙方之間的貿易成本,降低了雙邊貿易額。非關稅壁壘則以國家法律、行政措施等非經濟手段阻礙了沿線國家之間雙邊貿易的開展,提高了貿易成本。因此,非關稅壁壘和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負向顯著的關系。綜上,在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對雙邊貿易的影響仍呈現顯著正相關的關系。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不同類型交通基礎設施改善對雙邊貿易的影響
為了更加準確地探究不同種類交通基礎設施對雙邊貿易的影響,本文選取四種主要的國際貿易交通基礎設施作為子指標:航空(Air)、港口(Port)、公路(Road)、鐵路 (Rail),對國際貨運中的不同貨物種類和運輸性質做到基本覆蓋;并從《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獲取沿線國家四種不同基礎設施質量的評分,較為全面地對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子指標做出衡量。實證結果如表3中模型(1)至模型(4)所示,結果表明航空、港口、公路三種不同運輸方式的基礎設施質量均對沿線國家雙邊貿易額存在正向顯著作用,航空交通基礎設施質量提升對于雙邊貿易的促進效應最大,而鐵路交通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呈現不顯著的關系。可能的解釋是:其一,本文的研究對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仍為發展中國家,其航空運力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擁有較大富余潛力。完善以航空貨運樞紐網絡為核心的航空基礎設施有利于大幅度優化航空貨運營商環境,發揮規模效應。其二,對于工業化與城市化尚處于起步或加速時期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公路基礎設施在雙邊貿易中起重要作用,對于貨運的影響較大。因此,提升公路基礎設施質量有利于雙邊貿易額的提升;其三,海運作為眾多大宗商品的首選運輸方式,占貿易運輸的比例最大,海運的低運輸成本和較為悠久的發展歷史使得海港的基礎設施質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雙邊貿易活動的進一步開展;最后,在四個子指標的回歸結果中,只有鐵路交通基礎設施對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額沒有體現出顯著關系,可能是由于鐵路基礎設施具有投資高、建設周期長、占地面積大等特點,即使是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新建一批鐵路基礎設施的前提下,鐵路基礎建設的發展仍存在一定時滯性,對雙邊貿易的影響相對遲緩。

表3 不同類型交通基礎設施質量與雙邊貿易額的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本文在交通基礎設施質量的衡量上可能存在誤差,影響實證結果的正確性,鑒于此本文使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式,對實證分析的結果加以穩健型檢驗:首先,本文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指標(WDI)中的物流績效指標(LPI)。選取的原因如下:該指標構建中包括對于交通基礎設施質量的衡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的實證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1)至(2)的結果分別展示了加入以及不加入控制變量的結果,發現無論是哪一種模型,替換后的解釋變量物流績效指標對雙邊貿易額的回歸結果是正向的,并且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前文結論基本保持一致,驗證了基準結果的穩健性。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四)內生性檢驗
為確保所得實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還需要進一步通過內生性檢驗來探究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對雙邊貿易額的關系。交通基礎設施質量與其雙邊貿易額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即雙邊貿易額的提升可能反過來影響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促進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得到提升。為解決此內生性問題,本文選用中國對外投資追蹤數據里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數據和200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分別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檢驗。選取的原因如下:首先,從相關性來考慮,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國和主要參與國,對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對外直接投資占其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總量的比例較大,并且與該國的交通基礎設施高度相關。此外,交通基礎設施是一個投入周期和使用年限均較長的工程,在短期內相鄰年份基礎設施質量的相關度較大,所以該沿線國家2006年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與該國2009—2017年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也可能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其次,從外生性來考慮,中國的交通基礎設施對外投資不太可能與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的擾動項相關,2006年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對于后期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的影響也并非是直接的。
在考慮異方差和自相關問題后,本文擬采用兩步GMM法進行內生性檢驗。表5的模型(1)至(4)報告了內生性檢驗的相關結果,其中模型(1)和(2)中展示了GMM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發現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對外直接投資、2006年沿線國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這兩個工具變量與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存在正向顯著的關系,印證了工具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存在相關性。不可識別檢驗的統計量分別為28.457和577.919,且p值為零,均強烈拒絕了不可識別的原假設;識別是否為弱工具變量的統計量分別為27.196和573.582,大于臨界值規定的16.38,說明模型中關于弱工具變量的假設不成立。模型(3)和(4)的結果顯示,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依然對其雙邊貿易額起正向顯著作用,與上文中得到的變量結果吻合。

表5 工具變量法的內生性檢驗結果
六、交通基礎設施改善與雙邊貿易的異質性討論
(一)“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后的區分考察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互聯互通的目標,通過促進各國基礎設施完善,進而增加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這是本文探究的核心論述之一。因此,我們將2013年作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年份對樣本進行劃分,分析倡議提出年份前后時期內回歸結果的差異性。對比表6中模型(1)與(2)的結果可以發現,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交通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不顯著;“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交通基礎設施的回歸系數呈現正向顯著結果。說明“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顯著提升了沿線國家的設施聯通程度和設施質量水平,各沿線國加大了對國際和國內交通網絡的投資額度和維護力度,在設施聯通的前提下,貿易暢通程度提升,促進了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

表6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后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二)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分考察
“一帶一路”倡議所涉及的沿線國家發展水平差距大、資源分配不均衡。例如,南亞地區社會發展指數最低,主要由較低收入和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構成,而中東歐地區普遍屬于中高、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較多。本文依照世界銀行對于收入的標準,將樣本內的沿線國家劃分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三組進行異質性分析。實證結果如表7的模型(1)-(3)所示,發達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的提高對促進發達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并不顯著,其中的原因可能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較高,其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比較成熟完善,因此其交通基礎設施的質量提升對雙邊貿易的邊際效應較低,甚至不顯著。而交通基礎設施質量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對雙邊貿易額均表現出正向顯著作用。這可能是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水平較低,仍處于發展抑或是起步階段。落后基礎設施對貿易發展水平造成的較大限制,使其長期難以融入全球市場,在基礎設施水平提高之后,能夠顯著提升雙邊貿易額,這個結論也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后續貿易合作政策提供了經驗證據和方向,即幫助經濟水平較低國家提高其設施聯通度,以提升其貿易水平,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表7 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七、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的實證結果發現,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質量有助于促進雙邊貿易額提高。其中,沿線國家的航空、港口、公路方式的基礎設施質量也對雙邊貿易有著正向顯著作用,而鐵路基礎設施質量則不顯著。在進行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檢驗后,該結論依然成立。異質性分析的結果顯示,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質量正向顯著促進了雙邊貿易,但是在倡議提出前,兩者并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次,對于沿線國家中經濟水平和交通基礎設施質量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交通基礎設施對雙邊貿易的正向促進作用較為顯著。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加快構建“五通”的創新合作模式。部分“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受到空間分化效應的制約,交通基礎設施投資較少,阻礙外向型經濟發展。從本文研究結果看,中國可以通過資金、技術、人才輸出等投資方式,在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實現深度合作,逐步使各國設施互通水平得到穩步提升,通過降低貿易運輸成本增進貿易往來,進而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互通。并以企業為靈活載體,加強國內企業與東道國企業協同發展,進一步帶動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第二,有側重點地優化國際貿易區域分工。從子指標得到的結論看,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提出者,應加大對航空、港口、海運、公路等基礎設施聯通合理布局的引導力度,從而提升國際經濟分工效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雙方可以充分利用各國產業、資金、勞動力的差異性,配合基礎設施投資聯合投資建設和對外開放政策寬松,發展更有利于本國環境的交通運輸網絡,促進經濟增長。
第三,加大對地理位置、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力度。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和主要參與者,中國更需要做到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精準對接,實現基礎設施新增項目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把幫助沿線及周邊各國,尤其是使處于經濟、貿易水平等不利和邊緣地位的國家在基礎建設項目中獲得收益為前提條件。此舉有利于在更大程度上調動全球資源,有效幫助貿易國提升進出口水平和降低邊境延誤,助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減貧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