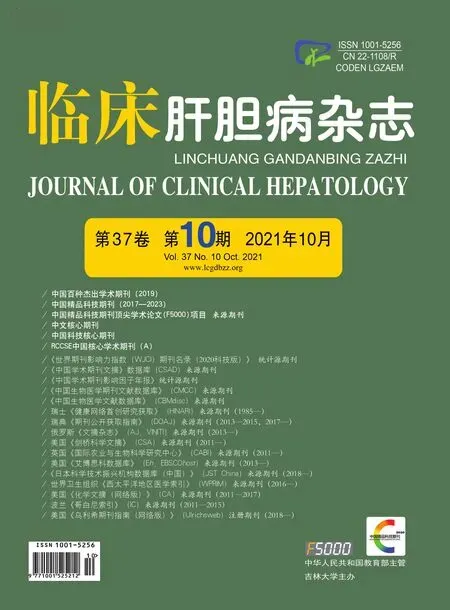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患者中樞神經系統改變相關研究進展
胡一男, 尚玉龍, 周新民
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 消化內科, 西安 710032
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BC)患者易出現瘙癢、疲勞、抑郁、記憶障礙和認知損害等中樞神經系統相關癥狀,這些癥狀的出現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無明顯相關,目前也缺乏針對相關癥狀的有效評價及治療方法[1]。為了更好地了解和探索PBC患者中樞神經系統相關癥狀,研究人員運用影像學等方法,以探究PBC患者大腦結構及功能改變與疾病癥狀的相關性。
1 瘙癢與神經系統改變
瘙癢是膽汁淤積性肝病患者的常見癥狀,如PBC、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膽道梗阻的患者常存在不同程度的皮膚瘙癢癥狀[2]。PBC患者瘙癢癥狀存在晝輕夜重現象,以手掌和腳掌為常見瘙癢部位,但也可出現全身瘙癢[3]。患者瘙癢程度輕重不同,嚴重時可能造成睡眠剝奪、抑郁情緒,甚至自殺傾向。研究人員通過顯微神經電圖證明,C-纖維通過背根神經節將瘙癢信號從皮膚傳遞到脊髓背角的第二神經元,交叉至對側并通過脊髓丘腦束投射到丘腦腹內側核。最終,信號被傳遞到初級感覺皮層、輔助運動區、前扣帶回皮質和頂下葉[4-5]。PBC患者體內存在許多潛在瘙癢原,可通過相應受體介導瘙癢癥狀的產生。既往對膽汁淤積性瘙癢的研究表明,膽汁酸鹽、內源性阿片肽、組胺、性激素被認為是潛在的致癢物質,但其與瘙癢程度相關性不高。目前,Alemi等[6]研究發現,G蛋白偶聯膽鹽受體過表達,小鼠基礎劃痕活動增加,瘙癢程度增加,推測G蛋白偶聯膽鹽受體可能在膽汁淤積性瘙癢的發生中起作用。瘙癢是PBC患者常見的癥狀之一,目前評價PBC患者瘙癢程度主要依靠視覺模擬評分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5-D瘙癢量表(5-D itchscale,5D-IS)等進行評價,均存在一定主觀性。隨著腦功能成像技術的進一步發展,Mosher等[7]通過靜息狀態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發現PBC患者瘙癢嚴重程度與杏仁核和海馬體靜息狀態功能連接度(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SFC)降低有關也與丘腦以及殼前扣帶回皮層的RSFC降低有關[7]。上述研究表明,RSFC可對PBC患者瘙癢程度進行客觀評價,提高患者瘙癢程度判斷的準確性。
2 乏力與神經系統改變
McDonald等[8]利用隨意收縮疊加法測量PBC患者肌肉最大自主收縮程度,研究發現,在PBC患者大腦中,存在中央激活,皮質抑制和興奮性回路異常。PBC患者運動前中樞活性明顯降低,在運動過程中更易出現外周疲勞。Mosher等[9]發現,PBC伴疲勞患者丘腦上頂壁和運動前區RSFC較高。Zenouzi等[10]對PBC伴乏力患者腦灰質進行了一項探索性分析,發現PBC伴疲勞患者右側額上回、左側顳下回、頂葉下回、右側邊緣上回和腦干灰質體積減小。
3 PBC疾病分期與大腦結構改變
早期PBC患者可無自覺癥狀,其生化指標及影像學結果也無明顯改變,這對臨床上診斷和治療造成一定困難。然而,大腦結構相關改變為盡早識別這類臨床前患者提供了新依據。腦磁化轉移成像可提供大腦細微結構的病理生理信息,反映基本的組織病理學改變,其指標磁化轉移率(magnetic transfer ratio,MTR)的差異取決于大分子的濃度和腦內不同組織結構的交換率[11]。目前MTR已被廣泛用于評價多發性硬化患者,在急性和慢性多發性硬化癥病變中MTR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12]。Grover等[13]發現,在早期PBC患者中,丘腦、殼核和尾狀核頭部的腦MTR降低,但晚期PBC患者腦MTR下降幅度與輕癥患者無明顯差異。
4 血清錳與神經系統改變
MTR可對組織特征進行量化,可發現普通磁共振成像下難以識別的異常改變。Forton等[14]發現,在非肝硬化PBC患者中,其蒼白球MTR顯著降低。PBC患者血清錳離子水平升高,蒼白球中 MTR下降程度與錳沉積量一致。Hollingsworth等[15]發現,PBC患者MTR變化與錳離子濃度一致。PBC患者疲勞嚴重程度也與蒼白球MTR下降,腦內錳離子濃度升高呈正相關趨勢,提示錳離子水平改變可能是引起PBC患者疲勞發生的重要原因。PBC患者體內錳穩態與疲勞有關,但因樣本量,納入人群標準等實驗條件不同,PBC患者體內錳離子水平與疾病的確切關系,仍待進一步闡明。
肝性腦病是指發生在終末期肝臟疾病患者中一種慢性神經系統綜合征,常見于血清錳離子含量增高的門體分流患者[16]。臨床表現常以帕金森綜合征和小腦癥狀相結合為特征,MRI表現為T1加權像蒼白球高信號,基底節和其他結構的MRI異常[17-18]。在正常生理情況下,體內錳離子隨膽汁排出體外,PBC患者由于膽汁排泄障礙造成錳離子在體循環中蓄積,最終導致中樞神經系統結構或功能改變[19]。PBC患者早期即可出現非特異性中樞神經系統癥狀,是否與患者肝內膽汁淤積、腦內或體循環中錳離子含量增高有關,以及是否可以通過限制高錳飲食或補充鐵離子緩解疲勞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5 PBC患者熊去氧膽酸(UDCA)的應答與神經系統改變
Mosher等[9]發現,在對UDCA治療應答完全的PBC患者中,其右側杏仁核、丘腦、左側顳中回海馬,RSFC較高。Duszynski等[20]使用紅外光譜分析發現,PBC患者存在腦缺氧、腦血紅蛋白濃度升高和腦血管活動改變。對UDCA治療應答良好的PBC患者,腦血紅蛋白含量低于不應答患者,這可能為提早判斷患者應答狀態以及在臨床中是否應用二線藥物提供了新的依據。PBC患者應答狀態與其遠期預后密切相關[21],目前評價PBC患者是否應答主要依據臨床生化指標,但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PBC患者相關神經系統改變,有望在未來為判斷PBC患者應答狀態提供新依據。
6 總結與展望
PBC患者出現膽汁淤積性相關指標異常之前,部分患者可能已經出現如乏力、瘙癢等中樞神經系統相關癥狀。以往由于對PBC患者中樞神經系統相關癥狀認識不足,未能將其視為疾病早期表現。隨著對PBC中樞神經系統認識的增加,中樞神經系統相關檢查可能成為PBC早期診斷的重要手段。對出現乏力、抑郁、認知功能改變等癥狀的患者,應除外PBC的可能。目前,由于缺乏大樣本對PBC患者中樞神經系統相關的基礎和臨床研究,未來仍需繼續研究中樞神經系統改變與PBC之間的關系。早期識別PBC相關中樞神經系統變化,為該病診治及機制明確提供幫助。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胡一男負責撰寫論文;尚玉龍負責修改論文;周新民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