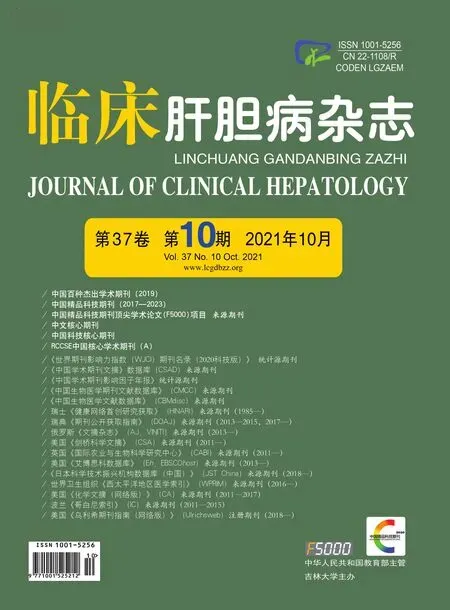特利加壓素聯合白蛋白治療肝腎綜合征效果的預測因素
曹倩玫, 梅浙川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消化科, 重慶 400010
肝腎綜合征(HRS)是終末期肝病的嚴重并發癥。國際腹水俱樂部最近將1型HRS(HRS-1)更名為HRS-AKI,并提出了其定義和診斷標準,取消了舊的亞型分類[1]。目前首選的藥物治療方案是特利加壓素聯合白蛋白治療。肝移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療方法。特利加壓素聯合白蛋白治療是等待肝移植的HRS患者的可靠橋接治療選擇,應用特利加壓素和白蛋白進行移植前治療可改善肝移植術后患者的預后[2-3]。
1 發病機制
1.1 有效血容量減少 HRS的病理生理學機制十分復雜,但其關鍵在于有效血容量的顯著減少,這是由于血液重新分配到內臟循環中和心輸出量相對不足引起的[4]。逐漸進展的門靜脈高壓導致內臟血管切應力增大,增加細菌腸道移位,內源性血管擴張物質大量產生,大量循環血容量聚集于擴張的內臟血管床中[5]。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發生后促炎細胞因子的釋放可加劇內臟和外周血管舒張[6]。最初這些變化通過高動力循環來代償,但隨著肝病進展,血管擴張程度超過可代償的范圍,平均動脈壓(mean artery pressure,MAP)進一步降低,最終導致組織和器官灌注不同程度受損[7]。
1.2 腎血管收縮 MAP的下降導致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AAS)和交感神經系統活動增加,RAAS和交感神經系統的激活引起去甲腎上腺素和血管緊張Ⅱ的釋放,導致嚴重的腎血管收縮和腎血流量減少,最終導致功能性腎功能不全的發生[7-8]。在肝硬化的動物模型中發現,其腎血管對去甲腎上腺素、血管緊張素Ⅱ的收縮反應增強[9]。另外,某些血管活性物質(如半胱氨酰白三烯等)的合成增加也可能影響腎血流量或腎小球微循環[9]。
1.3 白蛋白降低及功能障礙 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的內源性白蛋白不僅降低,而且功能受損[5]。白蛋白降低導致血漿膠體滲透壓下降,有效循環血容量減少。患者體內的有毒物質(如膽紅素、內毒素、NO和細胞因子等)可被白蛋白結合,并被免疫調節或解毒,白蛋白功能障礙導致這些有毒物質水平升高,而這些物質在HRS的病理生理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5]。
1.4 肝硬化性心肌病 心率、心輸出量和血容量增加是肝硬化高動力循環的顯著特征[10]。隨著疾病的進展,患者從高心輸出量狀態演變為心功能障礙狀態,其特征是心臟反應性遲鈍、舒張功能受損、心輸出量減少[10]。肝硬化性心肌病對循環的影響與低心輸出量導致腎血流量減少、腎小球濾過率(GFR)降低有關[11]。
1.5 腎上腺功能不全 肝硬化背景下發生的腎上腺功能不全——肝腎上腺綜合征,可能會影響25%~65%的失代償期肝硬化患者[12]。與腎上腺功能正常的患者相比,這些患者的動脈血壓較低,血清腎素和去甲腎上腺素濃度較高,患HRS-AKI的風險和短期病死率增加[13]。其機制可能是通過下調β-腎上腺素能受體數目、調節兒茶酚胺對心肌收縮及血管反應性的作用,進一步加劇血流動力學障礙[12]。
1.6 全身炎癥反應 近一半的HRS-AKI患者伴有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其與感染的存在無關[14]。全身炎癥反應可能導致血管擴張物質產生增加,從而進一步降低全身血管阻力和有效循環血容量[14]。血清促炎細胞因子在合并自發性細菌性腹膜炎或慢加急性肝衰竭的患者血清中進一步升高,而這兩者均是HRS-1常見的誘因[15]。
1.7 肝腎反射 目前有實驗證據支持肝腎壓力感受性反射的存在,該反射起源于肝臟,可引起腎交感神經活動的改變[12]。肝竇壓力的變化刺激腺苷的局部釋放,進而激活肝臟傳入交感神經系統,后者通過腎傳出交感神經系統繼而誘導腎血管收縮[16]。目前肝腎反射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具有潛在的治療意義。
2 藥物治療
目前首選的藥物治療方案是特利加壓素聯合白蛋白治療。
特利加壓素誘導內臟血管收縮使循環血液重新分配,有效血容量增加,腎臟灌注改善[17];同時也可通過收縮內臟血管降低門靜脈壓力和肝臟靜脈壓力梯度,從而改善HRS患者肝臟和腎臟的血流動力學[18]。現已證實,特利加壓素治療可增加HRS患者的心輸出量并降低其血漿腎素活性[19]。此外,特利加壓素通過降低門靜脈壓力,減少細菌移位,進而減少內毒素血癥和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20]。
高滲白蛋白可通過將液體吸入體循環促進內臟血容量重新分布。輸注白蛋白可降低NO和其他細胞因子水平[21]。白蛋白可改善心臟收縮功能障礙,可增加合并頑固性腹水HRS患者的心臟指數[22]。另外,有研究[23]表明,合并腹水的肝硬化患者應用白蛋白可使其血漿腎素活性、醛固酮水平和交感神經活性明顯降低。40%~50%的患者使用特利加壓素和白蛋白聯合治療后腎功能可顯著改善,HRS的逆轉與患者生存率提高密切相關[24]。
3 治療效果的預測因素
3.1 基線資料
3.1.1 年齡 一項前瞻性隊列研究[3]發現,年齡是HRS-1患者治療反應和生存率的獨立預測因素,年齡>65歲是90天生存率的負性預測指標。在沒有肝衰竭的年輕HRS患者中使用血管收縮藥物和白蛋白治療更有效。Hinz等[25]回顧性研究發現,年齡是與HRS患者治療反應唯一相關的因素,年齡>63歲是治療無應答的預測指標。Testro等[26]研究也發現年齡是HRS患者治療后腎功能改善的一個預測因素。因此,年齡對HRS患者的治療效果具有重要的預測價值,年齡較小的HRS患者有望取得更滿意的治療效果。但由于現有研究納入的病例較少,未來仍需大規模研究以確定具有最佳預測價值的年齡閾值。
3.1.2 MAP、心率、尿量 在一項前瞻性研究[27]中,多因素分析顯示基線MAP是治療反應的獨立預測因素,高基線MAP與治療應答有關。Rodríguez等[28]研究發現,與治療應答者相比,無應答者的基線心率更低。Ghosh等[29]的一項前瞻性研究中,多因素分析顯示基線尿量與治療反應相關。Martín-Llahi等[30]研究也發現基線尿量是腎功能改善的獨立預測因素。基線MAP、心率和尿量可反映HRS患者的初始有效血容量及循環功能情況,因此對治療效果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然而,由于目前相關研究證據較少,仍需更多研究來證實這些結論。
3.1.3 實驗室指標
3.1.3.1 血肌酐(SCr) Sanyal等[31]的一項前瞻性研究發現,基線SCr是HRS逆轉的重要預測指標。一項隊列研究[32]發現,基線SCr較低與HRS患者出現治療應答相關。多變量分析顯示基線SCr是治療反應的唯一獨立預測因素,基線SCr≥3.5 mg/dL與治療無應答相關。在一項多中心前瞻性研究[33]中,多因素分析顯示,當不考慮治療因素時,基線SCr水平是HRS逆轉的唯一重要預測指標。Martín-Llahí等[30]研究也發現基線SCr是患者腎功能改善的獨立預測因素。因此,基線SCr對HRS患者的治療效果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基線SCr越低,越有可能出現治療應答。然而,具有預測價值的基線SCr臨界值的確定仍需要更多研究。
3.1.3.2 肌酐清除率、血清腎素水平 在一項前瞻性臨床研究[27]中,多因素分析顯示基線肌酐清除率和血清腎素水平是治療反應的獨立預測因素。治療應答者的血漿腎素活性顯著降低,同時肌酐清除率升高,而無應答者中則無此效應,部分應答者中出現中度效應。基線肌酐清除率可反映患者初始腎功能情況,血清腎素水平可反映RAAS的活動情況從而間接反映腎灌注情況,兩者對HRS患者的治療效果均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但仍需更多研究證實。
3.1.3.3 膽紅素水平 Nazar等[34]的一項前瞻性研究中,多因素分析顯示基線血清膽紅素水平是治療反應的獨立預測因素,ROC曲線顯示其預測治療反應的最佳臨界值為10 mg/dL。Abdel-Razik等[35]的研究也發現基線血清膽紅素水平與治療反應相關,ROC曲線顯示臨界值(8 mg/dL)可很好預測患者的治療反應。因此,基線血清膽紅素水平對HRS患者的治療效果有較好的預測價值,但預測治療反應的最佳臨界水平仍不確定,高血清膽紅素水平與治療反應不佳有關的機制目前尚不明確,值得進一步研究。
3.1.3.4 白細胞計數(WBC)、白蛋白水平、INR值 一項前瞻性研究[30]表明,基線WBC是腎功能改善的獨立預測因素,治療無應答者的基線WBC更高。一項回顧性研究[36]發現,治療應答組和無應答組患者的初始白蛋白水平具有統計學差異,治療應答者的初始白蛋白水平更高。Rodríguez等[28]研究發現,與治療應答者相比,無應答者的基線INR值更高。三者對治療效果的預測價值仍需更多研究證實。
3.1.3.5 尿鈉、尿NGAL水平 在一項前瞻性研究[29]中,多因素分析顯示基線尿鈉水平與治療反應相關,治療應答者的基線尿鈉水平顯著高于無應答者。有研究[37]顯示,較高的尿NGAL水平與治療無應答相關,可能與這些患者中急性腎小管壞死的存在有關。兩者對治療效果的預測價值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3.1.4 臨床評分
3.1.4.1 Child-Pugh評分 一項回顧性研究[38]發現Child-Pugh評分是HRS-1患者治療反應和生存率的獨立預測因素。Heidemann等[36]研究發現,治療應答者組有更多的Child-Pugh A級患者,而無應答者組則有更多Child-Pugh B級患者。在一項前瞻性研究[39]中,多因素分析顯示僅有Child-Pugh評分與治療反應有關,ROC曲線顯示評分臨界值為10分。Child-Pugh評分是臨床上常用的一種肝功能分級標準,該評分的生化指標包括總膽紅素、白蛋白和凝血酶原時間,目前已有研究[34-36]證實基線總膽紅素水平和白蛋白水平對治療反應有獨立預測價值。因此,Child-Pugh評分對治療效果具有較好的綜合預測價值,但仍需進一步確定預測的標準。
3.1.4.2 MELD評分 一項回顧性研究[38]表明,MELD評分是HRS-1患者生存率的獨立預測因素,而MELD評分<20分與HRS-1患者的治療反應獨立相關。一項前瞻性研究[31]發現基線MELD評分是HRS逆轉的重要預測指標。一項多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40]中,多變量分析顯示HRS逆轉的唯一獨立預測因素是基線MELD評分。von Kalckreuth等[41]的研究也發現,MELD評分是治療反應的預測因素。對特利加壓素和白蛋白治療有反應并且可維持足夠腎功能的患者,有學者[42]建議使用基線MELD或MELD-Na評分作為肝移植候選人名單排序的依據。MELD評分是重要的終末期肝病評分模型,該評分標準整合了血清膽紅素水平、INR和SCr,目前有研究[28,30-35]證據支持這三者對治療反應的獨立預測價值。因此,基線MELD評分對治療效果具有良好的綜合預測價值,但仍需進一步研究以確定其預測標準。
3.1.4.3 CLIF-SOFA評分 一項前瞻性研究[28]表明,治療無應答者的CLIF-SOFA評分顯著高于應答者,ROC曲線顯示在具有治療反應預測價值的變量中,CLIF-SOFA評分最準確。由于目前相關研究較少,該評分的預測價值仍需更多研究證實。
3.1.5 SIRS 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發現,SIRS的存在能改善HRS-1患者對特利加壓素聯合白蛋白治療的腎臟反應,但機制目前仍不明確。在沒有合并感染的情況下,SIRS可能是識別對特利加壓素治療有反應的HRS-1患者亞群的一個額外的預測因素[43]。有研究[44]表明,在存在感染和炎癥反應增加的情況下,特利加壓素的作用會增強,而與促炎細胞因子水平的變化無關。目前相關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3.2 動態變化指標
3.2.1 MAP變化 Sanyal等[31]的研究發現,從基線到治療結束時MAP的總體升高值與治療反應相關,治療應答組的MAP增幅顯著高于無應答組。在Abdel-Razik等[35]的研究中,多因素分析顯示治療第3天MAP升高≥5 mmHg是治療反應的獨立預測因素。治療應答者的MAP上升通常發生在SCr下降之前,這表明由MAP大幅增加所預示的高動力循環的校正在HRS逆轉的過程中可能是關鍵和必需的。然而,約1/3沒有早期血流動力學反應的患者在治療結束時可表現出腎功能改善。因此,如果治療第3天MAP沒有改善,也不應停止使用特利加壓素治療。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45]根據治療后MAP是否早期大幅升高(3 d內升高>10 mmHg)將患者分為MAP有應答者和無應答者。研究發現,MAP應答者治療成功率顯著高于無應答者,這一結論在基于目標導向治療的前瞻性試點研究中得到進一步證實。一項薈萃分析[46]顯示,HRS患者在血管收縮藥物治療期間MAP的升高與SCr降低和尿量增加密切相關,并且與治療反應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HRS患者早期MAP的變化對治療效果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MAP早期大幅升高的患者有望取得較滿意的治療效果。
3.2.2 腎臟微循環變化 Schneider等[47]的研究發現腎臟超聲造影是一項量化HRS患者的腎皮質微循環情況的檢查。超聲造影衍生的腎皮質灌注指數顯示特利加壓素治療后腎皮質灌注的顯著變化。由于該研究規模較小,因此仍需進一步研究確定其預測治療反應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3.2.3 實驗室指標
3.2.3.1 SCr變化 一項前瞻性研究[27]發現,DCD4[(SCr基線值-治療第4天的SCr值)×4]>0.15 mg·dL-1·d-1可準確預測超過90%的患者的治療反應。Abdel-Razik等[35]的研究發現,SCr的早期降低可作為治療反應的預測指標。在治療第3天,SCr降低至少0.5 mg/dL的患者中有79%出現治療應答。一項多中心前瞻性研究[33]發現,治療第4天SCr仍未下降的患者對后續治療仍無應答。Rodríguez等[28]的研究也發現大多數治療應答者的SCr在治療早期即開始下降。因此,HRS患者早期SCr的變化對治療效果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SCr早期降低的患者有望取得較滿意的治療效果。
3.2.3.2 內皮素-1/一氧化氮(ET-1/NO)變化 ET-1和NO分別是重要的局部血管收縮物質和血管擴張物質,ET-1可能參與導致HRS的腎血管收縮[48],NO參與內臟血管擴張。有學者[35]認為,ET-1和NO水平失衡可能影響局部和全身循環障礙的病理生理過程。一項前瞻性研究[35]顯示,ET-1/NO的早期變化可預測治療反應。治療第3天時ET-1/NO降低0.15被認為與治療反應相關。由于該研究規模較小,因此仍需更多研究證實其結論。
3.3 治療方案
3.3.1 藥物劑量和治療時間 一項回顧性研究[41]發現,特利加壓素累積劑量和治療時間對治療應答有顯著影響,是治療反應的預測因素。而Sarwar等[32]的研究表明,HRS患者的治療反應與特利加壓素或白蛋白的劑量或治療時間之間無顯著相關性。一項Meta分析[5]顯示,白蛋白劑量與HRS-1患者的生存率之間存在劑量-反應關系,患者的治療逆轉率和生存率均不受血管收縮藥物的劑量、類型或治療時間的顯著影響。因此,目前兩者對治療效果的預測價值仍存在較大爭議,仍需大規模多中心研究以確定達到最佳治療效果的藥物劑量和治療時間。
3.3.2 利福昔明 一項回顧性研究[49]發現,使用利福昔明的肝硬化患者中急性腎損傷(AKI)和HRS的發生率比對照組顯著降低。在針對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的小規模研究中,利福昔明也被證明降低AKI和HRS的發生率,治療4周后患者的全身血管阻力和腎小球濾過率增加[50]。目前,治療前使用利福昔明對治療效果的預測價值及其機制的相關研究尚不足,值得進一步研究。
4 總結
HRS是進展期肝病的嚴重并發癥之一,患者短期病死率高。因此,早期診斷和治療HRS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目前,HRS的治療手段有限,首選的藥物治療方案仍是特利加壓素聯合白蛋白治療,該治療也是等待肝移植的HRS患者的可靠過渡選擇。因此,識別有助于預測治療反應的因素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不僅有利于為患者制訂適宜的治療方案、節約治療費用,還可作為肝移植候選人名單排序的依據。綜合目前研究,HRS患者的基線資料、治療后變化及治療方案等方面存在諸多指標可能對其治療效果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但目前仍缺乏可用于系統預測HRS患者治療效果的模型或評分系統,相關預測指標與疾病發展的關系及其機制也有待進一步研究。隨著對HRS這一疾病的認識的不斷深入,在今后的臨床工作中,根據HRS患者可能出現的治療反應盡早制訂針對其個性化的治療方案將變得愈加重要。
利益沖突聲明: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曹倩玫負責文獻收集,歸納分析并撰寫論文;梅浙川負責擬定寫作思路,指導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