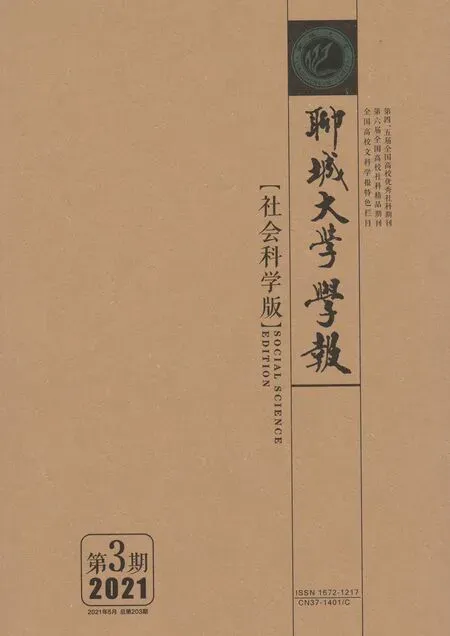《民法典》視域下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司法適用探析
程宇明
(聊城大學(xué) 法學(xué)院,山東 聊城 252059)
科學(xué)技術(shù)的更新迭代已使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傳播突破傳統(tǒng)載體的局限,在廣闊的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中自由流動(dòng),這種傳播方式盡管使公眾獲取信息更加快捷便利,卻也為侵權(quán)人獲取不正當(dāng)利益提供了溫床和滋養(yǎng),侵權(quán)者僅需使用技術(shù)或破解手段甚至無需任何實(shí)施成本,便可通過獲取和傳播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牟取利益,而在司法實(shí)踐中,僅適用遵循“填平原則”的法定賠償無法充分救濟(jì)權(quán)利人的實(shí)際損失,更無法懲戒和預(yù)防日益泛濫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作為現(xiàn)代社會各個(gè)領(lǐng)域智力成果的匯集和彰顯,應(yīng)承載相對于一般自然法更為豐富的社會責(zé)任和功能,因此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兼具法理和實(shí)踐的正當(dāng)性,可以實(shí)現(xiàn)侵權(quán)人與被侵權(quán)人之間的分配正義,并上升至高度文明社會整體的分配正義。《民法典》第1185條規(guī)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識產(chǎn)權(quán),情節(jié)嚴(yán)重的,被侵權(quán)人有權(quán)請求相應(yīng)的懲罰性賠償。①參見《民法典》第七編,侵權(quán)責(zé)任第二章,第1185條。以此為統(tǒng)領(lǐng)性規(guī)則和上位法依據(jù),輔以知識產(chǎn)權(quán)立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全面構(gòu)建懲罰性賠償制度已夯實(shí)基礎(chǔ),更有待司法實(shí)踐予以回應(yīng)、充實(shí)和完善,本文以比較研究和實(shí)證研究的方法,著重分析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shù)乃痉ㄟm用標(biāo)準(zhǔn),并探討應(yīng)明確適用懲罰性賠償?shù)膸追N類型,以期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司法適用提供論證理由和學(xué)理參考。
一、懲罰性賠償適用的理論基礎(chǔ)和正當(dāng)性
就《民法典》的立法構(gòu)造而言,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仍然在體系上歸屬于民法項(xiàng)下的范疇,故由知識產(chǎn)權(quán)引致的損害賠償應(yīng)屬侵權(quán)之債,應(yīng)適用侵權(quán)救濟(jì)中的填平原則,即侵權(quán)人所承擔(dān)之損害賠償應(yīng)基本相當(dāng)于其非法獲利或被侵權(quán)人的損失,但知識產(chǎn)權(quán)本身所不可忽視的無體性和高度流動(dòng)性使其與物權(quán)等單純私權(quán)明顯區(qū)分,填平原則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領(lǐng)域愈發(fā)體現(xiàn)出侵權(quán)救濟(jì)中的天然缺陷。在上述情勢下,將懲罰性賠償?shù)睦砟詈鸵?guī)則引入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以對被侵權(quán)者施以周到保護(hù),更突出對侵權(quán)者的警示和威懾,將更有利于促進(jìn)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健康發(fā)展。
(一)懲罰性賠償理論的發(fā)展和內(nèi)涵
懲罰性賠償在世界各國法律中濫觴已久,發(fā)端于《漢謨拉比法典》等多部法典,早期表現(xiàn)為由預(yù)定比例而確定的多維損害賠償。近現(xiàn)代意義上懲罰性賠償見于《英國復(fù)數(shù)損害賠償條款》,后傳入美國并確立內(nèi)涵、理念、要素及司法適用規(guī)則,美國《侵權(quán)法重述》第2版908條將其闡釋為“基于侵權(quán)者特別惡劣的行為,給予被侵權(quán)者補(bǔ)償性賠償之外,為懲罰侵權(quán)者的惡劣行為且阻遏其與他人將來實(shí)行類似行為設(shè)定的額外賠償”。①[美]肯尼斯?S?亞伯拉罕,阿爾伯特?C?泰特:《侵權(quán)法重述:綱要》,許傳璽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271頁。
我國傳統(tǒng)民法理論著重于侵權(quán)領(lǐng)域填平原則的適用,實(shí)為民法公平原則的秉持和延續(xù),即“任何人都不得從違法行為中獲取利益”②[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xué):法律哲學(xué)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第414頁。。在司法實(shí)踐中多以上述原則作為裁判指導(dǎo),以避免判決侵權(quán)人給予被侵權(quán)人超出其實(shí)際損失的賠償。而在現(xiàn)代社會中,信息傳播由互聯(lián)網(wǎng)主導(dǎo)和加持,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一旦公開發(fā)布,就立刻脫離所有人的控制和管理,侵權(quán)即時(shí)成本極低,侵權(quán)現(xiàn)象頻發(fā)且難以管控,司法實(shí)踐中僅適用填平原則易導(dǎo)致賠償標(biāo)準(zhǔn)難以認(rèn)定,公式化裁判不能充分填補(bǔ)被侵權(quán)人實(shí)際損失,更不具備威懾潛在侵權(quán)人的預(yù)防作用。故從2013年的《商標(biāo)法》修訂到2015年的《專利法》修訂,再到2020年的《民法典》的出臺和《著作權(quán)法》修訂,均引入了懲罰性賠償?shù)睦砟詈鸵?guī)則,以期回應(yīng)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侵權(quán)救濟(jì)的現(xiàn)實(shí)需求,彰顯對被侵權(quán)人的全面救濟(jì),強(qiáng)調(diào)對侵權(quán)者的警示和威懾,鑄就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侵權(quán)救濟(jì)的堅(jiān)實(shí)堡壘。
理論界對懲罰性賠償?shù)亩x各有不同。有學(xué)者直接援引英美法系的懲罰性賠償?shù)亩x,視其為當(dāng)侵權(quán)人以故意、惡意、放任甚至欺詐方式實(shí)施侵權(quán)行為導(dǎo)致權(quán)利人受損時(shí),權(quán)利人可獲得的除實(shí)際損失賠償金之外的損害賠償。③王利明:《懲罰性賠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0年第4期,第112頁。亦有學(xué)者從責(zé)任承擔(dān)角度詮釋其內(nèi)涵,認(rèn)為懲罰性賠償與補(bǔ)償性賠償二者責(zé)任對應(yīng),懲罰性賠償旨在通過讓侵權(quán)人承擔(dān)超出實(shí)際損失的賠償責(zé)任,以達(dá)到懲罰和遏制侵權(quán)行為的目的。④楊立新:《侵權(quán)責(zé)任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333頁。本文論證的懲罰性賠償,旨在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救濟(jì)范疇對其進(jìn)行概念的限縮和確定,特指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司法案件中,法院依當(dāng)事人申請,綜合考量侵權(quán)人主觀上的故意和惡意程度、被侵權(quán)人的實(shí)際損失和侵權(quán)人的違法所得及許可使用費(fèi)等因素,使侵權(quán)人在依填平原則補(bǔ)償被侵權(quán)人經(jīng)濟(jì)損失之外,承擔(dān)的具備威懾、懲戒和預(yù)防作用的經(jīng)濟(jì)賠償方式。
(二)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適用的正當(dāng)性
1.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演變的現(xiàn)實(shí)需求。現(xiàn)代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客體類型不斷演變和擴(kuò)充,愈發(fā)脫離有形載體而與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密不可分。一般網(wǎng)絡(luò)用戶均可通過搜索、觀賞、截取、下載和傳播等方式接觸到客體本身,權(quán)利人對于權(quán)利客體的控制可謂微乎其微,即使有技術(shù)保護(hù)措施也往往面臨被破解之虞,侵權(quán)行為的隱蔽性更令權(quán)利人無所追蹤甚至不知所以。⑤李揚(yáng):《論著作權(quán)懲罰性賠償制度——兼評〈民法典〉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條款》,《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0年第8期,第36頁。此種情況下,懲罰性賠償?shù)倪m用,其預(yù)防和震懾功能可使?jié)撛谇謾?quán)人出于經(jīng)濟(jì)利益的懲罰性喪失而放棄侵權(quán),降低侵權(quán)行為的發(fā)生概率,更在社會公眾知悉的領(lǐng)域確立正向的法律價(jià)值導(dǎo)向,激發(fā)公眾積極參與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熱情和動(dòng)力,實(shí)現(xiàn)全社會的科學(xué)技術(shù)和文學(xué)藝術(shù)繁榮。
2.司法裁判適用的路徑選擇。受客體屬性和侵權(quán)行為隱蔽性的影響,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案件中權(quán)利人多面臨舉證難題。即使舉證充分,如前所述,僅依填平原則也難以充分救濟(jì)被侵權(quán)人的實(shí)際損失,商標(biāo)權(quán)、專利權(quán)和著作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往往難以精確估量。目前,立法確定的賠償標(biāo)準(zhǔn)以被侵權(quán)人所受損失和侵權(quán)人所獲利益為依據(jù),并套用公式進(jìn)行計(jì)算,易導(dǎo)致裁判結(jié)果并不對應(yīng)實(shí)際損失的填補(bǔ)。如商標(biāo)權(quán)侵權(quán)中,由于侵權(quán)行為導(dǎo)致的商譽(yù)降低,權(quán)利人需支出的公關(guān)和營銷費(fèi)用及商品在一定時(shí)間的銷量下滑帶來的相對虧損,都無法通過公式化計(jì)算實(shí)現(xiàn)精準(zhǔn)償付。①朱丹:《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經(jīng)濟(jì)分析》,《東方法學(xué)》2014年第6期,第53頁。而現(xiàn)行立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已將具備故意、惡意和嚴(yán)重情節(jié)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在上述基礎(chǔ)之上加判1至5倍的懲罰性賠償額,既可以進(jìn)一步彌補(bǔ)權(quán)利人的實(shí)際損失,又可填補(bǔ)因侵權(quán)導(dǎo)致的市場份額減損和潛在客戶流失等可得利益損失。
3.對侵權(quán)人懲戒功能的特別彰顯。現(xiàn)行立法規(guī)定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賠償標(biāo)準(zhǔn),欠缺懲戒侵權(quán)人和威懾潛在侵權(quán)人的功能。在嚴(yán)格意義上超出填平原則的許可費(fèi)倍數(shù)賠償模式,侵權(quán)人也僅需要賠償最多至3倍的許可費(fèi),況且在司法實(shí)踐中,根據(jù)抽樣統(tǒng)計(jì),九千余份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司法判例中僅2份顯示適用了3倍許可費(fèi)標(biāo)準(zhǔn),司法適用比率極低。②曹新明:《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損害賠償計(jì)算標(biāo)準(zhǔn)新設(shè)計(jì)》,《現(xiàn)代法學(xué)》2019年第1期,第117頁。對于侵權(quán)人,大部分情況下侵權(quán)成本即使延續(xù)到訴后執(zhí)行階段,也不過是因侵權(quán)行為所獲得的實(shí)際利潤,難免不會再次侵權(quán),或使其他潛在侵權(quán)人蠢蠢欲動(dòng)。而懲罰性賠償采取與侵權(quán)無關(guān)之個(gè)人利益消除的方式來遏制不法行為的發(fā)生,通過施以嚴(yán)厲懲罰威懾其不敢再從事此種行為,更對其他潛在侵權(quán)人產(chǎn)生阻卻功能,大幅度增加違法成本,提高公眾遠(yuǎn)離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的守法意識,以營造尊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良好社會氛圍。
二、懲罰性賠償司法適用的標(biāo)準(zhǔn)
目前,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中的懲罰性賠償在司法實(shí)踐中存在界定不清、選擇偏差和標(biāo)準(zhǔn)模糊的情形。以上情形具體表現(xiàn)為在適用前提中將主觀認(rèn)定和客觀后果混淆;在裁判思路中將法定賠償和懲罰性賠償選擇不當(dāng);以及在適用懲罰性賠償?shù)倪^程中,對于其中的“基數(shù)”和“倍數(shù)”把握不準(zhǔn),導(dǎo)致判定結(jié)果有失公允。針對上述裁判困境,應(yīng)以條文本旨結(jié)合實(shí)踐進(jìn)路作出厘清、明晰和確定。
(一)“故意”、“惡意”與“情節(jié)嚴(yán)重”之厘清
對于懲罰性賠償?shù)倪m用情形,我國目前的《商標(biāo)法》采取了“惡意+情節(jié)嚴(yán)重”的表述模式,而《民法典》、《專利法》和《著作權(quán)法》采取了“故意+情節(jié)嚴(yán)重”的表述模式,此時(shí)應(yīng)首先將“惡意”和“故意”加以區(qū)分。民法理論中的故意一般是指,在明知自己實(shí)施行為會導(dǎo)致侵害他人合法權(quán)益的后果的前提下,行為人仍繼續(xù)實(shí)施這種行為并主觀上希望或放任后果發(fā)生的心理狀態(tài),根據(jù)心理狀態(tài)是希望還是放任,可進(jìn)一步區(qū)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③李世陽:《故意概念的再定位——中國語境下“蓋然性說”的展開》,《政治與法律》2018年第10期,第124頁。。在侵權(quán)賠償范疇中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的區(qū)分并無實(shí)踐意義,由于過錯(cuò)責(zé)任是侵權(quán)賠償?shù)囊话銡w責(zé)原則,理論上只要侵權(quán)人主觀上存在過錯(cuò)(包含故意和過失),無論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故意的程度如何,并不影響對被侵權(quán)人的賠償認(rèn)定。而惡意在主觀上的可責(zé)難程度明顯高于故意,被賦予更惡劣的法律評價(jià)。在司法實(shí)踐中我們可以看到,商標(biāo)侵權(quán)人的主觀惡意具體可表現(xiàn)為假冒和攀附馳名商標(biāo)、借合作和勞務(wù)關(guān)系濫用商標(biāo)商譽(yù)、多次反復(fù)侵權(quán)或以侵權(quán)為業(yè)。而其他領(lǐng)域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立法基本以故意為構(gòu)成要件,如前所述,故意的道德責(zé)難性明顯低于惡意甚至包括間接故意的情形,因此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故意進(jìn)行認(rèn)定不宜上升到惡意標(biāo)準(zhǔn),根據(jù)其一般定義明確懲罰性賠償?shù)闹饔^要件即可,以免遺漏掉未達(dá)到惡意標(biāo)準(zhǔn)的故意情形,即使侵權(quán)人存在惡意,法官亦可在法定賠償幅度范圍內(nèi)以存在惡意為加重裁量情節(jié)提高賠償額度。而惡意在主觀過錯(cuò)程度上應(yīng)明顯甚于故意,至少應(yīng)是直接故意,并將間接故意排除在外,以避免司法適用中將間接故意或情節(jié)輕微的直接故意認(rèn)定為惡意,產(chǎn)生矯枉過正的司法效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經(jīng)濟(jì)社會中的正常有序競爭。
相較于之前立法中“兩次以上”的片面界定,現(xiàn)行立法技術(shù)對“情節(jié)嚴(yán)重”采用了概括式的說明,在司法實(shí)踐中應(yīng)以侵權(quán)影響范圍、持續(xù)時(shí)間、涉及領(lǐng)域以及給被侵權(quán)人帶來的負(fù)面影響等綜合認(rèn)定是否情節(jié)嚴(yán)重而適用懲罰性賠償。前述“故意”和“惡意”是侵權(quán)人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可視為懲罰性賠償?shù)膬?nèi)在本質(zhì);而“情節(jié)嚴(yán)重”是侵權(quán)人主觀是否存在惡意或故意的客觀表現(xiàn),可視為懲罰性賠償?shù)耐庠谛问剑靶袨槿酥饔^狀態(tài)除本人外事實(shí)上難以確實(shí)把握,因此在方法上只有借助外界事實(shí)或證據(jù)進(jìn)行推敲”①曾世雄著:《損害賠償法原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第73頁。。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是,在司法實(shí)踐中,故意和惡意應(yīng)是懲罰性賠償?shù)暮诵囊楣?jié)嚴(yán)重在一定意義上僅僅是故意和惡意的客觀印證。不能僅依據(jù)侵權(quán)影響范圍、持續(xù)時(shí)間、涉及領(lǐng)域以及給被侵權(quán)人帶來的負(fù)面影響等認(rèn)定的情節(jié)嚴(yán)重而忽略主觀上的故意和惡意,直接適用懲罰性賠償;同時(shí)亦不可因侵權(quán)人主觀上已確定具備故意或惡意,但侵權(quán)情節(jié)嚴(yán)重程度難以界定而回避適用懲罰性賠償;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內(nèi)的懲罰性賠償立法本旨即在于對侵權(quán)人的主觀故意和惡意進(jìn)行懲戒,因此,對于符合主觀要件的侵權(quán)案件的情節(jié)嚴(yán)重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不宜過于嚴(yán)格,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應(yīng)對其進(jìn)行適當(dāng)降低以充分實(shí)現(xiàn)懲罰性賠償?shù)墓δ堋?/p>
(二)法定賠償與懲罰性賠償之選擇
當(dāng)前,我國司法實(shí)踐中仍以法定賠償模式為主,即在被侵權(quán)人無法提供證據(jù)證明其所受損失、侵權(quán)人所獲利益或許可使用費(fèi)的情況下,司法機(jī)關(guān)應(yīng)在法律規(guī)定幅度之內(nèi)行使自由裁量權(quán),通過綜合考量被侵權(quán)人的作品知名度、類型、投入成本和侵權(quán)行為的性質(zhì)、主觀狀態(tài)、次數(shù)、持續(xù)時(shí)間、地域范圍等因素,以確定侵權(quán)人應(yīng)支付賠償數(shù)額。②曹新明:《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懲罰性賠償責(zé)任探析——兼論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三部法律的修訂》,《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3年第4期,第9頁。如2020年《著作權(quán)法》修正草案中規(guī)定法院可依據(jù)侵權(quán)行為的情節(jié)嚴(yán)重程度判決侵權(quán)人向被侵權(quán)人支付500萬元以下的賠償額。在司法實(shí)踐中應(yīng)明確劃分法定賠償和懲罰性賠償兩種模式,避免交叉混同,原因如下:
1.二者計(jì)算基數(shù)不同。前者基于舉證困難,基數(shù)難以確定,法院需綜合上述因素形成自由心證以酌定賠償數(shù)額,此基數(shù)并無明確依據(jù)和相應(yīng)公式,但應(yīng)在法定最高賠償數(shù)額之下;后者適用前提須是被侵權(quán)人損失、侵權(quán)人獲利或許可費(fèi)用已明確,法院僅在此基數(shù)上結(jié)合侵權(quán)人故意或惡意程度,以確定相應(yīng)倍數(shù)計(jì)算出賠償數(shù)額,但無法定最高數(shù)額。③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qū)人民法院課題組:《商標(biāo)侵權(quán)懲罰性賠償?shù)闹贫葮?gòu)建》,《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0年第5期,第54頁。
2.二者舉證責(zé)任要求存在差異。前者舉證責(zé)任較輕,被侵權(quán)人僅需證明自身權(quán)利合法以及侵權(quán)行為已經(jīng)實(shí)際發(fā)生,對于實(shí)際損失、侵權(quán)人違法所得、許可使用費(fèi)以及侵權(quán)人的主觀狀態(tài)等并不需要承擔(dān)全部舉證責(zé)任;而后者舉證責(zé)任較重,在法定賠償舉證責(zé)任之外,還要對侵權(quán)人的主觀狀態(tài)、情節(jié)嚴(yán)重程度、實(shí)際損失、侵權(quán)人違法所得或許可使用費(fèi)等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
3.二者立法設(shè)定功能各異。前者是對民法傳統(tǒng)理論中“填平原則”的踐行,旨在解決侵權(quán)事實(shí)明顯存在但被侵權(quán)人舉證困難之情勢,確定賠償數(shù)額以“填平”被侵權(quán)人實(shí)際損失為主要目的,懲罰意味并不明顯;后者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兼具“填平”功能,但主要著重于“懲罰”故意侵權(quán)或惡意侵權(quán),帶有更為強(qiáng)烈的懲罰色彩和震懾功能,旨在向公眾宣示對侵權(quán)人的強(qiáng)烈道德責(zé)難,以遏制類似行為再次發(fā)生。④胡海容、王世港:《我國商標(biāo)侵權(quán)適用法定賠償?shù)男滤伎肌诒本┲R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5—2019判決的分析》,《知識產(chǎn)權(quán)》2020年第5期,第57頁。
法定賠償本身作為一種退而求其次的審理模式,自身即存在較強(qiáng)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其考量因素泛化籠統(tǒng),甚至司法實(shí)踐判決文書說理部分亦較少涉及考量因素和判賠結(jié)果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在上述前提下,如按照一般填平到特殊懲罰的思維路徑,以法定賠償為基礎(chǔ),加以依據(jù)主觀狀態(tài)和情節(jié)輕重仍需進(jìn)一步酌定倍數(shù)的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將會累計(jì)加劇二者的不確定性和減損司法判決的公信力,更使當(dāng)事人怠于舉證而濫化使用法定賠償。因此,法定賠償和懲罰性賠償擇一適用較為公允,即可在當(dāng)被侵權(quán)人在舉證困難的前提下,在法定賠償中將主觀故意或惡意程度和情節(jié)嚴(yán)重作為判決數(shù)額的考量因素,對于主觀故意或惡意程度高或情節(jié)嚴(yán)重的侵權(quán)人判付較高數(shù)額(不超過法定數(shù)額),以此明示法定賠償?shù)膽土P功能,亦可在當(dāng)事人舉證明晰和基數(shù)確定的前提下,著重適用懲罰性賠償,結(jié)合當(dāng)事人主觀狀態(tài)和情節(jié)輕重,酌定相應(yīng)倍數(shù)計(jì)算出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
(三)懲罰性賠償“基數(shù)”和“倍數(shù)”之確定
在舉證充分的前提之下,結(jié)合主觀狀態(tài)和情節(jié)嚴(yán)重的認(rèn)定,即進(jìn)入懲罰性賠償?shù)臄?shù)額計(jì)算和裁量,首先應(yīng)按照實(shí)際損失、違法所得或許可使用費(fèi)對“基數(shù)”進(jìn)行確定,再結(jié)合相應(yīng)因素乘以綜合判定出的應(yīng)乘“倍數(shù)”,最終得出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
1.“基數(shù)”確定。實(shí)際損失,即為被侵權(quán)人因侵權(quán)行為導(dǎo)致的其在正常情況下可以獲得利潤的喪失。顯而易見,在當(dāng)今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傳播速度一日千里,并以指數(shù)級程度在各大平臺、網(wǎng)頁、app上持續(xù)暴漲,在此種情況下,不僅權(quán)利人的損失難以確定,甚至與侵權(quán)行為的關(guān)聯(lián)性也趨向模糊,無法進(jìn)行司法確認(rèn),舉證亦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難以充分窮盡所有相關(guān)證據(jù)。①李揚(yáng):《日本解決IP侵權(quán)訴訟中權(quán)利人舉證難的組合拳制度》,《電子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7年第8期,第76頁。故近年司法實(shí)踐中以實(shí)際損失為基數(shù)維護(hù)被侵權(quán)人權(quán)益案例鮮有出現(xiàn)。
侵權(quán)人違法所得,即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侵權(quán)人因?qū)嵤┣謾?quán)行為而因引致的個(gè)人利益。從現(xiàn)實(shí)角度考量,侵權(quán)所得證據(jù)主要由侵權(quán)人自己掌握,盡管被侵權(quán)人可通過申請法院調(diào)取證據(jù),但將侵權(quán)所得從侵權(quán)人所有所得賬簿等記載中甄別和篩選需耗費(fèi)大量工作,且不論侵權(quán)人存在篡改、偽造和消除所得記載的情形。故在司法實(shí)踐中,以違法所得為基數(shù)計(jì)算懲罰性賠償亦較為少見。
許可使用費(fèi),即權(quán)利人授權(quán)他人在規(guī)定時(shí)間和地域以獨(dú)占、排他或普通許可方式使用其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并收取的費(fèi)用。在司法實(shí)踐中,若存在許可使用合同,多明確記載使用費(fèi)用以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shù),若無許可使用合同亦無約定許可使用費(fèi)用,權(quán)利人應(yīng)提交同類合同以作為司法裁判參考,權(quán)利人未提交的,法院也可以參照相關(guān)行業(yè)組織制定的類似合同中的計(jì)算標(biāo)準(zhǔn)確定基數(shù)。②王利明:《懲罰性賠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0年第4期,第119頁。綜上,以許可使用費(fèi)計(jì)算基數(shù)司法操作性和適用性較強(qiáng),近年來大量被侵權(quán)人對于懲罰性賠償亦傾向于選擇以此為基數(shù)標(biāo)準(zhǔn)主張。
2.“倍數(shù)”確定。對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的懲罰性賠償,在司法實(shí)踐中均以一倍至五倍乘以上述基數(shù)得出最終判付數(shù)額,而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之間如何界定具體倍數(shù),應(yīng)以侵權(quán)人主觀狀態(tài)和情節(jié)嚴(yán)重程度綜合判定,并可具象化為以下裁決考量因素:
一是具體考量侵權(quán)人主觀狀態(tài)。從間接故意,到直接故意,再到惡意,主觀過錯(cuò)程度遞增,酌定倍數(shù)參考值應(yīng)逐級遞增,間接故意參考值應(yīng)低于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參考值應(yīng)低于惡意。
二是具體考量侵權(quán)次數(shù)、時(shí)間、空間等情節(jié)。盡管現(xiàn)行立法不再僅以次數(shù)作為情節(jié)嚴(yán)重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但侵權(quán)行為次數(shù)仍然是不可忽略的衡量侵權(quán)情節(jié)的重要指標(biāo),反復(fù)侵權(quán)且直接故意或惡意侵權(quán)的應(yīng)適用較高倍數(shù);長期持續(xù)性侵權(quán)、侵權(quán)范圍較廣或共同侵權(quán)的,一般對權(quán)利人造成損失較為嚴(yán)重,侵權(quán)人收益亦顯著高于暫時(shí)性侵權(quán)、局部地域侵權(quán)或個(gè)人侵權(quán),應(yīng)適用較高懲罰倍數(shù)。①張新寶、李倩:《懲罰性賠償?shù)牧⒎ㄟx擇》,《清華法學(xué)》2009年第4期,第16頁。
三是具體考量侵權(quán)人是否為自然人。侵權(quán)人為自然人的,對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認(rèn)知程度參差不齊,甚至部分侵權(quán)人被訴法院時(shí)尚不得知自身已實(shí)施了侵權(quán)行為,加之以自身及其家庭財(cái)產(chǎn)作為最終執(zhí)行標(biāo)的,數(shù)額有限且須保障侵權(quán)人正常生活,故不宜適用高倍數(shù)懲罰性賠償;對于侵權(quán)人為非自然人的,一般個(gè)體工商戶應(yīng)根據(jù)其經(jīng)營規(guī)模、日常營利等綜合考量,而作為商事主體和法人主體,應(yīng)推定其知悉本行業(yè)內(nèi)依法經(jīng)營模式和法律風(fēng)險(xiǎn)承擔(dān),應(yīng)承擔(dān)較高注意義務(wù),結(jié)合情節(jié)嚴(yán)重程度而適用較高懲罰性賠償倍數(shù)。②孔祥俊:《當(dāng)前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保護(hù)幾個(gè)問題的探討——關(guān)于知識產(chǎn)權(quán)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5年第1期,第11頁。
四是具體考量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價(jià)值。對于馳名商標(biāo)、許可使用費(fèi)較高的專利以及作者具有顯著知名度的作品,應(yīng)認(rèn)定為客體價(jià)值明顯高于市場其他客體,與之相應(yīng)的侵權(quán)行為自然獲利高于普通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此種情況可適用較高倍數(shù)懲罰性賠償數(shù)額。
五是具體考量侵權(quán)是否有損公共利益。部分侵權(quán)人貪婪追逐侵權(quán)所得,不僅侵犯權(quán)利人合法利益,更罔顧社會公共利益。③袁秀挺、凌宗亮:《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定賠償適用之問題及破解》,《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年第6期,第120頁。如商標(biāo)侵權(quán)中,不符合食品、藥品等安全標(biāo)準(zhǔn)的生產(chǎn)銷售往往和冒用馳名商標(biāo)相伴相生,損害消費(fèi)者人身和財(cái)產(chǎn)利益;而在網(wǎng)文泛濫的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下,部分作者將他人弘揚(yáng)正向社會價(jià)值觀的知名作品肆意篡改,甚至加入黃暴情節(jié)博取點(diǎn)擊率,違背社會公德、污染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且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不限于以上所述,所有有損公共利益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行為均應(yīng)適當(dāng)提高懲罰性倍數(shù)以示懲戒和警示。
三、適用懲罰性賠償侵權(quán)類型
如前所述,在司法實(shí)踐中,依據(jù)當(dāng)事人主觀狀態(tài)和情節(jié)是否嚴(yán)重可酌定適用懲罰性賠償,但對于一些主觀直接故意或惡意和情節(jié)顯著嚴(yán)重的侵權(quán)類型應(yīng)予以明確適用懲罰性賠償,以充分彰顯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在《民法典》中予以規(guī)定的重要引領(lǐng),為科學(xué)適用懲罰性賠償指明路徑趨向,并回應(yīng)懲罰性賠償?shù)牧⒎ū局肌R韵聯(lián)竦湫皖愋瓦M(jìn)行列舉和闡釋,但該類型外延應(yīng)保持開放,伴隨時(shí)代發(fā)展和客體演變,有待其他類型進(jìn)一步充實(shí)和擴(kuò)展:
(一)生態(tài)化侵權(quán)
在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傳播廣袤無邊、一日千里的背景之下,現(xiàn)代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已然突破傳統(tǒng)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形態(tài),呈現(xiàn)出生態(tài)化侵權(quán)的特性。具體表現(xiàn)為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的一系列的轉(zhuǎn)發(fā)、截取、推送和播放等行為,并逐漸形成固定合作利益生態(tài)鏈條,鏈條中涉及的侵權(quán)人主要包括app和網(wǎng)站經(jīng)營者、微信平臺運(yùn)營者、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媒體意見領(lǐng)袖、銷售推廣者和大數(shù)據(jù)整合推送者等;生態(tài)化侵權(quán)并不囿于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線下亦存在多種形式的生態(tài)化侵權(quán),如注冊空殼公司只為從事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從而成為幕后操作者并進(jìn)行組織化的生產(chǎn)、宣傳、銷售等一系列侵權(quán)行為。以上侵權(quán)形態(tài)經(jīng)過組織者和參與者以獲利目的進(jìn)行的精密協(xié)作,而形成固定營利模式和分贓比例,存在明顯故意,并具有重復(fù)侵權(quán)和持續(xù)廣泛侵權(quán)的嚴(yán)重情節(jié),可直接適用懲罰性賠償。
(二)常業(yè)型侵權(quán)
相較于偶發(fā)或暫時(shí)性侵權(quán),常業(yè)型侵權(quán)主觀故意或惡意更加明顯,一般是指侵權(quán)人以知識產(chǎn)權(quán)侵權(quán)為主要經(jīng)營行為,并以之作為主要利潤來源。如故意模仿知名商標(biāo)、套用他人品牌故事、抄襲他人宣傳文案或店面裝潢,以使公眾產(chǎn)生混淆并獲得不正當(dāng)利益。近年的“茶顏悅色”一案中,作為易混淆商標(biāo)“茶顏觀色”的商標(biāo)權(quán)權(quán)利人廣東洛旗公司,屬于典型的山寨商標(biāo)權(quán)搶注公司,已多次惡意注冊知名商標(biāo),并對知名商標(biāo)提起惡意訴訟。①參見《長沙市岳麓區(qū)人民法院(2019湘1014民初14008號)民事判決書》,“原告廣州洛旗餐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州洛旗”)受讓“茶顏觀色”和“茶顏”的商標(biāo)存有明顯攀附意圖,并非善意,其行為不具有正當(dāng)性,駁回廣州洛旗的全部訴訟請求。”上述以侵權(quán)為業(yè)者或權(quán)利濫用人嚴(yán)重違反了誠實(shí)信用原則,對真正權(quán)利人的利益損害顯而易見且不可估量,更擾亂了市場秩序和影響了司法公正,可直接對其施以具備懲戒功能的懲罰性賠償。
(三)破壞信賴基礎(chǔ)的侵權(quán)
此種侵權(quán)多以合同關(guān)系為基礎(chǔ),即侵權(quán)人和被侵權(quán)人存在勞動(dòng)勞務(wù)、許可使用、銷售代理或代加工等合同關(guān)系,在合同履行期或合同終止后,侵權(quán)人基于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客體的知悉或占有而實(shí)施的侵權(quán)行為。②吳漢東:《知識產(chǎn)權(quán)損害賠償?shù)氖袌鰞r(jià)值基礎(chǔ)與司法裁判規(guī)則》,《中外法學(xué)》2016年第6期,第29頁。此種行為具備監(jiān)守自盜的惡意動(dòng)機(jī),對于外部公眾更具有欺騙性和隱蔽性,最終導(dǎo)致合同相對方與之的信賴崩塌和自身的商譽(yù)喪失,破壞了正常市場秩序下以知識產(chǎn)權(quán)為媒介形成的信賴基礎(chǔ),應(yīng)給予高度道德責(zé)難性的法律評價(jià),應(yīng)對此適用懲罰性賠償。
結(jié)語
懲罰性賠償制度重新調(diào)整了被侵權(quán)人在侵權(quán)法律關(guān)系的可得利益比例,并對侵權(quán)人施以嚴(yán)厲的懲罰性判付,從而實(shí)現(xiàn)了法律應(yīng)有的利益調(diào)整和懲戒預(yù)防功能。目前,以《民法典》為主導(dǎo),以其他單行法為重要支撐,懲罰性賠償制度在知識產(chǎn)權(quán)立法體系中已基本設(shè)立,有待司法實(shí)踐予以確認(rèn)和調(diào)適,在具體案例中靈活精準(zhǔn)地予以引用,同時(shí)積累審判爭議中的最優(yōu)解決方案以反哺指導(dǎo)實(shí)踐。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審判者應(yīng)大膽適用而不失謹(jǐn)慎,重點(diǎn)考量侵權(quán)人的主觀狀態(tài)、侵權(quán)情節(jié)和社會影響,力圖實(shí)現(xiàn)審判的標(biāo)準(zhǔn)化和精細(xì)化,推動(dòng)知識產(chǎn)權(quán)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落地實(sh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