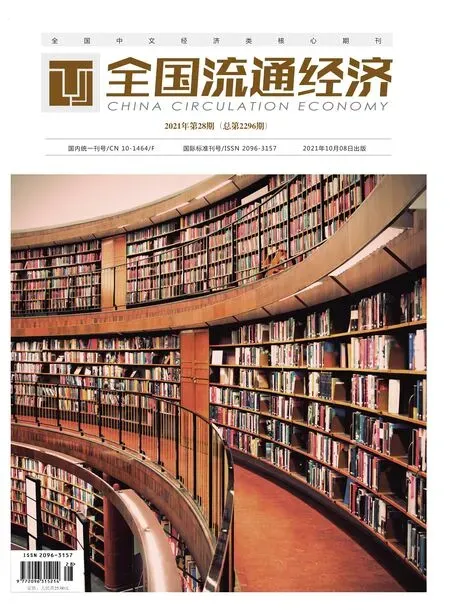ST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研究
李紅梅 曾馨瑢(通訊作者) 王 霞
(四川輕化工大學管理學院,四川 宜賓 644000)
一、引言
ST公司試圖短時間擺脫“*ST”或“ST”帽子,利用盈余管理調整公司虧損,以非經常性損益獲得不可持續盈余,雖降低了ST公司從根本上提升業績的難度,但導致我國較之其他資本市場退市率低。退市博元[600656]曾二度戴帽,2013年去ST,2015年再度戴帽,2016年退市;退市海潤[600401]曾三度戴帽,2016年5月去ST,次年再度冠以*ST,2019年退市。類似“不死鳥”的存在不合時宜,重塑適應市場變化的高質量制度迫在眉睫。2020年12月31日新規頒布并即日實施,新規對限制非經常性損益具有一定限制作用,警示資本市場正確理解非經常性損益在財報中的作用。雖然非經常性損益在財報中單獨列示披露,事實上,并未引起投資者廣泛關注。或者說,投資者普遍對非經常性損益理解不透徹,導致不正確投資行為。“殼”資源關系著管理層“操縱成本”與“預期收益”的衡量,提倡上市公司主動退市難之又難。
二、ST制度概況
ST制度是針對在滬深交易所中出現財務狀況或者其他狀況異常的股票而建立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風險警示制度[1]。被冠以“ST”或者“*ST”公司(以下簡稱ST公司)撤銷風險警示成為第一要務,在此規定下公司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其一徹底清除存在的所有風險情形并改善經營業績;其二,選擇重大資產重組,經會計師事務所嚴格審核后,認為重組顯著提高了公司經營業績。
鑒于資本市場不可避免存在虛有其表的劣績股,表面上可觀的數字化指標嚴重混淆投資者視線,阻礙資本市場良性發展。2020年征集意見稿公布,打響了貫徹注冊制理念的退市制度改革升級戰。2020年新規汲取多方反饋意見并借鑒國外成熟退市制度經驗,深化了在細化退市標準、簡化退市流程、重新設定重大違法強制退市的停牌時點及調整退市整理期的安排等多方面的變革。其中,重新設定了公司退市考量指標體系,由以往“連續年度凈利潤為負值、連續年度營業收入低于1000萬元”單一指標替換為“扣非前后凈利潤孰低者為負值且營業收入低于1億元”組合財務指標,將觸發期限統一縮短為兩年。
三、盈余管理屢禁不止的現實動因
盈余管理是管理當局在合法范圍內通過一定手段改變會計政策、會計估計或公司運行方針在短期改變表面經營狀況。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一直是資本市場討論熱點。學者們主要觀點是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會導致財務數據不夠可靠、公允,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人會選擇進行盈余管理以粉飾業績。應計盈余管理以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為破擊點,整調會計期間內企業盈余的分置情況;真實盈余管理則以日常經營活動涉及的范疇,偏離正常產品費用、生產、銷售、宣傳等階段的經營方向,縮減成本,達到影響短期價值的目的。不論ST公司如何更換“外衣”或變換“內在”,始終滯后的經營策略和結構無法徹底性地改善。另外,由于我國對盈余管理、非經常性損益的內涵和外延界定不夠清晰以及退市制度不夠完善,導致非經常性損益成為ST公司扭虧為盈普遍選擇的手段。
四、ST公司“自救”與“他救”動機
ST“家族”中大部分屬于高負債、大規模的制造業或國有企業,挽救這類企業動機甚多,不僅關乎企業自身,同時牽涉其他相關利益者。針對ST公司自身,只有維護上市公司這一“身份”,才能在對外融資方面獲取便利、提升企業良好形象以及獲得政府優惠政策支持。一旦企業被納入風險警示板塊,將給資本市場乃至投資者傳遞出負面信號,影響企業股價、業績等。不僅如此,上市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利益與業績表現相輔相成,為保護自身利益不被損害,力推各種手段挽救瀕臨退市ST公司[2]。另外,對于債權人、投資者、地方政府而言,若ST公司遭遇暫停上市或者終止退市,最終結果很可能是投入資本蒸發。由于民事賠償制度不夠健全,中小股東也可能自行承受巨額經濟損失,難以收回投資[3]。上市公司為地方經濟貢獻了巨額稅收收入,政府為了維護形象可能會實施大規模救助計劃,此舉可能會彌補經營管理短板、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但也可能造成企業對政府過度依賴,促成惰性發展。
五、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盈余管理現狀
ST制度是為了淘汰劣質上市公司,提高退市率,促進企業優勝劣汰,降低信息不對稱危害性,提醒ST公司關注并解決自身經營難題,警示投資者密切關注這類公司信息并理性判斷該公司股票是否具有投資價值。2013年~2019年期間,剔除因吸收合并、未在法定期限內披露年報原因,ST公司僅退市16家,且存在多次戴帽摘帽的現象。這使得ST制度實施效果不如預期,部分面臨退市風險ST公司在整頓期利用某些手段避免退市的現象一直存在。
1.我國上市公司非經常性損益信息披露情況
公告第1號②規定要求,上市公司應當根據文件規定、會計準則并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在附注中予以說明非經常性損益的情況[4]。相關規定賦予上市公司如何判定非經常性損益界限較大自主性。從非經常性損益相關規定發展與完善可以看出,規范披露非經常性損益定義、項目和金額是完善相關制度的墊腳石,想要資本市場獲得從長期繁榮和昌盛,還需要滿足資本市場以及投資者對反映上市公司真實盈利能力的迫切需求。
下文統計了2015年~2019年上市公司主要財務數據,縱向對比分析了非經常性損益披露情況以及在凈利潤中的比例,挖掘非經常性損益在ST公司中如何發揮力挽狂瀾的作用。
由表1可見,2015年~2019年上市公司凈利潤呈上升趨勢,其中2017年增長勢頭較強,僅2018年出現了較小縮減。另外,扣除非后凈利潤也伴隨凈利潤出現了相應幅度增長,但就增長幅度而言,扣除非后凈利潤增長幅度大于凈利潤。

表1 非經常性損益信息披露情況 (金額單位:億元)
值得關注的是,2018年總有297家上市公司突破了非經常性損益占凈利潤比例100%的界限,即使逐年下降的趨勢說明了上市公司整體市場盈利水平有所提升,但是也不能否認非經常性損益的影響力度。從最終保留數據來看,占50%以上的上市公司數量增多、規模擴大,整體趨勢增強。其中2018年整調非經常性損益實現凈利潤為正的公司高達159家,有93家公司扣非后凈利潤虧損,包括19家ST族公司,合計非經常性損益金額231.32億元,凈利潤總額為-655.04億元。因此,仍存在部分連續虧損公司在非經常性損益的庇護之下繼續經營并擺脫了退市困擾。
2.ST 公司運用非經常性損益進行盈余管理情況
為了解非經常性損益對凈利潤的影響程度以及盈余管理與企業價值的關聯性,本文選取2019年成功摘帽的21家ST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關注在ST公司“保殼”扭虧之戰當年財務數據,統計結果顯示有9家公司2018年度扣非后凈利潤為負,非經常性損益出現異常增長,占樣本公司的43%。可見依舊存在一部分公司未通過改善公司經營狀況而達到摘帽條件。在撤銷退市風險警示條件中,不存在限制扣非后凈利潤的要求,因此對上市公司會計核算嚴謹性、管理層職業判斷提出新挑戰,加大上市公司認定責任和證監會監督管理難度。

表2 2019年21家摘帽企業凈利潤變動情況(單位:萬元)
3.ST公司運用非經常性損益盈余管理案例分析
近年來,ST公司巧妙運用非經常性損益情況愈加嚴重,而帶來的是資本市場資源不能公平、公正進行分配的結果。ST公司之間劃分原則不夠標準以及業務之間的差異性,決定了非經常性損益截然不同的調整方向、幅度。根據企業會計準則和自身經營實際情況選擇易操作、易實現手段,主要方式包括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政府補貼收入、資產減值、投資收益或者降低期間費用等。因此,下文將通過列舉不同企業實施手段,分析如何調整企業內部資源配置剝離不良資產以粉飾財務指標,不僅迷惑投資者,而且達到摘星脫帽的目的[5]。
(1)非流動資產處置
貝因美[002570]屬于食品制造業,主要經營嬰幼兒奶粉產品,包括配方奶粉、營養米粉等其他嬰幼兒輔助食,在行業及消費者中擁有良好的美譽度。作為深交所第一支以奶粉為主要產品的上市公司股票,長時間位居于國產奶品牌領先地位。即使近幾年新生兒數量減少、消費人群下降、高端奶制品需求增長以及生產成本上漲,使得貝因美市場壓力不斷加大。但是,2018年中國突破了十四億人口大關,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為奶粉制品消費帶來了增長點,并帶動了三四線城市新消費群體覺醒,與抑制奶粉市場的消極因素大致抵消。隨著奶粉注冊制度落實,貝因美作為國內奶粉行業巨頭,連續幾年難看的業績表現與大好市場前景不匹配。
從公司歷年利潤表情況看出,2015年開始貝因美業績出現“斷崖式下滑”,2016年出現了首次虧損,2017年再度虧損105,704萬元。卻在2018年主營業務未發生重大實質性改變時,實現了41,11.35萬元凈利潤。僅僅在一年內,通過處置資產獲得收益共計6519.21萬元,收益主要來源于宜昌搬遷補償收益及公司出售房產,甚至2017年度董事會審議通過了出售房產決議,預先為2018年籌劃營謀。整體來看,貝因美2018年經常性損益金額變動幅度存在異常,扣非后凈利潤依然為負,當年所獲得收益占利潤總額89.92%,期間成本也有較為明顯下降,此番大動作背后反映了貝因美實際上未根據此前低迷市場前景制定轉型計劃,僅為貝因美暫時注入興奮劑。其現金流量比率由2018年0.112下降為2019年的0.022倍,由于變賣資產所產生后續推動作用逐漸削弱,該公司償債能力變弱,再次說明貝因美2018年資產處置的確短期內改善了公司償債能力并帶給公司盈余短暫增長,但僅過去一年就暴露出原形,恰好佐證了非流動資產處置直接關系到貝因美2018年度盈利還是虧損。
(2)接受政府補助
大型企業作為地方經濟支柱,不僅能協助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也是政府效益考量指標結構的重要部分,甚至關系官員、企業高管安危成敗。在幫助企業有效解決發展難題的過程中,政府往往樂意參與并采取政府補助的扶持形式。挽救“病危”企業不僅能為后續帶來可觀財政收入,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攻克就業、稅收等民生問題,推動基礎設施建設。除此之外,政府補助具有穩定性強、金額大的特點,是短時間內緩解企業虧損問題最方便且成本較低方式之一,因此上市公司為脫離退市風險,更傾向于借助政府“無形的手”合力救治。
石化油服[600871]是中國目前最大的綜合性油氣工程與油田技術服務公司,是一體化全產業鏈石油服務龍頭企業,而且該公司具有較強國企背景,曾借助儀征化纖成功上市。事實上,2012年~2017年,*ST油服連續6年扣非后凈利潤為負,2016年是虧損大年為-161.1億元,2017年繼續虧損105.9億元。其2018年主營業務收入,相較于2017年增長20%,上漲幅度正常。但是,來自關聯方收入高達28%,同年營業外收入拉動比例高達264%,剖析其中影響利潤增長主要因素是依靠大力度政府補助。回顧2016年至2018年石化油服獲得政府補助,2018年度共計73004.8萬元,同比增長96%,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較2017年增長近30倍,占凈利潤333%,遠超于其他年度。尤其2018年是改善業績的關鍵年度,根據業績預盈公告,隨著國際油價回升,2018年*ST油服在第一季度預計將實現3000萬元盈利。分析收益結構可知,政府以職工分流安置的名義后援3.5億元,以及債務重組舉獲1.2億元,致使第四季度凈利潤繼續虧空29791.8萬元。一方面,對比了該公司2017年度~2019年度資產負債率,發現2018年資產負債率仍高達90.50%,公司短期償債能力只是得到了短暫緩解。另一方面,綜合分析石化油服2018年~2020年ROE,石化油服僅2019年高于同行業平均值,該公司盈利能力得到了提升。但2020年ROE又跌入了低谷,位于行業排名第一的和順石油[603353]2020年ROE14.68是石化油服1.17的十多倍。在遭遇兩年連續虧損和主營能力持續下降時,政府補助依舊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最終盈利14205.6萬元,為“不死鳥”豐滿了羽翼,企圖剝殼摘帽振臂高飛。

表3 2016年~2018年石化油服基本財務情況(單位:千元)
(3)資產減值損失轉回
為了在一年時間內改善前兩年連續虧損情況,ST公司為了使得財務報表達到預期效果,往往會從資產減值準備方面獲取補償,一方面減少計提金額,另一方面最大幅度轉回以彌補虧損,其存在一定主觀性為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多選擇,操縱手段更加靈活。根據公告第1號可知,如果披露的年報信息顯示計提資產減值損失金額和發生頻率已經嚴重影響了財務報表使用者對該公司真實經營業績做出合理判斷,并且未對此番計提行為給出合理說明,那么此次計提的資產減值損失應納入非經常性損益范疇。中國船舶[600150]年報顯示,2016年、2017年分別計提資產減值損失375630萬元、269248萬元,相較于2015年出現了近12倍和9倍大幅度變動,而2018年只計提了39186萬元,比上年度減少230062萬元,其中存貨跌價損失占比最大,說明2016年和2017年資產減值損失金額出現了異常增長。同時,2016年、2017年虧損額也是最多的兩年,凈利潤分別虧損260682萬元、230006萬元,該年度凈利潤與所計提資產減值損失存在不匹配嫌疑,前兩年異常計提資產減值損失加大虧損額達到了在2018年扭虧為盈關鍵年度平滑利潤的目的,傳遞出企業經營狀況轉好的信號。

表4 2014年~2018年資產減值損失金額 (單位:萬元)
ST公司在合法范圍內玩轉盈余管理之技,利用退市制度漏洞,粉飾公司經營能力。然而隨著政策改革,或有的一次性經營業績也是禁不住驗證的。另外,新規施行前已暫停上市、處于恢復上市、終止上市及退市整理期安排環節中的公司,繼續適用原規則標準和程序及原配套業務規則。那么,可能給之前已暫停上市的公司提供了盈余管理空間,新舊退市制度銜接問題可能存在漏洞。任何一種制度都很難從根本上消除企業過度盈余管理現象,因此相關部門應當采取一定措施限制這類不合理行為,堅決抵制、杜絕上市公司通過盈余管理手段投機取巧的現象。
六、對策建議
1.加強企業自救能力
非經常性損益的確認標準受主觀意圖影響程度較大,然而任何制度不可能“窮盡”所有情況,隨著制度更新可能采取新手段避免退市,因此需要加強公司的“自救”能力。ST公司大多以制造業為主,大部分公司存在較高資產負債率,因此需要結合企業具體情況和項目類型針對性地選擇摘帽方式,不能一味地忽視主營業務增長乏力問題的存在,應當合理規劃非經常性損益,剔除不良資產合理優化企業資源,實現經營模式優化。另外,通過申請適當政府補助扶持產業升級轉型,改變陳舊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在適應市場需求的前提下,提升企業品牌效應,延長產業鏈,從根本上提高企業經營業績水平。
2.相關部門制定完善的制度
建議相關部門應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更加詳盡、具體指標,完善會計準則,規范非經常性損益制度勢在必行。當上市公司自主劃分非經常性損益時,可查詢到具體可操作性的處理方法,既能夠減少監管部門工作程序,又能壓縮ST公司盈余管理空間。新舊制度的銜接也是新制度實施過程中亟須解決的難題,以防范上市公司為了適應退市制度的改革,不惜創造新的手段扭虧為盈,沒有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經營能力,因此必然要切斷ST公司寄生的各種途徑。
3.遵循“因企訂規”
新退市制度主張嚴格遏制非經常性損益的負面影響,對防范操縱該方面盈余管理起到了一定作用,也應合理設置退市標準進行綜合性評價,不能因強調嚴格而忽略了行業的差異性。雖新退市制度被稱為“史上最嚴退市制度”,但在財務指標方面,“營業收入不得低于1億元”的規定應當結合具體行業,某些高利企業是否需要提高營業收入水平。因此,建議劃分行業構建區間性金額指標,不僅要考慮凈利潤絕對數大小,又要考慮企業經營能力增減情況。
注釋:
①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20年修訂)
②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1號——非經常性損益(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