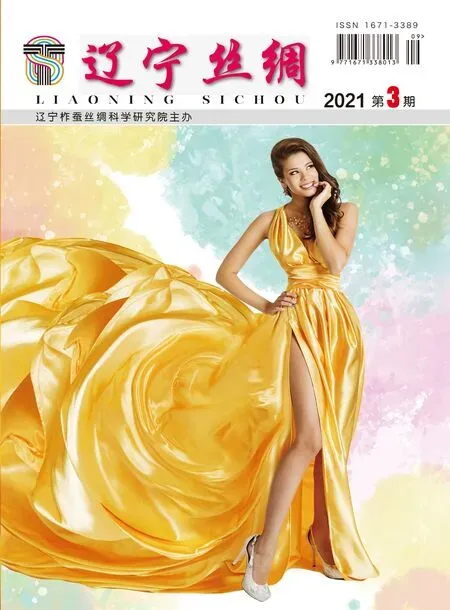勞動教育的價值回歸與經驗重構
張修良 張 穎
(1.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江蘇 南通 226000;2.南通市天元小學校,江蘇 南通 226000)
勞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勞動價值觀和教育觀是伴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整個進程的重要因素。建國70多年來,教育者一直在摸索著勞動教育的內涵與地位等問題。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明確了新時代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對加強勞動教育的新要求。這無疑再一次喚醒了教育者對勞動教育的更多思考,促使教育者進一步探索勞動教育的邏輯和意義。
一、價值的回歸——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的現實意義
勞動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回到馬克思,我們能夠發現勞動概念的本源,用馬克思主義勞動觀來指導中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一)歷史唯物主義與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歷史、創造了世界,也創造了人類自身。所謂勞動,即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人在生產勞動中,創造出自身賴以生存的物質,建立起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從中得到了自身質一般的提升與飛躍。勞動是人擺脫自然界原始束縛,通過自身的腦力和體力,改造世界、創造無數奇跡的有利工具,也是人不斷產生超越自然的道德情操、聰明才智、審美觀念的最為本質的動力。習總書記曾強調指出:我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人恩賜施舍的,而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用勤勞、智慧、勇氣干出來的!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在中國人民手中,不可能成為了可能。”這再一次顯示了勞動的力量之偉大,勞動的意義之深遠,也更加真切地印證了馬克思主義勞動觀的科學性、有效性和時代性。因此,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必須寄希望于全國人民付出辛勤的勞動,寄希望于勞動教育的有效實施。
(二)勞動價值創造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鞏固。馬克思認為,勞動者創造了商品的價值,而并非資本家。勞動的價值取決于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只有勞動才是社會財富的本源。“馬克思非常強調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者創造的,要生產出一個商品,就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一定量的勞動。”勞動至上、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對于現代的主流意識形態鞏固和學生的勞動教育,具有深刻的指導性作用。隨著后工業時代的來臨,傳統的勞動形式正逐漸被高科技、智能化所替代,社會意識形態中出現了一些非主流的聲音,人的價值觀,尤其是勞動價值觀出現了扭曲。是否付出勞動、應當付出怎樣的勞動,成為了人們心中的疑惑。有這樣的疑惑,其根本在于沒有理解勞動創造財富的唯一本源性,同時矮化了體力勞動,過度神話了腦力勞動,歪曲理解了新時期勞動形式的本質。因此,要牢牢樹立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觀理念和勞動榮辱觀,確立勞動創造財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觀點,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
(三)“教勞結合”與人的全面發展。“教勞結合”的觀點具有深遠的社會歷史背景,在工業化大生產之初,為了讓勞動者在勞動時適應當時先進的生產力,提升勞動者的文化水平,人們提出了在勞動中進行相匹配的教育,因此有了所謂的“教勞結合”的觀點。“教勞結合”是對剝削制度的顛覆,是勞動者獲得自身地位和實現個人價值的體現。也只有在工業化進程中,勞動的真正意義才得以逐漸釋放開來,勞動才不至于總是成為“奴役人的手段”,而不斷進化為“解放人的手段”。馬克思認為:“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來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與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在勞動中提升綜合素養與在教育中貫穿勞動觀念、勞動態度、勞動習慣、勞動技能等,有著密切的聯結。勞動教育不但應該成為獨立單列的教育內容,也應與智育、德育、美育、體育等育人形式相結合、相統一。勞動教育的目的應當是基于“教勞結合”,追求教育的勞動本源性和真善美,并不斷完成人的本質在新時期的解放。
二、經驗的重構——既往勞動教育實踐的現實反思
我國在勞動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具有寶貴而又豐富的經驗,早在建國初期,我國便探索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勞動的觀點,在教育領域加入勞動的因素。如在學校開辦校辦工廠,鼓勵開展勤工儉學等。
(一)從“體腦分離”到“體腦合一”。早在奴隸社會剝削制度建立的初期,所謂的“體腦分離”便已經形成。剝削階級為了搶奪勞動者的勞動價值,脫離了繁重的體力勞動。隨著社會的發展,到了資本社會,由于機器工業和勞動形式的精細化、社會分工的多元化,又導致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二次分離。我國在建國后,極大限度地扭轉了體力勞動者被剝削的現實。在教育領域,我國在1958年前后相繼推行了和勞動相關的方針和舉措,如在課程中加入了理論與社會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素材,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國民公德方面提出“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勞動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說馬克思當時提出的教勞結合,重在解決勞動者的知識化的話,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勞結合,則重在解決知識分子的勞動化問題。”因此,建國初期的教勞結合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勞動教育的雛形。當前,我國乃至世界已發展到了后現代工業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水平,要讓人的價值本質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體腦合一”是唯一的路徑,“體腦合一”意味著人的能力得到全面的開發,勞動的形式擺脫了腦力和體力的二元論,而是作為人的綜合能力素質的代名詞,這同時意味著教育的公平性和新時期較高層次的發展水平。
(二)從“勞動技術教育”到“勞動教育”。以“知識分子的勞動化”為核心的“教勞結合”是我國勞動教育的初期形態,這里的“勞動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體力勞動,最終演變為“去知識化”。隨著國家工作重心的改變以及經濟的復蘇,“知識”被重新審視,這從鄧小平提出的“三個面向”、“四有新人”的教育方針中可見一斑。隨著以往“去知識化”得到根本性的斧正,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博弈已經淡化,其重點和中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勞動教育很大程度上理解為“勞動技術教育”。這樣的教育傾向有其優越性,而至今,“勞動技術教育”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我國經濟實現質的飛躍的同時,勞動教育的概念應當被重新審視。那種追求功利的“技術性教育”不應該成為當前勞動教育的主要內涵,而只能成為真正意義上勞動教育的組成部分。勞動教育也不僅僅限于生產性勞動的教育,還包含了對生活勞動、服務性勞動以及公益性勞動的教育。勞動教育的關注點也不能僅僅是勞動技能的獲得,還應關注勞動觀念和勞動習慣的形成、勞動價值體系的構建以及與品德、審美、健康相融合的全面素質的培育。
(三)從“手段教育”到“全人教育”。我國的勞動教育從建國始總是被人為地充當某種“利器”,帶有一定功利主義色彩。首先,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到文革結束這段時期,勞動教育在特定時刻成為了拒絕知識、反資反修和改造思想的“利器”,勞動教育自然地與思想品德劃上了等號。這樣的等號,限制了勞動教育的內涵,同時也被極左地異化為通過勞動來取代科學知識的現象。第二,從文革結束到20世紀末,勞動教育成為了經濟快速恢復與發展的“利器”。這段時間,由于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崇尚知識和技術、追求國民生產成為了社會的主旋律,勞動教育在此時需要為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局服務,因而更多地被等同為技術教育和生產教育。第三,絕大多數歷史長河中的勞動內涵更傾向于體力勞動,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更是如此。勞動教育總是被矮化、僵化和弱化,這使得勞動的意蘊并沒有得到正式的澄清。有些教育者甚至將勞動作為訓誡的“利器”和管理的手段。總而言之,無論是什么樣的“手段教育”帶來的教育結果顯然是不利的,教育并非手段,而是合乎人性、詮釋人的本質、發展人的素養的有效形式和載體。勞動教育的核心應當是“價值觀教育”,且是一種“全人”的價值觀,其目的在于“完善人”、“成全人”,達到人的全面發展。
結語:勞動教育在當前時期被重新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其價值的回歸體現了國家、社會整體的不斷進步,也體現了教育在我國改革開放關鍵發展期的新思路、新舉措和新趨向。其經驗的重構對于勞動教育體系構建和運行機制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在正確勞動價值觀的引導下,勞動教育的實踐將沿著教育本真、教育全人的道路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