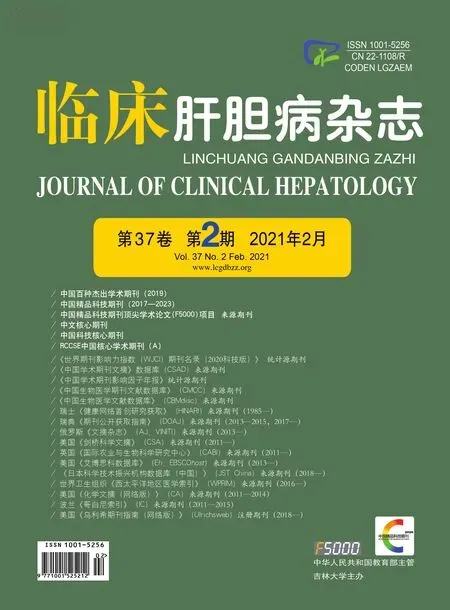瞬時彈性成像技術在慢性乙型肝炎中的應用進展
宋凱敏, 劉 俊
山西醫科大學附屬人民醫院 消化科, 太原 030000
HBV感染是重大公共衛生問題,據世界衛生組織報道[1],全球約有2.57億慢性HBV感染者,我國大約有7000萬,其中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2000萬~3000萬例[2]。CHB患者由于病毒持續存在,引發肝組織炎癥及壞死等病理改變,導致進行性肝纖維化,進一步發展為肝硬化和肝細胞癌(HCC)。因此,早期準確地評估CHB患者肝臟的損傷程度是防止疾病進展的關鍵。目前,肝活檢仍然是診斷肝臟疾病的“金標準”,但作為侵入性技術,肝活檢易致疼痛、出血和感染等,研究[3]估計并發癥的發生率約0.5%,死亡風險為0.05%;且病變的不均一性導致取樣和判讀誤差,有出血傾向及肝臟疾病嚴重的患者限制了該技術的開展。近十幾年來,已出現多種無創檢測方法評價肝臟病變,包括天冬氨酸轉氨酶和血小板比率指數(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to-platelet ratio index, APRI)、肝纖維化4因子指數(FIB-4)和Forns指數等血清學指標,瞬時彈性成像技術(transient elastography, TE)和聲脈沖輻射力彈性成像(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ARFI)等成像技術[4-5]。TE是通過肝硬度測定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LSM)來評估肝纖維化,其操作簡便、可重復、無創且安全,能夠較為準確地評估和預測CHB患者的肝臟損傷程度及并發癥,受到歐洲肝病學會、美國肝病學會及中華醫學會等多個指南的推薦。本文總結了TE在CHB患者中的最新應用進展,以期進一步促進TE的研究,為早期治療提供參考依據,有效防止CHB的疾病進展。
1 TE評估CHB患者肝臟情況
1.1 TE評估肝纖維化程度
1.1.1 TE在肝纖維化中的診斷效能 肝纖維化是指肝臟細胞外基質(膠原、糖蛋白和蛋白多糖等)的彌漫性過度沉積與異常分布,是CHB患者肝臟向肝硬化和肝癌發展的關鍵步驟及影響慢性肝病預后的重要環節。研究[6]報道,肝纖維化可逆轉,而肝硬化是不可逆的(部分早期肝硬化可逆),且多數肝纖維化乃至早期肝硬化無特異癥狀、體征及血清學指標變化;因此,早期準確地評估CHB的肝纖維化程度極為重要。多項研究[7-9]證實了TE在評估肝纖維化方面的價值。一項Meta分析[7]以METAVIR評分為標準,結果顯示TE診斷F≥2、F≥3和F=4的敏感度分別為0.806(95%CI:0.756~0.847)、0.819(95%CI:0.748~0.874)和0.863(95%CI:0.818~0.898),特異度分別為0.824(95%CI:0.760~0.873)、0.866(95%CI:0.824~0.899)和0.875(95%CI:0.840~0.903);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下面積(AUC)分別為0.88(95%CI:0.85~0.91)、0.91(95%CI:0.88~0.93)和0.93(95%CI:0.91~0.95),AUC均大于0.85,強烈提示TE能夠很好地診斷CHB的肝纖維化。韓國的一項研究[8]顯示,TE診斷不同乙型肝炎肝纖維化的AUC分別為≥F2組0.774、≥F3組0.849、F4組0.902,進一步證明TE可以準確評估CHB患者的肝纖維化程度;并且計算出≥F2、≥F3和F4的最佳診斷LSM分別為7.8、8.2、11.6 kPa。
《肝纖維化診斷及治療共識(2019年)》[9]建議,在CHB患者中,膽紅素正常,ALT<5倍正常值上限(ULN)的患者,LSM≥17.0 kPa時考慮肝硬化,LSM≥12.4 kPa考慮進展期肝纖維化,LSM≥9.4 kPa考慮顯著肝纖維化,LSM<10.6 kPa排除肝硬化可能,LSM<7.4 kPa排除進展期肝纖維化;膽紅素正常,ALT正常的CHB患者,LSM≥12.0 kPa時考慮肝硬化,LSM≥9.0 kPa考慮進展期肝纖維化,LSM<9.0 kPa排除肝硬化可能,LSM<6.0 kPa排除進展期肝纖維化。該共識對診斷界值進行規范化標準化,有助于未來TE在臨床工作中的進一步開展,并有效減少不必要的肝活檢。鑒于肝臟炎癥和膽紅素影響LSM,需要警惕高ALT水平對準確性的干擾,避免急性炎癥期結果的假陽性。ALT輕度升高(ALT≤2×ULN)的患者,丁榮蓉等[10]發現LSM與纖維化分期呈正相關(r=0.650,P<0.01),進一步細分為≤1×ULN和>1×ULN~≤2×ULN兩組后,發現LSM診斷≥S2期的AUC分別為0.857和0.813,界值分別為5.90和7.80 kPa;≥S3的AUC分別為0.890和0.892,界值分別為8.10和9.50 kPa;S4的AUC分別為0.925和0.908,界值分別為8.40和10.40 kPa。因此,LSM隨著ALT的升高而升高,TE檢測時需格外注意影響因素。
LSM對肝纖維化診斷,尤其是較高分期,具有重要價值,但在早期略顯不足。除肝硬度外,黏度也是肝臟健康狀況的重要屬性,但一直未受重視。剪切波衰減擬合系數(attenuation fitting coefficient, AFC)評估早期纖維化更加靈敏,可以彌補LSM的不足,在臨床上協助醫師準確診斷纖維化。Zhao等[11]入組99例患者研究發現,AFC和LSM診斷肝纖維化≥F2期的AUC分別為0.866、0.708,AFC指數的敏感度、特異度、診斷準確率(83.33%、81.48%、81.82%)均優于LSM(72.22%、70.37%、70.71%);因此,在區分早期纖維化方面,AFC較LSM更優。考慮到該研究入組病例少等局限,結果只具備參考價值,未來還需容納更多病例的多中心研究來證實AFC的價值。
1.1.2 TE與其他檢測技術的比較 國內外多位學者將TE與其他無創檢測技術進行比較,發現TE更優或基本等效。左中寶等[12]對FibroTouch和6種血清學指標(S指數、Forns指數、FIB-4等)進行研究,發現FibroTouch-LSM在S≥2、S≥3、S=4的AUC分別為0.89、0.90和0.85,顯著高于血清學模型,可見FibroTouch的診斷效能更為準確。趙帆等[13]分析發現FibroScan和ARFI區分F0、F1期無統計學差異;FibroScan診斷顯著肝纖維化(F2~F4期)的AUC(0.835)優于ARFI(0.70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表明FibroScan和ARFI均無法區分F0和F1期,但對顯著肝纖維化的鑒別,FibroScan更優。此外,Baldea等[14]發現,不同纖維化分期中,TE測量值的AUC分別為0.87、0.82、0.90、0.97;ARFI測量值的AUC分別為0.83、0.86、0.88、0.97,提示兩者在判斷肝纖維化和肝硬化方面同樣準確,與Zeng等[15]的研究結果一致。
近年來基于影像學和血清學的TE聯合診斷成為研究熱點;多指標聯合可顯著提高診斷準確性,呈現出巨大應用潛力。一項前瞻性研究[16]中,診斷顯著纖維化,M和XL探針(均為TE)、剪切波彈性成像(shear wave elastography, SWE)、APRI和FIB-4的AUC分別為0.771、0.761、0.700、0.698和0.697;診斷進展期纖維化的AUC分別為0.974、0.973、0.929、0.738和0.859;診斷肝硬化的AUC分別為0.954、0.949、0.962、0.765和0.962;因此在評估顯著纖維化和進展性纖維化方面,TE優于SWE;肝硬化方面,TE、SWE和FIB-4的表現相似。劉濤等[17]分別比較FibroScan、APRI、透明質酸及三者聯合,發現診斷肝纖維化的AUC分別為0.845、0.765、0.825和0.937。吳柳等[18]將不同成像技術和血清學模型聯合與單項進行比較,認為TE聯合ARFI與血清學標志可有效提高檢測能力。由此可見,關于TE和其他無創檢測技術的對比,不同研究有不同的結果,可能是研究病例數量不同、參考的肝纖維化分期不同、肝活檢和TE操作者的水平不一致等原因導致;但一致的是TE聯合其他檢測可以較大程度地提高診斷效能。因此,日后的臨床研究中,仍需要多中心、大規模的隨機對照試驗,探究不同組合方式的應用價值,將有助于TE更好的臨床應用。
1.2 評估肝脂肪變性 CHB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均為常見病,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NAFLD的患病率逐年增高,據報道[19],CHB并發NAFLD的發生率為13.6%~59.3%;并且CHB中脂肪變的存在可能加速疾病的發展,影響抗病毒藥物的療效,甚至增加肝硬化和HCC的風險。肝活檢是脂肪變的“金標準”。基于TE的控制衰減參數(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 CAP),多項研究報告了其在肝脂肪變性中的價值。徐曉鸞等[20]統計顯示,CAP值與脂肪變程度呈正相關(r=0.660,P<0.01),證明CAP可用于肝脂肪變性無創診斷。Ferraioli等[21]入組115例CHB患者,多元回歸分析證實CAP值與脂肪變程度(R=1.2,P<10-5)和BMI(R=4.1,P=0.03)相關;并估算S≥1的最佳界值為219 dB/m,AUC為0.76;S≥2的最佳界值為296 dB/m,AUC為0.82,因此CAP是CHB患者管理中檢測脂肪變的有用工具。部分學者[22]根據不同CAP值劃分脂肪變程度,即S0(無脂肪變性,CAP 0~247 dB/m)、S1(輕度脂肪變性,CAP 248~267 dB/m)、S2(中度脂肪變性,CAP 268~279 dB/m)和S3(嚴重脂肪變性,CAP≥280 dB/m)。
目前關于CHB和肝脂肪變的相互作用尚未達成共識,同時脂肪變和纖維化之間的關系在臨床實踐中存在爭議。Mak等[19]通過前瞻性研究病毒靜止期的CHB患者,發現持續性嚴重肝脂肪變性與纖維化進展獨立相關(OR=2.379,P=0.01),認為CAP可預測肝纖維化的風險。與此相反,Nan等[23]觀察到不同脂肪變程度CHB患者的年齡、性別、肝纖維化無統計學差異(P值分別為0.109、0.075、0.269);CHB患者中嚴重脂肪變性(S3)的ALT水平高于S0(P<0.001)和S2(P=0.047);認為肝臟炎癥與嚴重脂肪變性相關,而纖維化與脂肪變無關聯。故對于CHB患者肝纖維化的診斷,是否會受到NAFLD并存的干擾不甚清楚;TE在CHB合并NAFLD中對肝纖維化的診斷表現和界值尚未明確。Li等[24]選取116例患者,發現FibroScan在肝纖維化不同階段的診斷中表現良好,顯著肝纖維化AUC為0.87,進展性肝纖維化AUC為0.89,肝硬化AUC為0.94;并且得出診斷界值為10.8 kPa(顯著肝纖維化)和17.8 kPa(肝硬化)。但是該研究大多數患者處于CHB的免疫耐受期和免疫清除期,因此應謹慎解讀FibroScan的臨界值,并在大樣本量的隊列中和CHB的其他臨床階段進一步驗證。
目前臨床用于肝脂肪變的檢查有腹部彩超、CT等,國內外研究將CAP值與上述檢查手段進行對比發現,CAP同樣有獨特的優勢。Xu等[25]比較肝脂肪變指數(HSI)、CAP和超聲對脂肪變的診斷價值,結果顯示S≥1,CAP和HSI的AUC分別為0.932和0.755;S≥2,AUC分別為0.780和0.655;S3,AUC分別為0.990和0.786;可見CAP的診斷效能更高。代煉等[26]則比較了FibroScan和FibroTouch的評估能力,最終顯示二者均可定量檢測脂肪,但是FibroScan可以鑒別脂肪變的輕重,而FibroTouch不可以。
1.3 其他方面 Wang等[27]研究中,研究者未將肝臟炎癥視為LSM準確性的干擾因素,而是在不同病因肝病中,探索TE反映肝臟炎癥嚴重程度的潛在應用;其中,在CHB中,同一纖維化分期患者的LSM隨著肝壞死炎癥嚴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此外,ROC曲線顯示LSM可以識別中度和重度炎癥(AUC分別為0.779和0.838)。因此,LSM不僅可用于肝纖維化,同時具備診斷CHB患者肝臟壞死性炎癥嚴重性的潛在價值。
兒童CHB患者中,羅海燕等[28]發現TE對不同程度肝纖維化均有較好的診斷價值:診斷肝纖維化的AUC為0.850,最佳界值7.4 kPa;明顯肝纖維化的AUC為0.864,最佳界值9.2 kPa;進展性肝纖維化的AUC為0.840,最佳界值11.2 kPa;肝硬化的AUC為0.894,最佳界值為13.3 kPa。徐志強等[29]研究顯示,≤12歲患兒,LSM與肝纖維化顯著相關(r=0.447),診斷顯著肝纖維化、進展期肝纖維化的界值分別為5.8、7.0 kPa,AUC分別為0.74和0.94;>12 歲兩者同樣顯著相關(r=0.722),診斷界值分別為6.6、8.0 kPa,AUC分別為0.82和0.95。以上兩項研究均可見兒童診斷界值低于成人,表明兒童的LSM普遍低于成人;并且在不同年齡階段存在差異,因此不能采用統一標準評估。迄今為止,關于TE對兒童診斷效能的研究較為匱乏,由于兒童和成人在生長發育、機體免疫及個體需求等方面不同,就進一步提高和優化TE的兒童診斷效能尚待更多的研究分析。
TE作為無創技術,安全、簡便、可重復及動態連續觀察,能夠客觀地反映肝纖維化,不僅可用于監測CHB患者的纖維化和早期肝硬化,有效防止疾病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可以評價抗纖維化藥物和抗病毒藥物的療效,進而判斷藥物的應用價值,以及預測肝炎病毒學指標的轉歸情況;最終更好地提高CHB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質量[30-31]。Chen等[32]發現CAP高的患者在第12、24和48周時抗病毒治療的ALT正常化率和HBV DNA陰轉率明顯低于CAP正常者,提示CAP值高的CHB患者對抗病毒治療的反應較差。
2 預測CHB患者肝病結局
2.1 預測門靜脈高壓及靜脈曲張 CHB持續纖維化易進展為肝硬化,門靜脈高壓和食管胃靜脈曲張(gastroesophageal varices, GOV)是肝硬化的重要并發癥,而食管胃靜脈曲張破裂出血(esophagogastric variceal bleeding, EVB)是最常見的并發癥和最主要的死因,病死率為10%~20%[33]。肝靜脈壓力梯度(HVPG)是門靜脈高壓診斷和危險分層的金標準,但其有創且成本高,無法在臨床廣泛開展。胃鏡是診斷EVB的金標準,然而由于侵入性使部分患者無法耐受,因此尋找準確有效的無創檢測成為熱點。目前,大量關于TE預測能力的研究在臨床開展,取得較好的效果。
Cassinotto等[34]觀察到TE測得LSM和脾臟硬度值(spleen stiffness measurement, SSM)與HVPG均有顯著相關性,這為TE預測靜脈曲張程度提供了良好的理論基礎。Baveno Ⅵ共識[35]建議,LSM<20 kPa且血小板>150×109/L的患者存在高風險食管靜脈曲張的風險非常低,據此可以對人群進行初步篩查。林欣等[33]研究發現,LSM在有、無靜脈曲張和輕度、中重度靜脈曲張中的AUC分別為0.805和0.753,而SSM診斷的AUC分別為0.921和0.958;認為SSM的準確性更高,且可以區分靜脈曲張程度,與楊學平[36]觀察的結果一致。這可能是因為LSM更易受炎癥、膽汁淤積及年齡等影響,并且其主要反映肝纖維化,未能精確反映靜脈曲張;而SSM為脾大、脾淤血、門靜脈高壓及脾組織增生等多種病變的綜合結果,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GOV。因此SSM值得臨床推廣應用和研究。另有學者[37]聯合FibroScan和血清學指標進行評估,發現聯合診斷對GOV程度有更強的預測能力。
除靜脈曲張程度外,TE還可以預測EVB風險。劉加群等[38]研究發現,無出血、單次出血和多次出血的CHB患者肝脾硬度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TE在預測EVB方面有較好的價值。一項包括87例CHB患者的臨床研究[39]顯示,LSM和SSM預測EVB的AUC分別為0.734和0.874,由此可見,在預測出血風險方面SSM同樣優于LSM,最佳界值分別為33.05、65.80 kPa。無論是GOV,還是出血,早期一般無明顯癥狀,因此TE的早期診斷極為重要,同時動態監測隨訪可以避免頻繁的胃鏡檢查,防止急性出血的發生。但是相關研究目前仍不足,需要進行大規模的隨機研究,規范相關的標準以便臨床廣泛使用。
2.2 預測HCC 乙型肝炎肝硬化是肝癌的常見病因。目前HCC的發病率位居全球惡性腫瘤第5位[40],其起病隱匿,早期無明顯癥狀,一旦發現往往為晚期,且肝組織活檢和AFP存在自身限制,早期診斷困難,因此如何在CHB患者中發現HCC高危人群,有效監測和隨訪,具有重要臨床意義。關于HCC的診斷界值尚無統一的標準。臨床有35%~45%的HCC患者AFP陰性,這為臨床診斷帶來極大障礙。徐斌等[40]評估了TE對AFP陰性CHB患者發生HCC風險的作用,logistic回歸分析表明年齡、性別、LSM分別為HCC發生的獨立預測因素(OR值分別為1.053、2.432、6.803);LSM<10 kPa,10.1~15 kPa,15.1~25 kPa,>25 kPa時,HCC發生的分層特異度似然比分別為0.67、1.02、1.44、3.98,提示醫生可以據此進行重點篩查和隨訪。
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探究肝癌風險評分模型,以便科學規范的預測肝癌風險,包括:REACH-B評分和CU-HCC評分,基于肝硬度值的LSM-HCC評分和改良版REACH-B(mREACH-B)評分,以及抗病毒治療適用的PAGE-B和改良版PAGE-B[41]等。Wong等[6]采用LSM-HCC評分預測CHB肝癌,包括 LSM、年齡、血清白蛋白、HBV DNA,發現LSM-HCC評分預測HCC的準確率高于CU-HCC評分。最近Lee等[41]引入TE構建了更為準確的HCC預測模型——CAMPAS,該模型指標包含年齡、男性、超聲檢查、血小板計數、白蛋白和LSM,計算整體Harrell’s c指數為0.874;經過驗證發現CAMPAS評分可以預測不同程度的HCC風險,并且優于以往的評分模型。當前關于TE預測HCC風險方面,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以及構建新的模型,評估HCC監測策略的成本效益,監測低危患者的早期HCC,并為高危患者提供更準確的篩查方式,以便在進展為晚期肝癌前做到有效預防和干擾。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抗病毒藥物的研發獲得了重大突破,一些新型藥物能夠迅速有效地抑制HBV,這使得血清HBV DNA在肝癌風險方面的預測意義大大減低。在接受抗病毒治療的CHB患者中,Seo等[42]以肝活檢為標準,發現在3個LSM分層(LSM<8、8~13、>13 kPa)和組織學分期(F0~2、F3、F4)中,HCC累積發生率隨LSM的升高而顯著增高;多變量分析顯示,LSM是HCC發生的獨立預測因子(HR=1.041,P<0.001),而組織學分期則不是。可見TE在抗病毒治療的CHB患者中能夠獨立預測HCC的發生,但是基于LSM的優化監測方案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HCC的治療方法有手術切除、介入栓塞和肝移植等,目前TE在HCC患者預后方面的研究較少見。Liu等[43]首次將TE引入肝切除術后的CHB相關HCC患者中,研究術后1年內LSM對預后的預測價值,觀察到總體生存率、無病生存和復發結果方面,術后LSM增加的患者均比LSM降低的患者差;多因素分析表明,Child-Pugh評分(HR=1.209)和肝硬度變化(HR=1.891)是與總生存率相關的獨立因素。雖然此項研究存在樣本量小、回顧性設計及部分納入患者術后接受其他治療等限制,但提示肝硬度可作為HCC預后標志物,指導HCC術后患者常規隨訪,肝硬度增加的患者應該接受更頻繁的隨訪檢查。因此,日后臨床中需要深入探索TE在HCC預后方面的價值。
3 局限及影響因素
TE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穿透深度有限、對患者體位要求較高、腹水和肋間隙狹窄會影響剪切波傳播等。TE是通過測量肝臟硬度評估肝纖維化程度,而纖維化程度只是影響肝硬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他影響肝硬度的因素同樣會對TE的準確性造成干擾。根據EASL-ALEH臨床實踐指南[44],炎癥活動、BMI增加、肝外膽汁淤積或充血的存在可能會干擾LSM的測量。研究[45-46]表明,進食、年齡、凝血酶原時間、血清白蛋白、Ⅳ型膠原和肥胖等因子也是LSM不可靠或失敗的獨立危險因素。特別是在CHB患者中,HBeAg、HBV DNA等病毒學指標一定程度上會影響TE的診斷效能。因此,臨床應用TE評估肝臟情況和預測肝病結局時,需要結合不同的指標進行全面而充分的考慮。
綜上所述,TE具有安全便捷、可重復性好、無創及與組織學一致性好等優勢,可連續動態監測肝臟病變。尤其對于CHB患者,TE能夠較好地評估肝纖維化、脂肪變和炎癥程度,預測肝硬化并發癥及肝癌的風險,在臨床中有重要的應用價值。但是,需注意其易受一些干擾因素的影響,因此當前條件下不能完全替代肝活檢和胃鏡。目前TE在預測門靜脈高壓、食管靜脈曲張及肝癌方面的研究尚不足,對于TE聯合其他無創檢測可以顯著提高早期診斷效能,未來需進行多中心、大規模的隨機對照研究。隨著科技和診療水平的提高,相信TE在CHB患者及其他肝病診斷(如酒精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中有更廣泛的應用。
作者貢獻聲明:宋凱敏負責文獻搜集及論文撰寫;劉俊指導及修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