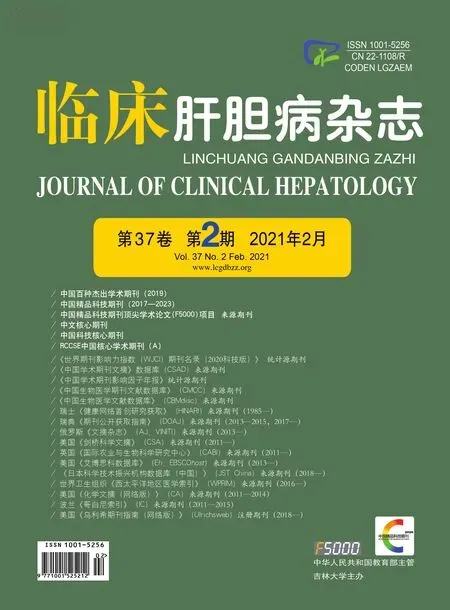循環(huán)microRNA作為肝細(xì)胞癌標(biāo)志物的研究現(xiàn)狀
謝惠君, Rashed Nasot, 寧 勇, 高 川
湖北中醫(yī)藥大學(xué) 檢驗(yàn)學(xué)院, 武漢 430065
1 肝細(xì)胞癌(HCC)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伴隨著microRNA(miRNA)的異常表達(dá)
HCC是最主要的原發(fā)性肝癌,也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癥之一, 僅美國(guó)在2020年就預(yù)期約有30 000人死于HCC[1]。當(dāng)前對(duì)HCC的臨床診斷除了依靠有限的血清標(biāo)志物,例如甲胎蛋白、甲胎蛋白異質(zhì)體以及異常凝血酶原之外,還需要比較先進(jìn)的影像學(xué)技術(shù)的支持[2]。而大多數(shù)HCC患者被確診時(shí)已經(jīng)處于晚期,可供選擇的治療手段有限[3]。更加全面的了解有關(guān)HCC發(fā)生的分子機(jī)制以開(kāi)發(fā)出可用于早期診斷的方法是當(dāng)前迫切的需求。
miRNA是一類內(nèi)源性、不編碼蛋白質(zhì)的小RNA。成熟的miRNA能引導(dǎo)RNA誘導(dǎo)沉默復(fù)合體作用于靶標(biāo)mRNA的3′-非翻譯區(qū),繼而影響其穩(wěn)定性和翻譯成蛋白質(zhì)的效率,最終“沉默”靶基因的表達(dá)[4]。miRNA對(duì)靶標(biāo)的識(shí)別是通過(guò)位于其5′- 端、長(zhǎng)度僅為6~8個(gè)核苷酸的種子(seed)序列,這使得單一miRNA能作用于多個(gè)靶標(biāo),而已發(fā)現(xiàn)的超過(guò)2000個(gè)人類miRNAs將能廣泛的調(diào)節(jié)基因表達(dá)[5]。與mRNA不同,miRNA在循環(huán)血中非常穩(wěn)定,這是因?yàn)榉置诘桨獾膍iRNA大多都包裹在外泌體、微囊泡之內(nèi)或者處于與蛋白質(zhì)(AGO2,高密度脂蛋白等)結(jié)合的復(fù)合體形式從而能抵抗RNase的降解[6-7]。miRNA的這些性質(zhì)使它們有希望成為用于臨床檢驗(yàn)的生物標(biāo)志物。
肝臟維持正常的生理功能需要miRNA。在胚胎期敲除了肝細(xì)胞中的Dicer1從而整體擾亂miRNA成熟過(guò)程的小鼠在2~4月齡時(shí)出現(xiàn)了嚴(yán)重的肝損傷[8]。在成年小鼠其肝細(xì)胞中敲除Dicer1的初期也會(huì)產(chǎn)生類似的表現(xiàn)型,部分能長(zhǎng)期存活的小鼠其肝組織主要由僥幸逃過(guò)Dicer1敲除的肝細(xì)胞構(gòu)成,它們中大多數(shù)在1年內(nèi)發(fā)展成源自殘留的Dicer1-/-肝細(xì)胞的HCC[9]。miR-122是肝臟中含量最豐富的miRNA[10],具有維持肝臟自穩(wěn)(homeostasis)的作用[11]。利用反義核苷酸部分阻斷內(nèi)源性miR-122會(huì)顯著降低小鼠體內(nèi)甘油三酯和膽固醇的水平[12],強(qiáng)制過(guò)表達(dá)miR-122則能緩解模型小鼠肝臟中因輸血性鐵過(guò)剩引發(fā)的炎癥反應(yīng)[13]。
miRNA廣泛參與HCC的發(fā)生和發(fā)展[14]。通過(guò)比較源自臨床HCC樣本的癌和癌旁組織中的miRNA表達(dá)譜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一系列差異表達(dá)的miRNAs,包括在HCC中常常低表達(dá)的miR-122、miR-199a、miR-133b、miR-200等以及在HCC中高表達(dá)的miR-18、miR-21、miR-221和miR-769等[15-20]。一般而言,在HCC中異常低表達(dá)的miRNA有抑癌作用,例如:miR-122可以通過(guò)調(diào)節(jié)M2型丙酮酸激酶來(lái)影響HCC細(xì)胞中的葡萄糖代謝[21],亦可通過(guò)調(diào)節(jié)cyclin G1而抑制HCC細(xì)胞的周期[22],還可以通過(guò)調(diào)節(jié)轉(zhuǎn)化蛋白R(shí)hoA來(lái)阻礙HCC的侵襲和轉(zhuǎn)移[23]。miR-199a和miR-122一樣在HCC細(xì)胞代謝葡萄糖的過(guò)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過(guò)表達(dá)miR-199a-5p可以降低M2型丙酮酸激酶以及HK2的表達(dá)從而抑制HCC細(xì)胞的生長(zhǎng)[24-25],而miR-199a-3p則可抑制對(duì)HCC增殖起促進(jìn)作用的PAK4/Raf/MEK/ERK、mTOR以及c-MET通路[26-27]。與miR-122及miR-199a相比,miR-133b在正常肝細(xì)胞中的表達(dá)不算豐富,而在HCC臨床樣本中的表達(dá)普遍更低[18,28]。在HCC細(xì)胞系中的研究表明miR-133b能通過(guò)調(diào)低SH3蛋白1和SF3B4來(lái)抑制癌細(xì)胞的生長(zhǎng)和侵襲。在HCC中異常高表達(dá)的miRNA往往有促癌作用。例如,miR-221在包括HCC在內(nèi)的許多癌組織中都被發(fā)現(xiàn)表達(dá)上調(diào)[29],它調(diào)節(jié)的靶標(biāo)有許多是涉及癌細(xì)胞增殖和侵襲的關(guān)鍵基因,包括CDNN1B(p27)、CDKN1C(p57)、mTOR以及抑癌基因PTEN和TIMP3等[29-31]。最近的研究[32]還發(fā)現(xiàn)miR-221可靶向調(diào)節(jié)Caspase-3來(lái)抑制細(xì)胞凋亡,它的高表達(dá)在HCC動(dòng)物模型和臨床樣本中都與癌細(xì)胞對(duì)Sorafennib的耐藥性呈正相關(guān)。無(wú)論是抑癌還是促癌的miRNA都有可能成為HCC的治療靶點(diǎn)和臨床診斷標(biāo)志物。
2 循環(huán)miRNA應(yīng)用于HCC臨床檢驗(yàn)和診斷所面臨的問(wèn)題
鑒于miRNA在循環(huán)血中的穩(wěn)定性以及在功能上與HCC之間存在的相關(guān)性,許多團(tuán)隊(duì)嘗試對(duì)循環(huán)miRNA進(jìn)行深度測(cè)序以探索它們作為HCC診斷標(biāo)志物的潛能。Li等[33]于2010年發(fā)現(xiàn)在HBV感染陽(yáng)性的患者中可以通過(guò)聯(lián)合檢測(cè)miR-25、miR-375和let-7f來(lái)區(qū)分HCC患者和對(duì)照者(特異度為96%,敏感度為100%);隨后,Zhou等[34]所進(jìn)行的類似研究中發(fā)現(xiàn)聯(lián)合檢測(cè)miR-122、miR-192、miR-21、miR-223、miR-26a、miR-27a和miR-801可以用來(lái)診斷HCC。Lin等[35]提出了使用由miR-29a/c、miR-133a、miR-143、miR-145、miR-192和miR-505等7個(gè)miRNAs組成的Cmi(miRNA classifier)用于檢測(cè)HCC,并發(fā)現(xiàn)其準(zhǔn)確性優(yōu)于單獨(dú)依賴腫瘤標(biāo)志物甲胎蛋白。還有一些學(xué)者聯(lián)合使用了循環(huán)miRNA和現(xiàn)有的HCC臨床診斷標(biāo)志物。例如:El-Abd等[36]發(fā)現(xiàn)血清miR-199a和miR-16水平與HCC的腫瘤結(jié)節(jié)大小和數(shù)量等指標(biāo)顯著相關(guān),聯(lián)合檢測(cè)血清miR-16與甲胎蛋白可以更好地區(qū)分慢性HCV相關(guān)的HCC(特異度為87.5%,敏感度為85%)。Nomair等[37]嘗試聯(lián)合檢測(cè)血清中的miRNA-224與甲胎蛋白來(lái)診斷HCC,也得到了類似的結(jié)果。這些研究為后續(xù)尋找新的用于檢測(cè)HCC的臨床標(biāo)志物奠定了基礎(chǔ),但是必須認(rèn)識(shí)到要在臨床實(shí)踐中應(yīng)用miRNA作為HCC的標(biāo)志物還有很多問(wèn)題亟待解決。
對(duì)臨床血樣中的miRNA測(cè)序后的組學(xué)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學(xué)分析屬于相關(guān)性研究而非功能性研究,從中得到的可能作為HCC標(biāo)志物的miRNA與HCC的生物學(xué)關(guān)系需要明確,這一工作困難重重。首先,要確定血樣miRNA的組織來(lái)源非常困難。不同于mRNA,miRNA的表達(dá)鮮有組織特異性,而在正常肝細(xì)胞中高表達(dá)的miRNA僅有miR-122、miR-92和miR-199a等少數(shù)幾種,其他絕大多數(shù)miRNAs都處于極低的基礎(chǔ)表達(dá)狀態(tài)(<10 TPM, transcripts per million)[27,38]。通過(guò)取樣的方式確定血樣中過(guò)表達(dá)的miRNA的組織來(lái)源在臨床上很難實(shí)現(xiàn)。此外,即便確定了miRNA的組織來(lái)源也并不意味著找到了研究對(duì)象。許多成簇(cluster)表達(dá)的miRNA由共同的初級(jí)轉(zhuǎn)錄本(pri-miRNA)編碼,進(jìn)行功能研究時(shí),需要考慮這些簇成員的選擇性胞外輸出特性和在成熟過(guò)程當(dāng)中以及對(duì)靶標(biāo)基因調(diào)節(jié)方面的協(xié)同作用[39-40]。而研究由mirtron編碼的miRNA時(shí),還需要顧及這些miRNAs與包含它們的基因在功能上可能形成的反饋回路[41-42]。此外,被其他組織釋放到胞外的miRNA經(jīng)過(guò)血液循環(huán)運(yùn)送到肝臟從而“遠(yuǎn)程”發(fā)揮作用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43-44]。綜合這些考量,鑒定循環(huán)血中發(fā)現(xiàn)的HCC相關(guān)miRNA的功能任重而道遠(yuǎn)。
使用循環(huán)miRNA作為生物標(biāo)志物還面臨一些技術(shù)層面的問(wèn)題。從血清、血漿和其他多種體液中提取miRNA并進(jìn)行分析早有先例[45],然而還難以做到對(duì)循環(huán)miRNA水平的公允評(píng)估[46]。首先,尚未發(fā)現(xiàn)可靠的內(nèi)參miRNA可以用來(lái)比較不同樣本中的循環(huán)miRNA的表達(dá)水平[47-49],使用其他內(nèi)源性小RNAs(例如U6)作為替代或者引入外參(例如cel-miR-39)的效果還存在爭(zhēng)議[50]。其次,在用臨床血樣制備血漿或血清的流程中,包括取血時(shí)對(duì)抗凝劑的選擇(例如肝素或EDTA)、樣本處理時(shí)離心條件的設(shè)定等均會(huì)影響到所取得的miRNA組(miRNome)的成分。另外,在執(zhí)行深度測(cè)序之前的一些步驟,比如RNA接頭連接、逆轉(zhuǎn)錄、擴(kuò)增等酶學(xué)反應(yīng),在應(yīng)用于miRNA研究時(shí)常常會(huì)表現(xiàn)出依賴于堿基序列的偏差。在當(dāng)前的技術(shù)條件下,從循環(huán)血中提取和檢測(cè)miRNA需盡可能使用一致、簡(jiǎn)單和快速的方法并且做到批量處理樣本以減少系統(tǒng)誤差,而今后的方法學(xué)應(yīng)該關(guān)注對(duì)miRNA樣本在不進(jìn)行復(fù)雜擴(kuò)增的情況下進(jìn)行有效的檢測(cè)[51-52]。
3 總結(jié)和展望
HCC因其高死亡率和不良預(yù)后已經(jīng)成為世界各國(guó)面臨的嚴(yán)重的健康問(wèn)題,早期診斷、持續(xù)監(jiān)測(cè)和新療法的開(kāi)發(fā)是HCC臨床管理的重要內(nèi)容。目前臨床對(duì)HCC診斷常依靠血清標(biāo)志物甲胎蛋白和影像學(xué)檢查,但是一方面,早期HCC患者甲胎蛋白指標(biāo)的假陰性率約40%[53],而影像學(xué)檢查受腫瘤大小等因素的影響常常不易區(qū)分肝臟良性病變與HCC。另一方面,從受檢者的感受考慮,創(chuàng)傷性的組織活檢不適合作為早期診斷和持續(xù)監(jiān)測(cè)的檢查項(xiàng)目。miRNA的異常表達(dá)是HCC中的常見(jiàn)現(xiàn)象,因此可以成為開(kāi)發(fā)檢測(cè)方法和藥物的依據(jù)。現(xiàn)有研究支持將血液中一些循環(huán)miRNA開(kāi)發(fā)成為HCC的臨床診斷標(biāo)志物,聯(lián)合檢測(cè)多種miRNAs或者miRNA與甲胎蛋白聯(lián)合來(lái)診斷HCC在實(shí)驗(yàn)中獲得了較高的準(zhǔn)確度和敏感度。目前仍需要進(jìn)一步深入研究miRNA與HCC分子機(jī)制之間的關(guān)系和解決一些臨床應(yīng)用層面的關(guān)鍵問(wèn)題,例如開(kāi)發(fā)更加便利的針對(duì)循環(huán)miRNA的提取技術(shù)和不依賴核酸擴(kuò)增的檢測(cè)技術(shù)等,為循環(huán)miRNA在臨床檢驗(yàn)和診斷中的應(yīng)用提供更加穩(wěn)固的理論基礎(chǔ)和技術(shù)支持。
作者貢獻(xiàn)聲明:高川、寧勇負(fù)責(zé)課題設(shè)計(jì);謝惠君、Rashed Nasot、高川撰寫論文初稿;Rashed Nasot、寧勇參與收集數(shù)據(jù)和修改論文;寧勇指導(dǎo)撰寫文章;高川、寧勇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