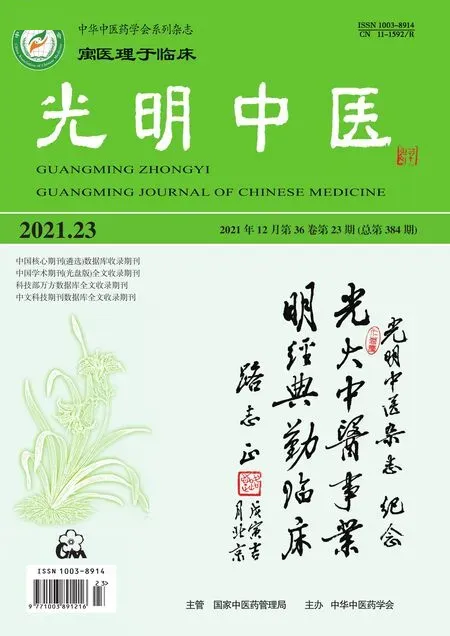桃紅四物湯聯合透天涼針刺手法治療創傷性膝滑膜炎臨床觀察
戰 美 陳 晶 王春生△
創傷性膝關節滑膜炎,臨床上多見于暴力外傷、勞損等導致的膝關節腫脹、疼痛、活動受限等癥狀。其原因多與外傷、過度鍛煉等引起的局部無菌性炎癥有關。研究表明,雖然膝關節病多發于50歲之后,但最初發病時間可能在20歲左右,多因創傷造成,最初發病時,癥狀輕微或呈一過性,故在疾病初期容易被忽視。隨著年齡的增長,關節退化、磨損加重,癥狀逐漸明顯,如活動量加大還可反復發作,腫脹、疼痛、活動受限往往成為就診的主要原因。故早期治療對改善預后、減少復發顯得尤為重要。現代醫學主要通過關節鏡手術、非甾體抗炎藥(NSAIDS)或超短波等來治療創傷性滑膜炎。雖然方法眾多,但效果局限,且長時間使用NSAIDS類藥物可增加消化道出血等嚴重不良反應,增加患者痛苦[1-3]。此次研究收集了門診就診的60例患者,均因運動、創傷、勞損等原因導致膝關節腫脹、疼痛、活動受限,西醫診斷為創傷性膝關節滑膜炎,中醫診斷為膝痹,辨證分型為瘀血阻絡型,筆者運用桃紅四物湯加味結合透天涼針刺手法治療創傷性膝關節滑膜炎,收到良好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納入2016年5月—2018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北部戰區總醫院門診患者60例,應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30例和對照組30例。治療組中男13例,女17例;年齡29~66歲,平均 (37.90±6.72) 歲;病程1~18 d,平均(8.27±3.51)d。對照組中男16例,女14例;年齡21~48歲,平均(37.40±4.78) 歲;病程1~15 d,平均(7.30±3.20)d。2組患者性別、年齡及病程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例,
1.2 診斷標準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4]有明確膝關節創傷史,臨床表現為膝關節腫脹、疼痛、活動受限,浮髕試驗陽性,膝關節彩超提示膝關節積液。關節腔穿刺積液呈淡黃色或淡紅色。中醫診斷為膝痹(瘀血阻絡型),癥狀有膝關節腫脹,針刺樣疼痛,痛有定處,關節活動受限,舌紫暗或有舌下脈絡迂曲,苔薄白或薄黃,脈弦澀。
1.3 納入標準①符合本病臨床表現及影像學診斷,及中醫證候分型屬膝痹(瘀血阻絡型);②運動損傷、創傷、勞損造成的膝關節損傷建議保守治療者;③年齡為18~70歲。
1.4 排除標準①合并嚴重心腦腎或血液系統疾病者;②暈針等不能耐受針刺者;③孕期、哺乳期婦女;④其他原因導致滑膜炎者。
1.5 脫落標準①因個人原因治療未滿21 d者;②治療過程中出現藥物或針刺不耐受者;③依從性差者;④因病情需要增加其他療法,從而可能干擾試驗結果者;出現以上情況出現任何一項即為脫落。
1.6 方法
1.6.1 藥品與儀器一次性毫針(規格:蘇州醫療器械廠有限公司,華佗牌 0.25 mm×40 mm),超聲診斷儀(型號:PHILIPS XC50,L12-3探頭,頻率3~12 MHz),桃紅四物湯加味由門診中藥局配置,每劑采用雙煎法煎成300 ml藥液,分裝成2袋,每袋150 ml。
1.6.2 治療方法治療組和對照組均囑調暢情志,清淡飲食,注意休息,減少行走及上下樓梯等活動,膝關節保暖。對照組給予常規保守治療(三維微波、低頻脈沖電治療、雷火灸)。治療組在常規保守治療的基礎上給予桃紅四物湯加味及針刺透天涼針刺手法。處方如下:熟地黃15 g,當歸15 g,白芍10 g,川芎8 g,桃仁9 g,紅花9 g,獨活10 g,木瓜8 g,牛膝10 g,五加皮8 g,澤蘭6 g。每日150 ml,早晚各1次,每7 d為一個療程,共3個療程。給予針刺,患者患側膝關節屈曲90°,選取一次性毫針,局部常規消毒,針刺穴位為梁丘、血海、鶴頂、內膝眼、犢鼻、膝陽關、曲泉、陽陵泉、陰陵泉、足三里。其中梁丘、血海、鶴頂向委中方向斜刺1.0~1.5寸,內膝眼、犢鼻向關節腔內直刺1.0~1.5寸,務必使針刺入關節腔內效果方佳,曲泉、膝陽關、陽陵泉、陰陵泉、足三里直刺1.0~1.5寸。針刺內膝眼、犢鼻時采用透天涼法,其余穴位正常進針提插捻轉至得氣即可。透天涼具體方法:將進針深度等分為淺、中、深3段,進針至應刺深度的下1/3,逆時針捻轉針柄3~6周,待針下沉緊感后連續輕按重提6次,產生涼感后提至中1/3,繼續捻轉提插6次,得氣后提至上1/3,捻轉提插6次,如此反復操作3次,將針提至上1/3留針。整個過程囑患者采取口吸氣鼻呼氣[5]。留針20 min。隔日1次,每周3次,共3周。
1.7 觀察指標
1.7.1 疼痛評分疼痛視覺模擬評分法(VAS評分),0~10分,0分為無痛,1~3分輕度疼痛,4~6分中度疼痛,7~10分為重度疼痛,根據患者主觀感受于治療前后分別打分。
1.7.2 功能評分LYSHOLM膝關節功能評分,總分為100分,分別于治療前后從功能、癥狀、穩定性等8個方面對膝關節進行評定。
1.7.3 腫脹評分采用門診超聲科膝關節彩超,通過測量治療前后髕上囊積液深度的改變,進行對比。
1.8 療效判斷標準根據《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4]。治愈:膝關節疼痛、腫脹消失,關節活動正常,浮髕試驗陰性,局部皮溫正常;顯效:膝關節疼痛、腫脹基本消失,局部皮溫正常,關節活動基本正常,浮髕試驗陰性,過度活動稍微有輕微疼痛;有效:膝關節疼痛、腫脹減輕,關節活動基本正常,局部皮溫稍高;無效:自覺腫痛和功能活動無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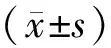
2 結果
2.1 VAS評分和LYSHOLM評分2組治療后VAS評分、LYSHOLM評分明顯優于治療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治療后VAS評分、LYSHOLM評分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患者治療前后VAS評分和LYSHOLM評分比較 (例,
2.2 髕上囊積液深度2組治療后積液深度明顯低于治療前(P<0.05);治療組治療后積液深度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3 臨床療效治療組總有效率90.0%,明顯優于對照組總有效率63.3%,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3 2組患者超聲探查髕上囊積液深度比較 (例,

表4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3 討論
創傷性滑膜炎是由于創傷導致滑膜充血水腫、產生無菌性炎癥,分泌大量滑液,關節腔壓力增高,局部血液及淋巴回流受阻,而引起膝關節紅腫熱痛、活動受限等[6,7]。如未能及時治療,控制炎癥,致使滑膜反復被刺激,滑膜增厚,關節腔出血,進而發展為纖維化、關節腔粘連,甚至關節畸形[8,9]。
膝乃筋之府,《黃帝內經》記載:“病在陽曰風,病在陰曰痹。故痹也,風寒濕雜至,犯其經絡之陰,合而為痹。痹者閉也,三氣雜至,壅閉經絡,血氣不行,故名為痹”[10]。《素問》又云:“久行傷筋”,說明外傷勞損后血液瘀滯,不通則痛,表現為膝關節疼痛;血瘀則氣滯,氣滯濕阻,水濕停聚局部關節,則為腫脹。久之氣血津液衰竭而致筋脈失養,關節拘急,攣縮不用,出現活動受限等功能障礙。治療上應活血祛瘀、消腫止痛、舒筋活絡。桃紅四物湯為清初吳謙《醫宗金鑒·正骨心法要旨》所載, 為活血化瘀之祖方。本方由桃紅四物湯化裁而來,方中桃仁活血化瘀、活血通脈、消腫止痛,與澤蘭同用治療跌打損傷、瘀血腫痛。當歸、紅花聯合補血活血,研究表明當歸與紅花合并煎煮后能夠加強療效[11],且二者配伍比例相近時活血效果最好[12]。川芎通達氣血,為治療氣滯血瘀證之首選,白芍、木瓜舒筋活絡祛濕,五加皮、獨活祛風除濕、強筋健骨、利水消腫,牛膝引諸藥下行。全方補肝腎、通血絡、養血活血、有散有收,共奏祛瘀血、生新血、調氣機的作用。
桃紅四物湯可加快微動靜脈血流速度,使循環血量增加,微血管擴張,延長凝血時間,降低血黏度,抑制血小板聚集,證明桃紅四物湯有很好的活血化瘀的功效[13-16]。桃仁含有的苦杏仁苷成分具有抗炎作用,其機制與通過脂蛋白刺激小鼠膠質細胞BV-2中的環氧合酶2,并促進一氧化氮合酶mRNA的表達有關[17]。紅花中的羥基紅花黃色素 A,可拮抗二磷酸腺苷的促血小板聚集作用,競爭性抑制血小板激活因子,正向調控VEGF 的表達,促進血管新生[18]。桃紅四物湯中被證實具有抗炎、抗血栓、抗氧化、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而發揮這些作用的成分與其中的阿魏酸、芍藥苷、藁本內酯等有關,它們共同作用,促成了桃紅四物湯的抗炎活性[19]。
透天涼,最早見于明代徐鳳的《金針賦》,書中有言:“瀉者一飛三退,邪氣自避”[20]。其手法之精妙處在于口吸氣時空氣進入口腔中溫度較低,使人產生涼感,當經過肺部氣體交換后經過鼻呼出,溫度較前有所升高,使人產生熱感[5]。所謂“邪氣盛則實”,創傷性滑膜炎早期關節紅腫熱痛,屬于經脈瘀滯,屬實證、熱證,而透天涼對實熱證具有良好的瀉熱效果[20],“一進三退”配合口吸鼻呼之間邪熱隨針尖的退出被引至體外,使原本腫痛之處頓感輕松。
針刺處方中血海、梁丘、鶴頂為股四頭肌肌腱與髕骨移行處,針刺此穴可促進股四頭肌肌腱炎癥的吸收;陰陵泉乃脾經合穴,曲泉乃肝經合穴,二穴疏肝解郁,祛濕止痛,且為鵝足肌腱附近,為治療鵝足肌腱炎要穴;足三里乃治痿痹效穴,治療諸虛勞損;陽陵泉乃筋之會穴,治療下肢筋病,可舒筋健骨;膝陽關為膽經穴,可治療膝髕腫痛攣急;內膝眼乃經外奇穴,聯合犢鼻治療膝關節腫痛無力效果顯著[21]。方中各穴配合舒筋通絡、活血化瘀,可達強筋健骨、祛風除濕之效。另外,根據筆者經驗,針刺深度和角度對促進積液消退吸收也起著重要作用,如犢鼻穴和膝眼穴進針時要求患者采用屈膝90°體位,進針角度垂直皮膚表面,深度直達關節間隙內部方能收到良好效果。
本研究證實,桃紅四物湯加味結合針刺透天涼法內可活血化瘀,外可清熱消腫,內外兼治,能夠顯著改善臨床癥狀,減少積液,提高患者生活質量,臨床上具有較好的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