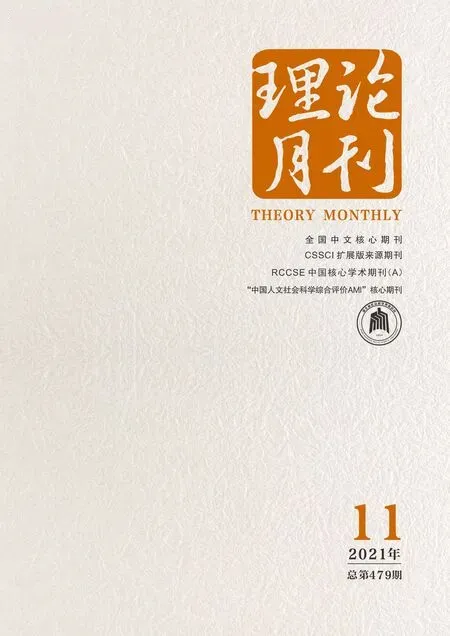西方算法民粹主義:生成、表征及缺陷
張 鵬
(華東政法大學(xué) 政治學(xué)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上海201620)
自21世紀(jì)初以來,新一輪民粹主義浪潮正在全球范圍內(nèi)興起。但與前三輪民粹主義浪潮所不同的是,本輪民粹主義浪潮中數(shù)字技術(shù)所發(fā)揮的作用得到了極大的提升①當(dāng)今民粹主義浪潮屬于人類歷史上第四輪浪潮,第一輪浪潮發(fā)生在19世紀(jì)的美俄,20世紀(jì)中期的拉美出現(xiàn)第二輪浪潮,第三輪民粹主義浪潮發(fā)生在20世紀(jì)90年代的亞太地區(qū),第四輪浪潮則是21世紀(jì)初開始于北美、西歐、東歐等地。參見林紅.當(dāng)代民粹主義的兩極化趨勢及其制度根源[J].國際政治研究,2017(1);俞可平.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民粹主義[J].戰(zhàn)略與管理,1997(1).。對此,關(guān)于民粹主義與數(shù)字化技術(shù)之間的關(guān)系引發(fā)了相關(guān)學(xué)者們的廣泛討論①關(guān)于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發(fā)展對民粹主義的影響引發(fā)了“數(shù)字民粹主義”“網(wǎng)絡(luò)民粹主義”以及“技術(shù)民粹主義”等研究的出現(xiàn)。See Jamie Bartlett,Jonathan Birdwell,and Mark Littler.The New Face of Digital Populism[M].London:Demos,2011;Paolo Gerbaudo.From Cyber-Autonomism to Cyber-Populism:An Ideological History of Digital Activism[J].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2019,17(2);Sunny Yoon.Techno Populism and Algorithmic Manipulation of News in South Kore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ern Asia,2019,18(2).。最初,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對民粹主義的影響方面。而隨著西方國家政黨政治逐漸進(jìn)入算法政治階段,算法技術(shù)正與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相結(jié)合在新一輪民粹主義浪潮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shí),當(dāng)“預(yù)測算法”“分類算法”“細(xì)分算法”以及“個(gè)性化推薦算法”等算法技術(shù)被西方部分政客們用于民粹主義的傳播之后,一種新形式的民粹主義——算法民粹主義正頻繁地出現(xiàn)在西方國家的政治領(lǐng)域中。針對這一現(xiàn)象,本文嘗試分析算法民粹主義的生成緣由,并在此基礎(chǔ)上總結(jié)算法民粹主義的基本表征及其本體缺陷。
一、西方算法民粹主義的生成緣由
目前人類正處于第三次工業(yè)革命與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交接時(shí)期②一般認(rèn)為,第一次工業(yè)革命開端于18世紀(jì)60年代,以蒸汽機(jī)的發(fā)明和使用為標(biāo)志;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發(fā)端于19世紀(jì)60年代,核心推動(dòng)是電力和內(nèi)燃機(jī);第三次工業(yè)革命起源于20世紀(jì)40—50年代,核心特征是信息革命,呈現(xiàn)為計(jì)算機(jī)革命、互聯(lián)網(wǎng)革命和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革命的階段性特征;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則發(fā)生于當(dāng)下,其重點(diǎn)是對人類智能的模擬和提升,內(nèi)核是人類已有活動(dòng)規(guī)則的算法化。目前,正處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交接期。參見高奇琦.智能革命與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初探[J].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2020(7).。在這樣的時(shí)期下,人類社會(huì)正進(jìn)入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算法等數(shù)字化技術(shù)高速發(fā)展的時(shí)代。第三次工業(yè)革命時(shí)期,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已經(jīng)被證明對于民粹主義傳播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而到了數(shù)字時(shí)代的當(dāng)下,數(shù)字媒體與算法技術(shù)的結(jié)合使其不但能夠影響政治話語的傳播,還能夠?qū)е缕胀癖姷男袨槟芰Πl(fā)生改變。同時(shí),受到新自由主義以及西式政黨政治弊端的影響,西方國家中的政治精英與技術(shù)精英正進(jìn)行合謀,由此西方國家出現(xiàn)“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tái)”等一系列算法民粹主義事件。
(一)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算法民粹主義的出現(xiàn)提供可能
如前文所言,在關(guān)于數(shù)字技術(shù)對民粹主義傳播影響的前期研究中,其關(guān)注點(diǎn)主要集中于網(wǎng)絡(luò)民粹主義方面。例如,較早對這一領(lǐng)域進(jìn)行研究的杰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等人在其著作《數(shù)字民粹主義的新面孔》一書中,雖然使用的是“數(shù)字民粹主義”這一概念,但全書所談?wù)摰膶ο笠琅f是“網(wǎng)絡(luò)民粹主義”[1]。而近年來以伊科·馬利(Ico Maly)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學(xué)者則開始圍繞算法技術(shù)與民粹主義之間的關(guān)系展開研究。對此,馬利把當(dāng)今的民粹主義總結(jié)為:“數(shù)字媒介化的時(shí)空交流與話語關(guān)系。”[2]在馬利看來,當(dāng)代民粹主義是一種交際關(guān)系,一種社會(huì)技術(shù)的集合,民粹主義學(xué)者針對當(dāng)代民粹主義的研究必須考慮社交媒體平臺(tái)中的算法性質(zhì)。這是因?yàn)椋瑪?shù)字媒體中的算法性質(zhì)有助于構(gòu)建適應(yīng)這種新的數(shù)字生態(tài)的民粹主義。而卡里金·萊杰梅克(Karlijn Raaijmakers)則使用算法民粹主義討論了西方政客是如何把算法機(jī)器人與民粹主義相結(jié)合,進(jìn)而增加其追隨者[3]。以上研究都是數(shù)字技術(shù)被運(yùn)用到民粹主義中的現(xiàn)實(shí)寫照,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與算法技術(shù)。需要說明的是,即使是針對算法民粹主義的研究也并沒有忽視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在算法民粹主義傳播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換言之,以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以及算法技術(shù)為代表的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算法民粹主義的出現(xiàn)提供了可能。
毋庸置疑,關(guān)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對于民粹主義的影響已經(jīng)得到學(xué)界的共識(shí)。作為一項(xiàng)顛覆人們?nèi)粘I畹募夹g(shù),互聯(lián)網(wǎng)曾被廣泛地討論對于數(shù)字民主的益處。但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人們發(fā)現(xiàn)數(shù)字民主正成為一種迷思。對此,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認(rèn)為,網(wǎng)絡(luò)并沒有讓政治更加民主化,同時(shí)也沒有擴(kuò)大普通民眾的權(quán)利與限制精英的權(quán)力[4]。與此相對,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在改變?nèi)藗兩罘绞脚c認(rèn)知習(xí)慣的同時(shí),也助長了民粹主義的生成與傳播。在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影響下,民粹主義已經(jīng)從一種有限的廣場政治演變?yōu)闆]有邊界的網(wǎng)絡(luò)政治[5](p60)。這是因?yàn)椋ヂ?lián)網(wǎng)技術(shù)既提供給每個(gè)網(wǎng)民自由表達(dá)的渠道,但同時(shí)也造成“信息繭房”與“回音室”的效應(yīng),進(jìn)而引發(fā)群體極化①關(guān)于群體極化,凱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認(rèn)為:“團(tuán)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xù)移動(dòng),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diǎn)。”參見[美]凱斯·R.桑斯坦.社會(huì)因何要異見[J].支振鋒,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6:53.。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具備全球化性質(zhì)的技術(shù),互聯(lián)網(wǎng)讓信息傳播很容易突破現(xiàn)實(shí)的邊界,這也導(dǎo)致民粹主義從最初地域性演變?yōu)橐环N全球性的政治活動(dòng)。而算法民粹主義雖然凸顯了算法作為底層技術(shù)的重要性,但同時(shí)也需要以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tái)為傳播載體。因此,當(dāng)下西方國家中的社交媒體已經(jīng)成為新的政治戰(zhàn)場。對于民粹主義者而言,由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構(gòu)成的社交平臺(tái)已經(jīng)成為他們傳播民粹主義主張的關(guān)鍵[6]。并且,作為當(dāng)代民粹主義的主要活動(dòng)場所,互聯(lián)網(wǎng)依舊是一種中心化的等級結(jié)構(gòu)。因此,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的不平等性也有利于政治精英與社會(huì)精英實(shí)現(xiàn)民粹主義的話語壟斷和社會(huì)動(dòng)員。而算法與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結(jié)合則加劇了民粹主義“聲音”病毒式的傳播。
與此同時(shí),早在1999年西方學(xué)界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利用博客中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來推測用戶屬性的研究[7](p7-20),從那以后互聯(lián)網(wǎng)與“預(yù)測算法”之間的緊密關(guān)系便引起了相關(guān)研究者的關(guān)注。如果說“預(yù)測算法”對于人們政治生活還無法造成重大的影響,那么“分類算法”“細(xì)分算法”以及“個(gè)性化推薦算法”等算法技術(shù)的發(fā)展則深刻地影響著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傳播。這是因?yàn)椋惴翊庵髁x者可以在“預(yù)測算法”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運(yùn)用“個(gè)性化推薦算法”等技術(shù)來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與政治選擇。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與算法技術(shù)的結(jié)合主要體現(xiàn)在當(dāng)今的社交媒體以及搜索引擎之上。對此,克里斯托弗·E.懷特(Christopher E.Whyte)曾經(jīng)針對2012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的議程設(shè)置以及信息搜索等內(nèi)容進(jìn)行研究,最后發(fā)現(xiàn)社交媒體以及搜索中的算法過濾器可以在人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來決定哪些信息最符合使用者的要求[8](p1680-1697)。而這些由算法過濾器提供的信息并不一定總是客觀的。也就是說,雖然普通民眾可以在互聯(lián)網(wǎng)以及算法技術(shù)的幫助下得到自身需求的信息,但這些信息卻可能是被算法過濾器改造后的結(jié)果。而在算法民粹主義者的有意推廣下,一些被算法設(shè)計(jì)好的信息還會(huì)按照主動(dòng)、自選以及預(yù)定的方向推送到他們的視線[9](p341-366)。對此,以互聯(lián)網(wǎng)與算法技術(shù)為代表的數(shù)字化技術(shù)正為算法民粹主義的出現(xiàn)提供可能。
(二)新自由主義原則的流行為算法民粹主義提供契機(jī)
自19世紀(jì)初以來,西方國家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便把經(jīng)濟(jì)看作是一個(gè)在原則上與宗教、政治以及其他社會(huì)領(lǐng)域相分離的體系。對此,西方社會(huì)開始把市場看作是一個(gè)能夠自我調(diào)節(jié)的領(lǐng)域,并且假定了市場體系是在一個(gè)比國家更高、更普遍的秩序之中運(yùn)作②例如,從古典學(xué)派中的亞當(dāng)·斯密(Adam Smith)和大衛(wèi)·李嘉圖(David Ricardo),再到新古典主義學(xué)派,最后到當(dāng)代的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他們都持有一種強(qiáng)有力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市場具有自我調(diào)節(jié)的能力,特定社會(huì)的國家應(yīng)當(dāng)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參見鄭永年,黃彥杰.制內(nèi)市場:中國國家主導(dǎo)型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M].邱道隆,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35-36.。因而,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認(rèn)為:“自律性市場必須將社會(huì)在體制上分割為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與政治領(lǐng)域……這樣的一個(gè)制度,除非能使社會(huì)屈從于它,否則是無法運(yùn)作的。”③但是,波蘭尼在《巨變》(又名《大轉(zhuǎn)型》)一書的核心觀點(diǎn)卻是純粹的自律性市場只是一個(gè)烏托邦。參見[英]卡爾·波蘭尼.巨變:當(dāng)代政治與經(jīng)濟(jì)的起源[M].黃樹民,譯.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7:126-127.雖然由于“1929年世界經(jīng)濟(jì)大危機(jī)”,凱恩斯主義曾短暫成為美歐等發(fā)達(dá)國家的治國理念,但在西方國家中這種政府干預(yù)的治理原則卻并不占據(jù)主流地位。并且,隨著“凱恩斯主義”政策工具于20世紀(jì)60年代后失效,美歐國家的大企業(yè)就開始借機(jī)重構(gòu)資本主義政治經(jīng)濟(jì)體系,并將新自由主義理念推上了歷史的前臺(tái)。最后,以1989年“華盛頓共識(shí)”為標(biāo)志,新自由主義作為理論依據(jù)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廣為傳播。而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人類社會(huì)的發(fā)展是一種“自生自發(fā)”的過程。所以,自由市場是一種完美的國家治理體制,而國家與政府的過多干預(yù)則會(huì)將人類引入一條通往極權(quán)的“奴役之路”[10]。因此,西方發(fā)達(dá)國家大多把市場樹立為首要原則,而政府與社會(huì)則在市場原則之下發(fā)揮作用。
對此,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信奉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市場化的原則,并且在其國家治理中主張即使是必要的政府干預(yù)也要遵循市場原則[11](p114)。這就導(dǎo)致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而言,國家與政府的角色只在于創(chuàng)造并維護(hù)一個(gè)讓市場自由發(fā)展的制度。而當(dāng)前西方國家中數(shù)字媒體的算法以及一般功能都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之上,并且這些原則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對等級、競爭以及贏者通吃價(jià)值觀的追求[12](p21),因此,市面上的數(shù)字媒體不再是使用者之間信息交流的中立平臺(tái),反而具備潛在的意識(shí)形態(tài)。在這些數(shù)字媒體中,獲得更多網(wǎng)民的喜愛是民粹主義領(lǐng)袖獲得民眾支持的重要體現(xiàn)。“你擁有和建立的關(guān)聯(lián)性越多,你就越有價(jià)值。因?yàn)檫@會(huì)讓更多的人認(rèn)為你很受歡迎,因此想要和你建立關(guān)聯(lián)性。”[12](p13)而由于新自由主義原則,“如果政客,特別是民粹主義領(lǐng)袖想要以人民的名義發(fā)言,就必須建立大量的聽眾。每個(gè)帖子都需要吸引能在數(shù)字媒體上進(jìn)行互動(dòng)的民眾,以便算法向這些民眾推薦相關(guān)的信息。每個(gè)帖子都必須有‘喜歡’、‘轉(zhuǎn)發(fā)’以及‘評論’”[6]。在這樣的邏輯下,作為一名替民眾“發(fā)聲”的民粹主義領(lǐng)袖,如果在數(shù)字時(shí)代不具備一定數(shù)量的在線支持者將是不合格的。
而與此同時(shí),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原則是崇尚市場以及懷疑政府,因此,在缺少政府必要干預(yù)的情況下,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往往會(huì)出現(xiàn)不受國家與社會(huì)控制的商業(yè)巨頭。但這在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中被看作是一種合理的現(xiàn)象。例如,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便提出了“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觀點(diǎn)。在他看來,資本積累最強(qiáng)大的手段是將一個(gè)過程或產(chǎn)品置于大型企業(yè)的手中[13]。而這在算法民粹主義中則體現(xiàn)為“諸如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社交媒體允許政客們在社交媒體上控制自己的聲音和信息,但他們只能在他們所使用的社交媒體的特定格式內(nèi)進(jìn)行控制”[6]。這就導(dǎo)致一些實(shí)力雄厚的網(wǎng)絡(luò)超級平臺(tái)凌駕于政治之上。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即使特朗普還在任期內(nèi),其社交賬號依舊會(huì)被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封禁。更為重要的是,由新自由主義引領(lǐng)轉(zhuǎn)型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引發(fā)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地位的同時(shí)還塑造了個(gè)人成敗只取決于個(gè)人能力與個(gè)人努力的觀念[14](p87)。這就強(qiáng)化了資本家以及政治家們精英主義的思維。在他們看來,民眾只是其獲得利潤或獲得選票的工具。因此,可以用算法民粹主義來操縱民眾的行為。
(三)西式競爭型政黨政治的弊端為算法民粹主義提供動(dòng)力
兩黨制或者多黨制是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主要形式,也是構(gòu)成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內(nèi)容。在眾多西方學(xué)者看來,通過選舉及自由競爭的方式實(shí)現(xiàn)輪流執(zhí)政,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民主制度。與此同時(shí),輪流執(zhí)政以及自由競爭可以充當(dāng)西方科層制度的糾偏機(jī)制,既可以達(dá)到監(jiān)督執(zhí)政黨的作用,又可以充分實(shí)現(xiàn)少數(shù)群體的意見。但是,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政黨在經(jīng)歷精英型政黨、群眾型政黨、全方位型政黨以及卡特爾型政黨這四個(gè)發(fā)展階段后[15](p19-20),如今正逐漸以獲取選票為中心,并開始與社會(huì)公眾發(fā)生疏離。這就導(dǎo)致在當(dāng)前西方國家政治生活中,政黨不但弱化了其利益整合與調(diào)節(jié)功能,反而傾向于贏得選票與獲取公職。由此,西方政黨開始失去特色,政黨政治游戲化[16](p36)。而對于部分西方政黨而言,民粹動(dòng)員與算法動(dòng)員是數(shù)字時(shí)代下獲得民眾支持最便捷、最迅速的兩種途徑[17]。因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如今西方國家的政黨在進(jìn)行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同時(shí),也開始紛紛使用民粹主義言語來吸引民眾的支持。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競爭性以及執(zhí)政前提使算法民粹主義以及算法民粹政黨流行。相比過去,數(shù)字化時(shí)代下政客同時(shí)使用民粹動(dòng)員與算法動(dòng)員是最“理性”的選擇。
一方面,民粹動(dòng)員有利于政客在較短的時(shí)間內(nèi)與“人民”產(chǎn)生共鳴。當(dāng)代西方民粹主義的共同特征在于它發(fā)生在長期實(shí)行普選制度的政治環(huán)境中。在當(dāng)代針對民粹主義的定義中,除了把其定義為“一種薄薄的意識(shí)形態(tài)”之外①學(xué)界對于民粹主義的定義莫衷一是。其中,以卡斯·穆得(Cas Mudde)為代表的學(xué)者把民粹主義定義為一種薄薄的意識(shí)形態(tài)。這一觀點(diǎn)得到大多數(shù)學(xué)者的認(rèn)同。See Cas Mudde.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還有兩種觀點(diǎn)也極具影響力。一種是把民粹主義定義為一種溝通方式或政治風(fēng)格[18](p319-345)。另外一種則把民粹主義看作一種策略、話語或運(yùn)動(dòng)[19]。對此,筆者認(rèn)為,從1870年俄國民粹主義運(yùn)動(dòng)到21世紀(jì)初從歐美國家開始的民粹主義運(yùn)動(dòng),民粹主義越來越表現(xiàn)出工具性與政治策略性的一面。如今西方各國的民粹主義也主要充當(dāng)政黨政治的武器。因而,專門研究民粹主義的學(xué)者卡斯·穆得(Cas Mudde)等人曾認(rèn)為,在總統(tǒng)制國家反體制的政治候選人可以直接訴諸選民,進(jìn)而加強(qiáng)其人格化領(lǐng)導(dǎo)[20](p58)。而現(xiàn)實(shí)中也是如此,據(jù)統(tǒng)計(jì),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在各種選舉中吸引了近25%的選票,而在20世紀(jì)90年代它們只能夠獲得5%至7%的選票[21](p13)。并且,由于西式的民主政治是通過簡單的民意相加來獲取合法性,因此,對于西方政客們而言,他們獲得選票以及謀取公職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與民眾產(chǎn)生共鳴,進(jìn)而獲取民眾的支持。
另一方面,算法動(dòng)員則有利于擴(kuò)大政客們的政治影響力。西方國家政黨間競爭的現(xiàn)狀賦予了算法中心的地位。在最新的西方民粹主義活動(dòng)中,算法營銷已經(jīng)成為一種主流。在算法的幫助下每一個(gè)民眾都可以成為被精準(zhǔn)觀察的目標(biāo)。通過將人們分解成多樣的群體,民粹主義者以不同的聲音與內(nèi)容向不同的觀眾展示了不同的興趣。據(jù)特朗普競選團(tuán)隊(duì)宣稱,之前特朗普在其競選的一則Facebook的廣告中就有50000個(gè)不同的版本。而隨著人類已經(jīng)進(jìn)入數(shù)字化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空間已經(jīng)成為人們參與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徑。因此,馬利在“算法民粹主義”的基礎(chǔ)上,還提出了“算法行動(dòng)主義”。在他看來,數(shù)字化時(shí)代不僅催生了“算法民粹主義”,同時(shí)還催生了“算法行動(dòng)主義”。“這種類型的行動(dòng)主義有助于傳播政客或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的相關(guān)信息,通過在數(shù)字媒體中的互動(dòng)來觸發(fā)媒介的算法,進(jìn)而提高該信息及其傳遞者的受歡迎程度”[6]。而這種有計(jì)劃的行動(dòng)主義是被刻意安排的,算法民粹主義政客不僅需要在數(shù)字媒體上與民眾進(jìn)行互動(dòng),還需要了解數(shù)字媒體的功能與算法結(jié)構(gòu)。
二、西方算法民粹主義的基本表征
如前文所述,與前三輪民粹主義所不同的是,數(shù)字技術(shù)在本輪民粹主義的傳播中充當(dāng)著關(guān)鍵的作用。筆者在先前研究的基礎(chǔ)上曾簡要分析算法民粹主義的含義。在筆者看來,“算法民粹主義指的是一些善于借助算法及大數(shù)據(jù)作為輔助的政治家們把民粹主義當(dāng)作獲取普通民眾支持的工具,他們通過聘請專業(yè)技術(shù)團(tuán)隊(duì)將普通民眾基本信息進(jìn)行數(shù)據(jù)化整合,并在已有數(shù)據(jù)分析的基礎(chǔ)上運(yùn)用算法機(jī)器人、網(wǎng)絡(luò)超級平臺(tái)廣告推送等技術(shù)去影響乃至改變民眾的行為”[22](p17)。對此,算法民粹主義則以算法為技術(shù)支撐,以社交媒體為傳播載體,以克里斯瑪型人物為推動(dòng)者。
(一)以算法為技術(shù)支撐
借助民意測驗(yàn)和統(tǒng)計(jì)技術(shù)對選民進(jìn)行觀察早在20世紀(jì)60年代便已經(jīng)成為西方國家競選活動(dòng)中的常態(tài)現(xiàn)象。在數(shù)字化和數(shù)據(jù)化出現(xiàn)之前,西方國家的政治競選活動(dòng)只能通過主流媒體中的報(bào)道以及廣告才能吸引民眾對其的關(guān)注與支持。但這個(gè)現(xiàn)象在當(dāng)前的算法民粹主義時(shí)代發(fā)生了改變。從2012年貝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運(yùn)用數(shù)據(jù)競選連任以后,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們便習(xí)慣性聘請專門的團(tuán)隊(duì),運(yùn)用大數(shù)據(jù)以及算法進(jìn)行政治競選。例如,奧巴馬在競選之初便雇用了吉姆·梅西納(Jim Messina)作為競選經(jīng)理。在梅西納等人的幫助下,奧巴馬專門組建了一個(gè)運(yùn)用新技術(shù)競選的數(shù)據(jù)軍團(tuán)。該軍團(tuán)雇用了包含軟件工程師、數(shù)據(jù)分析師以及網(wǎng)絡(luò)和電子郵件專家團(tuán)隊(duì)在內(nèi)的300多名員工。這些數(shù)據(jù)軍團(tuán)在利用算法技術(shù)精準(zhǔn)說服選民支持奧巴馬的同時(shí),還輔助奧巴馬獲得更多的籌資募款[23](p604)。而隨著奧巴馬連任的獲勝,算法角逐也成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一種主流。對此,丹尼爾·克雷斯(Daniel Kreiss)曾經(jīng)將數(shù)據(jù)化競選活動(dòng)描述為“網(wǎng)絡(luò)病房政治”,并將其與大眾媒體出現(xiàn)之前的美國政治時(shí)代相比較[24](p217)。在過去,美國政治競選中每一個(gè)候選人都需要聘請專門的工作人員與選民在日常生活中互動(dòng),進(jìn)而對他們的需求、問題和偏好有著深刻的了解。但是現(xiàn)在,他們只需要通過數(shù)據(jù)軍團(tuán)提供的信息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公眾的需求,并以越來越有針對性和參與性的方式與公眾進(jìn)行溝通。
以上這些在算法民粹主義中更得以體現(xiàn),在算法的幫助下每一個(gè)選民都可以成為被量身觀察的目標(biāo)。算法民粹主義政客的數(shù)據(jù)軍團(tuán)可以把“分類算法”與“個(gè)性推薦算法”等算法技術(shù)相結(jié)合,在對普通民眾的數(shù)字行為進(jìn)行歸類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分類精準(zhǔn)推送能夠影響民眾行為的信息。因此,算法政治時(shí)代下的民眾日常眼中所看到的宣傳信息可能是個(gè)性化以及量身定制的。而這在特朗普競選時(shí)期也同樣得以體現(xiàn)。2016年,特朗普獲勝以及英國成功脫歐讓劍橋分析公司被人們所熟知。根據(jù)劍橋分析公司當(dāng)時(shí)的首席執(zhí)政官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的公開聲明,特朗普的競選團(tuán)隊(duì)從2016年7月開始便設(shè)計(jì)了三種不同的算法模型來幫助特朗普贏得選舉。第一種是針對特朗普鐵桿支持者而設(shè)計(jì)的,其目的在于增加籌資募款;第二種模型是為了確定不同類別選民的投票偏好;第三種模型則是為了發(fā)現(xiàn)民眾所感興趣的議題[2]。通過三種算法模型的建構(gòu),特朗普的數(shù)據(jù)軍團(tuán)能幫助特朗普精準(zhǔn)鎖定支持者與潛在支持者。
與此同時(shí),從民粹主義者的角度,政治是“純粹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之間的對抗性政治。無論是左翼民粹主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都是排他的,左翼民粹主義把人們在階層之間進(jìn)行了分離,右翼民粹主義把人們在種族之間進(jìn)行了分離。因此,對于任何試圖以民粹主義“聲音”來贏取選民支持的政客而言,他們必須在社會(huì)上刻意引發(fā)“人民”與“精英”、“本土居民”與“外來移民”之間的對立。例如,“英國脫歐”中的投票就很能體現(xiàn)出這一點(diǎn)[25](p87)。而這些人群一旦被算法民粹主義政客們所利用,就極容易導(dǎo)致民粹主義事件的發(fā)生。
(二)以社交媒體為傳播載體
算法民粹主義的興起是以算法為底層技術(shù),同時(shí)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還需要以社交媒體為傳播載體。需要說明的是,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不僅僅只在社交媒體上,除此之外,電視、報(bào)紙等傳統(tǒng)主流媒體也都充當(dāng)了傳播載體的角色。但是,相比傳統(tǒng)主流媒體,現(xiàn)代社交媒體在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中發(fā)揮著關(guān)鍵的作用。這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自2008年經(jīng)濟(jì)危機(jī)以來,西方民眾對于傳統(tǒng)媒體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根據(jù)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數(shù)據(jù),只有18%的美國人對美國傳統(tǒng)國家新聞媒體持相信的態(tài)度[26](p752)。在普通民眾看來,2008年主流媒體并沒有及時(shí)發(fā)出“經(jīng)濟(jì)危機(jī)”的信號,這一事件讓主流媒體獲得“不吠叫的看門狗”這樣的角色[27]。而社交媒體讓人直接參與的特點(diǎn)則讓民眾更加相信上面所發(fā)布的相關(guān)信息。另一方面,則在于由算法技術(shù)構(gòu)成的民粹主義需要一個(gè)即時(shí)性操作的媒體。諸如電視、報(bào)紙等傳統(tǒng)主流媒體由于自身媒介的特點(diǎn),只能夠在固定時(shí)間、固定信息容量的基礎(chǔ)上向廣大民眾傳遞信息。但現(xiàn)代社交媒體突破了這一束縛,現(xiàn)代社交媒體的即時(shí)性以及可推送性等特點(diǎn)能夠讓信息可以在任何時(shí)間被傳遞到民眾的視線范圍。
社交媒體作為傳播載體支持了算法民粹主義運(yùn)動(dòng)的興起,這歸因于算法中嵌入的聚合邏輯及其可以吸引原本分散的人們注意力的方式。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后果之一便是導(dǎo)致社會(huì)上原子化的個(gè)人的出現(xiàn),而這又造成了當(dāng)今西方社會(huì)中個(gè)人的孤獨(dú)。社交媒體則提供了一個(gè)聚集空間,在有利于作為分散的原子個(gè)人可以聚結(jié)的同時(shí)也造成了群體極化的后果。例如,比利時(shí)極右翼政黨弗拉芒利益黨(Vlaams Belang Party)在2014年范·格里肯(Van Grieken)擔(dān)任黨魁前經(jīng)歷了較長時(shí)間的衰退期。格里肯上任后,弗拉芒利益黨開始利用Facebook社交平臺(tái)的相關(guān)功能建立數(shù)字社區(qū)。與此同時(shí),格里肯還利用社交媒體多次發(fā)布民粹主義請?jiān)富顒?dòng),進(jìn)而使該黨在短短的幾年內(nèi)迅速得到民眾的支持[28](p444-468)。2018年該黨甚至還因抗議《移民問題全球契約》,組織5500多人向歐盟總部發(fā)動(dòng)游行示威活動(dòng)。更為重要的是,同樣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如今在西方社會(huì)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以Twitter、Facebook為代表的超級平臺(tái)。這些超級平臺(tái)直接影響著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無論是民粹主義的政黨還是非民粹主義的政黨都需要依靠這些超級平臺(tái)才能更好地宣傳其思想。因此,技術(shù)寡頭們對于算法民粹主義的流行也秉持助推的態(tài)度。
如前文所述,馬利在“算法民粹主義“的基礎(chǔ)上還提出了“算法行動(dòng)主義”。對此,馬利曾專門針對特朗普競選進(jìn)行了三種“算法行動(dòng)主義”的劃分,分別是:(1)使用點(diǎn)擊農(nóng)場(click farms)。數(shù)字時(shí)代下的民粹主義者受到民眾支持最主要的體現(xiàn)就是其在社交媒體上發(fā)布的文字、視頻得到普通民眾的喜歡、分享與轉(zhuǎn)發(fā)。因此,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者便通過雇傭海外的“點(diǎn)擊農(nóng)場”來營造自身在社交媒體上深受歡迎的假象。(2)政治機(jī)器人。據(jù)統(tǒng)計(jì),在2016年大選期間,大約有40萬個(gè)政治機(jī)器人參與了關(guān)于總統(tǒng)選舉的討論。這些政治機(jī)器人在為民粹主義候選人增加追隨者方面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而這些政治機(jī)器人則是由算法構(gòu)成的。(3)MAGA和另類右翼激進(jìn)分子。這種類型的“算法行動(dòng)主義”以人力為基礎(chǔ),其基本行為就是人為轉(zhuǎn)發(fā)關(guān)于特朗普的相關(guān)事跡或者使用簡單的腳本機(jī)器人做同樣的事情,其目的也在于營造特朗普在民眾中受歡迎的假象[2]。而這三種“算法行動(dòng)主義”都以社交媒體為傳播載體,可以說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在數(shù)字化時(shí)代的流行對當(dāng)今算法民粹主義的盛行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以克里斯瑪型政客作為推動(dòng)者
克里斯瑪型權(quán)威最初由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于《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一書中所提出,又稱“超凡魅力型權(quán)威”。在書中韋伯總結(jié)了傳統(tǒng)型、克里斯瑪型以及法理型三種不同的統(tǒng)治類型,其中克里斯瑪型統(tǒng)治的合法性來源于領(lǐng)袖個(gè)人的超凡魅力以及追隨者賦予其的品質(zhì)[29](p241)。這種類型的統(tǒng)治權(quán)威一般出現(xiàn)在社會(huì)動(dòng)蕩時(shí)期,并且領(lǐng)袖個(gè)人自身帶有特定的使命。在研究民粹主義的學(xué)者看來,民粹主義與克里斯瑪型政治有著特殊的關(guān)聯(lián)[30](p61-62)。而當(dāng)今西方世界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民粹主義運(yùn)動(dòng),都需要依靠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lǐng)導(dǎo)者的推動(dòng)。這種超凡魅力的領(lǐng)袖通常需要對外宣稱它們能夠帶領(lǐng)人民脫離現(xiàn)狀且反對現(xiàn)有的精英統(tǒng)治。
對于算法民粹主義來說,一個(gè)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領(lǐng)袖往往能夠激發(fā)大眾的政治熱情。因此,在算法民粹主義傳播的過程中往往需要一個(gè)領(lǐng)袖進(jìn)行引領(lǐng)。例如,特朗普就在多個(gè)場合上宣稱自己是美國人民的“彌賽亞”,只有他才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與此同時(shí),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發(fā)展也讓克里斯瑪型領(lǐng)袖的誕生環(huán)境發(fā)生了一定的變化。韋伯所論述的克里斯瑪型領(lǐng)袖一般出現(xiàn)在傳統(tǒng)社會(huì)或者國家的重大動(dòng)蕩年代,諸如拿破侖、愷撒等人的人格魅力來自其對國家的重大貢獻(xiàn)。但是數(shù)字化時(shí)代下克里斯瑪型領(lǐng)袖的誕生環(huán)境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他們不需要花費(fèi)大量的時(shí)間來證明其個(gè)人成就或道德,轉(zhuǎn)而依賴一些具有表演性質(zhì)的話語符號來刺激民眾的情感,進(jìn)而獲得合法性[31](p44)。而在算法民粹主義傳播的過程中則以社交媒體平臺(tái)為展示空間,并通過算法精準(zhǔn)推送等形式來與普通大眾產(chǎn)生共鳴,激發(fā)其政治熱情。
具體而言,算法民粹主義以克里斯瑪型人物作為推動(dòng)者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點(diǎn):首先,克里斯瑪型政客聘請專業(yè)數(shù)據(jù)軍團(tuán)針對民眾進(jìn)行基本的數(shù)據(jù)整合。劍橋分析公司的案例已經(jīng)證明,數(shù)字化時(shí)代下的人們其日常行為已經(jīng)被數(shù)據(jù)化。對此,克里斯瑪型政客可以通過聘請專業(yè)化的數(shù)據(jù)團(tuán)隊(duì)運(yùn)用算法歸納、分析等技術(shù)了解民眾的所處位置、投票偏好以及社交關(guān)系等內(nèi)容。例如,劍橋分析公司就曾經(jīng)宣稱“我們擁有超過2.3億美國選民的5000個(gè)數(shù)據(jù)點(diǎn)……使用這些重要信息來吸引、說服和激勵(lì)他們采取行動(dòng)”[32]。其次,克里斯瑪型政客在已有數(shù)據(jù)分析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選民的喜好在各社交媒體上進(jìn)行魅力型表演。克里斯瑪型政客魅力型表演的核心是與民眾產(chǎn)生情感上的共鳴,只有這樣他才可以既讓民眾相信其主張具有說服力,又可以使“人民”成為具體的政治主體。對此,有研究表明特朗普與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分別在Twitter上給自己構(gòu)建了“反抗者”和“普通人”的形象以及“民族復(fù)興”和“道德辯護(hù)”的使命[33](p268)。最后,通過政治機(jī)器人、社交媒體廣告推送等技術(shù)去影響乃至改變民眾的行為。通過數(shù)據(jù)整合以及克里斯瑪型政客形象構(gòu)建后,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還需要運(yùn)用政治機(jī)器人以及社交媒體廣告推送等技術(shù)進(jìn)一步擴(kuò)大算法民粹主義領(lǐng)袖的影響力。例如,德國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領(lǐng)導(dǎo)人愛麗絲·韋德爾(Alice Weidel)就被揭露其Twitter支持者中存在由算法構(gòu)成的在線機(jī)器人[33]。
三、西方算法民粹主義的本體缺陷
算法民粹主義是技術(shù)發(fā)展的產(chǎn)物,代表著一種工具理性,其在長期運(yùn)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一套擯棄價(jià)值的規(guī)則與制度。就目前而言,關(guān)于算法民粹主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現(xiàn)象以及算法對于民粹主義傳播的影響方面。即使是馬利等人的后期研究也更多的是以具體案例來展示算法民粹主義在西方社會(huì)中的運(yùn)用。但是,當(dāng)前算法民粹主義的出現(xiàn)與傳播已經(jīng)對西方世界產(chǎn)生著重大的影響。
(一)導(dǎo)致普通民眾政治主體性的喪失
一般而言,信仰人民是民粹主義主體邏輯的起點(diǎn)與終點(diǎn)[34](p10)。如前文所言,隨著西式競爭型政黨政治的發(fā)展,民粹主義正被當(dāng)作一種工具流行于西方國家,而算法技術(shù)在民粹主義傳播中的運(yùn)用則更加劇了民粹主義工具性的趨勢。而隨著算法民粹主義的廣泛傳播,西方國家中的普通民眾正面臨政治主體性喪失的困境。關(guān)于政治主體性,一般指的是“政治主體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掌握和借助公共權(quán)力、承載和傳播政治思想文化、創(chuàng)建和鋪設(shè)政治制度設(shè)施、發(fā)動(dòng)和規(guī)制政治行為的自主性、自覺性、能動(dòng)性和創(chuàng)造性”[35](p28)。一定程度上,純粹的民粹主義是一種民眾個(gè)人主體性張揚(yáng)的表現(xiàn),是一種追求主體權(quán)力和主體責(zé)任有機(jī)結(jié)合的體現(xiàn)。例如,民粹主義思想來源的提出者——盧梭的“人民主權(quán)論”所追求的就是人應(yīng)當(dāng)為人所具備的主體性。但算法民粹主義的出現(xiàn)卻引發(fā)一種悖論般的現(xiàn)象,即民眾在做出政治選擇以及政治行為的時(shí)候看似是自主性的抉擇,但其背后卻是政客以及算法的意志。
并且,在當(dāng)今西方世界所流行的算法民粹主義中,其算法以及算法載體都已經(jīng)被設(shè)計(jì)者賦予了其想要賦予的意志。目前,由于信息大爆炸以及信息過量傳輸,人們不得不依賴于個(gè)性化內(nèi)容的推薦。這種推薦本質(zhì)上就是算法的結(jié)果[36](p93)。而這種算法推薦已經(jīng)逐漸從早期通用的初級階段發(fā)展到基于機(jī)器深度學(xué)習(xí)推薦的智能化階段,算法已經(jīng)可以理解更為復(fù)雜的用戶需求、隱匿偏好等信息,并在這一基礎(chǔ)上將大量相互分散的數(shù)據(jù)重新聚集分析并形成高效的處理結(jié)果。這意味著,算法將會(huì)在了解以及服務(wù)你的同時(shí),對你的行為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控制作用。因此,佩德羅·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曾談?wù)摰溃骸敖虝?huì)計(jì)算機(jī)關(guān)于你的東西,你教會(huì)它越多的東西,它就越能更好地為你服務(wù)(或者操縱你)。”[37](p338)這也是為什么在“英國脫歐”之后,有大量的民眾要求重新投票。因?yàn)椋麄儺?dāng)時(shí)的選擇并不完全是出自政治主體性的行為。
然而,純粹的民粹主義追求的是一種真正的政治,是一種人之為人的民主政治,一種人民作為一個(gè)獨(dú)立主體其個(gè)人權(quán)利與義務(wù)相統(tǒng)一的政治,這接近于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t)提出的“本真政治”。對此,阿倫特曾認(rèn)為,政治的本質(zhì)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礎(chǔ)上的支配,而是平等的主體之間通過言語而進(jìn)行的協(xié)調(diào)一致的行動(dòng)[38](p123-124)。換言之,“本真政治”要求在政治生活中交互主體之間主體間性的平等性。因此,當(dāng)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民眾的個(gè)人權(quán)利以及訴求得不到滿足的時(shí)候就容易發(fā)生民粹主義事件。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以及算法等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發(fā)展,人類正逐漸進(jìn)入“后真相時(shí)代”。這在極大地減少民粹主義政客發(fā)動(dòng)民粹主義運(yùn)動(dòng)所耗費(fèi)的成本的同時(shí),也讓普通民眾所面對的客體世界是一個(gè)被篡改了真實(shí)性的世界。在這個(gè)時(shí)候,普通民眾所做出的抉擇就不再具備自主性、自覺性、能動(dòng)性和創(chuàng)造性等主體性特征。
(二)造成技術(shù)寡頭社會(huì)層面的全面壟斷
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西方國家正一度主張絕對的市場化,否認(rèn)政府干預(yù)的積極作用。這就導(dǎo)致在西方社會(huì)中,一些不受國家以及政府控制的超級數(shù)字企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如前文所述,算法民粹主義以算法為技術(shù)支撐,以社交媒體為傳播載體,以克里斯瑪型政客為推動(dòng)者。就目前而言,以劍橋分析公司、Twitter、Facebook等為代表的技術(shù)寡頭雖然在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中還只是充當(dāng)一種輔助性的角色,但在西方國家的社會(huì)層面,技術(shù)寡頭全面壟斷的苗頭已經(jīng)出現(xiàn)。這不僅體現(xiàn)在西方國家的政客以及民眾對于由技術(shù)寡頭所控制的數(shù)字化企業(yè)的依賴的現(xiàn)象上,還體現(xiàn)在這些技術(shù)寡頭自身權(quán)力的不斷膨脹上。
一方面,技術(shù)寡頭正逐漸蠶食西方國家的政治領(lǐng)域。算法動(dòng)員與民粹動(dòng)員是當(dāng)今西方國家競爭型政黨政治中贏得選舉最有效的兩種方式。目前,以“英國脫歐”以及“特朗普上臺(tái)”為代表的一系列算法民粹主義事件已經(jīng)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產(chǎn)生了示范效應(yīng)。例如,有研究發(fā)現(xiàn),一些傳統(tǒng)建制派政黨的領(lǐng)袖有時(shí)也不得不使用民粹主義的修辭,進(jìn)而出現(xiàn)了精通數(shù)字技術(shù)的“建制派民粹”[26](p752)。這就導(dǎo)致西方國家的政客對于這些由技術(shù)寡頭控制的數(shù)字化企業(yè)的依賴程度正逐漸加深。在金融資本主義時(shí)期,美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華盛頓與華爾街之間旋轉(zhuǎn)門機(jī)制。而如今,西方國家中的技術(shù)寡頭在挑戰(zhàn)金融寡頭在政治領(lǐng)域地位的同時(shí),還在不斷地?cái)U(kuò)大自身的影響力。這是因?yàn)椋缃駭?shù)據(jù)化的社會(huì)是由一系列算法交織而成。無論是算法還是數(shù)據(jù)的使用都需要專門的人員進(jìn)行操作,而這些都是傳統(tǒng)政客所不擅長的。因此,隨著算法民粹主義在西方國家流行程度的加深,技術(shù)權(quán)力也隨之正蠶食政治領(lǐng)域。
另一方面,技術(shù)寡頭正對普通民眾產(chǎn)生控制效應(yīng)。隨著算法民粹主義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技術(shù)寡頭正成為新形式的克里斯瑪型領(lǐng)袖。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由于平民與精英之間利益的差異,常常在某些問題上產(chǎn)生沖突,而處于弱勢地位的平民往往需要依靠一位克里斯瑪型領(lǐng)袖才能匯聚力量與之對抗。因此,在大多數(shù)民粹主義運(yùn)動(dòng)中都有一位具有超凡魅力領(lǐng)導(dǎo)者的存在。如今,西方社會(huì)人工智能等技術(shù)領(lǐng)域的發(fā)展正被少數(shù)幾個(gè)改變世界的“超人”所主導(dǎo),這些“超人”背后公司的巨大市值反映了普通民眾對于這些“超人”觀念的認(rèn)同[39](64-65)。換言之,技術(shù)寡頭正成為新形式的克里斯瑪型領(lǐng)袖,他們正替代政治領(lǐng)袖來發(fā)動(dòng)民粹主義事件。例如,在2021年1月底美國金融領(lǐng)域發(fā)生的“逼空大戰(zhàn)”中,埃隆·馬斯克(Elon Musk)便發(fā)揮著催化劑的作用。與此同時(shí),算法民粹主義的傳播案例也證明了其背后的數(shù)字化企業(yè)一般都處于國內(nèi)外的壟斷地位。例如,韓國漢陽大學(xué)教授尹仙熙(Sunny Yoon)就認(rèn)為,韓國最大搜索引擎和門戶網(wǎng)站Naver便在2018年運(yùn)用算法民粹主義(原文用的是“技術(shù)民粹主義”一詞)助推了文在寅政府操縱輿論丑聞,而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這個(gè)社交媒體的壟斷地位[40](p33-48)。而隨著算法民粹主義對于普通民眾吸引程度的加深,普通民眾個(gè)人數(shù)據(jù)的不斷輸入也在不斷鞏固這些技術(shù)寡頭的壟斷地位。
(三)引發(fā)西方國家治理的危機(jī)
就技術(shù)而言,算法民粹主義中的算法屬于一種分離算法。算法民粹主義同時(shí)包含當(dāng)今的左、右翼民粹主義,并且通過算法選擇、排序、傳播等方式造成“信息繭房”與政治極化的現(xiàn)象。西方民眾個(gè)體長期受到算法的控制,能接受到的信息只是算法民粹主義政客想要民眾看到的信息,而不是那些在價(jià)值上更加中立的內(nèi)容。由此,這種分離算法也造成了西方社會(huì)在階層、種族以及宗教等方面的分裂。與此同時(shí),由于算法民粹主義同時(shí)包含著算法與民粹主義兩種元素,因此它可以在國家和政府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突然爆發(fā)。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競選失敗后,其支持者沖進(jìn)國會(huì)造成混亂便是長期受到算法民粹主義影響的結(jié)果。特朗普只需通過Twitter便可以引發(fā)川粉占領(lǐng)國會(huì)。同時(shí),算法民粹主義正從政治領(lǐng)域向經(jīng)濟(jì)等領(lǐng)域發(fā)展。例如,2021年1月底在美國金融圈上演的“逼空大戰(zhàn)”便是一次算法民粹主義運(yùn)動(dòng)。斗爭雙方明面上是散戶與金融大鱷,但其背后是多頭與空頭之間的斗爭。究其源頭,在于三個(gè)月前,有人在reddit上發(fā)布的兩條帶有“反精英”“仇恨主義色彩”的短視頻。“逼空大戰(zhàn)”的背后充斥著民眾對于美國金融精英的仇恨思維。
與此同時(shí),由于“英國脫歐”以及“特朗普上臺(tái)”等算法民粹主義事件所產(chǎn)生的示范效應(yīng),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也正發(fā)生異化。政黨應(yīng)該如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言:“政黨是人們聯(lián)合起來,根據(jù)一致認(rèn)同的某種特定原則,通過共同努力來促進(jìn)國家利益的一種團(tuán)體。”[41](p13)算法民粹主義的流行在加劇西方國家中政黨卡特爾化的同時(shí),還導(dǎo)致其對算法和數(shù)據(jù)的過分依賴。無論是算法還是民粹主義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特點(diǎn),那就是只關(guān)注民眾喜歡什么而很少關(guān)注什么是正確的。這就一方面導(dǎo)致民粹主義政黨的算法設(shè)計(jì)更多的是為了政黨以及政客的利益,并不能促進(jìn)國家利益。例如,希臘“激進(jìn)左翼聯(lián)盟”以反緊縮為訴求上臺(tái)執(zhí)政,但是上臺(tái)后很難解決國家所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進(jìn)而導(dǎo)致其很快下臺(tái)[42](p123)。這也是算法民粹主義政黨上臺(tái)執(zhí)政的危害之一,即執(zhí)政前的政治承諾缺乏可行性與合理性進(jìn)而導(dǎo)致執(zhí)政時(shí)間不具備持久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算法技術(shù)的專業(yè)性,西方國家的政黨只能單方面依靠數(shù)字化企業(yè)。但是這些企業(yè)的數(shù)據(jù)收集具有簡單量化、機(jī)械以及偏向的特點(diǎn),進(jìn)而容易導(dǎo)致決策的失誤或者引發(fā)新的社會(huì)問題。
算法民粹主義的流行也正對西方國家的國家安全造成實(shí)質(zhì)影響。如前文所述,流行于當(dāng)下西方國家的算法民粹主義屬于民粹主義第四輪浪潮,而從第一輪民粹主義浪潮到第四輪民粹主義浪潮,民粹主義的影響范圍正在不斷地?cái)U(kuò)大。但與以往民粹主義所不同的是,算法民粹主義由于算法技術(shù)的原因也更容易跨越國界對他國的政治生態(tài)產(chǎn)生影響。對此,一些外部政治力量便可以運(yùn)用算法及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散布謠言來影響有關(guān)國家的社會(huì)輿論,加劇社會(huì)分裂。例如,法國便指責(zé)俄羅斯通過社交媒體來煽動(dòng)“黃馬甲運(yùn)動(dòng)”,而英國也指責(zé)俄羅斯在“英國脫歐”中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42](p122)。除此之外,外部政治力量也可以反向操作算法民粹主義來干擾國內(nèi)政治,影響國家安全。對此,塞爾維亞前任議員瑟丹·諾戈(Srjdan Nogo)就在Srbin Info網(wǎng)站上發(fā)文披露,為Dominion Voting Systems(美國大選中使用的三個(gè)主要投票軟件之一)工作的技術(shù)專家在為Dominion投票機(jī)編寫的軟件中包括一種算法,該算法將降低特朗普的選票[43]。
四、結(jié)語
一般認(rèn)為,民粹主義是對代議制民主精英化的反抗。然而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和算法等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民粹主義產(chǎn)生了新的變化。掌握巨量數(shù)據(jù)的資本精英逐漸成為民粹主義的操控者,它們通過算法營銷和算法動(dòng)員在選舉中獲得巨大優(yōu)勢。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民粹主義的數(shù)據(jù)化也就意味著民粹主義的資本化、精英化。在代議制民主的理想狀態(tài)下,資本精英與政治精英合謀共生,一起利用算法操控民眾,通過民主程序?qū)崿F(xiàn)新舊執(zhí)政者的穩(wěn)定更迭。然而情況并非如此簡單,算法民粹主義蘊(yùn)含著更深刻的民主危機(jī)。
算法對民眾的操控同時(shí)也意味著對民眾的迎合。當(dāng)政客們通過數(shù)據(jù)整合、算法推薦以及社交平臺(tái)傳播的方式操縱民眾的時(shí)候,民眾也在選擇那些最能夠迎合他們的精英。特朗普的上臺(tái),即是這一前路的預(yù)演。算法以資本為核心,而資本的逐利性將不可避免地引導(dǎo)、迎合甚至放大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的盲目性將在資本的操控下無限膨脹,一旦精英階層喪失共識(shí),代議制民主將可能迎來理論上和制度上的雙重崩潰。若我們回首歷史,羅馬共和國的輝煌有賴于民眾和貴族的妥協(xié),而兩者的斗爭導(dǎo)致共和國的覆滅。民粹主義在算法的加持下,將使民主與民粹的撕裂變得更加不可預(yù)知。算法民粹主義是否會(huì)威脅到民主制度本身,是否會(huì)從內(nèi)部瓦解代議制民主的基礎(chǔ),這是我們下一步要研究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