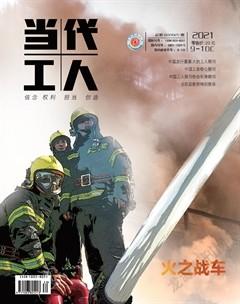賈樟柯與他的村莊故土
2020年,賈樟柯導演新作《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在第七十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全球首映,柏林首映結束后,有觀眾評價道:“攝像機凝視的主體不再是江湖兒女,而是每一個普通平常的人,存在于歷史洪流和故土眷戀中的深情,是對所謂的當代鄉土文學最好的注解。”
對故土的深情是賈樟柯電影的特點,這部影片里的幾位作家,講述了他們的私人故事,這也是中國人的共同“心事”。賈樟柯說:“我希望能夠通過四代作家的接力表達,來談一談幾代中國人的心事。四位作家的私人記憶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就好像一個情感的索引,我們可以沿著這條線索,最終游進去的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情感大海。”
藝術家三部曲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是繼關于畫家劉曉東的《東》(2006年)和關于服裝設計師馬可的《無用》(2007)之后,賈樟柯將關注點又一次投向藝術家群體,可稱為賈樟柯“藝術家三部曲”的最終章。
賈樟柯表示,拍完《東》和《無用》之后,他想拍攝一部關于中國作家的紀錄片。“這并不是因為我有所謂的‘三部曲’情結,而是因為作為一個讀者,我一直對那些即使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都能用筆為我們帶來這個世界最新消息的作家心存敬意。我發現我自己故鄉的一個村莊——賈家莊與中國當代文學有著密切的關聯,當我們以這個村莊為起點開始拍攝之后,很快意識到我們進入的不僅僅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旅程,更是當代中國人的心靈歷程。在文學之外,我們的鏡頭前不知不覺出現了這部影片的另一個主角:農民。”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的開場頗為震撼,那是賈家莊的一處養老院,各種衰老的面孔聚集在食堂中排隊打飯,呈現出人生的沉沉暮色。
賈樟柯表示,最近幾年,中國城市化進程迅猛推進,大量年輕人離開自己生活的農村或小城市,前往大城市生活,農村衰敗,很多地方只留下了老人。對于擁有數千年農業生活方法的國度來說,農村的衰落代表著傳統生活方法、人際關系、道德倫理的改變。對青年一代來說,他們擁有更多的是城市經驗,農村經驗倒是缺乏的。因此,他認為有必要拍攝一部電影來談鄉村記憶與“我們”的關系。
恰恰在這時候,賈樟柯發現中國一些作家開始反向流動,“他們的注意力從大城市返回農村或小鎮,在最基層的社會中捕捉這種新的動蕩。作為對中國人精神結構影響最深的元素,農村為我們理解當代中國提供了落腳點和歷史維度。這讓我開始想拍攝一部以作家為中心人物的紀錄片,我將它跟我的前兩部紀錄片統稱為‘藝術家’三部曲,延續‘精神肖像’的描繪。”
在賈樟柯看來,這些作家為歷史留下了證詞。“通過紀錄片了解歷史,就要尋找一些歷史的證人。優秀的作家是優秀的信使,我們的生活發生了什么,他們會在第一時間告訴大家。為什么他們的反應這么迅速?因為文學是最古老、最便捷的表達方法,所以我們總是從文學中最早知道世界發生了什么。由作家來作為這部電影的講述者,是因為很多作家都來自農村,過去就是農家子弟,通過寫作變成作家,他們長時間地觀察著農村,也在長時間地用寫作表達農村。”
對于文學,賈樟柯更是充滿敬畏:“現在生活中的閱讀很多是碎片化的,這是現實情況,所以文學就顯得更加珍貴,嚴肅的閱讀是在碎片化的氛圍中需要堅持的閱讀方法。因為優秀作品總是有著明顯的系統性思考,呈現出來自社會維度和歷史維度的雙重視線。”
中國往事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以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賈平凹、余華和梁鴻作為最重要的敘述者,他們與作家馬烽之女段惠芳一起,重新注視社會變遷中的個人與家庭,展現了1949年以來的“中國往事”。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最初的片名是《一個村莊的文學》,提及改為《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的原因,賈樟柯說,影片就像一個“海水版的愚公移山”的故事,蘊含了中國內在變化的一個力量,每個人最善良的生活愿望或者一種韌勁——遇見很多事情,還在堅持往前走。選擇這四位作家作為講述者,是因為賈樟柯認為,他們的生活和寫作正好覆蓋了1949年后,中國70年的當代歷史。
馬烽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義市,20世紀40年代起開始進行文學創作。他長期于農村生活、工作,以一系列樸實、生動、富有泥土氣息的農村題材小說、劇本廣受好評,是中國“山藥蛋派”代表作家。賈樟柯表示,已故作家馬烽的寫作伴隨著劇烈的社會改造,“‘革命文藝’是描繪中國精神肖像不能回避的部分,集體主義解決了什么問題,同時產生了什么問題,這是理解中國當代社會結構、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起點。”
賈平凹生于20世紀50年代,他講述的重點充滿60、70年代的創傷與無奈。賈樟柯說:“片中賈平凹敘述的家庭與父親的關系,完全就是我自己父親的樣子,可能因為都姓‘賈’,有了一種天然的親緣感。”
1960年出生的余華是影片中的第三位作家,他回憶的重點在80年代,也即中國的改革開放階段,那是社會解凍、個人主義開始復蘇的年代。賈樟柯說:“20世紀80年代,余華以先鋒作家的姿態進入中國文壇。余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從個體化的感受去描繪中國社會。他慣用的美學場景是小鎮,這是農村和城市雙方面信息的交匯處。小鎮本身就具有結構性,它將土地、農民、傳統與城市并置,更多的意義不是兩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兩者并置所揭示出的景觀。”

梁鴻出生于70年代末,致力于鄉土文學與鄉土中國關系研究,她的代表作《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對河南梁莊的留守者以及這個村莊的外出打工者進行了深入觀察,清晰地展現當代鄉村與中國社會的真實形象,使河南梁莊成為認識中國鄉土現在與未來的醒目標本。她在紀錄片中對于母親和家庭的回憶也頗為感人,賈樟柯認為她的記憶與當下重合,梁鴻是他的知音。“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種現實和歷史里,梁鴻是用文字,我是用影像,雖然從事的語言不一樣,但關心的問題和捕捉的社會氛圍是非常相似的,用不同的媒介反映同樣的觸動,是會消除一種創作的孤獨感。”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共分為18個章節,結構如流云般散漫。賈樟柯說:“這個國度中前行的人們如河流通往大海,一路心事沉沉,遠方一片蔚藍。每一個腳印都極其相似,每一個腳印都不該被遺忘。”
影片中,先是四位主要人物各為一個章節,其次,梁鴻章節延伸出了母親父親兒子三個章節,這是人類基本的家庭結構。其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會碰到的基本問題,比如吃飯、戀愛、生病等。賈樟柯的用意不是單純揭示宏觀的社會政治變化,而是去理解這些社會政治變化如何影響到了個人,“個體經驗,特別是個體記憶中的細節描繪對理解歷史來說是重要的,只有這樣,我才感覺真正走進了歷史。”
留下一段證詞
影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雖然以作家的訪談為主,但也在盡量向著縱深延展,比如,許多片段是由素人來朗誦自己喜歡的作家的經典語句,對于電影與文學、文學與個人的關系形成一種互動和互補。
賈樟柯認為有些感受是只有影像才能抵達的,有些感受是只有文字才能抵達的。“電影《站臺》的開場,是1979年的時候,一群農民在農村劇場的壁畫前抽煙聊天。這一幕是在賈家莊拍攝的,劇場墻上的壁畫名為‘新農村建設規劃圖’。拍攝《一直游到海水變藍》的時候,我們又來到了賈家莊,我們想找到這張壁畫,但它已經被拆掉了。我們在賈家莊的村史館看到了一張新的壁畫,內容仍然是農村的規劃,相比70年代的那一張,已經多了許多高樓和電子通訊的信息。當我看到游客拿出蘋果手機對著壁畫拍照時,我又想起了不同于此的《站臺》中的那些人。電影中,我將兩張壁畫剪輯在一起,世界的改變一目了然。”
如同電影與文學的同行,劇情片和紀錄片對于賈樟柯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大概每拍一兩個劇情片都會去拍一個紀錄片,紀錄片讓我保持拍電影的快感,它讓我覺得我在拍電影。每天我都不知道會拍些什么,但每天拍攝都會給我很多新的感受。”
在賈樟柯看來,中國發展太快,很多事情如果不去拍攝可能就遺忘了,很多當事人也就消失了。“我們處在自媒體時代,處在巨大的社會撕裂中,很多事情,張三說發生過,李四說沒發生過,都會有找當事人的好奇。所以,無論是《二十四城記》《海上傳奇》,還是《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很重要的就是口述歷史,經歷過這段生活的人,把自己的生活經驗講出來,把他們作為一個文獻、一種證人、一種證詞,留下來很重要。”
因此,賈樟柯說自己這幾年對拍攝人物的紀錄片有興趣。“我覺得有很多事情不能忘記,電影的獨特魅力就在于它不僅把經歷過、發生過的事情記錄下來,而且更關鍵的是拍攝的人物在多少年之后,他們在一起談起那些經歷是怎么反應的?他是怎么表現的?用什么樣的語氣?用何種表情?他的沉默、他的長噓短嘆、他的顧左右而言他、他的欲言又止,所有的東西都是時代信息,我覺得這是電影不同于文字的特別。非虛構的寫作現在也非常流行,但為什么仍然需要紀錄片?因為除了這些內容之外,我們可以把人物講述這些內容時的情感狀態同步傳遞出來,它變成了雙重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