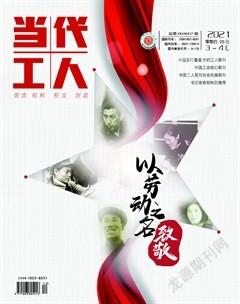明星困在數據里


數據里藏著走紅密碼
30萬名藝人每天都在被各種各樣的數據監測。
在這里,他們的“生命”是另一種形態:數據是血肉,榜單是肢體。每一個數字,是最基礎、最精細的細胞,用來量化、檢測每一個藝人的“生命力”。
花5萬元買一個賬號,你便能解鎖一個藝人的“生命報告”。
一家數據公司向所有人開放了上述付費通道。無論誰買,無論買什么咖位的藝人,報價都是5萬元。從付費成功開始計時,有效期一年。
無孔不入的數據網,7×24小時實時丈量著藝人的價值,也試圖引領人們的認知。這個數據產品分七大脈絡,分別為:輿情監測、風險分析、粉絲運營、商業價值、粉絲戰斗力(全網討論量)、無效聲量占比(俗稱水軍數據)、有效聲量占比(又叫脫水數據)。
垂直之下可以更垂直,細分之后需要再細分。商業價值被定義為由熱度、口碑、專業、代言決定,熱度又由粉絲、媒體生產內容、用戶生產內容全網搜索量構成。
你可以用一種互聯網產品邏輯重新理解粉絲與藝人的關系——粉絲是用戶,藝人是產品。鐵粉、普通粉、路人粉,這三種類型的用戶,以不同的周期和頻率,“登錄”“使用”著作為產品的藝人。在這套數據體系下,任何可以被觀測的行為,都能被評估價值。
某數據公司總裁曹總把藝人的數據報告形容為“體檢報告”。藝人付費除了問診自己,買競品、對家的數據也是普遍現象。位居榜單第一的明星數據,總是被爭相購買。
他們會適時為藝人提供服務。針對當紅藝人的叫“護航”——“因為最火的(藝人)擔心自己出事”。提供給二線藝人的叫“領航”,他們的訴求往往是“我怎樣能重回一線?”給不知名藝人的分析,叫“導航”。譬如一個練習生,在娛樂圈沒有姓名,“但是我想看鹿晗當年怎么火的,就可以買鹿晗的數據。”
數據里藏著走紅的密碼,也能給出避免犯錯的預警。“翻車”藝人的數據報告是硬通貨。“他們買的永遠是看風險的那個模塊”。
娛樂圈藝人多如過江之鯽,曾經品牌靠經驗和體感尋找代言人,但現在,一個明星、一部電視劇、一首歌到底火不火,不同的人群擁有截然不同的體感。他的個人特質是否與品牌匹配,是不是有隱藏的風險,粉絲和購買人群的重合度,帶來多少獲客成本、節省多少推廣成本……看起來,數據是最穩妥的參照標尺。
打工人
入行5年,劉露絲的電腦里有無數個以藝人名字命名的PPT。它們的版本通常隨熱搜更新,隨時做好準備,發給導演或品牌方,將藝人推向市場。
這份PPT通常以藝人最新的寫真做背景,首頁是身高、體重、代表作。基本信息之后,接下來是近年來最重要的數據,比如他的微博粉絲是多少,什么時候登上過熱搜。
轉評贊要找水軍公司。100個轉發的單價通常在2元~3元之間浮動。劉露絲的經驗是,轉發量3000,加上評論和贊,差不多一萬的數據——這樣一單,大概2000元左右。
至于粉絲數,劉露絲說,雖然明星可以因為單個事件掉粉,雖然水軍漲粉/補粉會收到來自微博神秘力量的限制,但長久來看,“那么多年,哪有明星的微博粉絲數降下來過?”
除了粉絲,明星本人的自尊心也需要數據加持。“我一個《偶練》明星怎么可以被一個《青你》的明星壓在下面?我的轉發量一定要比他高!”這是劉露絲親身經歷過的明星心態。
粉絲數、轉評贊、熱搜……這些數據的意義最終都導向明星價值,而明星價值的終極體現,是帶動消費的能力。品牌對藝人的常規要求是,發一條微博,帶電商官方店鋪鏈接,然后他們就可以從店鋪后臺查詢,這個渠道進來的人有多少。
這也是市場對流量藝人新的要求:不僅要充分開發、調動粉絲群體的情緒和能量,在需要的時候,使其極盡狂熱、死忠,具備高效的號召力和行動力,還應該在必要的時候,精準地引導、控制,甚至撲滅它。
把熱搜寫進合同里
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如今天一般,明星和產業會如此需要粉絲。用藝人宣傳安津津的話來說,無論如何明星都一定不能激怒粉絲。你能做的就是沉默,讓粉絲滿意、高興,讓他們留下來。
流量藝人有數據女工沖鋒陷陣,非流量、知名度不夠的藝人,就只能靠買。數據維護費用是藝人宣傳工作的固定成本。安津津帶的藝人是一位初出茅廬的女演員,粉絲不是很能打。除必須的營業外,女演員只能聽從工作人員的規勸,少發無關的微博。“你每個月花出去在數據上的錢就很多了,又沒有賺那么多的錢。”公司最近給這位女演員的規劃是接一些仙俠劇——按照規律,這類劇的用戶和追星少女群體比較匹配,“希望她能擁有能打的粉絲,為她去做數據、做宣傳,這樣起碼我們也省一點錢。”
捍衛數據繁榮的巔峰之戰,是對熱搜位的爭奪。營銷公司老板張小腸稱,每月總能遇到一到兩位客戶,要求“把熱搜數寫進合同里”。“說實話,這是不合理的事,因為不是花錢就能辦到的。”
《乘風破浪的姐姐2》開播前,張小腸接待了一位70后“浪姐”。這位女藝人多年來遠離娛樂圈一線,但最近緊隨潮流,陷入對熱搜的狂熱追逐中。她不打算為張小腸列出的熱搜渠道費全盤埋單,但需求不容動搖:“死命地要熱搜——前三。”
節目開播當天,“30個姐姐都在沖熱搜”。張小腸氣惱:“就因為她跟我砍價,耽誤了最好的時機,導致我們4點才開始操作。結果那天曝了華晨宇的事,熱搜榜變得特別難沖。”
把他賣掉
只要是產品就有迭代,就有淘汰。
劉露絲見識過市場對產品的無情。她記得2019年底,公司一位藝人在練習室跳舞,老板帶著宣傳團隊在隔壁會議室盤賬。經紀人抱怨:幾個月的宣傳費都沒有結過,水軍天天催債。老板質問:他到底還能不能賺錢?
“我們這幫人,平時和他很親近的人,在旁邊的會議室討論怎么把他賣掉。”劉露絲無法把老板的“賤賣”計劃告訴藝人,“但你會對你的朋友保留這些事情嗎?所以我們根本也不會是朋友,我們無法交心。”
作為文化資本創造物的一部分,藝人的命運極不穩定。供大于求,是這個行業的基本運行邏輯,少數人的成功掩蓋了大多數人的窘迫。
每年,選秀機器會為市場帶來幾百張新鮮面孔,行業競爭和淘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殘酷——這正是數據公司的生存空間所在。從事娛樂數據行業的曹總認為,“只有穩定的50個人可以選的時候,你不需要太復雜的分析,因為怎么選都不會太錯;突然變成500個人的時候,就一定會用數據。”
數據預測不了生老病死,預測不了一個人何時犯錯,甚至也無法阻止一個藝人減肥或者發胖。
劉露絲看著曾經共事的那位藝人日漸消沉。至今,這位藝人都沒有被賣掉——因為沒有一家公司愿意接手。所有人對這場買賣都已經厭倦,包括他本人。唯有數據系統永不停歇地高速運轉,不帶一絲情感地抓取、記錄著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的一舉一動——即使他們已經被市場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