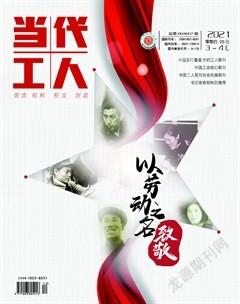他們捧紅她,他們殺死她
閆如意


之前《奇葩說》有道辯題,“20歲有一個一夜成名的機會,該不該要?”
你會如何選擇?能堅定說不的人大概并不多。成名意味著更多的機會,更多的選擇,還有更多的財富與榮光。
96歲的玉珍奶奶一夜成名了。她是河南周口人,在鄭州擺攤賣菜饃30多年。日子過得辛苦卻也規(guī)律:每天晚上12點到凌晨5點出攤。一段短視頻給她帶來了很多關(guān)注,她通透的生活態(tài)度激勵了不少人:“年輕年老,不就是眼一睜一合的事嗎?”6塊錢一個,掙錢不多但她內(nèi)心安寧:“快樂,心里沒執(zhí)著。”
然而,成名僅8天以后,玉珍奶奶就選擇了“退圈”。此前,高齡和辛苦勞作都沒有讓她退卻,但這次意外走紅,卻徹底打破了奶奶生活的寧靜。
奶奶曾經(jīng)說:“只要錢來得正道,沒有不容易的事兒,來得不正道,再容易也不容易。”但網(wǎng)紅流量這筆“容易錢”,多少人蹭得心安理得。反而是像玉珍奶奶這樣的“老實人”,只想黯然離去。
人吃流量,還是流量吃人?
和玉珍奶奶一樣,拉面哥也曾是這樣一名受流量青睞又被流量吞噬的“老實人”。
玉珍奶奶的菜饃,只賣6元錢,里面放著滿滿的餡料,她覺得年輕人掙錢不容易,起碼要讓人們吃飽;拉面哥堅持一碗面3塊錢,10多年沒漲價,他覺得老百姓的錢賺的不容易,希望“兄弟姐妹們都能吃得起”。幾個月前,拉面哥也是一夜爆紅。
好客的山東人不排斥這樣的走紅,村民們甚至主動幫忙從村口擺渡到拉面哥家;村外的停車場也有人義務幫忙指揮停車。他們用滿滿的熱情迎接蜂擁而至的人群,卻沒想到人群的“熱情”,遠超出他們的想象。
拉面哥的家門口,成了“牛鬼蛇神”的集中營。
大小的網(wǎng)紅們,從全國各地集中到這個沂蒙的小村莊。有人向拉面哥示愛,有人“賣身葬父”,有人開著直播要給拉面哥轉(zhuǎn)錢,表達“感恩”。拉面哥附近方圓幾里的土地,都被劃成攤位、標上了價格。靠近拉面哥家的、面積大點的,要200元一天;遠的、小的,也要20元一天。
攤位上賣什么的都有。還有收費保證跟拉面哥合照的、打著拉面哥旗號募捐的……甚至有粉絲半夜趴在拉面哥家的圍墻上,要求半夜吃一碗拉面,“我是個重度殘疾的人,我享受這個待遇。”拉面哥終于還是受不了了。
爆紅幾天后,他突然消失了一天。電話關(guān)機,連家人也聯(lián)系不上。在后來很多次的采訪中,他都崩潰表示,自己只想做個普通人。這個30多歲、面容滄桑的男人,掩面痛哭,但沒有人放過他。
一個月后,拉面哥的妻子,在面攤因低血糖暈倒。圍在拉面哥家門口日夜不歇甚至翻圍墻偷拍的主播們,終于“手下留情”了。他們達成了共識:晚上6點到早上6點不再吵鬧,讓拉面哥和家人能好好休息。
拉面哥曾經(jīng)問記者:“你說人有名好,還是平淡好?”不等記者回答,他說:“我不喜歡這樣,不喜歡出名。”
流量開始偏愛老實人了,他們身上的力量和光芒可以溫暖人心。但偏偏是這樣的老實人,扛不住追隨流量而來的人群。他們就像被蝗蟲卷襲的莊稼地,等蝗蟲退去,就只剩下一地狼藉,和一個可以預見的荒年。
直到走紅很多日以后,拉面哥心里最大的愿望都是繼續(xù)賣自己3塊錢一碗的拉面。他覺得自己總有一天會變得不火了的,到時候一切就都會走回正軌。
但如今看來,原點是再也回不去了。
流量之下,誰才是贏家?
很多人都說,這最好的時代,每個人都屬于自己的3分鐘。
流量的紅利滾滾而來,幾乎毫無門檻。只要把握住,身處淤泥之中也能翻身成功。于是人們絞盡腦汁想要跟上這趟順風車。那些看似瘋魔,形容可憎的流量追逐者,真的原本就是那么“可憎”的嗎?
一個臉上涂得花花綠綠的阿姨哭著說,自己只是為了生活。
她出現(xiàn)在很多個名為“拉面哥家門口的魑魅魍魎”的視頻中,頭上用紅色塑料袋扎著大花,穿著紅襖,臉上抹著有些可笑的夸張腮紅。在一條難得安靜的采訪視頻中,她說自己一年多了也沒找到工作,想來這里漲漲粉絲,“只有在這里,才能看到一線希望”。
在此之前,她干了25年的美容美發(fā),因為疫情停業(yè)了;后來又去送水,一桶水50斤,她干了五六天,腰受不了了;然后,她慢慢開始了直播。她毫不遮掩地說,直播就是“網(wǎng)絡乞丐嘛”“要飯嘛”。這在她看來,都是掙錢。
而另一位媽媽,帶著11個月大的女兒趕來拉面哥家門口直播,她也想掙點錢。家里的兒子患有自閉癥,每年的治療費都不菲,而現(xiàn)在因為沒錢,治療已經(jīng)停了。還在哺乳期的媽媽,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拿著手機支架,來到拉面哥家門口臨時搭建的棚子里。只因為在臨沂這里,這個地方有流量。
走紅一個月后,拉面哥對“蹭流量”的態(tài)度,從最初的不安,變得妥協(xié)接受。他說:“他們也得用他們的方式掙錢。蹭流量的,都是為了生活。”
我們當那些為了蹭流量沒有下限的人是小丑,可小丑又是如何成為小丑的呢?流量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
一個蹲守拉面哥直播了7天的主播,說自己7天粉絲漲了三四千。
這些增長的粉絲可以為他帶來些什么?拉面哥一碗拉面賣3塊,利潤是五六毛。而最初拍火拉面哥的彭佳佳,一晚上直播收益有四五千塊錢,相當于拉面哥賣出8000多碗拉面。
直播掙錢,是網(wǎng)絡時代的紅利,但時代滾滾前進,有人被碾壓,有人害怕被拋下。上面這位主播說,自己也很擔心拉面哥的身體吃不消,但“網(wǎng)絡時代,你必須跟上節(jié)奏”。
被流量裹挾的,遠不止被迫走紅的人。謀生活的人開始追逐流量。一個不具名的主播說,自己打開直播就是被罵,說他蹭流量的、不要臉的,怎么難聽的都有,但他不怕。因為根據(jù)算法,直播室里發(fā)文字互動的越多,被推薦的流量就越多。招罵,早就成了人們心照不宣的吸引流量方式。
為了在越來越多的視頻內(nèi)容里脫穎而出,人們開始愈發(fā)地劍走偏鋒。南京一位賣月亮饃的阿姨,因為待人熱情、給料足走紅。10塊錢一個的月亮饃,阿姨會給塞上滿滿的腸、煎蛋、里脊肉、豆腐皮,如果你說不夠,還能再多給些,生怕“孩子吃不飽”。
探店的人越來越多,單純“打卡網(wǎng)紅月亮饃”已經(jīng)無法從同類視頻中脫穎而出爭奪流量,于是有人故意為難阿姨。
問我夠不夠?如果我永遠說不夠會怎么樣?好一點的,不挑加啥料,阿姨多加些豆皮也不致于虧本太多。一些視頻的最后,阿姨加到忍不住發(fā)問:“孩子,你是很愛吃豆皮嗎?”更過分一些的,指名要加肉,是粉絲、長身體、不夠吃,都是借口,明知自己被為難的阿姨也不好翻臉,只能面露為難。
而這些,都是阿姨“假暖心真營銷”的證據(jù),被飛快地傳播出去。視頻成功了,雖然覺得過分的罵聲一片,但那又如何?流量喜人,粉絲飛漲。這是一個對流量趨之若鶩的時代。但不論是被動走紅的人,還是主動追求的人,都被困在了流量里。
面對奇葩說20歲成名的那道辯題,選擇“拒絕”持方的辯手小鹿有個明確的觀點:“命運隨手給你的不一定是饋贈,也有可能是潰瘍。”
而聰明如當年的流浪大師沈巍,當年一夜爆火以后不甚其擾,干脆自己開了直播當網(wǎng)紅。但在被流量強勢改變了許多以后,沈巍的熱度也過去了。“前幾天,我在網(wǎng)上檢索‘沈’字,那時,我的名字——‘沈巍’還排在最前面。現(xiàn)在再查,已經(jīng)到了后面。”
看清了流量沉浮后——就像主動丟棄一張中了500萬元的彩票券一樣——沈巍宣布退網(wǎng)。沈巍說:“你看那些形形色色搞直播的人,這個社會是不是有點兒病態(tài)。”
如今,問題依舊沒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