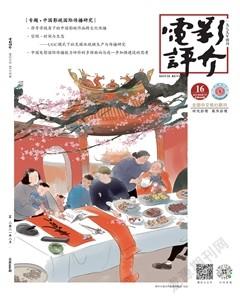扶貧題材專題片敘事策略
徐海星
電視專題片是電視的特有節目類型,最早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是紀實性節目的一種。電視專題片通過運用現在時或過去時的紀實手法,對社會生活的某一領域或某一方面,給予集中的、深入的報道,內容較為專一,形式多種多樣,允許采用多種藝術手段表現社會生活,允許創作者直接闡明觀點。[1]
不難看出,電視專題片兼具新聞的特性,通過現實生活取材取景,拍攝社會生活中發生的真實故事和人物,有明顯紀實風格;但同時又可以采用多種藝術手段表達,講究藝術性。電視專題片的重要功能是對事實和對真實自然的人及人性的高度尊重和揭示。從風格上劃分,電視專題片分為紀實性電視專題片、寫意性電視專題片、寫意與寫實綜合的電視專題片。作為電視專題片的重要類型之一,紀實類專題片普遍用來反映新聞事件或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
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決戰決勝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貴州作為全國脫貧攻堅主戰場,堅持把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舉全省之力、聚各方之智,深入實施大扶貧戰略行動,按年度分季度推進系列攻堅工作,推動全省脫貧攻堅連戰連捷,再戰再捷。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省923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66個貧困縣全部摘帽、9000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歷史性撕掉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標簽,書寫中國減貧奇跡的貴州精彩篇章的生動實踐和取得的偉大成就。
在這樣一個歷史性的關鍵節點,由貴州廣播電視臺制作的紀實專題片《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于2021年4月22日起在《貴州衛視》播出,該片分為《千秋愿景》《夢想花開》《貴州答卷》《續寫華章》四集,主要講述了貴州扶貧工作措施與成效,用鏡頭記錄了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貴州戰法”,通過故事化的呈現、典型人物的塑造、精心的敘事安排等,全方位展現了貴州攻克脫貧攻堅最后堡壘的偉大實踐。《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傳達著貴州各族干部群眾為實現脫貧夢想的不懈努力,各級政府的積極作為和各方力量的有力援助,折射出我國扶貧事業的巨大成就。
一、故事化的敘事表達
敘事是伴隨著人類的歷史發展軌跡一起形成的,存在一切時代、一切地方、一切社會,沒有哪一個民族不存在“敘事”,也沒有哪個地方不存在“敘事”[2]。敘事是一種“故事化”的陳述再現模式,著重尋求事物之間的特殊關系[3]。故事化的敘事是電視專題片常用的敘事手段,是保證其傳播效果的有效方法。在紀實專題片中,故事化的敘述方式,能有效擺脫傳統教條式說教,通過有意識的選取具有典型意義的故事和人物,通過故事化表達,設置沖突和懸念,能夠極大豐富專題片的敘事元素,從而增加專題片張力,增強趣味性和可看性。
電視專題片的“故事化敘事”目的是服務主題,《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選取了大量基層人物,講述老百姓、小人物有溫度的真實故事,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塑造真實有生命的形象。通過以小見大的故事化敘事,以小故事講述大情懷,用普通人的故事闡釋脫貧攻堅夢想的實現,將人民群眾的生活與脫貧攻堅的主題緊密結合起來,將個體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相結合,從而達到引導受眾產生共鳴的效果,加深觀眾對內容的接受程度。
如《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第2集講述了黔西市畢架村村民金生華脫貧的故事,他在20多歲時候左手因意外受傷被迫截肢,后來又檢查出患了肺結核,生活接連的打擊讓他生活變得一貧如洗。轉機出現在2017年,這一年他被精準識別為村里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成為重點幫扶對象,為他量身定制了“一人一策”幫助他脫貧致富。2019年,余生華賣掉了20頭生豬,收入10來萬元,徹底摘掉了困擾他半生的貧窮帽子。正是通過這種微觀敘事,從小角度切入,采用故事化的敘事表達,用金生華的生活經歷展現精準扶貧的舉措與成效。在《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專題片中,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全片用鏡頭記錄了脫貧攻堅戰中一個個鮮明的人物形象,生動呈現了人物真實的心路歷程,傳遞了貧困地區干部群眾努力脫貧的精神面貌。正是通過這種故事化的敘事,將宏大的主題落腳于具體的人,展現了更為豐富的細節內容,更容易引起觀眾共鳴,從而在潤物細無聲中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
同時,《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還巧妙設置懸念和沖突,以增強故事的可看性。如《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第3集中,六盤水市海嘎村駐村第一書記楊波2010年滿懷熱情到達位于貴州屋脊的貧困村海嘎村時,發現當地村民們安于現狀,對楊波的到來冷眼旁觀,使他的工作無法開展。隨著楊波的堅持和不懈努力,在駐村10年中不斷為村里爭取扶貧資金、項目,帶領當地群眾發展產業,他逐漸得到當地群眾的認可和贊許。到2020年,海嘎村300戶1325名貧困人口全部清零。在這部分內容中,專題片通過巧妙設置懸念沖突,推動著情節的發展,使該片呈現出更加細膩的敘事風格。
二、靈活多變的敘事視角
敘述視角又稱為敘述聚焦,是敘述者在對事件內容展開觀察、判斷、認知的基礎上,所選擇的述說事件的特定角度。法國結構主義批判家熱奈特,采用聚焦的方式,把敘述視角分為純客觀視角、限制視角和全知視角三種[4],稱為三分法。全知視角又稱為零視角,是通過敘述者大于人物的方式對事件內容進行訴說。全知視角的優勢在于對事件的來龍去脈把握精準,能夠給受眾帶來真實、客觀、公正印象。限制視角又稱為內視角或內焦點敘事,是通過敘述者等于劇中人物的方式來對事件內容進行訴說。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具有較強的可信性和親和力。客觀視角又稱為外視角或外交點敘事,是以敘事者小于劇中人物的方式來對事件內容進行敘述。優勢在于只是客觀的記錄事件的表明現象并不深究背后的來龍去脈具有很強的客觀演示性和戲劇性。
不同的敘事視角創造出不同的敘事體驗,對專題片而言,敘事視角的轉換有利于故事的展開,增強專題片的可觀性。作為一部反應脫貧攻堅成就的專題片,《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采用了多種敘事視角,展現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時采用零視角,在講述具體的脫貧工作時采用內視角,這種視角轉換有利于觀眾把握整體主題,又能激發觀影興趣。
《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第2集,采用全知視角,講述了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創造了“黃金十年”快速發展期,實現從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到全國減貧人數最多省份,山鄉面貌發生歷史性巨變,人民生活實現歷史性跨越,群眾精神風貌實現歷史性轉變。《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第3集,在講述貴州打贏脫貧攻堅戰役時,同樣采用全知視角,使觀眾更清晰準確認識到貴州交出的讓人民滿意的答卷,四通八達的交通讓深山峽谷變成“高速平原”,易地扶貧搬遷讓192萬人從深山住進城鎮,農村產業革命喚醒了沉寂的土地資源,基本實現不愁吃、不愁穿,重點解決了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安全住房“三保障”和飲水安全問題,電商扶貧讓貴州風物走向了世界。
《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專題片還充分采用了內焦點敘事,片中有大量第一人稱視角的自述,通過一個個脫貧攻堅工作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的視角,講述其戰貧斗窮的經歷過程,極大增強了專題片的親和力和感染力,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使觀眾在心理感情上與之產生共鳴。如《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第1集中,通過羅甸縣大關村村民的講述,再現了大關村民在亂石之中,經過12年的奮戰開出了1038畝良田,創造大關村奇跡的歷史。通過羅甸縣麻懷村黨支部書記鄧迎香的講述,回顧了她堅持打通麻懷村的出山道路的緣由,“幸福,如果你不用雙手去勤勞創造,你是得不到的”。正是憑著這樣一股沖勁,鄧迎香和村民們用錘子、鋼釬,用了13年的時間,在山崖上的溶洞里打出了一條216米的隧道。《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第4集中,通過黎平縣蓋寶村駐村第一書記吳玉圣的自述,講述了他到蓋寶村后發現當地有著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卻不被外人所知,決定在蓋寶村做視頻直播,通過對侗族民族文化的搶救與展示,帶動村民脫貧。最后,他用了兩個月時間,組成了侗族“七仙女”歌班,一經推出迅速走紅,隨著人氣的提升,“七仙女”開始在網上推薦當地的土特產,不僅傳播了侗族文化,還直接帶來了經濟效益。
三、嵌套使用的敘事結構
所謂結構,就是布局,也就是電視專題片為了更好的體現主題思想,對其具體材料的組織和安排。敘事理論中存在敘事結構,核心事件是對核心內容貫穿始終的主線,是一種垂直邏輯的敘事方法。衛星事件也可稱為非核心事件,其作用是圍繞著核心事件進行輔助敘述的描述,從而使其構成完整的整體,這樣的構成稱之為敘述結構[5]。
電視專題片是一種“以情感人”或“以理服人”的電視節目形態[6],其核心功能是引導觀眾接受其闡述的理念。因此敘事結構對電視專題片的創作尤為重要。《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圍繞脫貧攻堅這一主題,對各種素材進行巧妙組合,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對主題進行詮釋和表達,積極采用了多種敘事結構組合,讓脫貧攻堅的價值意義變得更為鮮活。
中心串聯式的敘事結構,是電視專題片常用的敘事結構之一,主要是通過設定中心線法來選定一條或者若干條貫穿全片的中心線,通過中心線把各部分零散的素材串聯貫通,從不同角度和側面表現并升華主旨。
通過分析《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內容發現,該專題片以脫貧攻堅為貫穿始終的中心線,4集內容通過4個不同的角度從不同側面表現這一主題。《千秋愿景》講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貴州干部群眾在脫貧攻堅道路上“敢與天斗”“敢與地斗”的奮斗精神和脫貧軌跡。《夢想花開》講述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省干部群眾苦干實干,實現了千百年來擺脫貧困的夢想。《貴州答卷》聚焦貴州“四場硬仗”、農村產業革命等,全面展現了4000萬貴州兒女交出的脫貧攻堅答卷。《續寫華章》講述了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之后,貴州持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接續推進鄉村振興的探索實踐。
通過這種結構布局,全方位展示了貴州脫貧攻堅工作這一共同的主題,將分散的素材貫穿在一起,既從歷史的縱向視野展現了貴州人民擺脫貧困的不懈努力,闡述了貴州人民追求小康的夢想,同時又講述了貴州戰勝貧困的路徑方法,全省各族干部群眾牢記囑托、感恩奮進,向絕對貧困發起總攻,實現66個貧困縣全部摘帽,923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實現了貴州大地的“千年之變”,迎來了鄉村振興的新起點。既關照了歷史與現實,又展望了美好未來,內容更加豐富全面,對主題內涵的解析也更加深刻。
板塊并列式的敘事結構,主要是圍繞明確的主題來進行板塊的劃分,每個板塊都有自己獨立的線索和發展軌跡,雖然板塊與板塊之間看似并不存在某種必然的關聯性,但依靠各版塊并列的組織方式,仍然能夠完整詮釋主題的內在蘊意,這也是電視專題片創作中常見的敘事結構。
板塊并列式的敘事結構能夠清晰展現較為復雜的內容,在統一的主題下,能夠將不同的內容組織成一個整體,有利于展現主題的方方面面。如《千秋愿景》分為4個獨立板塊,包括畢節市生機鎮在絕壁上秀溝渠將旱地變良田,興義市冷洞村用10個礦泉水瓶拯救金銀花,威寧縣石門鄉泉發村黨支部書記宋冰帶領村民種植牽藤草烏,羅甸縣麻懷村黨支部書記鄧迎香帶領村民修建麻懷隧道。《夢想花開》聚焦了威寧縣迤那鎮五星村探索精準識別“四看法”,六盤水市海嘎村第一書記楊波駐村10年,江蘇省善港村整村幫扶沿河縣高峰村等獨立板塊。《貴州答卷》講述了興仁市流水寨、銅仁市旺家社區、息烽縣立碑村的脫貧故事。《續寫華章》通過陳潤華等人才投身鄉村振興,“七仙女”以侗族文化為載體帶貨致富,以及阿歪寨實施鄉村治理的事例,展現了貴州推進鄉村振興的生動實踐。不同地區、不同人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現狀雖然是不同的,表面上看沒有聯系,但他們有共同的特點,共同詮釋著主題內容。
四、敘事元素分析
紀實類專題片與常規電視節目類似,也是借助畫面元素和聲音元素來展現信息,聲畫結合的方式可以提升節目真實性和可信度。視聽語言的運用構成了影像敘事的內容,直接決定敘事效果的好壞,視聽語言的關鍵內容有:畫面的構圖、鏡頭拍攝角度、鏡頭的組合以及聲畫的關系。
情景再現本質是對過往事件的再現[7],是電視專題片一種常用的敘事元素。所謂情景再現是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通過扮演或搬演的方式,通過聲音與畫面的設計,表達客觀世界已經發生的、或者可能已經發生的事件或人物心理的一種電視創作技法[8]。為了更好的傳遞電視專題片的內在深蘊,使觀眾身臨其境的感受影片所表達的情感和主題,通過情景再現可以做到情與景交融,背景與事件融合,引發觀眾共鳴。
如在講述農村道路建設重要意義時,專題片再現了家住興仁市波陽鎮楊柳井村流水寨組的韋歡妹上學的場景,天還沒亮就要起床,戴著頭燈翻越大山去山崖另一邊的楊柳井小學上學,不僅要走兩三個小時而且十分危險,農村道路建設的重要意義通過情景再現得到直觀展現。鏡頭語言服務于主題,運用不同的鏡頭可以呈現出不同的效果。鏡頭的遠近、左右和上下變換使得畫面縱深感和廣闊感更強,畫面內容更加立體;豐富的大遠景、中景、近景和特寫的組合使用可以增強專題片的趣味性。《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采用了多鏡頭拍攝,呈現出更強的立體感和豐富性。如20世紀50年代,畢節市生機鎮坐落于赤水河畔,卻因大山阻擋成為老旱區,缺水少糧,當地群眾生活艱辛。從1956年起,生機人開始在懸崖峭壁修溝渠引水。一錘一釬一雙手,不甘貧困的生機人用兩年時間打通了長達8千米的衛星大溝。不懼危險劈山引水,10條大溝給生機鎮帶來了徹底的改變,萬畝土地成良田,窮鄉僻壤變成了魚米之鄉。該片在闡釋這段歷史時,采用了多種鏡頭的組合,既有遠景畫面交代生機鎮的地理位置,又有近景、特寫等畫面表現修渠的艱辛與不易。多鏡頭的拍攝使畫面更加豐富立體,闡釋了生機人民戰天斗地的精神。
電視是聲音和畫面的結合,扶貧主題專題片拍攝周期普遍較長,拍攝素材瑣碎,聲音語言能將眾多的鏡頭串聯起來,增加畫面信息,使結構、內容和主題趨于合理完整。《千年夢想 決勝今朝》專題片通過大量旁白解說,起到了交代背景、連接情節、升華主題的作用,如第四集中通過旁白解說,交代了安順經開區阿歪寨從亂到治的探索,作為一個有著1000多年歷史的布依村寨,阿歪寨卻因為有黑惡勢力成為問題村寨,后來通過探索以黨支部為核心,村合作社、協會等群眾共同參與的村級自治體系,帶來了村容村貌的徹底該表。同時,本專題片有著大量親口講述,這些口述雖然會有一些口音,但這種聲音更有感情,更接地氣。如第4集中,赫章縣雙坪鄉高明村村民的口述,“一天能挖六七十塊錢,這個就主要需要耐心,不管多少嘛,你不來做這六七十塊錢從哪里來。”這些充滿人情味的口述讓全片更加真實、具體,讓影片內容更具有力量。
參考文獻:
[1]高鑫.電視專題片創作[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5.
[2]張寅德.敘述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2.
[3]阿瑟·阿薩·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10-11.
[4][法]熱拉爾·熱奈特.新敘事話語[M].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129.
[5]西摩·查特曼,徐強.故事與話語:小說和電影的敘事結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6]高鑫.“電視紀錄片”與“電視專題片”界說[ J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2(03):32-34.
[7]張文.淺析紀錄片創作中情景再現的使用[ J ].記者觀察(中),2019(3).
[8]鄭德梅.淺析紀錄片創作中“情景再現”的使用[ J ].電影評介,2010(6):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