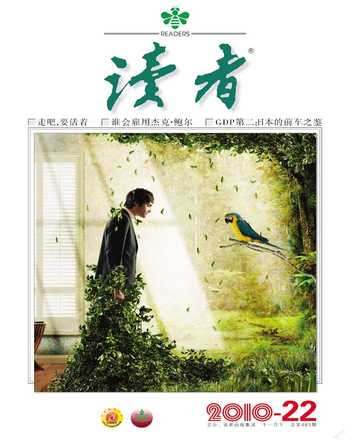愿你盡享世間美好
Bob Perks
不久前,我在機(jī)場(chǎng)無(wú)意中聽(tīng)到一對(duì)父女的對(duì)話。他們站在安全門(mén)旁,互相擁抱道別。
父親說(shuō):“我愛(ài)你,愿你盡享世間美好。”
女兒回答:“爸爸,我們一起共度的時(shí)間比什么都重要。你對(duì)我的疼愛(ài)就是我所希望的一切。我也愿你盡享世間美好。”
道別過(guò)后,女兒離開(kāi)了機(jī)場(chǎng)。
那位父親走到窗邊,這正是我所坐的地方。我看到他站在那里,離別帶來(lái)的悲傷讓他忍不住要流淚。我無(wú)意侵犯他的隱私,但他主動(dòng)和我交談起來(lái)。
“你有沒(méi)有過(guò)和誰(shuí)說(shuō)了‘再見(jiàn),而你明知道那是你們最后一次見(jiàn)面?”
“是的,我有過(guò)。”我說(shuō),“不過(guò),請(qǐng)?jiān)徫姨岢鲞@個(gè)問(wèn)題——為什么這是最后一次見(jiàn)面?”
“我年紀(jì)已經(jīng)大了,而她又住在那么遠(yuǎn)的地方。接下來(lái)的日子里,我要面對(duì)衰老和疾病的挑戰(zhàn)。事實(shí)上,她下一次回到這里,可能是為了舉辦我的葬禮。”他說(shuō)。
“當(dāng)你們道別的時(shí)候,我聽(tīng)到你說(shuō)了句‘愿你盡享世間美好,我可以問(wèn)問(wèn)這句話的含義嗎?”
他開(kāi)始微笑。“那是我們家族世代傳承下來(lái)的一個(gè)祝愿。我的父母就曾對(duì)身邊的所有人這么說(shuō)。”他稍作停頓,看上去似乎在回憶更具體的細(xì)節(jié),然后,他笑得更深了,“當(dāng)我們說(shuō)這句話時(shí),表達(dá)的意思是希望對(duì)方的生命里充滿足夠多的美好事物,伴隨他、支持他走過(guò)接下來(lái)的人生旅程。”他轉(zhuǎn)過(guò)身來(lái)面朝著我,說(shuō)出下面這段話,像是翻出了記憶深處的一個(gè)片段,與我分享:
“我希望你擁有足夠的陽(yáng)光,好讓你永遠(yuǎn)保持樂(lè)觀的態(tài)度,不管生活看上去是多么令人消沉;
“我希望你擁有足夠的雨水,好讓你更加感激那些陽(yáng)光普照的日子;
“我希望你擁有足夠的苦難,那么即使生命里最小的快樂(lè)也會(huì)顯得大一些;
“我希望你擁有足夠的收獲,好滿足你的需求;
“我希望你擁有足夠的損失,好讓你珍惜所擁有的一切;
“我希望你擁有足夠的問(wèn)候,好讓你度過(guò)每一次離別。”
人們常說(shuō),找到一個(gè)對(duì)你來(lái)說(shuō)很特別的人只需一分鐘,感激他的存在需要一小時(shí),去愛(ài)他需要一天,可是要忘了他卻要用去你的整個(gè)人生。記得告訴你的家人和朋友,你愿他們盡享世間美好。也希望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盡享世間美好。
(阿敏摘自《美好生活》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