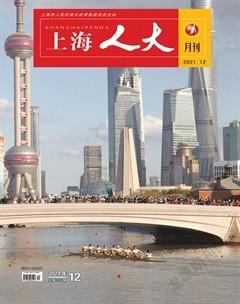把握好“法、理、情”的統一
馬超杰
近年來,社會上時常會出現一些受到輿論熱議、關注的司法案件,其中尤以刑事案件居多。諸如許霆盜竊案、王立軍無證收購玉米被判非法經營案、趙春華擺射擊攤被判非法持槍案等。熱議、關注的焦點又常常圍繞著案件裁判中的法理與情理的沖突與矛盾展開,法官專業化的判斷結論與社會民眾直覺化的正義情感并未產生同頻共振,導致案件定罪結論屢遭質疑與抵觸。分析原因,自然存在多種因素,個人以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案件處理未能準確把握好“法、理、情”的統一,實現法理與情理的融會貫通。
所謂情理就是人情事理,注重感性;而法理則是法律所依據的原理,偏重理性。情理是法理的現實基礎與來源,法理是情理的規則升華與結晶。但由于法律規定的不完善、滯后性,中國人情社會對于“情、理、法”認同次序的特殊文化傳統、執法者機械執法等因素,均會導致在某些案件處理中,法理與情理之間產生不協調甚至沖突。
任何法條背后必然有基本的“常識、常情、常理”的支撐,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就是這層意思的通俗表述。但這里的“人情”不是指個體的私情私利或人情世故,而是指特定時期一般社會人的基本情感、基本道德與社會習慣,故法律規定一般是蘊含、符合常識、常情及社會的倫理道德的。所謂“法亦容情”,這正是法律得到大多數人遵守與接受的重要因素。法律人強調法律至上,主張“法不容情”,側重于表達執行法律不要受私人感情、私人利益的干擾,應當堅守法律的框架與底線,而不是理解為裁判過程只講法理不談情理,排斥法律適用中對情理因素的關注、考量與運用。
面對案件處理中法理、情理的沖突,執法者并非只能強調法律規定就是如此而無能為力,只追求裁判結果符合案件事實所對應的法條規定就萬事大吉,做一名機械適用法律的搬運工;而應當發揮執法者的主觀能動性與創造性,通過能動地解釋法律、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積極調解等多種手段與方法,最大限度將情理因素涵攝入處理結果之中,努力填補、彌合兩者沖突可能形成的縫隙與裂痕,以確保案件處理既經得起法律檢驗,又符合社會公平正義觀念。在具體的案件中,執法者如何找到法理與情理的最佳連接點、平衡點、融合點,盡最大努力消除法理與情理發生重大沖突的現象,既是司法能動性的具體體現,也是對每一個執法者的智慧、良知、能力的重大挑戰與考驗。
司法是一項復雜、充滿智慧與創造性的活動。擔當活動重要角色的法官,除了居中裁判者的主要身份外,還兼有糾紛化解者的身份與職責,需要傾聽不同的聲音、權衡不同的利益、斟酌不同的觀點、兼容不同的思維,為裁判結果進行充分說理,在堅守法律底線的同時,善于運用“常識、常情、常理”原則,多角度思考、把控、解決法律問題及實體糾紛,確保案件處理于法有據、于理應當、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觀念,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依照事實與法律得出裁判結論,尚不能稱圓滿地完成了審判工作的全部內容。只有強調案結事了、得出結論的同時,努力推動糾紛的實質化解,才能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讓裁判結論獲得社會公眾的廣泛認同。
此外,強化庭審、裁判文書釋法析理的工作也是減少、消融法理與情理沖突的重要途徑。要圍繞案件爭議焦點和社會關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準確、細致地闡明案件處理的依據和理由,有效回應當事人和社會的關切,使庭審成為全民普法的法治公開課,使裁判文書成為法制宣傳的最好教材,以法理彰顯司法理性,以情理展示司法良知,讓公平正義的抽象理念成為具體案件中活生生的生活現實。
記得一名檢察官在總結自己的執法理念與辦案經驗時提煉了八個字——“不傷法意、不絕人情”。這表達了執法者的共同心聲,也是對執法辦案中如何實現“法、理、情”統一,維護公平正義的很好詮釋。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