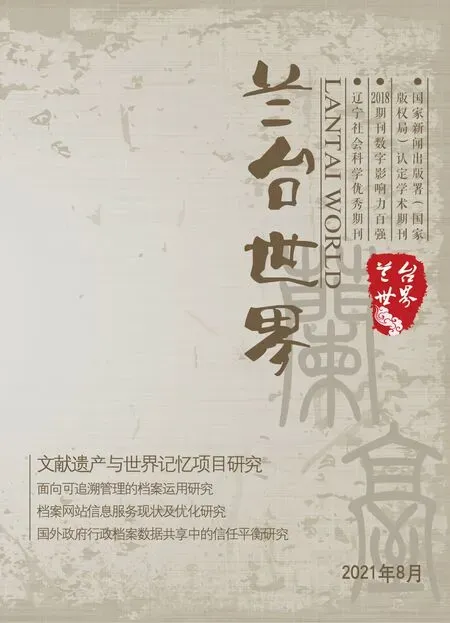中國古代監獄人犯的囚糧供給問題考察
張 波 趙玉敏
一、秦漢
1.秦代。秦代以前,囚糧如何解決,未見記載。秦代囚糧,主要由官方供給。《秦律十八種·屬邦律》記:“道官相輸隸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稟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無有,受者以律續食衣之。”[1]65《秦律十八種·倉律》記:“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小城旦、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1]32秦代采取官方供給囚糧的做法,其直接原因應在于大多數人犯都是徒刑,即服役刑,或修長城,或建皇陵,或服役宮中,人犯家屬無法供給飲食,只能由官方供給囚糧。
2.漢代。漢代應是沿襲秦代做法。據《后漢書》記,東漢初年,會稽名士陸續被逮入洛陽獄,其母前往探視,未獲允準,只好做了飯菜央求門卒送入獄中。“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2]卷81《獨行傳》如果該記載無誤,那么可以斷定,東漢人犯應是由官方供給囚糧,否則,陸續之母前來送飯,就不應被禁止。
二、魏晉隋唐
1.西晉。西晉最早明文規定了囚糧的供給。其《獄官令》記:“家人餉饋,獄卒為溫暖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3]168其后各朝基本沿襲。
2.唐代。《唐律疏議》記:“準獄官令:囚去家懸遠絕餉者,官給衣糧。家人至日,依數征納。”[4]700又,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奏閿鄉縣禁囚狀》稱:“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數十人,并積年禁系,其妻兒皆乞于道路,以供獄糧。”[5]3355
據此可知,唐代囚糧主要還是由人犯家屬供應,只是對家屬居住遙遠而無法送飯者,先行借給囚糧,其家屬后來繳還。
此種方式的成效未見記載,在唐代中前期,因為國家的興盛和均田制的推行,應該是沒有問題。而到中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亂后,則應該是難以為繼,人犯很可能是久系獄中,嗷嗷待哺,甚至是坐以待斃,所以才會出現白居易所稱的現象。
3.五代十國。五代十國應是承襲了唐代。后周顯德二年(955)四月,曾發布敕令稱:“應諸道見禁罪人,無家人供備吃食者,每人逐日破官米二升。”[6]164
三、宋代
兩宋為囚糧問題的一個重要轉折期。北宋雖然一直被視為積貧積弱,事實上,其統治的疆域、人口并不輸前代,故在囚糧問題上仍可以沿襲前代。但到南宋,因為疆域、人口都大為削減,已經力有不逮。
1.北宋。北宋在承襲唐代、后周做法的基礎上,略有改變。一般人犯仍是自行籌備囚糧。例如,據(宋)葉夢得記: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烏臺詩案被逮入詔獄,與其子蘇邁約定,每日“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一月后,蘇邁所帶錢財用盡,不得不前往陳留籌集,于是,只好請一位親戚先代為送飯。不料,臨行匆忙,蘇邁忘記說密約之事。這位親戚恰好弄到一條鮮魚,于是烹煮好送進監獄。蘇軾“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7]79。
如果人犯家屬居住較遠,無法每日前來送飯,則由官方先行供給囚糧,待到人犯“家人至日,依數征納”。如果人犯家境貧寒,家屬根本無力送飯,則由官方每日發給“官米二升”[8]535-536。
2.南宋。南宋初期一度將發放囚糧改為發錢。宋高宗紹興十三年(1143)詔稱:“禁囚無供飯者,臨安日支錢二十文,外路十五文。”[9]4969但此種做法應是推行未久,便改回發放囚糧。據記載,南宋州一級的監獄人犯囚糧,規定“以常平或義倉米支破”[10]6728。但縣級監獄未有明確規定,所以多有餓死。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便有官員稱:“縣獄不支糧,多有饑死。”[10]6728又,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亦曾稱:“準《令》,給囚之物許支錢。準《格》,在禁之囚許支米。錢則許于贓罰、頭子、運司等處隨宜撥支。米雖立定升數,而無顯然名色。”“諸處縣獄尤無指擬,凡長吏賢者,至或巡門乞米,以為一粥之資,吏或不賢,亦不可常得。”[11]2853
鑒于此,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五月二十三日詔令,嗣后“縣獄如州兩獄例,以常平或義倉米支破糧食”,并且將人犯餓死數量作為有關官吏年終考核的內容之一[10]6728。
盡管針對州縣兩級的囚糧問題,南宋政府都作出了可以動支常平或義倉的指示。但其指示存在一定的問題,例如,囚糧可以動支多少?動支之前是否需要提交申請?動支之后如何報銷賠補?如果動支超額而又賠補不上,有關官員是否會被處罰?或者,常平或義倉并無足夠的積儲,又應該怎么辦?這些都未規定。所以,囚糧的問題實際上仍是懸而未決。常平、義倉積儲不夠或者根本沒有積儲者固不待言,即使是有足夠積儲者,各州縣官出于上述顧慮,往往亦不敢輕易動用。
然而囚糧又一日不可或缺,為解燃眉之急,各州縣只好沿襲原來的“陪辦”之法,“私取于役戶,分甘于同禁之人”[10]6728。此法不足之處極多,包括:(1)根本無法滿足囚犯對于囚糧的需求。(2)不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萬一某段時間沒有案件,無費可收,則人犯就要忍饑挨餓了。(3)容易開啟獄卒等人趁機敲詐勒索、克扣侵吞之弊。
對此,嘉泰三年(1203)十一月十一日,宋寧宗便提到:“訪聞州縣違戾,卻將合給禁囚飲食,止令獄子就街市打掠,或取給于吏卒,病囚藥物抑勒醫人陪備。是致禁囚飲食不充,饑餓致病,醫人無錢合藥,病囚無藥可服,多致死亡,誠可憐憫。”[10]6728
所以,朝廷再次強調了可以動支囚糧的意見,“可自今赦到日,應合給囚糧并仰守令于轉運司錢內分明取撥,置造飲食;病囚藥物并于贓罰錢內支破修合。各具赤歷收支。”并且,要求各州縣停止原來的囚糧籌集辦法,“不得仍前再令獄子輒于街市打掠,及勒醫人陪備藥物。如違,仰監司按劾以聞,重置典憲”[10]6728。
盡管如此,各州縣官考慮各自地方的實際情形,仍繼續持保守態度。官員孫夢觀便曾奏稱:“臣近者出守于宣,嘗考五年版籍,額二十五萬余石,除災傷檢放、運司寄納、諸縣截留、遠年逃閣人戶拖欠之數,所入多則十萬余石,少則六七萬石。若并以斛面而諭之,農寺總制所以苦不足而截上供以充府用者,止萬余石。官兵請給、宗子孤遺歸養暨囚糧雜支乃至六萬余石。移東補西,委難支吾。宣為藩府,猶且若此,其它小壘,抑又可知。”[12]483顯然,在此種情形下,如果貿貿然地遵循朝廷的規定,再動支有關錢糧,萬一有意外發生,實屬冒險之舉。所以,州縣官員不能不心存顧慮。
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便有官員疏稱:“切見縣獄苦無囚糧,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許于運司錢內支,往往縣道不敢支破。”[13]卷173,刑考六宋寧宗嘉定八年(1215)六月十三日,有官員疏稱:“夫州縣之獄凡為民害者,朝廷因臣僚奏請,屢嘗戒飭,獨囚糧一事未見施行。獄戶沈郁,易于生疾,一有乏食,病輒隨之。州縣但謂之獄瘟發動,而不知其端蓋在于此。江浙州郡皆有囚糧,遠州僻郡大率疏略。”[10]6728
對于地方官員的此種顧慮,朝廷亦感無奈,所以在宋寧宗嘉定八年(1215),又推行了“囚糧歷”做法,即囚糧動支的報銷制度,借以規范、敦促各州縣遵照朝廷指示解決囚糧問題。具體做法為:“令提刑司免其解發,別置循環歷二本,名曰‘囚糧歷’,日具支破姓名,取其著押俾隨禁歷月口申提刑司,以備參考。”[10]6731
一方面是朝廷的一再敦促,以及對“陪辦”之法的查禁;另一方面,則是對動支倉儲的重重顧慮,左右為難之下,獄田開始悄然誕生。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浙江昌國縣“縣令于縣治之西,取在官之田,歲可入粟十斛,又取富都中莊洋官田一十七畝,歲可入粟二十三斛,吏為掌之,以濟在囚無親族之供贍者”[14]707。是為所見最早的獄田設置記載。
綜上,盡管兩宋王朝就囚糧問題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但各地方的囚糧問題始終未能妥善解決。究其原因,就在于當時統治疆域、人口的局限,所導致的地方財力嚴重不足。
四、元代
元代對囚糧的問題關注較早,元世祖中統四年(1263)七月,中書省便奏準:“獄囚有親屬者,并食私糧。無親屬者,官給每名日支米一升,于雀鼠耗內支破。雖有親屬,若貧窮不能供備,或家屬在他處住坐未知者,糧亦官給。”[15]402
相對而言,元代的規定更為詳細明確,不僅規定了每人每天一升的供給量,而且明確了撥付來源,“于雀鼠耗內支破”。此外,還擴大了囚糧供給范圍,雖有家屬而實在貧困者,官方亦供給。但元代囚糧的供給仍存在一些問題。
(1)雀鼠耗名下的糧食數量有限,難以完全滿足囚糧的需要,所以在實際的操作中,又出現另一問題,即有些地方在未到征收糧食時間,卻不得不向百姓預先征收雀鼠耗,以保證囚糧的供給不至中斷。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九月,有監察御史在奉旨前往大都路錄囚時,便“體知得大都路司獄司見禁囚人每日合用糧食,有司獄司官止于街市鋪戶處逐旋借借,鋪戶取要加耗,中間克減石斗,在后卻于官倉內撥還,不惟如此,囚人隨時不得食用”[15]402。在此種情形下,該監察御史建議先令監獄方面每月底統計人犯數量和所需囚糧數量,然后報送上級衙門,由本地倉儲統一撥給,然后等到征收完雀鼠耗后,再補還倉儲。戶部和中書省同意了該項建議,并且進一步明確規定了每名人犯月支米二斗五升的標準[15]402。
(2)元世祖中統四年(1263)七月的囚糧規定供給范圍有限,并未將縣級監獄的人犯包括在內。(元)張養浩即提到:“諸在縲紲無家者,皆給之糧,惟縣獄不給也。意者縣非待報之官府,故令略詰其然而上之州。”[16]18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囚糧發放范圍才擴大到縣級監獄人犯,但仍舊限于“委無供送人等”,而一般人犯則依然無法享受囚糧[15]402。
因為上述諸方面,就整體而言,元代囚糧的實際解決狀況并不樂觀。元順帝至正二年(1342),監察御史王思誠便曾奏稱:“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17]卷183,王思誠傳又,鄭元佑《趙州守平反冤獄記》載:王畊“冤入淮幾二載,囚糧不可以飽,畊諸兄弟更貸以救。”[18]卷九,趙州守平反冤獄記
五、明代
明代在囚糧問題上經過了多次變動。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規定,人犯“無家屬者,日給倉米一升”,“于本處有司系官錢糧內支破,獄司預期申明關給,毋致缺誤”[19]167。洪武十五年(1382),重申此項規定。但不知何故,洪武二十四年(1391),又下令取消了囚糧的供給。直至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才又恢復,每囚每日仍是給米一升[19]168。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針對重囚、強盜人犯,作出削減:“重囚每日七合。強盜三合。”[19]168
明代關于囚糧的規定,存在問題較多。
(1)囚糧發放范圍有限,而人犯數量眾多。依照規定,明代囚糧的發放范圍僅限于“無家屬者”,而人犯數量遠超前代,其中無家屬者數量眾多,即使是有家屬者,或因家貧無力供給,或因居住遙遠難以輸送,或因他故不愿輸送等,其中亦有不少需要供給囚糧者。在此種情形下,囚糧之發放僅以有無家屬這一標準來劃分,無疑太過武斷,將許多需要供給囚糧的人犯排除在外,令其陷入困境。
(2)各地方錢糧有限,不敷分發。需要供給囚糧的人犯數量眾多,地方顯然難以承擔。(明)呂坤便曾說道:“有司錢糧原不寬綽,若囚糧一概全給,豈能人人均沾,年年常繼?”[20]550如果選擇性給發,又勢必導致一些人犯忍饑挨餓,甚至是餓死,有悖教化。明神宗時,山西保德州知州胡柟便曾說道:“強盜劫財,本王法所不容者,然議獄緩死,則法中有仁寓焉。囚糧之設,正為緩死計也。有一囚即與一糧。不問其為人命,為強盜,亦不問其有供給,無供給,一概不與,又疑于太刻。知其必死而坐視其死,此心所不忍也。”[21]580所以,圍繞究竟如何給發囚糧的問題,明代地方官員實際上是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
(3)未指定明確的囚糧撥付來源和渠道,地方官員不知所措。明朝廷規定由“系官錢糧”內撥給囚糧,但未指明何項“系官錢糧”。地方錢糧有限,又皆有定額,顯然難以隨意動支。此外,從行政隸屬關系上講,監獄歸刑部管轄,而地方倉儲多歸戶部管轄,兩部及其下屬機構立場不同,從各自職守出發,難免認識分歧,無法在囚糧問題上達成一致。地方官員同時接受刑、戶兩部管轄,更難尋求到一個折衷點,以妥善解決囚糧問題。
明熹宗天啟年間(1621—1627),安徽繁昌知縣呂元學即說道:“按屬重犯月糧取之倉稻,所從來也。顧積貯國家之大命,犴狴既多靡費,則賑濟未免有虧。而況部文申飭諄諄,不許以倉稻給囚糧,未有令諸囚駢首餒斃者,若聽有司之設法,終屬紙上之空言。”[22]90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但是囚糧關系匪淺,若犯人因缺糧而瘐斃,影響非同一般。對國家而言,最高統治者有失于其“仁政”之美名;對囚犯而言,則失去對其懲戒的意義;對有關官員而言,則有失職守。鑒于此,從明代開始,有關官員便不得不努力探尋囚糧的其他解決方案。
(1)置辦獄田[23]。
(2)分別人犯類型,實行差額供給。例如,明神宗時,山西保德州知州胡柟便將本州登報贖谷分別等第發給人犯:“如系人命,每月給谷三斗。系強盜,別州縣人,則給谷二斗;系本州人,則給谷一斗五升……至雖系山西人而有妻有子及本州人之有供給者,俱不敢妄為干澤也。”[21]580又,(明)呂坤亦實行了此種辦法,將人犯分為三等,“除罪大惡極死有余辜者不準給,家不甚貧有人供應者不準給外,有情稍輕而家極貧或無家供應者,給與全糧;情稍輕而家次貧日用不足者,給與半糧;至于新獲賊盜,真假未分,果無供給,亦當有處”[20]550。
(3)收取折杖等以購置囚糧。(明)余自強便記稱:“各處陋規往往俱折銀不等,謂之折杖。間有自好官府,每不欺問其實,安保皂隸往往交通私折,瞞官入已。故此一項雖陋規,而卻亦有用。用之何如?分付刑房立簿一扇,每遇上司批到,即將枷責寫上,照依地方舊例折多折少明注簿中,暇時清監,除已經允決重囚有囚米外,又除未經定罪有親戚供送或有手藝者外,余或遠來駁審囚犯,或無供送冤民,每月將前銀買米買塩菜若干,每十日親自一散。”[24]544
(4)鼓勵人犯從事日常生產,自謀生計。在實行差額供給囚糧的同時,呂坤還提出了鼓勵人犯自謀生計的建議,具體做法是讓人犯在獄中從事“挑網巾、結草履、作布鞋一切不礙關防生藝,初給半年囚糧,令作工本,待藝習頗通之日,令自為生。其有應賣之物,待放飯之時,各付所親辨買,以資衣食。門禁驗明照出,不許刁難。”[20]579但在當時條件下,無疑很難真正大規模地推行。究其原因,一方面,人犯無法集中從事某一種物品的大量生產,畢竟沒有相應的訂貨方或者供貨商等;另一方面,單個人犯的產品無法尋找到穩定的買方市場,難以為繼。
總之,上述種種嘗試,雖然都體現了有關官員的良苦用心,可惜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明代囚糧的供應問題。明神宗萬歷三十八年(1610)六月,閣臣葉向高便曾題稱:“刑部掌印無人,獄囚莫為問斷,囚米無措。”[25]712明熹宗時,刑部尚書孫瑋等亦奏稱:“獄囚眾多,囚糧不足,因餒告斃者相繼。”[26]卷34天啟三年五月壬子
囚糧供給始終是歷代監獄所面臨的最主要,也是最令人頭疼的問題之一。從秦漢至明清,歷代政權幾乎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圖尋找到解決辦法,然而都未成功。究其原因,就在于囚糧的供給并非是單純的監獄或者司法系統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時代的縮影。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司法公允,監獄人犯數量自然就會較少,囚糧的供給隨之亦不是一個問題。反之,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妥善解決這一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