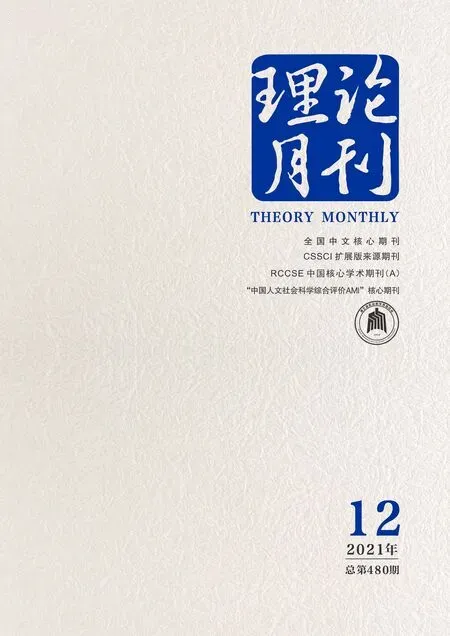因境而化: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發生學考察
□楊章文
(上海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444)
“意識形態”既是關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概念,又是體現生產力決定作用的根本需要,還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過程中的基本遵循。歷史視野中的意識形態概念最早由特拉西提出,經馬克思的批判性運用后傳入中國,爾后隨著唯物史觀的興起逐步形成中國化的理論體系。從其豐富的傳播史中可以窺知,這一概念在中文語境的出場中并非被直接闡發為“意識形態”。除1919年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使用了“意識形態”①“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的構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所適應的真實基礎。”參見《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頁。這個表述以外,郭沫若把“意識形態”一詞譯為“觀念體系”②“關于德意志觀念體系的一書,凡是已經完成了的,在馬克思與昂格斯所遺留下的稿件中是存在著的。”參見《德意志意識形態》,郭沫若譯,言行出版社1938年版,第25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中則將其譯為“意識形式”①“對思辨的法哲學的批判既然是德國過去政治意識形式的堅決反對者……”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頁。。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中多次提及“意識形態”,但并未對這一概念進行明確界定,這就為不同語境中的理解帶來了諸多困難。從國內的既有研究來看,有學者考察了意識形態概念在西方的流變,如鄭海俠指出,自特拉西初次闡述意識形態概念之后,其含義已然發生了非科學性、實存性、科學性、非價值性、泛文化性等五次重大轉向[1]。也有人指出,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中國化歷經三次飛躍,形成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理論體系。雖然這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意識形態概念的中國化進行了闡釋,但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演進脈絡和運思理路仍待厘清。基于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生成邏輯,我們應如何理解中國傳統的社會觀念與意識形態概念的銜接?西方社會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理解對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有何影響?20世紀上半葉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核心內涵到底是什么?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演進歷程著手來理解這一時期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現實圖景,以管窺這一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傳播與接受史。
一、意識形態概念的演進歷程
“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外來詞匯,歷經多重語義轉換。從“意識形態”的概念演變來看,它在一開始被西方學者引入政治學的知識體系,并因特拉西將其闡述為“觀念的科學”而被賦予了新的使命。在此之后,經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闡發,意識形態概念的內涵逐漸穩定下來,形成系統的理論框架。
(一)“意識形態”的詞源學溯尋:從西到中
“意識形態”是“一個內涵漂浮不定的概念,它擁有巨大的語義威力”[2](p1)。溯其根源,“意識形態”這一語詞是希臘文?δ?α和λ?ογ?的結合體,原義指一種概念、觀念、學說[3](p1097)。英文中“意識形態”被表述為“Ideology”,由“理念”(eidos)和“邏各斯”(logos)共同構成。除英國以外,在法國和德國的語言系統中,此詞的含義都為“觀念科學”(science of ideas)或“觀念學說”(doctrine of ideas)。邁克爾·曼的《國際社會學百科全書》將“意識形態”闡述為:“當德斯圖特·德·特蕾西在18世紀末創造這個術語時,其含義僅為關于思想的科學(與‘形而上學’相對照)。”[4](p285)因此,從詞源學上來看,意識形態概念最初是以“思想的科學”或“觀念的科學”為起點的,屬于思想觀念上的一種劃分方式。
古漢語中并未直接出現“意識形態”一詞,更多的是含義與之相近的“思想”“觀念”等語詞,如“思想避難之處,乃望褒城投奔相識而去”[5](p4)等。在不同語境中,其含義可以是“思維”“相思”“思忖”“思想意識”等。相較于“意識形態”的英文詞源,古漢語中的相關語詞有“思想觀念”的含義,卻沒有“觀念科學”的含義。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意識形態概念有很多,如儒學、道學、佛學等,但這些都不能視作對近代歷史語境中“意識形態”內涵的指稱。其原因在于,古代中國社會尚未在觀念上明確區分科學和非科學,因而未能形成自覺的觀念科學意識。
(二)意識形態概念的古典演繹:從柏拉圖到特拉西
在西方古典社會中,“意識形態”一開始就被西方學者引入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關于意識形態概念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圖提出的“高貴的謊言”和“洞穴比喻”。柏拉圖認為統治者編織“高貴的謊言”的目的在于,讓公民熱愛其所在的城邦,維護統治者自身的統治根基,實質是將其統治建基于對世界的虛偽言說之上。從廣義層面上看,“高貴的謊言”為后來意識形態概念的生成孕育了基本要素,可謂是意識形態概念演變圖譜的起點。“洞穴比喻”則生動地指出了人類從現象世界走向理念世界、從無知走向有知的過程。
歷經漫長的中世紀,柏拉圖關于“靈魂轉向”的理念并未如期實現,各種“錯誤的觀念”和“虛假的意識”反而使人的精神和靈魂深陷與現實世界相脫離的幻象之中。所以,意識形態概念作為近代觀念的“衍生品”而登場并非出于偶然。培根的“四假象說”被認為是近代意識形態概念的源頭。1620年,培根率先對中世紀神學和經院哲學錯誤觀念展開批判,并在《新工具》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說”,即種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場假象和劇場假象。從認識論的邏輯視域看,“四假象說”對于意識形態概念的出場有著較為突出的貢獻。
之后經過法國啟蒙思想運動的洗禮,哲學家特拉西率先提及“意識形態”這一名詞。在《意識形態的要素》中,他將“意識形態”闡發為如下兩方面意思:一方面,特拉西從本體論角度將“意識形態”理解為“經驗心理學”,指出唯心主義的權威知識之所以是“謬論”,就在于這類思維理念無法將自身直接復歸為感性認知,“而意識形態的唯一任務就是這種包羅萬象的還原”[6](p34)。另一方面,特拉西從政治學視角將“意識形態”理解為“政治社會學”。在其著述中,他細致地闡述了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關于建立共和國的政見,并樂觀地認為這門學科是“積極的、有用的、非常精確的”[7](p126)。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誕生后不久,這一“觀念的科學”的理念便被拿破侖否定了,作為一門新科學的“意識形態”尚未來得及真正建立就被扼殺在搖籃里。
(三)意識形態概念的唯物主義轉向:從馬克思到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盡管“意識形態”在法國被統治者否定,但在同時期的德國,“意識形態”卻成為一種“時髦”的話語,并兼具“褒”與“貶”雙重含義,而貶義在與褒義的交鋒中處于絕對上風。也正是在這里,意識形態概念獲得了批判性的內涵。對于馬克思而言,在眾多研究者中對其影響最深的無疑是黑格爾。科特·蘭克指出,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所有的決定性環節都已經在黑格爾的異化理論中預先構成了”[8](p114)。可以說,德國哲學的批判理性直接促成了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誕生,是意識形態理論從唯心主義走向唯物主義的關鍵要素。
從馬克思的文本來看,他至少在三重意義上揭示了“意識形態”所內蘊的機理。一是認識論維度的“虛假意識”。這里所說的“虛假意識”,指基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視角而形成的德意志批判話語。二是價值論意義的“統治階級的意識”。為盡可能地鞏固自身的利益根基,統治階級往往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從而“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9](p180)。三是社會學意義的“社會意識形式”。唯物史觀認為,人類自從有了獨立的精神創造活動也就具有了相應的社會意識,因而馬克思恩格斯便把體系化的社會意識形式納入上層建筑的邏輯框架之內。之后,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識形態思想被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所繼承和發展。但包括拉法格、拉布里奧拉和梅林在內的大多數第二國際理論家依然堅持關于意識形態的否定性觀點。
被譽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漢諾夫對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顯然要深刻得多。在其哲學研究中,他首次在中性意義上使用了“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的表述。他將意識形態表述為“一定的精神狀況和道德狀況”[10](p186)以及“一定時間、一定國家的一定社會階級的主要情感和思想狀況”[10](p272-273)。普列漢諾夫的意識形態理論扮演著由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向列寧的意識形態理論過渡的“中介”角色。列寧第一次以“建構性”的樣態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概念,并賦予了“意識形態”以肯定的內涵。就此而言,列寧將“意識形態”區分為“科學”和“非科學”兩種類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是與客觀真理和絕對自然相符合”[11](p96)的,所以屬于“科學的意識形態”范疇;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虛假的”和“非科學的”。正是基于對兩種不同類別的意識形態的深入剖析,列寧論證了作為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武器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功能。
此后,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盧卡奇和葛蘭西,在列寧意識形態思想的影響下,亦在肯定層面上使用這一概念。他們嘗試以意識形態革命的形式改變現實狀況,進而實現“人的發展”和“人的解放”。與之相反,法蘭克福學派從否定角度指出: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生產者為維護階級利益而蓄意虛構的一種意象,旨在支配人們的思想,操控人們的生活;“人的發展”和“人的解放”就是為了擺脫意識形態的感性桎梏,揭穿意識形態的真實面目。
二、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發生過程
實際上,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在中國的傳播從一開始就不是孤立的,它是伴隨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道從西方傳入的。不同于單一的學術理念傳導,意識形態概念在中國的“生根”和“發芽”,不僅是一個社會思想“西學東漸”的歷史過程,而且還是那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價值觀念和社會革命運動進行探究和認知的結果。在包含唯物史觀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初入中國之時,以陳溥賢、李大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有識之士在譯介和傳播這一“新學”的過程中也將意識形態概念攜入中國。
(一)根源追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基因的隱性代入
毋庸諱言,在意識形態理論最初的傳播過程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疑起到了重大作用。除此之外,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等對意識形態的相關理論也有過或多或少的譯介和傳播。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基因在這一過程中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
1.中華民族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關心政治或者說是最政治化的民族。《尚書》中說:“道洽政治,潤澤生民。”自古以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政治便是公共事務。儒家學說中有許多相關內容,如“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從古代中國傳承下來的對政治關心的態度,促使意識形態理論一經傳入便引起了較大反響,得到了國內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如1919年8月5日至1919年12月24日《學燈》連載的羅琢章、藉碧所譯的《馬克司社會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中就出現了“意識形態”一詞[12];1932年瞿秋白在探討“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的問題時,就將“Ideology”一詞直譯為“意識形態”,并進一步提出了“文藝現象是……意識形態的表現”[13](p515)的觀點。
2.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本質上契合于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求變”“求新”思維。盡管求穩守舊的思維在古代中國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因時而變的觀念種子業已悄然播撒。“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系辭下》),意指事物本身在成長過程中遭遇困境時應當以“求變”思維沖破事物運行的阻塞。自近代以來,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外患不斷、內政腐敗,追求變革是勢之所趨、民之所向。從“經世致用”的更法主張到“變法自強”的洋務運動,從“百日維新”的戊戌變法到“救亡圖存”的政治革命,從“革陳啟新”的文化革命到“破舊立新”的社會革命,貫穿其間的一個共同信念就是以“求變”改變生存境況,以“求新”推動社會進步。故而,意識形態在社會變革時期不可避免地在中國生根發芽,并被不同領域的學者引入和研究,使之得到進一步的擴散式發展。
3.作為中國古代的官方哲學和主流意識形態,儒學日益式微,嚴重制約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在此境遇下,社會迫切需要新思想和新哲學的引領。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訴求愈發凸顯,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問道西方以探求真理”的思想文化歷程。這樣一來,盛極一時的全球性文化思潮,如無政府主義、基爾特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浪潮般地涌入中國,并與儒家傳統觀念中的“大同主義”交匯。一時之間各領域知識分子皆以“大同”為焦點展開言說,促使中國思想界、學術界達成廣泛共識——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與此同時,伴隨各種“意識形態”的傳入,中國人在選擇和接受之時潛移默化地對意識形態概念本身產生了認同。
(二)進路演繹:早期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覺醒
“意識形態”一詞最早傳入中國的時間是1919年,見于陳溥賢和李大釗等人對河上肇介紹唯物史觀的相關著作的節譯。彼時為紀念馬克思誕辰101周年,《晨報副刊》連續四期刊載了陳溥賢(筆名為“淵泉”)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以介紹日本學者河上肇的關于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論述。其中,“意識形態”一詞出現在1919年5月6日刊出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原文為“在這基礎(即由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的經濟基礎——引者注)之上,再構造法制上政治上的建筑物,適應社會的意識形態”[14]。此文被認為是“馬克思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第一篇文章”[15]。同年9月,李大釗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亦使用了“意識形態”一詞。值得一提的是,胡漢民于1919年寫成的《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一文中對唯物史觀的價值取向和階級屬性有過諸多論述,文中同樣出現了“觀念上的形態”“社會的意識形態”[16](p10-11)等詞句。
在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厘清——最初經由日本學者河上肇譯介而來的“意識形態”所對應的是否就是德文語境中的“Ideologie”(現代中文一般譯為“意識形態”)一詞?答案顯然為否。我們找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簡稱“《全集》”)中文版中的相關譯文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的譯文完全相同,皆為:“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3卷第8頁,或第2版第31卷第412頁。與之對照便會發現,由河上肇初創(“意識形態”)、陳溥賢等人譯介的“意識形態”一詞,在《全集》中被譯為“意識形式”。需要追問的是,這兩個詞語到底哪個更為精確呢?我們通過查閱MEGA2(即《全集》歷史考證版)德文原版的相應段落②MEGA2中收錄的德文原文為:“Die Gesamtheit dieser Produktionsverh ltnisse bildet die konomische Struktur der Gesellschaft,die reale Basis,worauf sich ein juristischer und politischer Ueberbau erhebt,und welcher bestimmte 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formen entsprechen.”參見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 Gabe,II/2.,Dietz Verlag Berlin,1980,S.100。,不難發現,河上肇譯文中的“意識形態”是由德文“Bewuβtseinformen”翻譯而來,而非“Ideologie”。基于當今通用的闡述視角,不管是河上肇版本的日譯,還是陳溥賢版本的中譯,皆在一定程度上對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概念產生了誤解,也就是將馬克思文本中的“意識形式”概念誤譯為了“意識形態”。那么,“Bewuβtseinformen”究竟該做何解釋呢?根據陳溥賢的譯文,“‘社會的意識形態’,是指現在社會上所流行的思想上精神上的主義風潮”[14]。僅從譯法上看,這里的“意識形態”一詞在語義上所指的是“社會意識形式”。那么,馬克思原本的意識形態(Ideologie)概念去哪兒了呢?確切地說,首位把“Ideologie”遷移至中文語境中的人是瞿秋白。他在192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每一派自成系統的‘社會思想’(Ideologie),必有一種普通的民眾情緒為之先導”③瞿秋白的“社會思想”指的就是“意識形態”概念,釋義見下文。。實際上,瞿秋白亦是第一個在中文語境中明確定義了唯物史觀意識形態概念(以“社會思想”的形式)之人——“社會思想是指每一時代普通民眾的思想方法以及他們對于宇宙現象及社會現象的解釋”[17](p255-256)。把“意識形態”作為Bewuβtseinsformen、Ideologie的共同譯語,與其訴諸漢語的牽制,毋寧歸因于早期中國知識分子對唯物史觀意識形態概念的理解視域相對而言比較局限。
相比于瞿秋白,李達對于唯物史觀意識形態概念的論述稍顯滯后,但卻并不妨礙他成為第一個在馬克思文本意義上使用“意識形態”一詞的人。1926年,李達在《現代社會學》一書中闡釋社會上層建筑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時指出:“社會之政治的、法律的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皆依據經濟關系而成立,復有維持經濟關系之作用。”[18](p246)艾思奇也在《非常時的觀念形態》中提出:“觀念形態,也有人寫作‘意識形態’……就是文學、哲學、科學、宗教、道德、法律之類”[19](p294),“能夠代表某一集團的共同意識的形式,就是意識形態,或觀念形態”[19](p297)。在這里,艾思奇指出了一般意識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差別,整體性和階級性則是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征。
由此觀之,對于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概念在中國的傳播而言,1919年可謂是一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節點。正是在這一年,中文語境中的“意識形態”作為對Bewuβtseinsformen的翻譯得以首次出場,而且Ideologie也以“觀念形態”“意識形式”等譯法映入國人眼簾。
(三)過程反思:對“社會意識形式”的誤用與糾偏
中國社會最初的意識形態理論,并非是馬克思主義經典式的。一方面,從日本學者河上肇譯文中“移植”而來的“意識形態”,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意識形態”,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誤認和誤用。另一方面,當時中國學者欠缺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相關研究,因而在闡釋意識形態理論時,極少有人援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意識形態的敘述。與此相反,大部分人并非純粹地對“觀念形態”或“意識形態”進行譯介,而是加入了自身的主觀理解。這種對意識形態概念的最初認知對后來者影響至深。以李大釗為例,其論著中頻繁談及意識形態的問題,然而他對于意識形態的概念界定和內涵闡釋卻含混不清。他將“意識形態”直接譯為“社會意識形式”,這顯然與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概念之間存在較大間距。
從早期意識形態概念的傳播歷程來看,盡管學者對此概念的譯法和表述混雜多樣,但在中國早期的理論界,大多論者更加傾向于以“觀念形態”的樣式引用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并堅定地把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述說為“社會意識形式”。之所以出現這種理解,還需追溯到日語的“誤譯”。這就導致不少人將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視為與“意識形式”“社會意識形式”等概念相等同的概念。這種將意識形態概念理解為一般社會意識形式的做法,實際上是對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擴大化”。事實上,這一現象不足為奇,幾乎所有外來的新理念在導入本土的個體或群體的思維歷程中,都會與本土的個體或群體頭腦中既有的思想相碰撞,進而展現出“抵牾—拒斥—接受—革新—交融”的理解框架,意識形態概念也是如此。
三、意識形態概念與中國實際的深入互嵌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概念的中國化有一個從發生到實踐、從個體到群體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意識形態概念逐漸深嵌于中國實際,體現在話語的實踐陣地、實踐參照和實踐訴求中。
(一)以報刊為載體:“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實踐陣地
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使用最早源自20世紀上半葉的報刊,其原因在于報紙是當時知識和事實傳播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20]。隨著知識分子對“馬克思學說”及“唯物史觀”的高度關切和期待,時人對“意識形態”的使用也陸續見諸報端。從1919年北京《晨報副刊》連載陳溥賢的譯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到同年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再到胡漢民于1919—1920年在《建設》雜志上發表《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等文章,中國學者皆以報刊為載體探討和傳播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并且在這些論述中,“意識形態概念”的內涵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
囿于當時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陳溥賢、李大釗等人對“意識形態”的譯介出現偏差倒也無可厚非。但我們仍要明確,在研究和運用馬克思的理論觀點時,首先要實現從“靜態思維”到“張力思維”的轉變。靜態思維指把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看成“一潭死水”,突出的是一種“非對即錯”的二元對立思維;張力思維所側重的是由“獨一”到“之一”的轉換,彰顯的是一種富有彈性的關系思維。當今我們在面對意識形態理論研究過程中的思辨與實證、人本與理性等關系時都需要張力思維的介入。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研究是一個永續建構的現實歷程,“它只會有運動形態、發展形態,而永遠不會有完成形態、終極形態”[21]。換言之,如果我們對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的理解只停留在馬克思的某些字句,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簡單化、抽象化和刻板化”了[22]。其次,要結合時代背景,充分利用新的傳播手段,宣傳馬克思主義觀點。相對于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被稱為“第五媒體”的互聯網新媒體在當今時代無疑是最高效、最快捷、影響最大的[23]。新媒體的發展形成了虛擬的網絡新社會,使信息傳播樣態發生了翻轉性的變化,不僅融視頻、聲音、文字于一體,而且使微信、微博、貼吧、論壇成為話語傳導的“驛站”,破除了時空間距的限制,拓展了人們認知和理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途徑。這就使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再局限于白紙黑字的論述,而是緊跟當前社會發展的熱點議題,嵌入各個微觀領域。
(二)以域外譯本為抓手: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實踐參照
從20世紀上半葉的整個歷史過程來看,時人總是在搖擺不定中使用“意識形態”一詞。但是,我們依舊可從中找到一個重要共通點——將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置于唯物史觀的話語構境之中進行探討[24]。就實踐的參照系而言,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除了報刊等形式以外,在譯著中也較為普遍。這是因為有些學者本身就是國外相關理論著述的譯介者。譬如,瞿秋白將研究重心集中在蘇俄馬克思主義及第二國際理論家的觀點之上。他先后翻譯過列寧、郭列夫、梅林和普列漢諾夫等人有關唯物史觀的著作,而這些翻譯論著對于同時期學界理解和闡發意識形態概念產生了積極作用。李達也翻譯過郭泰的《唯物史觀解說》、愛森堡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塔爾海瑪的《現代世界觀》。這些著述在中文境域中的陸續出場,無疑深刻影響著當時國人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界定。
對當前我國的翻譯工作而言,一方面,我們要明確地意識到,“基本概念”是譯介工作的“指導線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處理好堅持自我革新與借鑒“他山之石”之間的關系。這里的中樞節點在于,我們不但要跨越“狹隘經驗主義”的陷阱,而且還要鑿穿“亦步亦趨”“水土不服”等壁壘。要想把我國的翻譯工作向前推進,還需探明問題癥結,深耕中國土壤,以進一步打造具有實踐特色、時代特色、中國特色的譯介話語體系。
(三)以本土教材為依托:“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實踐訴求
在國人的漸進式理解中,意識形態概念逐步走向了中國化,且以極具中國特色的話語形式在教材中得到展現。總括地說,其“特色”主要呈現如下:其一,盡管國人已經開創性地實現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與中文語境的“意識形態”的深入嵌套,并在20世紀20年代之后漸趨固定地沿用這一話語表達,但由于最初日本學者河上肇的“誤譯”和“誤用”,直接導致部分學者仍將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與“意識形式”“社會意識形式”等概念歸于同一范疇。其二,在探尋意識形態各樣式之時,國人一方面側重于在文藝層面上展開意識形態的探索,主要以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瞿秋白的《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及其他教材的論述為主;另一方面又偏向于在道德維度內對意識形態進行闡述,包括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李大釗的《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等學科教程。其三,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的唯物史觀話語框架開始逐步轉向“辯證唯物主義”,這是顯性的實踐訴求與思想觀念轉變的結果,其中以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為主要代表。
20世紀上半葉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中從誤譯到正譯、從哲學到文藝與道德、從“歷史唯物主義”到“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轉向,為后來者進行相關學術研究至少提供了兩方面的啟迪。一方面,要著眼于在文本互動的過程中實現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真正解決。雖然在文本詮釋和交互的過程中,通過不懈努力以逐漸縮短原本和譯本之間的距離十分之必要,但要徹底消除這一溝壑極為困難。原因十分簡單,深植于兩種迥異的文化邏輯中的兩種不同語言意味著積淀了數千年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僅憑文本互動無法被徹底消除。然而這里的重點不在于完全消除這一文化差異,而是通過對語言符碼的加工轉換,使人們懂得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解釋和改造客觀世界。在馬克思看來,“思想通過語詞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的問題,變成了從語言降到生活中的問題”[25](p525)。這就意味著,語言作為將理論與實際連接起來的繩索,其生命力量的彰顯不在于文本,而在于對實際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辯證返本與創造開新的統一是促進馬克思主義“觀點”中國化的理論之基。我們在辯證剖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維持其原生態話語表達的同時,也要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及其后繼者的理論創生與自身鮮活的生活實踐有機結合起來,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注入新血。能否有力解決現實問題,是判斷馬克思主義“觀點”中國化程度的根本度量。故而,要實現馬克思主義“觀點”中國化,就需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時偕行,扎根現實生活,把握時代脈搏,依此邏輯準確剖析當前的實際問題,充分彰顯其方法論功能,從而有效指導實際問題的解決。
四、結語
20世紀上半葉,中國語境下的意識形態概念發生于翻譯學研究,但并未對意識形態理論的相關內涵作出規定。對于究竟何謂“意識形態”,學術界意見紛呈,至今未有統一定論。梳理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由西方傳入中國的進程可以全方位揭示意識形態的發生過程,也可以為現今的意識形態研究提供理論基底。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中國化的最大特征即因境而化。意識形態概念與中國實際的深入互嵌體現在話語的實踐陣地、實踐參照和實踐訴求轉向中,表現出“以報刊為載體”“以域外譯本為抓手”“以本土教材為依托”等別具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內在意蘊。在新時代,我們同樣需要在動態理解中捕捉其深刻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