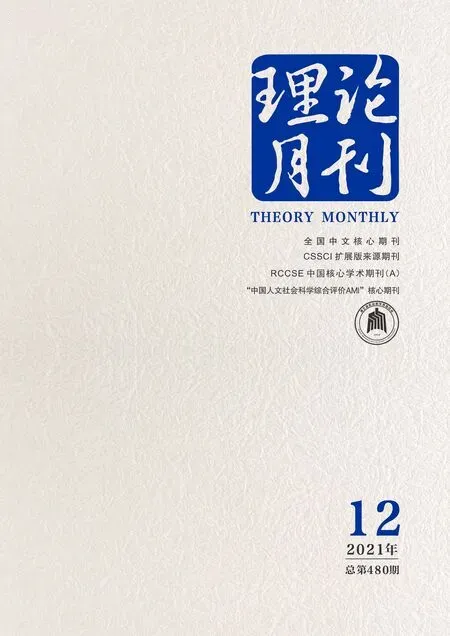政治穩控邏輯與業務調適邏輯:我國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治理行動的博弈與走向
□任昌輝,巢乃鵬
(1.南京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2.深圳大學 傳播學院,廣東 深圳 518060)
發展與秩序歷來是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追求,比之單純的發展問題或秩序問題,對于當代中國社會而言,更為關鍵的是兩者間的協調平衡問題。正如馮仕政所言,“絕大多數社會問題既不單純是由發展不足或片面發展造成的,也不單純是由社會失序或過度維穩造成的,而是由發展與秩序這兩種需求相互抵牾、扦格,甚至尖銳對立造成的”[1](p1)。我國各級政府在網絡空間場域中同樣面臨著上述發展與秩序的權衡抉擇。
互聯網通過技術賦權與組織賦能,加速改變著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方式和權力運作結構,形塑出“個人被激活”的話語傳播格局。規模化的網民群體競相通過互聯網表達觀點、闡述意見、宣泄情緒,網絡空間隨之成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會輿情的放大器,并溢出了地方政府與科層機構的法定職能與能力范圍。網絡輿情是“事件、現實矛盾、社會情緒與網絡交互作用的結果”[2](p10),網絡空間與風險社會的雙向疊加更引發了網絡輿情的持續發酵及其治理風險的線性遞增,政府應對處置不當,極易演變為輿情危機乃至公共危機。當前,網絡輿情監管治理業已成為我國政府網絡執政與社會治理領域難以回避的緊要問題。
在既有研究中,諸多學者普遍將區域性政府視作單一主體予以看待,鮮有研究關注探討地方政府橫向部門間輿情應對的差異性行為。事實上,我國各級政府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呈現出“條塊分割、層級節制”的“碎片化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的權力結構[3](p2),其間內部各職能部門對于網絡輿情治理的認識態度、行動偏好千差萬別,由此導致的治理碎片化使治理風險劇增。因此,近年來國務院頒發年度《政務公開工作要點》,要求政府職能部門主動加強與網信、宣傳等機構的聯系溝通,建立起快速反應、協調聯動機制。此外,地方領導(包括地方黨政主官與各職能部門主要領導)與網絡輿情治理主導機構——網信部門間的治理態度取向同樣不乏差異與矛盾,這點為學界所普遍忽視。筆者在實地調研過程①筆者曾參與東部某省委網信辦主持的某項重點課題,并于2019年、2021年作為調研組成員對該省網絡空間風險防控及網絡輿情治理實踐進行實地調研,調研范圍覆蓋該省全部城市,其中著重調研了7個地級市及其下屬縣(市、區)級網信辦,調研采用深度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搜集到大量來自一線的寶貴資料,初步形成對地方政府網絡輿情綜合治理態勢的全景式認知。中,多次在非正式場合注意到網信(宣傳)系統②目前,我國已基本建立起中央、省、市三級網信管理工作體系,多數縣(區)網信辦雖已掛牌成立,但多數掛靠在黨委宣傳部。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網信系統的組織結構是非常獨特的“雙層次”構造,既是黨委序列(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也屬于政府序列(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體現出黨政協同領導的趨勢,以及中央決策層對互聯網安全與發展的高度重視。管理人員對地方輿情管控思維的吐槽和抱怨現象,同時也觀察到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治理行動各種與時俱進的創新之舉。由此,筆者基于實地調研和相關文獻資料,沿用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概念為參照框架,抽離出地方網絡輿情治理的兩種主要行動邏輯,即以地方政府權力意志為導向的政治穩控邏輯和網信系統專業素質引領下的業務調適邏輯。在中央層面自上而下的制度壓力傳導與網信系統自下而上的科層嵌入推動下,我國地方網絡輿情治理正呈現出從政治穩控邏輯轉向業務調適邏輯的演變趨勢。當然,地方政府的兩種行動邏輯取向并非是單向線性的迭代關系,而是雜糅交互,在不同的治理場域和情境中,兩者不斷競爭博弈也交織共生,呈現出有進有退的復雜態勢,共同形塑出網絡輿情治理的多維面向。
一、政治穩控邏輯下的網絡輿情管理路徑
所謂政治穩控邏輯是指地方政府為追求任期內屬地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而對地方網絡輿情發展態勢施予的強制干預行為。有學者指出,我國地方政府“總體上陷入一種‘不穩定的幻想’中,把所有的矛盾和沖突都視為穩定的對立物,一有風吹草動首先想到的就是動用一切手段消除表現出來的沖突狀態”[4](p107)。在如此偏差性的穩定觀視域下,部分地方政府未能客觀看待網絡輿情,其基于自身利益及政治影響考慮將負面輿情視為一種“他者”化的異己力量。尤其是在壓力型體制和晉升錦標賽[5](p36-50)機制驅動下,某些地方領導對于社會秩序穩定有著近乎偏執的追求,會基于維穩的價值取向而強化輿情管控,借穩定之名回避甚至是壓制公眾的自由表達和合理訴求。當屬地出現負面網絡輿情之際,不少地方政府及領導官員習慣于傳統的危機處置方式,依賴于“用命令、強制的方式封鎖信息,控制事態發展”[6](p68),阻止輿情外溢擴散。正如張佳慧所指出,當前中國政府機構的輿情治理目標較為單一,出發點仍為消除負面影響,維護政府形象和社會穩定[7](p127)。湯景泰持有相同觀點,認為我國地方政府的輿情治理仍以傳統的管控為內核,以應急為重心,以平息為旨歸,體現出濃厚的維穩色彩[8](p116)。概言之,政治社會秩序穩定路徑依賴下的穩控邏輯表征為如下三個層面:
(一)延續傳統與因應現實的對抗路徑
毛澤東曾宣言“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源于革命時期的階級定位(如敵人、反革命)、政治運動[9](p38-67)等斗爭傳統并未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而完全消逝,其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至今仍影響著公共生活實踐,形成了蔚為大觀的“斗爭哲學”,顯現彌散于社會多個領域。黨的十八大以來,為加強和改進宣傳思想和新聞輿論工作,尤其是應對西方意識形態加速滲透的嚴峻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要深入開展網上輿論斗爭”“盡快掌握這個輿論戰場上的主動權”等重要論述,作出了“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這一重要判斷。筆者在調研過程中也發現“輿論斗爭”等戰爭隱喻詞匯已成為地方網絡執政和輿情治理的高頻政策話語。毋庸諱言,當前網絡空間輿論斗爭形勢嚴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占據著網絡空間的“話語霸權”,正加緊對我國實施意識形態滲透,其通過主動介入突發網絡輿情事件等方式試圖操控我國的輿論指向,因此開展輿論斗爭顯得尤為緊迫。
與此同時,輿論斗爭思維又有意無意地被某些地方政府所曲解與擴大,部分政府機構片面性地視負面網絡輿情為異己的挑戰性力量,視民眾為客體化的管理對象。網絡空間日趨升級的意識形態斗爭更加劇了地方政府的應激性反應,也為其網絡管制行為提供了某種“正當性”理由。因此,當地方政府遭遇負面輿情沖擊時,某些領導干部習慣性地將正常的交鋒爭論和質疑批評上綱上線為對抗政府,偏激地將屬于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歸類為有西方敵對勢力滲透下的對抗性敵我矛盾,把不同觀點、不同聲音想象為“洪水猛獸”,斥之為“別有用心”“不明真相”“污蔑政府”“攻擊體制”。如2020年“4·18”河南原陽兒童被埋事件發生后,原陽政府視媒體正常的輿論監督報道為挑戰政府權威,街道辦阻撓記者采訪,發動地方工作人員進行新聞跟帖評論,干擾網絡輿論,并“創造性”地發明了“涉媒體從業人員”等說法,地方政府層層加碼行為誘發的次生輿情超過原生輿情事件,造成持久的網絡集體圍觀,成為輿論場中的奇觀。
(二)壓力型體制下的擺平路徑
“壓力型體制”由榮敬本等學者提出,是指地方黨政組織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和其他目標,采取任務數量化分解和物質化獎懲相結合的一套管理手段和方式[10](p4-11)。壓力型體制深刻地揭示出地方政府是如何被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所驅動運行的。在社會治理領域,屬地政治社會秩序穩定成為地方治理者的首要目標追求,守土有責在多方壓力擠迫下往往被異化為“不出事”為上。壓力型體制的嵌入形塑與強化了地方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擺平路徑,正所謂“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無事就是本事,妥協就是和諧”,地方領導干部只求在其任期內不出現威脅政治社會穩定大局的危機事件即已達標(達到“不被淘汰”[11](p124)的考核下限)。
地方政府慣性的擺平思維同樣延伸到網絡輿情治理過程中,以盡可能地規避屬地輿情的發酵失控風險。具體而言,一是體現在媒介公關層面。某些地方政府試圖以政治邏輯規制乃至同化或驅逐媒介專業主義邏輯,積極謀求與各類媒體、網絡大V形成良好的合作關系,尤其是注重對屬地外重點媒體的公關,以建立利益共同體為手段達到降低屬地負面輿情聲量的目的。如筆者調研期間發現,某市級網信辦與某互聯網媒體達成戰略合作關系,當地方爆出負面輿情事件時,通過屏蔽過濾、降低推送等方式為地方輿情“降溫”。二是體現為輿情責任的切割。為避免輿情危機引發連帶問責和危及政府形象,部分地方政府在事件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際,即急于蓋棺定論,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匆匆予以定性,從重從快處理相關責任人,以求得輿情的快速平息冷卻。但此類責任轉移切割的應急公關未必能取得正面效果,反而可能引發公眾對政府推諉避責的不滿和負面聯想,也與“速報事實,慎報原因”等輿情處置基本原則相違背。此外,筆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運用科層吸納[12](p1475-1508)、人情關系壓力[13](p121-128)、物質讓步(“花錢買平安”)[14](p5-25)等正式與非正式手段相結合的方式化解社會沖突,也成了某些地方政府“擺平”輿情事件的經常性策略。
(三)一元化組織下的全能路徑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傳統“皇權不下縣,縣下行自治”的“雙軌政治”[15](p45-53)模式演變為一元化組織模式,黨政權力無限延伸到社會各個領域。組織一元化意味著,正式制度覆蓋一切,官僚之軌單獨行使。延伸費孝通先生的比喻來說,官僚之軌不僅修到了家門口,而且一直修到了臥室(人口政策)和廚房(計劃經濟)[16](p24)。鄒讜對此創造了“全能主義”(Totalism)的概念,用以形容當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意指“政治權力可以侵入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個人生活的諸多方面,在原則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的限制;在實際上(有別于原則上)國家侵入社會領域和個人生活的程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強或弱”[17](p223)。改革開放后,全能主義結構模式日漸松弛,國家在社會和經濟層面逐步放權以激發社會發展活力,但其管控慣性依然強大。正如李永剛指出,當代中國呈現出一種“強國家、弱社會”權力格局,這一格局對權力效用高度迷戀,對民間自治普遍懷疑。它既展示了權力主體“一定能管好”的自信,也呈現出“不管一定亂”的自卑,兩者都能推導出一種監管邏輯:“既然能管好,當然要管;既然不管要亂,還是只能管。”[18](p144)在“無限政府,無限責任”的壓力情境下,愈發高漲的輿情危機引發地方官員對于秩序失控與上級問責的集體性焦慮。尤其當網絡輿情危機威脅到政權安全或社會穩定時,基于全能主義的管控慣性,某些地方政府偏好行使專斷權力,直接訴諸權威意志強力管束那些輿情亂象及“有害、不良”信息,但往往又過猶不及,不惜動用公檢法等國家力量對合法輿情表達進行壓制,造成“偏刑主義”盛行(簡單粗暴運用刑事手段打擊網民輿論監督行為)[19](p17)和“壞事不出門”的不正常現象[20](p69)。
二、政治穩控邏輯偏好的歸因及引發的整體性困境
(一)政治穩控邏輯偏好的歸因
追根溯源,當前某些地方政府偏好穩控管理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領導決斷性權力的賦予及地方政府基于“經濟人”角色利弊權衡后的“理性”選擇。
首先,地方政府穩控管理邏輯偏好源于地方領導擁有屬地專斷性權力。我國封建王朝時期素有“一人政府”[21](p11)的說法,現行的政治權力格局雖已發生重大變遷,但一元化組織、全能型政府帶來的依然是“一把手”的絕對性權力。推而廣之,地方領導尤其是黨委書記擁有對屬地和行業管理的絕對專制權,所謂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按照邁克爾·曼的界定,“是指針對市民社會的國家個別權力,它源自國家精英的一系列運作,而這些運作不需要與市民社會群體作例行公事式的協商”[22](p78-79)。因此,地方領導群體關于網絡輿情治理的認知意圖及模式策略必然對地方輿論生態產生深遠影響,某種程度上直接決定著地方輿情治理圖景。當地方領導群體尊重網絡輿情所呈現的民情民意及演變規律,秉持“術業有專攻”的理念,地方網信(宣傳)系統即擁有較大的自主處置權,繼而順應網絡輿情發展規律與演變趨勢加以統籌協調與科學應對;當地方政府“官本位”傾向嚴重,偏好以主官意志自我決斷代替專業處置,封堵打壓急于“滅火”,以權力壓制事態發展,則易引發輿情治理的衍生風險,導致輿情危機陷入惡性循環。典型如2019年無錫高架橋坍塌事件,事發后地方政府阻撓記者采訪、發表網評“懟”網民等行為背后或多或少都摻雜著領導權力意志干預的色彩,體現出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穩控“慣習”。
其次,政治穩控管理邏輯偏好也源于上級政府的激勵—問責強度及地方政府的利弊權衡后的“理性”抉擇。地方政府已經形成了關于政績考核的共識,“經濟發展工作相當于赫茲伯格‘雙因素理論’中的激勵因素,因而做好經濟發展工作可以使中央政府滿意自己的工作;而社會秩序工作相當于保健因素,因而維護好社會穩定只能消除中央政府對自己的不滿意,不能增加滿意度”[23](p151)。在此種共識下,地方政府在社會秩序維持層面普遍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避責態度。對于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治理而言,其主要職責在于保障網絡空間安全有序,至于網絡空間能否煥發生機活力,網絡輿情能否提供民意鏡鑒,“與網民的政治素養、政治效能感、政治參與等諸多因素緊密相關,這既非政府的分內職責(不納入績效考評加分,筆者注),亦不是力所能及之事,且在短期內難以見效”[24](p24)。因此,地方政府基于“理性經濟人”角色進行利弊權衡和價值排序,輿情治理更多遵循“不出事”的底線邏輯。所謂“不出事”,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什么事情都不發生,而是相對于“出大事”而言,是指不能出現引起媒體和上級政府關注的事情,不能出現影響地方政府政績的事情,不能出現超出地方政府控制范圍的事情[25](p29-34)。究其實質,“不出事”體現出的重結果輕過程、重眼前輕長遠的價值傾向是地方官員“穩定壓倒一切”心態的自然反應。當然,對于網絡輿情的應對處置,地方政府及領導干部的行動取向亦不可一概而論,多數情況視輿情的性質、類型、影響分類分級應對,但普遍呈現出選擇性應對的情形,如對某些關涉地方經濟發展的輿情選擇性忽視(冷處理),對涉及政治意識形態類的輿情選擇性限制(嚴打管控)。
(二)政治穩控邏輯偏好引發的整體性困境
任何國家治理都必須解決兩個基本問題,即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問題[26](p129)。由此觀之,地方政府傳統的基于領導權力意志導向下的政治穩控模式必然會導致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陷入雙重困境。這種困境并非是局部性的,極易衍生出整體性危機,表現為輿情治理機制僵化及規制效率低下,政府與民眾間彌漫著不信任與不認同態勢,由此造成國家與社會間關系的持續緊張,帶來網絡空間輿情生態的惡性循環。具體而論,上述整體性困境表現為治理效力不足、社會矛盾激化、超越合理限度和政府權威消解四個方面。
1.治理效力不足的風險。在傳統媒體時代,地方政府通過“新聞、舊聞、不聞”等方式,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策略,將社會危機化解限定在地方層面。但隨著網絡社會的崛起,卡斯特所言的“流動空間”(Spacesof flow)逐漸取代傳統的基于共同經驗載體的“地方空間”(Spacesof place)[27](p518-524),構建了人人可以置身其中的網絡輿論場,網絡的無界化、彌散化、去中心傳播特質導致網絡輿情能輕易突破過往屬地地理邊界和參與限制,快速擴散蔓延至全國乃至全球。同時,在網絡輿情治理實踐中,不少地方政府仍沿襲著“刺激—反應”式的消極防范路徑,進而基于維穩偏好使用封堵、禁言、過濾敏感詞等技術控制方式干預輿情信息自由流動,網民則針鋒相對,通過換用同義詞、諧音字等靈活變通策略聲東擊西、暗渡陳倉,輕而易舉地突破政府設置的重重防線,帶來“對敏感詞進行解構的過程也是加速對敏感詞及其事件的擴散過程”[28](p108)的逆火效應。如此,政府輿情監管的效果勢必大打折扣。此外,地方政府傳統的單向穩控模式愈發不能適應網絡常態,諸多事實早已證明,自上而下權威支配向度下的網絡輿情規管往往是僵化且低效的。政府一旦壟斷網絡治理權力,結果“只會使自身在網絡輿論引導工作中陷入單兵作戰的窘境”[29](p51),同時也將面臨對網絡輿情治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質疑和追問,陷入“越維越不穩”的尷尬境地。
2.加速激化社會矛盾。網絡輿情作為現實社會矛盾問題在網絡空間的映射,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實施信息管控與動員主流媒體引導輿論并不能解決社會的深層結構性問題,只是干預和掩蓋了社會矛盾。不少地方領導偏頗地認為輿情來源于“網上”,追求暫時平穩或表面和諧的“以平息事態為標志”的形式主義績效,在短期內可能抑制了輿情發酵。但在本質層面,揚湯止沸式的“輿情平穩觀”并不能從根本上化解社會危機,亦不能消除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政治穩控模式“很可能使網絡輿情治理變成服務于個別地方、個別部門或者個人私利的工具,對黨和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造成長期的損害”[30](p188)。更為嚴重的是,網絡輿情穩控管理模式破壞了網絡作為“社會安全閥”的情緒疏解功能,加速激化了社會矛盾,引發民眾通過線上線下動員,以“問題化”甚或“政治化”等“鬧大”策略訴諸集體抗爭,亦使得民眾與地方政府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造成社會問題淤積與社會信任撕裂,醞釀出更大的公共危機。如2008年貴州“6·28”甕安事件,地方政府慣性的敵對思維、回應滯后、信息不公開導致民怨沸騰、謠言四起,加之社會矛盾長期積累,最終導致震驚中外的打砸搶惡性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3.超越規制的必要限度。對于網絡輿情發酵過程中暴露出的網絡話語暴力泛濫、網絡推手惡意炒作、商業資本操縱輿情、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等現象,強制性的干涉管控必不可少,但也應注意管控的合理限度所在。不容忽視的是,某些地方政府時常超越必要的規制限度,亦不能平衡網絡空間發展秩序與生機活力的辯證關系,對屬地負面網絡輿情簡單粗暴地使用刪帖屏蔽、封鎖消息、刑事懲處等方式阻撓媒體的監督報道,干涉網民的自由表達,阻礙輿論公共空間的形成。這種以國家強制力為支撐的穩控管理模式可能引致“部分網民對網絡表達和網絡政治參與的疑慮,使網民群體進行網絡表達時自我審查或訥于發聲”[31](p141),造成桑斯坦所謂的輿論場“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又或者民意“彈簧”因不堪其重而出現報復性反彈,刺激了輿情的擴大“再生產”。如2018年廣東醫生譚秦東因發帖《中國神酒“鴻茅藥酒”,來自天堂的毒藥》被內蒙古涼城警方跨省抓捕,引爆輿論強烈聚焦。地方政府“民事糾紛刑事化”的處置方式飽受輿論質疑,引發公眾對涼城政商勾結、地方保護主義的無限遐想,形成了極為強烈的負面輿論漩渦。
4.消解政府權威與公信力。李連江曾提出當代中國公眾政治信任存在著對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程度的“差序格局”,民眾對于層級越高的政府信任程度越高,而對于層級越低的則信任程度越低[32](p228-258)。后續諸多調查也證實了中國公眾普遍存在著政府認同結構上的二元化傾向,如“切割性評價”[33](p9),“央強地弱的信任格局”[34](p49)等,人們對中央作為“抽象政府”的信任度遠高于作為地方“具體政府”的信任度。當前,政府層級間的政治信任差序格局和二元傾向同樣顯現在網絡輿情事件的社會態度中。更為嚴峻的現實是,地方政府重經濟發展輕民生保障的執政導向以及輿論場中剛性管控措施的頻繁使用因輿情信息流通的可見性而成為削弱地方政府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屏蔽與刪帖之類的技術措施以及與此相類似的對于言論與表達自由的過度干預,很容易引起人們對輿論宣傳的不信任,對強勢群體的不信任,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35](p86),繼而導致公眾對政府公開回應的不信任、不認同,甚至是對抗性解讀。正如調研過程中有網信部門管理人員表示,現在相當多的情形下,政府輿情回應和事件處置事實上并無明顯的不妥之處,卻總能引起網民的戲謔化甚至是對抗性解讀,此種現象可歸因為政府權威形象和公信力被削弱后的衍生后果。
三、業務調適邏輯下的網絡輿情治理路徑
不少學者通過田野觀察表明,“由于互動對象的差異和基層工作環境的復雜性,不同于‘治吏’的地方長官強有力的創新行為,作為‘治民’的基層干部表現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工作狀態,以及象征性服從、策略性執行的行為模式”[36](p28)。筆者在田野調研過程中觀察到的卻是有所分殊的現實,在日常治理實踐中,某些地方政府偏好管制的路徑依賴效應依然凸顯,而作為治民的網信系統管理人員更具創新意識和行為①當然上述情形也不可一概而論,實地調研發現當前地方網信系統編制內(包括行政編制與事業編制)人員和編制外人員(市場代理)的薪資待遇、角色地位及工作職責相差甚大,編制外人員私下和筆者談及工作待遇及發展前景時怨言頗多,輿情治理工作過程中的角色認知、工作投入狀況等方面也因此差異頗大,但此類內部人員的行動取向差異不在本文的考量范圍之內。,其對輿情治理的能力素養、策略運用明顯優于地方領導干部,由此引發地方政府剛性的政治穩控邏輯與柔性的業務調適邏輯的間歇性博弈。
所謂業務調適邏輯是指地方政府在網信系統專業組織的統籌協調下,遵循網絡空間固有規律和專業業務運作流程所采取的輿情治理行動。從發展變遷視角予以審視,我國地方網絡輿情治理行動正經歷著從傳統的政治穩控邏輯轉向業務調適邏輯,其轉型動因主要指向中央層面自上而下的制度壓力傳導(治理的道德合法性)與網信系統自下而上的科層嵌入推動(治理的成效合理性),加之社會層面多元能動主體的呼吁倒逼作用。在專門的互聯網管理機構——互聯網信息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網信辦”)設置前,我國網絡空間及輿情治理呈現出“九龍治水”的格局,“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權責不一”的組織架構設計導致網絡整體規制乏力。為破解這一尷尬局面,2011年5月,國家網信辦成立,成為互聯網管理的主導部門,并逐步將內容管理、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等網絡核心業務予以整合,標志著互聯網管理向專門化、整體性的方向邁進。2014年2月,黨和國家層面機構重組,成立最高規格的互聯網領導機構——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2018年改為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委員會),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總理擔任副組長,同時設立小組辦公室(中央網信辦,正部級實體)作為辦事機構,意味著網絡治理權力與中央權力機構之間建立起直接聯系,“開啟了以國家意志對網絡空間進行統一規劃和系統治理的新時代”[37](p18)。同年,國務院重組國家網信辦,并與中央網信辦合署辦公,形成了黨政協同領導的組織體系。按照“上下對口”的“職責同構”原則[38](p101),省市兩級網信辦隨后也成為獨立于宣傳系統的互聯網專門性監管機構,地方網信領導小組(2018年后改組為網信委)同樣由地方“一把手”擔任領導小組組長。
網信辦作為網絡空間治理的統籌協調組織,在輿情治理行動中扮演著管理主體的角色。事實也證明了治理權力升級所帶來的正向效應,當前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治理出現了若干積極的變化,其治理認知和應對能力也隨之提升,體現出地方政府的行政理性和調適能力。所謂調適(Adaption),是指通過主動調整使之達到適應的狀態。與早期學界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缺乏調適性特征且無法調適的觀點不同,如今政治學者傾向于認為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政府逐漸顯示出調適的特性,并創建成為“對社會各領域、各層次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應性的政治系統”[39](p5),“學習型政權所具有的高度觀察力、判斷力、靈活性、應變性和機動性,使其能在復雜多變的內外環境中,以充足的彈性和適當的剛性,保持政權系統的韌性”[40](p14)。這種調適能力與實踐同樣體現在網絡輿情治理領域,表征為治理組織重構(各級網信委的成立)、治理權力升級(網信系統的獨立設置)、治理工具優化(網絡問政等引領型工具和政企發包等混合型工具的引入使用)[41](p40-51)、治理關系調整(網絡意見領袖的吸納統戰、互聯網企業黨建的政治嵌入)等層面,并由此初步實現了從被動滅火向主動出擊,由孤軍奮戰壟斷管理到局部有限合作治理的漸進調整。在地方政府層面,輿情治理業務調適邏輯體現在主體層面的多方聯合路徑、技術層面的技術加持路徑以及行動層面的學習調適路徑三個方面。
(一)多方聯合路徑
當前,我國逐步形成“公權力主導,多主體協調”的治網格局,具體到網絡輿情治理層面,政府治理主體呈現出以網信(宣傳)部門統籌協調為主,公安網警和通信機構為輔,涉情部門和其他組織(個體)相機介入的組織格局。囿于地方市縣網信系統執法權受限,可動用的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42](p241-247)亦相對稀缺,導致其處于一種權責不對等,有心無力頗為“尷尬”的境地。加之輿情天然的敏感特質,多數部門往往避之不及、推卸責任,科層制慣有的職能分工和權責設定導致政府內部溝通協同機制并不順暢。因此,為提升輿情治理的政治勢能,目前地方網信部門強化“借力權威”機制(網信委主任由地方黨委書記擔任)和“部門捆綁”機制[43](p136-147),以網信委領導小組的名義傳導政治壓力,通過吸納公安、教育等重點部門成為網信委成員單位,構建起多部門一體的網信工作格局;同時,注重發揮政治組織的規模優勢,網信系統已牽頭組建起層級性、體系化的網評網宣隊伍、網絡發言人隊伍、網絡不良信息舉報隊伍,希冀以規模對規模,多元對多元,形成“大網信”“大宣傳”的統一戰線,甚至有地方政府提出打造“全黨管網”的全民模式,以占據主流輿論陣地,對沖制衡負面輿情。對于網信部門而言,其治理屬地輿情主要肩負兩方面職責:一是統籌協調涉情部門回應引導,以求盡快平息事態;二是對不良輿情、違規輿情(如網絡謠言、網絡暴力)及時管控。
首先,面向屬地網絡輿情事件的應急管理,網信部門扮演著統籌協調的角色,同時也牽涉到多個職能部門,如涉情部門應承擔具體調查及公開回應的雙重責任,公安部門則肩負著監管執法的責任。為確保屬地網絡輿情的及時高效處置,調研發現地方網信系統充分借力領導權威,以權力高位協調的方式巧妙地將“條”的任務轉化為“塊”的任務,進而推動構建聯席例會機制、信息溝通對接機制、應急處理機制、聯合執法機制以打破科層架構可能帶來的治理瓶頸,目前大致形成了多部門齊抓共管、協同推進的網絡治理及輿情應對的局面。其次,對于違規網絡輿情內容的處置,市縣網信部門囿于執法機構設置、程序規則、人員力量等層面均不完善,缺乏輿情信息內容治理的直接抓手,對地方網民、自媒體大V及網絡平臺構不成有效威懾。在這種被動受限的情形下,地方網信部門主動運用“借力權威”機制和借助國家層面自上而下的專項整治行動(如“清朗”“凈網”行動)等契機,聯合公安網警、通管機構、市場監管等多個部門,開展聯合執法,以營造屬地風清氣正的網絡輿論氛圍。
在政社合作層面,多數地方網信部門摒棄傳統單向的管制思維,開始摸索踐行制定規則、搭建平臺和共營生態的“守夜人”角色[44](p9-12),通過行政吸納、政治嵌入、情感動員等制度安排激發屬地網絡意見領袖、網絡社會組織、互聯網企業及網民群體在網絡治理中的正向作用,強化了對屬地網絡空間及各類主體的覆蓋面和可及性。
(二)技術加持路徑
有研究者認為,當前輿情治理既有的“回應治理路徑”和“法治治理路徑”是一種基于路徑依賴的被動式治理方式,往往是在公共事件發生并引起較大的網絡輿情后,相關部門才介入處理,存在明顯的滯后性,容易陷入治理失靈的境地[45](p65-73)。為提升輿情治理的預見性和有效性,運用建基于“代碼”規制[46](p136)的信息化技術,以強化輿情監測及阻斷不良信息傳播擴散逐漸成為地方治理者的共識。在實踐層面,網絡輿情治理的“監測預警—研判報送—應急處置—監督考核”等系列流程均需要技術支撐,輿情治理的首要環節——及時發現、動態預警更是依賴于技術驅動,唯其如此才能有助于地方政府掌握輿情應對主動權,實現輿情風險的預防性治理。
當前地方政府網絡輿情監測預警雖倚重于網信系統專業人員的深度研判,但人工研判偏向于輿情信息搜集后的定性分析,而基于規模輿情的定量、定向、定類搜集研判亟須大數據采集、智能過濾及自動聚類等新興技術支撐,先進的網絡輿情監測系統不可或缺。因此,各地政府紛紛向輿情監測服務供應商(代表性的有拓爾思、人民網等)購買服務或定制需求,開發出“敏感話題聚類與識別、熱點話題分析、網絡輿情警報、生成輿情統計報告等功能”[47](p70),實現對屬地負面輿情和敏感信息的全面監控與精準研判。筆者在調研過程中甚至發現,某縣域網信辦副主任為提升輿情監測效率,曾自行研發輿情監測軟件,以實現對屬地輿情的有效監管。同時,網絡輿情監測公司基于經濟效益考量亦積極謀求推動各級政府加大專項技術投入,因而普遍以先期免費使用等方式培養網信系統管理人員對輿情監測軟件的使用依賴。
此外,調研發現,隨著網信系統的獨立建制,各地政府加快升級網信技術體系,目前已初步打造出統籌協調、上下聯動的一體化“管網治網技術體系”,涵蓋事前監測預警的輿情監測分析系統,事中應急調控的網絡傳播效果監測系統與網絡評論引導系統,以及事后追溯懲處的網絡聯合執法系統,旨在助力地方涉情機構實現輿情快速發現、引導調控和穩妥處置。同時,輿情治理中的刪帖禁言、限流封堵、(微博)話題解散等信息干預措施,用于輿情治理輔助決策的案例庫、數據庫建設以及對于少數關鍵主體的精準監管同樣離不開技術的支撐加持。
(三)學習調適路徑
所謂政府學習,是指政府組織不斷解讀環境,進行威脅和機會分析,在信息處理過程中,提高自身能力并不斷調適自我,在與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實現組織發展和環境改造雙重目的的活動和過程[48](p18-19)。我國政府始終重視構建學習型政權,擅長探索各種類型的學習模式,王紹光認為,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已堪稱分權式政策或制度創新的典范[49](p114),體現出中國政權基于實踐學習的強大適應能力。
在網絡輿情治理領域,地方政府的快速學習與模仿能力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筆者在實地調研過程中多次發現地方網信系統的學習特質。尤其是市縣網信部門并沒有被賦予實施政策的完整資質,也沒有機制順暢的執法權(落地執法需要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的支持),尚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摸索實踐階段。在這種情境下,為達成維持屬地網絡輿情“平安”的目標要求(有時是“一票否決”的政治任務),地方政府選擇主動出擊、模仿學習先進經驗,希冀實現二次創新,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有著成功經驗的政府單位絕對不是僅僅被動地移植政策原型,而是將其作為知識點進行選擇性的吸收與改造[50](p11-23)。與政府學習行為相伴隨的是調適行為,學習與調適構成一體兩面的政府行動,形成了學習中不斷調適、調適中不斷學習的動態循環。地方政府網絡輿情調適治理中最為典型的例證即是縣級網信部門約談制度的建立。2015年,國家網信辦發布《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約談工作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授權地方網信辦建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約談制度,但行政約談權力僅授權至省市級層面,即縣級政府并未被授予明確的政策執行資質。實地調研則發現約談已成為縣級網信部門的常態治理手段,并在《規定》定性的“事件性約談”(約談的觸發條件是互聯網信息服務單位違反文件規定的9種情形,如未及時處置違法信息)外亦開拓出定期的常規性約談(重在事前的提醒預防),約談觸發條件與約談實踐方式也更為靈活,究其實質是對頂層設計的學習模仿與本土調適,是典型的學習模仿與迭代創新過程,體現出地方政府彈性變通的治理特質。此外,學習調適路徑也體現在地方網絡輿情治理的多個環節,如網絡問政(輿情吸納“再中心化”)、網絡舉報(圈群輿情線索的發現)等舉措中。
四、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治理兩種邏輯的博弈與走向
探討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治理邏輯的博弈與走向不能唯趨勢論,本文兼顧宏觀結構和中觀行動兩個維度,從央地分權以及治理有效性與合法性的視角予以分析,以期更為深入地闡明兩種邏輯的發展趨向。
(一)央地分權
論及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治理行動邏輯的博弈與走向需要將其置于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整體視野中加以關照。關于中國國家治理研究,一個重要領域即是探討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為便于把握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基本特征,學界普遍認同如下假設,中央政府掌握著調整央地分權程度的主導權,并使之調整到有助于同時實現兩個目標:一是保持中央政府的政權穩定,或者說降低治理風險;二是在保持政權穩定的前提下,提升國家的治理效率和經濟發展水平[51](p52-69)。
周雪光在論述中國國家治理的特征時,認為在央地關系上不可能形成穩定的結構,表現為“集權—分權”的周期性調整和循環性波動,由此中央政府在提高治理效率和維護政權穩定上存在著根本性的沖突。他將此種沖突概括為“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具體指涉中央統轄權與地方治理權的緊張和不兼容:中央集權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強化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卻削弱了地方政府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最終導致權威體制的有效治理能力下降;反之,如果增進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又易于引發地方政府的各行其是和偏離失控,對中央政府的一統體制構成威脅[52](p12-29)。
在網絡輿情治理領域,“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再度凸顯,突出體現在作為主導者的中央政府與作為執行方的地方政府間差異化的治理思維和行動偏好。事實上,對中央—地方政府不同行動偏好的把握,是厘清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治理邏輯的必要性前提。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囿于網絡輿情的“雙刃劍”性質,網絡輿情治理被置于一種交織著發展邏輯與控制邏輯的監管模式之下,由此形成了“開發型權威主義”[53](p160-170)的政策特征。延續威權主義的控制偏好,控制邏輯某種程度上優先于發展邏輯,同時中央也在努力尋求兼顧兩者間的平衡,即控制社會風險與激發網絡活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一樣,既要提倡自由,也要遵守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54]質言之,國家重視網絡輿情正面效用的前提是將輿情沖突和危機控制在既定政治秩序范圍內,而不能對現有政權和社會穩定造成嚴峻挑戰,在此基礎上希冀發揮輿情正面功效以監督規范地方執政行為,這也呼應了有學者提出的“容忍批評政府卻拒絕運動(禁止群體煽動)”觀點[55](p326-343)。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則更為依賴控制邏輯遠甚于發展邏輯,尤其是地方領導干部基于仕途平安的利弊權衡,更為重視的是任期制下的社會秩序穩定。但地方政府傳統的慣性管制路徑依賴實質上偏離了中央的施政意圖,甚至對中央政府的有效統治構成了威脅。因此,為確保政權穩定,中央政府面對網絡空間新型風險,實行增量改革以重構網信系統,在深化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發展布局的同時,也在試圖糾偏地方政府慣性的穩控管理模式。從上述意義而言,中央層面縱向的政治壓力傳導是推動地方政府網絡輿情規制從剛性管控轉向業務調適的重要驅動力。
(二)治理的有效性與合法性
中國獨特的壓力型體制與晉升錦標賽模式制度設計,不斷驅使地方政府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在網絡輿情治理領域,治理有效性突出體現為地方輿情治理從剛性的政治穩控邏輯邁向柔性的業務調適邏輯。在實地調研過程中筆者發現,當前地方政府已普遍出臺程序化、流程化的輿情應對處置辦法,制定出網絡輿情危機應對預案,同時主動學習并著力創新行動策略,有效地提升了對屬地網絡輿情的回應管控能力。另外,在中國政治語境下,地方主要領導擁有對統轄區域的決斷性權力,以權力意志為主導的政治穩控邏輯隨時可能凌駕于以專業經驗為指引的業務調適邏輯,尤其是當地方遭遇突發危機或負面事件之際,輿情處置的常規機制往往被擱置,代之以領導權力決斷而非依循專業經驗處置。因而地方政府輿情治理轉向并非是單向線性的發展過程,而是存在著諸多變數,兩種治理邏輯在不斷博弈互嵌的同時也將長時間共存。
無可否認,權威意志引領下的穩控管理模式已然陷入整體性困境,難以為繼,網信系統的獨立設置則為地方輿情治理帶來新的積極變化。伴隨著網信系統作為專業性統籌協調組織的制度性嵌入,當前地方政府網絡輿情格局也生成了新的治理秩序。可觀察到的事實是,當前地方政府已不再過度依賴傳統的“封、刪、堵、捂”等剛性管制方式,而是主動借鑒社會公共治理領域的成功經驗,推行彈性行政和調適治理,通過媒介技術的主動采納和各方資源的巧妙調配,并配合上下聯合、內控外引、軟硬兼施、疏堵并舉等彈性化手段的綜合運用,以期多措并舉策略性地擺平網絡輿情,控制事態發展,展現出地方政府在強硬管控之外權宜調適的另一面向。
在網絡輿情調控治理過程中,地方政府始終面臨著激發網絡活力與保持網絡秩序的兩難抉擇,相較于“一管就死”,地方政府更為懼怕的是“一放就亂”,擔憂因過度自由表達帶來社會激進失控風險。在網絡輿情風險日益擴張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臨著日益強化的行政問責、“一票否決”等考核壓力,基于仕途平安的利弊權衡,地方政府更為偏愛“擺平術”“搞定法”等問題解決方式。因此,地方輿情治理業務調適邏輯是在風險總體可控條件下的一種積極嘗試,既能提升網絡輿情治理成效,也部分消解了民眾的不滿情緒,甚至能轉嫁限制言論、干預輿論可能引發的道德風險(由互聯網平臺負責網絡內容審查的代理監管機制)。這也是“中央治官、地方治民”上下分治機制[56](p1-41)在政府輿情治理領域的延續,通過屬地負責、政企發包、行政吸納等方式分散控制和化解來自社會與民眾的統治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網絡輿情治理的業務調適邏輯并非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優選擇,其實踐底色尚未擺脫傳統維穩主義路徑,某種程度上依然是政府慣性“擺平”策略的變通延續。雖然當前地方輿情治理能力與成效穩步提升,但輿情危機與治理風險卻呈愈演愈烈之勢,意味著網信部門嵌入推動下的主體、技術和行動等層面的優化更多是“術”的創新,某種程度上只是達到輿情暫時平息的“形式績效”,而非矛盾化解、信任重構的“實質績效”,這也揭示了“通過創造有效性來積累合法性的國家秩序建設路徑”[57](p46)可能行之不通。從根本上講,網絡輿情善治呼喚“道”的變革,亟需地方政府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思維理念的革新,適配制度的供給以及權力行使的審慎。
最后,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視角予以關照,“公共權力在網絡輿情治理中的運用不能僅遵循工具理性,以實效為終極旨向;還需要關注價值理性,注重公共權力運用的合法性”[58](p139)。當前地方政府業務調適治理模式的內核呈現為工具理性主導、價值理性衰微的態勢,網絡輿情作為民意呈現、溝通協商與情緒疏導等功能并未得到應有重視。這也表明某些地方網絡輿情治理業務調適模式雖然在治理有效性層面取得相當程度的突破,但在治理合法性層面并未贏得社會認同。正如殷輅所言,“權力的行使出自當然之理(法)而不是特殊意志,秩序的維護是治理主體的共同責任”[59](p11)。因此,基于價值理性驅動下的公共協商多元共治格局[60](p21-28)和“網民整合”模式[61](p21-26)理應成為我國地方政府輿情治理的更高目標,由此實現維權與維穩的法治合一,保障自由與適度干預的辯證統一。當然這種更高層次的現代化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地方政府主動放權、更新思維的同時,亦離不開公共精神的塑造以及政社之間良性互動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