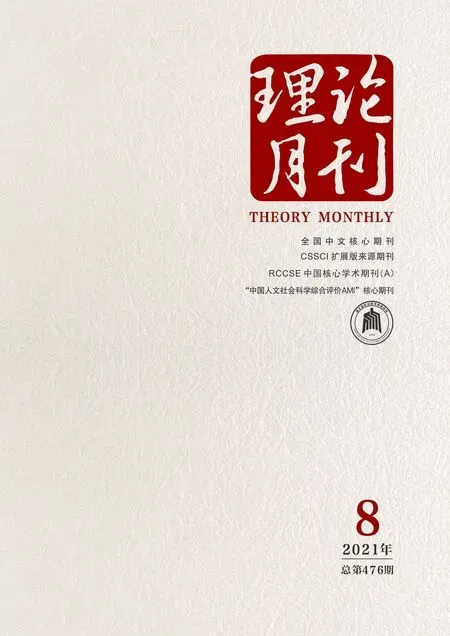馬克思恩格斯生產力觀的雙重邏輯線索及其內在關聯
□張 鷟,李桂花
(吉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生產力概念是歷史唯物主義最根本的理論基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產力既是一個貫穿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概念,又是一個貫穿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因而他們的生產力觀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生產力觀進行了一定的研究,這些研究大多是富有建設性的。但由于受到蘇聯教科書體系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的影響,這些研究大都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產力觀主要體現在科技生產力方面,并認為這種生產力是一種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質性力量,因而將他們的生產力觀冠以只見科技、不見自然的“經濟決定論”“生產力主義”等稱謂。事實上,這是對他們生產力觀的嚴重誤解。通過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相關文本的梳理,我們發現,他們的生產力觀也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綠色意蘊。基于此,本文認為貫穿馬克思和恩格斯生產力觀的內在邏輯線索主要有兩條,即作為顯性邏輯線索的科技生產力觀與作為隱性邏輯線索的生態生產力觀。
一、顯性內在邏輯線索:科技生產力觀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考察過程中,深刻認識到科學技術的生產力促動效應,形成了系統的科技生產力觀,成為他們生產力觀最為突出的方面,構成了他們生產力觀的顯性邏輯線索。該線索主要體現在科學技術與生產的基本要素、資本主義批判、共產主義之間的內在關系上。
首先,從科學技術與生產的基本要素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全面滲透于生產的基本要素之中。其一,就勞動者要素而言,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規律和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勞動者的技藝。在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中,簡單的分工協作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規律使生產過程的每一局部操作獲得了適合局部工人的特殊形式,并將這種特殊的勞動技巧發展到了極致,從而使總體工人的成員獲得了特殊的發展。同時,資本家為使工人更熟練地進行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便對工人進行勞動技能培訓。大量工人以此提升了自身在社會文化方面的智力和勞動技藝。正如馬克思所言:“對于正在成長的人來說,這個直接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訓練,而對于頭腦里具有積累起來的社會知識的成年人來說,這個過程就是[知識的]運用,實驗科學,有物質創造力的和對象化中的科學。”[1](p204)其二,就勞動對象要素而言,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使勞動對象愈益豐富,使用高級的勞動對象逐漸成為可能。在傳統生產條件下,加工技術條件的限制和生產工具的簡單粗陋,導致工人經常因缺乏生產所需的材料而陷入長期的停工,致使工業生產、消費需求長期得不到擴大和滿足。新機器的發明與技術改進不僅有效解決了勞動對象對生產的限制,而且也推動了煤、鐵、玻璃、陶瓷等材料的加工技術的發展。同時,生產的發展也為自然科學的進步創造了條件,而自然科學的進步又大大推動了材料加工、創造與廢料回收利用的能力,“從而無須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2](p699)。其三,就勞動工具要素而言,科學技術的應用極大地促進了勞動工具形態的革新,科學技術逐漸成為直接的生產力。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改變了原有生產工具的簡單落后狀態,創造了自動的機器體系并塑造了機器大工業。馬克思以機械性勞動資料的固定資本衡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動的機器體系作為固定資本的成熟形態,以生產力的形式出現并憑借其龐大的機器“器官”使工人本身的生產力作為無限小的力量趨于消失,從而使生產力的發展直接從屬于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所以馬克思指出:“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1](p198)
其次,從科學技術與資本主義批判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構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重要視域。一方面,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深刻地改變了社會原有的階級構成與宗法關系,造就了大批無產者。在傳統生產方式下,從事生產的工人大多是散居在農村的農民。他們在宗法制度下過著田園詩般的較為自由的生活,雖然清貧,但還不是一無所有。然而,以機器生產為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3](p34)無情地斬斷了他們溫情的田園詩般的宗法關系,同時也剝奪了他們僅有的生計來源,大量農民被迫變成無產者,淪為一種不得不出賣自身活勞動能力的特殊商品。可以說,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把最后的一些還對人類共同利益漠不關心的階級卷入了歷史的旋渦”[4](p390)。另一方面,科技異化構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敘事,深刻表現在馬克思關于異化勞動的話語展開中。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充當了異化勞動的“催化劑”,使工人的生存境遇更加悲慘。其一,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加劇了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的異化,使人具有物之性格。在科學技術的催化效應下,工人以更高的生產率在更大的規模上生產出與自身相對立的異己存在物,從而加速了工人與自己的無機的身體的分離。由此,工人喪失了自身勞動的客觀條件,人格物化的程度愈益深化,最終淪為僵死的物一般的存在。其二,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加劇了勞動過程中的異化,使勞動者逐漸簡單化。勞動本應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自由發揮,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只是在肉體的外在強制下被迫勞動。在科學技術的“催化”作用下,工人的片面發展達到極致。在機器大工業中,自動的機器體系代替了大量工人的手工操作,工人只是作為機器體系的一個環節、一個零件而存在。恰如馬克思所言:“在使用機器的情況下……單個人只是整體的一個環節……是以死的自然力即某種鐵的機構的有節奏而均勻的速度和不知疲倦的動作而工作著。”[1](p320)在如死的機器一般的工作狀態下,工人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單向度的“機器人”。其三,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進一步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化,使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斗爭更為激烈。(1)科學技術所塑造的機器大生產保證了生產的連續性,為剩余價值的榨取提供了技術保障。資本家通過提高機器的轉速和工人的勞動強度,使單位勞動時間內充滿更多的勞動,以致工人因肉體與精神方面的過度勞累而早衰。正如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揭示了,在中世紀深受反動派稱許的那種人力的野蠻使用,是以極端怠惰作為相應補充的。它第一個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成就。”[3](p34)(2)機器生產的替代性勞動使大量的成年熟練工人被婦女和童工所取代,成為“過剩”的產業后備軍。因而失去了生計來源的大量成年工人便與婦女和兒童處于更為激烈的競爭之中,進一步惡化了工人的生存處境。(3)“由于自然科學被資本用作致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學的人為了探索科學的實際應用而互相競爭。”[1](p359)正是由于工人、資本家、科學研究者之間的異化相互交織,從而使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斗爭更為殘酷和激烈。
最后,從科學技術與共產主義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為人類解放創造了條件。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4](p185)。雖然科學技術的應用加速了私有財產的積累,使人深陷于異化與物化的奴役之中,但馬克思并未反對科學技術的應用,而是透過科技的異化表象看到了其在促進人類社會形態變革中所蘊含的推動人類解放的巨大力量。這主要體現在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三形態的基本判斷之中。其一,在“人的依賴關系”[1](p52)的最初社會形態下,社會生產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個人還是“一定狹隘人群的附屬物”,不具有獨立性。其二,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1](p52)的第二大社會形態下,工業生產實踐為自然科學的進步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物化為機器形態的科學技術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但在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商品面前,即在物性的虛幻表象下人又再度喪失了自身,深陷于商品、貨幣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之中。僅僅建立在物的依賴性基礎上的相對獨立性并非真正的獨立性,人尚未真正脫離物的生活真正進入人的生活。也就是說,在物的依賴性基礎上,人有限的相對獨立性并沒有消除人所經受的諸種異化、物化,在科學技術加倍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物的奴役反而變得更加普遍、更為突出,人依舊戴著沉重的鐐銬。但馬克思并未據此就否認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的促動效應,相反,馬克思肯定了作為生產力的科學技術的必要性。“全面發展的個人……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這種生產才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相異化的普遍性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p56)這表明,馬克思認為科技發展進程中伴生的異化、物化現象有其所處的歷史階段的必然性,是個人獲得自由解放的必經之路。只有在科學技術造就的巨大生產力的基礎上,個人的全面發展和充足的社會物質財富才得以可能。其三,在“人的自由個性”的第三大社會形態下,即在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3](p53)。而作為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恰恰是實現每個人自由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必然要素,盡管我們在邁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必然還要遭受科技異化的侵擾,但科技生產力量的積累必然會產生質的飛躍,實現社會形態的變革。
總的來說,科技生產力觀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生產力觀最為突出的方面,貫穿于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的始終。只有科學地理解科技生產力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產力觀中的地位,才能對其生產力理論乃至歷史唯物主義作出科學的闡釋與時代化發展。
二、隱性內在邏輯線索:生態生產力觀
通過文本梳理,我們便會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產力觀除是顯性的科技生產力觀外,也是與自然生態緊密結合的、蘊含著豐富生態意蘊的生態生產力觀。這構成了他們生產力觀的一條隱性內在邏輯線索,主要表現在生態生產力與生產勞動、資本主義批判、共產主義之間的內在關系上。
首先,從生態生產力與生產勞動的關系來看,生態生產力主要體現為馬克思的自然生產力思想,自然生產力構成了人類生存與社會生產的天然物質基質。長期以來,學術界受蘇聯教科書體系的影響,將生產力視為“人類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改造和影響自然以使其適合社會需要的物質力量”[5](p116)。該認識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直接影響了部分學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生產力觀的正確認知。因為這個定義尤為突出生產力概念中人的能動性與主體性,強調的只是人對外在自然界的控制、征服與改造,卻將社會生產力得以產生與持續發展的自然根基完全閹割掉了。“它離開社會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因素,孤立地侈談‘人的能力’,只突出了生產力的社會性,似乎‘生產力’僅僅是指‘社會生產力’”[6],因而也就嚴重忽視了馬克思的自然生產力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外部自然界是人類生命和物質生產發展得以存續的首要前提與天然物質根基,并指出“一切生產力都歸結為自然界”[1](p170)。就勞動者要素本身的自然生產力而言,這種自然力是勞動者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最基本的力量,其歸根結底來源于自然的供給。因為外部自然對象無論以何種形式存在,均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的來源,即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4](p161)。就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要素而言,無論是天然的自然資源或“經過形式變化而適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質”[2](p211)皆來自外部自然界,離開外部自然界,我們便什么也不能創造。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馬克思專門闡述了自然力應用于社會生產的問題,“大生產……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風、水、蒸汽、電大規模地從屬于直接的生產過程,使自然力變成社會勞動的因素”[1](p356)。通過對自然生產力在物質財富生產活動中地位與作用的考察,馬克思認為,自然生產力是社會生產力的前提和基礎。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進一步認為,在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既定的條件下,絕對剩余價值的單純存在是以自然生產力為前提的。也就是說,自然生產力充當了一定量的必要勞動,從而構成了剩余價值存在的基礎。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認為,同其他生產部門相比,自然生產力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更為突出,因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及其所體現的使用價值量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土地的生產率。因此,馬克思指出自然生產力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
其次,從生態生產力與資本主義批判的關系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態異化現象。正是通過對這一現象的揭露,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堅持了外部自然的優先性,而且進一步深化了生態生產力觀。一方面,資本主義過分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而導致生產力片面發展,造成了人與自然的緊張對立。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前的諸生產方式下,盡管生產力發展低下,但總體來說人表現為生產的目的,人與自然保持著一種天然的同情和共感。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主義過分追求經濟利潤的最大化,生產成為人的目的,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積聚建立在對人與自然的極度剝削的基礎上,人與自然只是作為生產的前提條件和手段而存在,這就導致人與自然的異化。
在資本邏輯的策動下,資本憑借其強大的宰治力在全球范圍內到處擴張,素被尊崇的自然淪為資本增殖的工具,自然被視為完全缺乏任何經驗、情感、內在關系、內在價值的僵死之物,僅僅作為一個天然資源庫成為依據資本增殖而被任意使用和破壞的客體。這些做法不僅對自然界造成了毀滅性的損傷,也破壞了生產力持續增長的物質根基。誠如恩格斯在談及英國煤炭業發展受限時所指出的那樣:“由于土地耕作的改良和森林砍伐殆盡,木炭越來越貴,產量越來越少。”[4](p398)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深刻闡述了機器大工業在農業中的使用所造成的人與土地物質變換斷裂的現象。馬克思認為,機器大工業雖然在農業生產中發揮了革命性的作用,但是這種革命性的作用是以對土地的破壞和土壤肥力的衰退為代價的。正如馬克思所言:“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2](p579)同時,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個國家……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基礎,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2](p580)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進一步將自然生態提升到文明興衰的高度。他通過列舉人類為短期利益破壞自然生態而喪失生產根基的事例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7](p559-560)在這里,恩格斯既通過鮮活的歷史教訓批判了資本主義過度追求經濟利益而肆意干預自然的短視行徑,也劃定了人類干預自然的限度,指明了人類生產發展的永恒生態限制,從而警醒人類必須在正確認識和利用自然規律的基礎上與自然進行合理有度的物質變換,更要注重生產力發展方式的綠色化、生態化。否則,對自然的無節制開發必然會引發生態災難,招致自然無情的報復。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過分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的生產力片面發展還造成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資本主義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剩余價值,不斷擴大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交換價值的生產,因而也就需要不斷擴大對外部自然的索取。這必然造成自然資源的加速耗費以及生產廢料的大量堆積,從而引發社會生產發展與自然物質變換的中斷,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絕對規律”。所以,資本主義差不多每十年就要遭受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一方面大量的自然資源被浪費,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通過時空的壓縮加速對自然的掠奪。這對自然生態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毀傷,因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注定是不可持續的。正如馬克思所言:“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3](p37)因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達到了同它的外殼不相容的地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滅亡。可以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非生態性這一痼疾,必然超越自然所能承載的限度,無論其在生產中如何節約,都無法逆轉這一不斷衰退的趨勢,從而必將被一種綠色的生態化的發展方式所取代。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雖未明確提出生態生產力概念,但通過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我們可以看出其生產力觀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生態思想。
最后,從生態生產力與共產主義的關系來看,生態生產力是邁向共產主義社會進而實現人與自然雙重解放的必然路徑。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闡述了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4](p185)在這里,馬克思的理論路徑非常明晰:他把共產主義理解為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也就是對奴役人的一切關系的積極揚棄。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認為以上諸種矛盾皆根源于私有財產。因而,共產主義對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便意味著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這不僅指明了人與自然矛盾的制度根源,也表明了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是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而不僅僅是人的解放。
資本主義在大量占有與消耗自然資源基礎上所創造的巨大生產力,雖然為邁向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創造了條件,但在其非生態性的生產方式下人與自然只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所以,資本主義不僅不能真正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也無法消除生產力發展的永恒生態限制,更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至多是實現人的物性意義上的相對自由,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本不存在生態關懷。馬克思認為,隨著生產力的極大發展,我們將超越物的依賴性之下的人與自然對立的“虛幻共同體”,進而邁向社會生產力從屬于“人的自由個性”的真正共同體。“真正的共同體”,即共產主義社會,將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共同體。到那時人類將擺脫資本邏輯的發展桎梏,外在自然不再是生產力發展的永恒界限,“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8](p928-929)。也就是說,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對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對人的關系,正像人對人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對自然的關系”[4](p184),從而實現了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的社會性的統一。因此,在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我們更要注重生產力發展方式的綠色化、生態化,這樣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的終極關懷,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進而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而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態生產力觀的重要體現。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明確提出生態生產力概念,但從生態生產力的幾個側面——生產勞動、資本主義批判、共產主義——來看,生態生產力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擁有基礎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這樣一來,我們就從根本上駁斥了國內外學者對他們生產力觀的批評指責,彰顯了他們生產力觀的科學性、革命性、真理性。
三、內在關聯:科技生產力觀與生態生產力觀的辯證關系
科技生產力觀與生態生產力觀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生產力觀的雙重內在邏輯線索,構成了他們生產力觀的整體性視域。那么,兩條邏輯線索的內在關聯便成為我們當前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生態生產力對科技生產力的影響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生態生產力對科技生產力具有承載功能,是其存續的自然前提與物質基礎。科技生產力作為改造自然的巨大物質力量,其產生是人通過生產實踐活動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的過程,因而也是通過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工具三要素得以實現的。而這三要素歸根結底建立在自然的根基之上,離開了外部自然,它們只能作為抽象的生產力構成要素而無法現實地作用于生產過程。就勞動者要素而言,無論勞動者智力、文化水平的高低,他們都是自然環境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因而馬克思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4](p220)就勞動對象要素而言,勞動對象是科技生產力得以實現的重要條件。無論是未經人類加工就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還是在科學技術作用下經人類加工而產生的勞動對象,皆是自然資源或自然資源形態變化的產物,其終極來源皆是自然界。因而,外部自然是人類生產的現實勞動對象和可能的勞動對象的總和。就勞動工具而言,勞動工具是科技生產力的集中顯現。無論是最初應用于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簡易工具,如石器、磨、風車、水車等,還是隨后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機器、自動的機器體系等,其生產的材料、原料、動力來源的燃料能源等,皆來自自然界。因而馬克思將自然界視為“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9](p428)。可以說,離開了自然資源或自然力,就沒有勞動工具的存在,科技生產力也就無法存續。關于自然資源或自然力在生產力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撇開社會生產的形態的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系的。”[2](p586)并將外部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分為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土壤的肥力、水產豐富的河流)和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奔騰的瀑布、森林、煤炭礦產)兩大類。馬克思認為,在科技生產力發展的初期,生產力發展取決于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在科技生產力發展的高級階段,生產力發展取決于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這就從勞動者對自然界的本原性、勞動資料對自然界的根源性、勞動工具對自然界的依賴性等方面,揭示了生態生產力對科技生產力的前提性與根基性作用。因而,馬克思將“一切生產力都歸結為自然界”[1](p170)。
另一方面,生態生產力對科技生產力也具有制約性或顛覆性影響。誠然,自然資源所蘊含的巨大自然力作為不費分文的資本生產力,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為資本家積累了超額利潤,也為科技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支撐。可以說,自然資源的豐裕度或自然生產力的大小與科技生產力的發展是成正比的。按照馬克思“一切生產力都歸結為自然界”的思想,科技生產力的基本要素皆是在與自然的互動過程中作用于生產過程的,因而必然從根源性上受到外部自然的制約。馬克思認為,生態生產力的這種制約性在農業生產中表現得最為直接,“農業勞動的生產率是和自然條件聯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然條件的生產率不同,同量勞動會體現為較多或較少的產品或使用價值……在這里,價值體現在多少產品中,取決于土地的生產率”[8](p924-925)。即自然條件的優劣決定了農業產量、使用價值的高低。盡管科學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優化了傳統的耕作方式,改變了土壤的原有條件,實現了對土地的科學管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肥力與勞動生產率。但歸根結底,無論科技生產力在農業中表現出怎樣的革命性,始終不能消除自然條件的永恒限制。在工業生產中,馬克思指出“就各個單個資本來說,再生產的連續性有時或多或少地會發生中斷”[10](p121),比如十八世紀的工人經常因缺乏勞動資料而停工。這種中斷突出表現在季節性的生產部門因自然條件的限制而發生的不同程度的中斷上。盡管強大的科技生產力消除了勞動資料短缺對生產造成的困擾,也通過對自然規律相對科學的認識、利用以及對自然的全面改造,最大限度地保證了生產的連續性,但是科技生產力仍然處處受到自然條件的制約,仍面臨著被顛覆的威脅。目前,我們雖然擁有高度發達的科技生產力,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消解人與自然的對立,全球仍面臨著生態危機的威脅,仍被可持續發展挑戰的焦慮所困擾。這是因為,“人類進步的一切偉大時代,是跟生存資源擴充的各時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11](p32)。總之,科技生產力面臨著生態生產力的永恒限制。
(二)科技生產力對生態生產力的影響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對科技生產力的不合理使用改變了人們對生態生產力的看法。科技作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第一要素,為資本主義創造了巨額的社會物質財富,因而被資本家有意識地加以利用與發展。正是科技生產力這種強大的支配力,使資本邏輯得到空前發展。資本邏輯將生產力的片面發展、經濟利潤的最大化作為生產的價值歸宿。這樣,其過分追求的經濟利潤最大化是建立在自然資源大量耗費與毀損的基礎上的,必然以犧牲生態生產力為代價,會導致科技生產力的片面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言:“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2](p589),“自然條件的豐饒度往往隨著社會條件所決定的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地減低”[8](p289)。科技生產力的片面發展在觀念層面形成了見物不見自然的“拜物教”,即對商品、貨幣、資本等物質要素狂熱追求的物役經濟,使人們從思想意識深處弱化了自然及其內蘊生命的價值。由此,自然被視為完全缺乏任何經驗、情感、內在關系、內在價值的僵死之物,僅僅作為一個被動客體成為“依據我們的目的加以使用的‘它’”[12](p218)。這為資本主義瘋狂地開發、掠奪自然資源,榨取自然生產力提供了意識形態的辯護,使其具有了“合法性”的外觀,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基于資本主義對科技生產力的不合理使用而引發的一系列生態問題的批判,進一步發展與深化了生態生產力思想。
另一方面,科技生產力與生態生產力的有機結合,既可以促進生態生產力的發展,又可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如前所述,沒有生態生產力,科技生產力就無從談起,而沒有科技生產力,生態生產力只能在狹小的范圍內得到有限的利用,而不能大規模應用于生產過程,也就不能使大多數人受益。馬克思在談到影響生產力發展的因素時指出:生產力是由“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2](p53)所決定的。因而,我們可以將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視為影響生產力發展的科技因素,將之歸屬于科技生產力范圍;將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自然條件視為影響生產力發展的自然因素,將之歸屬于生態生產力范圍。可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科技生產力與生態生產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二者缺一不可。科技生產力既改變了自然生產力的自在狀態,也放大了自然生產力所蘊含的生產效能。正如馬克思所言,“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2](p444),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綜上所述,科技生產力觀與生態生產力觀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生產力觀的雙重內在邏輯線索,既強調了科技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更強調了生態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產力觀是與自然生態緊密相連、充滿綠色意蘊的科學理論,而絕非是一些國內外學者所認為的只見科技不見自然的“生產力決定論”。因此,只有充分認識自然生態在他們生產力觀中的重要地位,才能科學而完整地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產力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