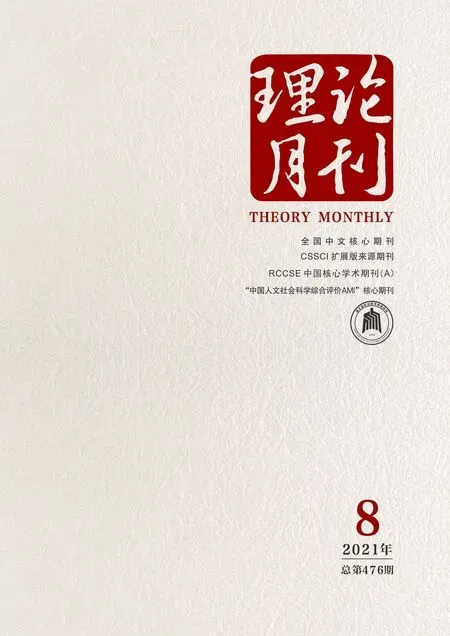零工經濟資本與勞動之間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閆境華,石先梅
(1.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430073;2.北京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871)
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人類生產生活領域的滲透,對傳統的用工模式與勞資關系產生了沖擊。零工經濟這種新業態在數字經濟時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2020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中國零工經濟大概能夠容納2億人就業,這種新業態正在蓬勃發展。億歐智庫發布的《2020年靈活用工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靈活用工市場規模為7258.2億元,測算出2016—2019年靈活用工市場規模年均增長率為45%,預計2020—2022年靈活用工市場規模年均增長率為30%,預計2022年將達到12246.95億元的市場規模。但是,以數字平臺為依托的靈活用工與傳統用工模式存在較大差異,大資本數字平臺公司高利潤與零工勞動力低收入并存。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零工經濟業態下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為協調數字經濟時代勞資關系,促進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借鑒。
一、零工經濟新業態的特點
“零工經濟”(gig economy)中的“零工”(gig)一詞,在20世紀初最早出現在美國,當時是指雇傭音樂家演奏的某一特定曲目或僅持續一晚的演出[1](p171-188),后來指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量任務的非正式計件工作。這里的“零工”盡管體現了工作形式的靈活性,但并未呈現出以互聯網平臺為媒介的特征,零工經濟也并未作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出現。
零工經濟興起的關鍵是數字技術在生產領域的滲透,尤其是互聯網平臺的建立與發展。在傳統的產業部門,勞動力之間的分工比較明確,勞動力從一個行業部門轉向另一個行業部門需要較高的培訓成本。傳統產業部門勞動力流動受地域與行業的限制較大,勞動力流動成本較高,當某一行業現有勞動力的供給飽和時,勞動力選擇轉入其他行業并傾向于長期固定下來,而不是同時從事多項工作。數字經濟的發展催生了一批勞動復雜程度較低、勞動形式較為自由的行業,一個人同時掌握多項技能并從事多項工作變得更加容易,與此同時大資本數字平臺的發展使得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匹配的成本大幅降低,零工經濟這種新業態得以催生。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零工經濟”這一概念2009年1月12日首次出現在美國新聞網站The Daily Beast上的一篇名為The Gig Economy的文章中,2015年《紐約時報》對“零工經濟”下了這樣的定義:工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技能和時間,選擇接受不同的工作,具有自我管理和多樣性的優點,這類工作一般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和時間,從業者一般是臨時工、合同工、個體戶或者兼職人員。這一定義突出了零工經濟工作選擇的多樣性與工作形式的靈活性,但沒有突出零工經濟以數字平臺為依托這一重要特征。
勞動者通過數字平臺利用閑置的資源在某一時間段內提供某種特定的服務,這個資源可以是資本、時間或者自身的人力資本,數字平臺大大提高了閑置資源的利用效率,這是零工經濟的核心特征[2](p25-35)。同為數字經濟的新業態,分享經濟與零工經濟經常結合在一起,例如當勞動者利用自己的房間、車輛等閑置資產提供勞動與服務時,體現出分享經濟的特征。對“零工經濟”可以給出以下定義:勞動者借助數字平臺,利用閑置的資源在某一時間段內提供某種特定的服務,不再長期受雇于某一組織或機構的經濟模式。零工經濟具有工作時間碎片化、交流遠程化、合作管理平臺化等特點,這些特征隨著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進程的推進不斷顯示出來,并對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產生重要影響。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在運用零工經濟術語時,集中體現用工模式的靈活性。
可以分別從勞動力與雇主雙方來體現零工經濟用工模式的靈活性。從勞動力一方的角度來看,在零工經濟模式中,勞動力可以同時從事多份工作,成為“斜杠青年”。勞動力不再限定于與一家公司簽訂勞務合同,勞動者甚至可能擁有自己的企業。勞動力可以較為自由地選擇提供勞動服務的時間,有時去公司規定的地點工作,有時在家里提供勞務。一般說來,在零工經濟模式中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工資待遇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不是固定的,可能是事先規定好的,也可能視勞動力提供勞動生產出的成果而定。從雇主一方來看,在零工經濟模式中,雇主不一定就是勞務關系的總負責人,雇主有可能只起著中間介紹人的作用,而且雇主可能本身就從事著零工經濟服務。零工經濟用工模式的靈活性主要體現在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自主協商,用工條件自由組合,大多數情況下沒有簽訂正式的合同,而是以勞務派遣以及業務外包為主要服務形態。雇主對雇員的管理方式非常靈活,一般不提供固定的工作場所,也不會對勞動力提供一系列的保障,因為勞動服務者并非本企業的正式員工,雇主不會選擇為其承擔風險,即使簽訂用工合同,也是以短期合同為主。
對于參與零工經濟勞動服務的勞動力而言,在承擔更大的失業風險的同時,也獲得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靈活的生活方式。零工經濟模式通常是借助于互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對零工勞動的供給方與需求方進行匹配,“斜杠青年”通過微信、58同城等社交軟件就能夠找到許多兼職信息,大大提升了零工經濟勞務提供者與企業達成協議的效率并降低了交易成本,加快了供需雙方的匹配速度與擬合程度。盡管零工經濟的出現擠掉了一些固定工作,但是與此同時也提供了更多的時間較短但是更為靈活的工作機會。在零工經濟勞動關系中,勞動力面臨著更大的失去原有兼職工作的風險,但是同時也擁有了更多的選擇其他工作的機會。總的來說,零工經濟模式避免了勞動力長期從事一份不稱心工作的弊端,在固定用工模式中勞動力由于辭職后面臨著長期失業的巨大風險以及高額的待業成本,不敢輕易更換工作,但是零工經濟的出現大大降低了辭職的代價,使得勞動力有了更多的選擇與更加豐富的人生體驗。
二、相關文獻綜述
作為一種數字經濟新業態,學者們對零工經濟的特征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許多學者在研究零工經濟特征時,注意到零工經濟模式中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同傳統經濟模式存在較大差異。
零工經濟的特征,以及零工經濟與分享經濟、平臺經濟等其他經濟業態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學者們做了較為充分的研究。鄭祁、楊偉國認為可以以網絡平臺媒介的使用為節點,將零工經濟分為傳統零工經濟和現代零工經濟[3](p106-115)。謝富勝、吳越、王生升認為新經濟形式是伴隨著數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興起的,從新經濟組織形式的范疇上看,主要有平臺經濟、共享經濟、分享經濟、零工經濟,而“數字經濟”和“數字資本主義”逐漸成為基于數字技術體系日益龐大的新經濟形式的總括概念[4](p62-18,200)。崔學東、曹櫻凡認為以零工形式存在的民宿、網約車等雖然起到了充分利用社會閑置資產和能力的作用,但這種共享的實質是將家庭生活資料和勞動力再商品化或資本化,并且被平臺控制從而為數字平臺提取剩余價值的[5](p22-36)。韓文龍、劉璐認為在數字經濟時代零工經濟并沒有更加自由,零工勞動力往往由于互聯網平臺招用零工門檻極低而出現供過于求的情況,在勞動者就業機會增加以及自由安排工作時間的同時,零工之間的競爭力度加大,從而使勞動力的工作強度加大,資本家對零工勞動力的控制力度也就加大[6](p55-57)。有些學者盡管用的不是“零工經濟”而是“分享經濟”的概念,但是二者存在大量交叉部分,王利君通過研究分享經濟的特征以及在我國的發展狀況,指出制約我國分享經濟發展的瓶頸,即結構不合理、從業者安全保障不足、消費者權益保障不足、法律法規滯后[7](p225-232,327),這也是我國零工經濟發展遇到的瓶頸。可見學者們在闡釋零工經濟的特征時,基本上都突出了互聯網平臺的作用。
在對零工經濟新業態的研究中,零工經濟模式下資本與資本、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成為研究重點。崔學東、曹櫻凡認為實質上的雇傭勞動關系不會因為平臺資本雇傭勞動形式的消失而消失,勞資矛盾更不會因此消失。臨時向平臺資本出賣勞動力的零工勞動形式與傳統的在一定時期向資本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形式,本質上資本都占有了勞動力的剩余勞動[5](p22-36)。謝富勝從數字技術變革條件下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總體角度,對新經濟組織形式中大平臺與小平臺之間的資本關系,以及平臺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指出這種生產與再生產的新組織形式仍然是數字技術體系下因應資本積累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們在推動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同時,也蘊含著其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4](p62-81)。初浩楠等認為在零工經濟中勞動力雇傭與被雇傭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多元化勞動關系萌芽已經出現。接受多元化勞動關系既可以促進用工方式的創新與規范化,又促進了平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8](p95-99)。楊濱伊、孟泉認為零工經濟雇傭形式的靈活性具有兩面性,脫離傳統雇傭形式工作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增強,零工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更加被動的地位,與此同時零工經濟使得高技能者在利用零碎時間勞動的同時擠占了低技能者的崗位[9](p95-99)。閆境華、石先梅認為零工經濟、分享經濟這兩種新業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資本數字平臺對社會生產過程的控制力度,同時加劇了中小資本之間、零工勞動力之間的競爭程度[10](p26-28)。
以數字技術的運用為核心的新經濟形式,無論是稱為平臺經濟、共享經濟,還是零工經濟,資本結構都較傳統經濟模式更為復雜。數字經濟多種新業態中的資本,作為資本一般兼具生產功能屬性與生產關系屬性。零工經濟新業態中的資本,就其生產功能屬性而言,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水平而逐漸擴展開來;就其生產關系而言,生產集中必然導致一部分企業資本規模急劇擴張,使得不同資本在剩余價值索取中處于不同的地位[11](p39-47)。零工經濟新業態中通常涉及以下四種資本:勞動力的自有資本、非數字企業資本、大資本數字平臺資本以及跨國數字壟斷公司資本。零工經濟新業態中資本結構的多重性,使得其中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也呈現出多重性。
三、零工經濟資本結構的多重性
零工經濟的興起與繁榮,體現了數字經濟時代信息與資源在市場中的充分流動。在大資本數字平臺的連接作用下,零工經濟模式中至少包括三方,即需求方、供給方以及大資本數字平臺。大資本數字平臺在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起著關鍵的連接作用,極大地提高了供需匹配的效率,減少了供需匹配的成本。零工勞動力既可以作為需求方出現,又可以作為供給方出現,還可以作為聯通供需之間的中介力量出現。當零工勞動力作為供給方出現時,網約車、民宿等經濟模式中勞動力以自有閑置資本提供勞務,線上教育、線上心理咨詢直接通過數字平臺對接需求方提供勞務;當零工勞動力以需求方出現時,在各種招聘網站上他們是工作的需求者,在消費市場上他們是商品的需求者;當零工勞動力作為聯通供需雙方的中介力量出現時,快遞員、外賣員、帶貨主播將商品以更快的速度傳遞到消費者手中,大資本數字平臺對零工勞動力的形成起著關鍵作用。
(一)零工經濟中勞動力的自有資本
勞動者利用閑置的資源在某一時間段內提供某種特定的服務,這個資源可以是資產、時間甚至是自身的人力資本,當勞動者利用的閑置資源中包含房屋、車輛等固定資產時,這種自有資本以一定的形式與勞動者自身相結合。以大資本數字平臺為依托,零工經濟中勞動力的自有資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零工經濟業態中,與勞動力相結合的自有資本并非源于資本原始積累或資本積累,更多的是一種儲蓄的積累。資本一般說來通過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產生,并通過資本積累過程進一步擴大,資本原始積累過程造成了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分離,而資本家支付勞動力的報酬僅供勞動者滿足生活消費,使得勞動者沒有能力獲取生產資料,那么勞動者可用于結合勞動力的自有資本從何而來呢?勞動者擁有一定的儲蓄在經濟實踐中是一件非常常見的事情,儲蓄既可以來源于意外的收入,例如中彩、接受饋贈、獲得遺產等,也可以是通過消費資料的節約而來,畢竟現代社會中勞動者的工資不都是在最低生活水平線上,這就使得絕大多數家庭都有積累儲蓄的可能性。與勞動者自身結合的自有資本主要來源于儲蓄的積累。
第二,零工經濟業態中,勞動力與自有資本結合的關鍵條件是依托于大資本數字平臺,這也是勞動力的閑置資產被稱為資本的主要原因。“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正常條件下經營某種行業所需要的單個資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較小的資本擠到那些大工業還只是零散地或者不完全地占領的生產領域中去。”[12](p722)生產規模的擴大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勞動者的儲蓄要想參與到大規模生產領域之中,通常只能通過購買股票、債券的形式,儲蓄轉化為獨立的產業資本通常只是在小規模生產領域出現,例如餐飲以及傳統的手工工藝。在互聯網平臺出現以前,儲蓄向資本的轉化并非以零工經濟的模式出現,一方面一般居民對股票、債券的持有并不能形成對企業的控制權,這些資本并不能與自由勞動力結合從而像民宿、網約車那樣受個人支配;另一方面資本在不同行業之間的進入退出仍然需要較高的交易成本,絕大多數資本進入一個行業就不再轉出了。這種情況下,轉入到新行業中的資本盡管可能處于金融壟斷資本以及其他壟斷資本的控制范圍內,但并不需要依附于大資本數字平臺。互聯網平臺的建立使得進入某些行業的初始資本以及成本極大降低,是儲蓄轉化為零工經濟業態中的這種自有資本的關鍵條件,這一關鍵條件也造成了自有資本對平臺資本的嚴重依賴。仍然以民宿與網約車為例,房子作為自有資產在較低的生活水平下,僅夠滿足勞動者家庭的居住,在積攢足夠的儲蓄之后可以換成較大的房子,這使得短期出租給他人居住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而互聯網平臺的建立使得房主能夠以非常小的成本較為穩定匹配到租客,于是閑置的自有房間就成了能夠帶來收入的自有資本。同樣地,只有有了一定的儲蓄,勞動者才能夠獨立購買到網約車這種能夠帶來收入的自有資產,并在較低的交易成本下匹配到乘客。一旦離開了大資本數字平臺,網約車、民宿就失去了運作賴以繼續的條件,這就使得零工經濟業態中閑置資產只有在平臺資本的控制下才能成為運動中的資本。
第三,勞動力必須投入一定的零工勞動與這種自有資本相結合,這意味著勞動力實際上是在平臺資本的控制下為平臺企業創造利潤。如果勞動者將儲蓄轉化為一定的資產而無須投入任何勞動,那么這種資產因為被他人管理而成了一種資本,這與購買股份從本質上沒有差異,由于勞動者沒有投入一定的勞動服務,這種閑置資源的利用不屬于零工經濟。仍以民宿、網約車為例,民宿訂單的接受與處理,引導客戶看房、入住,為租客提供必要的其他服務等都屬于提供勞動服務。在產業資本領域,建造房屋投入了大量的勞動,在商業資本領域,大量從事房屋出售業務的人員也投入了大量的勞動,零工經濟業態中房主同樣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務勞動,這種勞動服務以租客獲得更好的住房體驗為目的。有價值的勞動成果不局限于產品,還包括服務,民宿房主提供的勞動服務也創造了價值[13](p15-23)。同樣地,網約車的所有者親自提供載客服務,或者將車輛租給他人使用,而不是將車輛租給他人用于提供勞務。從表面上看,在這種資產與勞動結合的形式中,既不存在雇傭他人的勞動,也不存在受他人的雇傭,但實質上勞動者在運用自有資本的同時卻在為平臺企業創造利潤,因為大資本數字平臺最終必然會對民宿、網約車等的每一筆交易收取一定的提成。
(二)零工經濟中的數字平臺資本
數字平臺的建立需要高端先進的數字技術的應用,并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通常只有在建成大資本數字平臺之后才能在資本競爭中存續。在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數字經濟中,大資本數字平臺的出資情況存在較大差異,零工經濟業態中亦是如此。在產業數字化領域,出資主體是原有的生產者,只是在數字化過程中受到大資本數字平臺的影響;在數字產業化領域,大資本數字平臺起主導作用,企業最為核心的資源就是數據生產要素。零工經濟中的平臺資本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資本數字平臺通常是互聯網科技公司建立的。直播行業的主要出資者是建立并管理數字平臺的互聯網科技公司,例如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最早將人工智能應用于移動互聯網的企業之一,其旗下最早的數字平臺是“今日頭條”客戶端,通過海量信息采集、深度數據挖掘和用戶行為分析,為用戶智能推薦個性化信息,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新聞閱讀模式。字節跳動在2019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中排名第八,2020年1月9日字節跳動以市值5300億元位列《2019年胡潤中國500強民營企業》第七位。但是人們對字節跳動的熟知度遠遠比不上今日頭條、抖音、火山、西瓜視頻等App,實際上后者都是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產品,此外Top Buzz、Vigo Video、Tik Tok、Hello等產品在海外則被廣泛使用。抖音、火山、西瓜視頻等都可以作為直播平臺開展直播業務。僅就直播平臺的建立而言,就需要消耗大量資本構建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化設備,投入使用并獲益還需海量數據以及大量數字技術人才,這使得大資本數字平臺往往只有處于高技術產業的互聯網科技公司才能做大做強。
第二,數字平臺資本必須在不斷地融資中擴張,才有可能占據優勢地位。互聯網科技公司通過不斷地融資而得以發展,武漢斗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在2014年4月1日完成天使輪融資后,先后完成了A輪、B輪、C輪、C+輪、D輪以及E輪融資,其中E輪融資的投資方為騰訊,投資金額為40億元,2019年7月17日斗魚(DOYU)在納斯達克上市。平臺企業具有天然的壟斷傾向,這也使得平臺資本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才能在競爭中存續,這種壟斷傾向與數據生產要素的特點高度相關,至少可以在以下兩個方面得到解釋。一是數據生產要素具有典型的規模效應,少量的數據與用戶無法起到盈利的效果,當數據規模逐漸增大時,加工、處理與管理數據的邊際成本是遞減的,甚至接近于零,但是數據的邊際收益在一定范圍內甚至是遞增的。二是數據生產要素的通用性與范圍經濟。數據生產要素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至少在數據的收集上,平臺企業不必局限于某一個行業的用戶信息,而是匯集多個行業領域的一般數據,更大的消費者數據樣本反過來提高了對消費者偏好進行捕捉的準確度,從而提升了對消費者的控制力度。這種跨行業、多種類的數據收集與加工,使得大數據生產要素甚至通用于數字經濟全域產品的生產,大大擴張了范圍經濟的邊界,提升了范圍經濟效果的強度。平臺資本要想在競爭中充分發揮數據這種核心資源的規模效應、通用性與范圍經濟效應,關鍵的一條就是通過融資擴大資本規模。
第三,大資本數字平臺通常并不與零工勞動力、中小企業簽訂長期固定合同。數字平臺大資本廣泛向各行各業滲透,涉及多個經濟活動主體與經濟領域,很難一一簽訂固定合同。以直播行業為例,除了少數主播與公會或平臺簽約之外,大部分主播都屬于沒有與公會或平臺簽訂合約、直播時間非常零散的業余主播,簽約的主播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兼職主播,可以同時從事其他工作。對于兼職主播和業余主播來說,僅憑直播的收入一般不能滿足主播的生活開支,主播還必須從事其他工作,兼職與業余直播是一種典型的零工經濟,這種情況下很難將他們稱為大資本數字平臺公司的員工,也不可能簽訂固定的雇傭勞動合同。網約車、民宿等與數字平臺之間的合同同樣非常靈活,網約車、民宿本來就是想要通過數字平臺進行宣傳,這種合作關系類似廠商與廣告公司之間的關系,網約車、民宿乃至中小企業完全有可能選擇其他數字平臺或者其他宣傳模式,合同持續的時間通常取決于平臺資本壟斷實力的強弱。
第四,跨國數字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在數字化基礎設施、大型數字化設備以及大資本數字平臺建立起來以后,數字公司總是不惜以巨大的代價形成壟斷地位。谷歌2006年收購了油管網,2014年收購了筑巢實驗室(NestLabs);臉書(Facebook)2012年用7.15億美元收購了13名員工的照片墻,2014年又以190億美元收購了瓦次普(WhatApps);微軟2016年以262億美元,超50%溢價收購了領英;亞馬遜2017年以137億美元收購了美國全食超市。起初這種壟斷是在一國范圍內形成的,后來則將數字壟斷資本伸向全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巨型數字跨國壟斷公司,將眾多中小數字企業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企業變成自己的價值創造節點,榨取各個國家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數字資本不僅控制了勞動力,還將勞動力產生的數據轉化為資本進一步形成剝削手段。巨型數字跨國壟斷公司對數字技術落后國家造成了深遠影響,在低成本乃至無償占有落后國家數據資源的同時,也大量占有了零工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尤其是當跨國數字壟斷資本與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相結合時,這種影響更為明顯,甚至可以左右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重大決策。
(三)零工經濟中的中小企業資本
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與互聯網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與數字平臺發生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餐飲、小吃、生鮮以及零售店等通過美團、餓了么等互聯網平臺展開銷售,催生了外賣行業;心理咨詢、健康咨詢以及教育機構等通過互聯網平臺進行疏導、引導以及輔導,催生了一系列線上服務行業。在平臺經濟發展起來以前,這些企業已經運營起來了,只不過只能進行線下銷售或提供服務,平臺經濟的發展使得快遞員、外賣騎手、線上心理咨詢師、線上輔導老師參與到這些企業的運作過程中來,形成零工經濟。在零工經濟業態中,這些中小企業資本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這些行業中,企業的投資是核心,數字平臺是作為第三方合作平臺而存在的。例如,盡管推出美團外賣的北京三快在線科技有限公司在2020年1月9日發布的《2019年胡潤中國500強民營企業》中以市值5500億元位列第6,但是其資產與加盟美團的億萬家實體企業的資產規模總和不具有比擬性。在教育行業中,有些大型教育機構推出了自己建立的數字平臺,如北京學而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考研幫App,北京小船出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作業幫App。這些教育類App與百度、58同城等通用型數字平臺,成了眾多補習機構、考研機構、考公機構發布招聘信息以及招生信息的重要場所,對于線上教育服務而言,投資的主體仍然是教育機構,而非數字平臺。
第二,與這種資本構成相對應,零工勞動直接結合的主要是企業投入的資本,而非數字平臺投入的資本。億萬家美團加盟店集中在產業資本部門,加盟美團外賣大大減小了產品銷售環節耗費的流通費用,盡管外賣騎手的工資直接是由美團支付的,但是美團用于支付外賣騎手的工資來源于加盟企業銷售額中的提成。因此,外賣騎手的零工勞動本質上是與加盟企業相結合,作用在了產品流通領域。教育機構聘請相關專業人才為學員授課,例如考研機構聘請在讀研究生給考研學子輔導專業課,是一種典型的零工經濟模式。在教育機構的零工化教學模式中,授課名師或研究生的勞動服務主要是與機構的資本相結合,數字平臺雖然提供了關鍵信息與聯絡手段,但是真正使得學員與老師快速相匹配的是教育機構。老師的勞動報酬是由機構直接支付的,數字平臺獲得的只是機構支付的少量廣告費。
第三,中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對大資本數字平臺讓渡了自己的企業利潤。短期來看,中小企業通過加盟大資本數字平臺可以獲得一定的市場競爭優勢,維持企業的利潤率,甚至高于原先的利潤率。但是當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都被納入大資本數字平臺中來時,中小企業之間在線上的競爭同樣巨大,并在更大程度上擠壓了線下消費。例如,為了獲得競爭優勢,許多外賣的價格在加上配送費之后甚至低于堂食的價格。在較低的商品價格下,企業還要承擔配送費這項成本,長期來看,絕大多數企業的利潤率不會上調。根源就在于,盡管數字技術的發展大大減少了流通費用與交易成本,但是零工勞動力與企業員工創造的很大一部分剩余價值轉移到大資本數字平臺公司,以至于平臺企業獲得高額壟斷利潤的同時,企業獲得較低的利潤率,零工勞動力以及專職快遞員、外賣員獲得較低的工資收入。
四、零工經濟中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多重關系
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隨著交易成本的降低,資本更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之間流動以及競爭的充分展開,等量資本傾向于獲得等量利潤,但平均利潤率的形成會受到壟斷資本的阻礙。壟斷資本在數字經濟時代以新的形式存在,在小資本競爭加劇的同時,大資本的壟斷也在加劇,零工經濟中勞動力自有資本、中小企業資本與數字平臺大資本處于不同的地位,獲利能力存在明顯的差異,使得資本與勞動之間存在著多重關系。
第一,數字平臺大資本有著天然的壟斷傾向,甚至可以稱為自然壟斷。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大型互聯網企業完全有能力同時占有多個數字平臺,甚至這些數字平臺涉及的是有著天壤之別的行業。擴大數字平臺的成本遠遠小于重新建立起新的數字平臺的成本,擴大互聯網公司的成本也遠遠小于重新建立互聯網公司的成本,這種邊際成本極低的特征與自然壟斷幾乎無異,因此造成了少數互聯網巨頭企業占有大多數數字平臺的局面。在近幾年共享單車的角逐中這一點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2016年底以來,成百上千的初創共享企業向各大城市投入共享單車搶占市場,共享單車的使用必須經過數字平臺的管理,短短兩年后只有哈羅單車、摩拜單車等數家企業存活,其余的或遭破產、或遭兼并。大型互聯網公司通過建立具有壟斷性質的大資本數字平臺,在零工經濟業態中具有最強大的獲利能力。
第二,數字平臺引起的資本、信息、員工等在各個部門、各個企業之間的充分流動,加劇了中小企業,尤其是以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為主的企業之間的競爭。大資本數字平臺雖然可以壟斷數字的收集與處理,但平臺組織仍需依賴非平臺組織才能完成價值增值的過程,或者說數據本身并不能創造價值,只有將數字收集、分析、處理得出的有用信息運用于生產性企業的運營決策之中,才能夠創造出更強大的生產力,從而創造出價值。在大資本數字平臺的控制之下,各個企業的運營需要迅速地運用數字技術以及數字分析技術,大平臺可能缺乏足夠的靈活性,這為小資本數字平臺的創立和成長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核心技術始終掌握在大資本數字平臺手中,大小平臺始終處于動態的嵌套型層級結構和競爭中。零工經濟業態中,各種餐飲業、微商、淘寶店家、家政服務、教輔機構以及小型數字平臺處于激烈的競爭狀態之中,同一行業各個企業的運營模式非常接近,產品存在細微的差別,資本在不同行業之間流動的障礙很小,企業的獲利能力遠不如大資本數字平臺以及大型制造業企業。
第三,通過數字平臺以自有資本進行經營的零工經濟乃至一部分高度依賴于數字平臺的中小企業接近于完全競爭狀態,并且零工勞動力市場也接近于完全競爭狀態。通過數字平臺運營的民宿、網約車等,幾乎沒有任何一家具有較強影響價格的能力,客戶的流動性非常大,而且只有通過數字平臺對商家進行了解,民宿之間、網約車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差異,商家只能盡力提高好評率。隨著數字平臺的不斷升級與完善,民宿、網約車的數量急劇上漲,這也使得該種零工經濟業態中商家之間的競爭更加劇烈。此外,零工經濟中的勞動力無論是從事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對勞動報酬基本上沒有任何議價能力。數字平臺上有眾多的零工勞動力供給,各項零工勞務的工資早已是約定俗成的了。例如,即使是像考研專業課一對一輔導這樣的必須具備專業知識的勞動,在大數據平臺的作用下,考研機構并不擔心以這樣的價格找不到專業課老師。這種接近于完全競爭的狀態,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零工勞動者持久的低收入狀態。
總結來看,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的零工經濟業態中,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多重關系存在以下特征。一是中小企業的雇傭員工不僅在為本企業創造剩余價值,還在為大資本數字平臺創造剩余價值;二是零工勞動力在廣泛利用社會閑置資源,減少產業資本流通費用的同時,也在為大資本數字平臺創造剩余價值;三是大資本數字平臺通過排擠、控制、并購小資本數字平臺占據優勢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除了平臺企業內部員工創造的剩余價值之外,這些壟斷利潤主要來源于其他企業剩余價值的轉移;四是跨國數字壟斷資本趨向于建立數字霸權,獲取數字弱國的剩余價值。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產業部門出現了零工化的現象。零工經濟作為一種由數字技術發展興起的新業態,在一定時期內仍有著繼續發展的趨勢,直到零工勞動大量被人工智能替代,這有賴于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提高。分層次分析零工經濟業態中數字平臺大資本、中小企業資本以及勞動者自有資本所處的地位,有利于進一步理清數字經濟時代價值創造與價值轉移過程,理清不同資本之間的壟斷與競爭關系。就零工經濟業態中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而言,零工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更多地向大資本數字平臺轉移,中小企業與零工勞動力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一方面是大資本數字平臺市場控制能力的增強,壟斷利潤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中小企業、零工勞動力競爭壓力的增強,收入的降低。這里從零工勞動力與大資本數字平臺兩個方面簡要提出政策建議。
第一,提高對零工勞動力權益的保護力度。勞動者個人相對于企業本身就處于弱勢地位,零工經濟模式中的用人單位,尤其是大資本數字平臺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其應當承擔的部分責任,這時就應當更加提高對勞動者的保護力度。對于一些想要借助零工經濟模式惡意規避用人單位必須承擔的責任的行為,必須嚴格進行管制。必須切實保護兼職、自由職業者以及合同工這三類零工經濟勞動服務提供者的合法利益,尤其是提高對零工經濟從業者的個人保障,堅決打擊發布虛假招聘信息的行為。
第二,對大資本數字平臺公司的監管要比對一般行業的監管嚴格,尤其是嚴格管制平臺企業濫用市場控制地位以及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大資本數字平臺公司有形成壟斷的趨勢,是市場監管的重點,但是不能過度限制數字產業生產規模的擴大。為了緩和數字經濟時代的勞資矛盾,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政策的制定應當規范市場準入、企業合并并購、零工招聘條件等。在保障零工勞動力基本權益的同時,防止大資本數字平臺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對一些經營業績優良的中小企業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讓資源更加有效地流動。對于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而言,雇傭勞動不必通過固定的形式進行,零工經濟雇傭勞動形式的靈活性不可否認地減少了交易成本,在提倡這種雇傭形式的同時,要清晰地認識到基于該種雇傭形式下資本與勞動的內在關系,并制定相應的市場規范,從而在發展零工經濟的同時,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