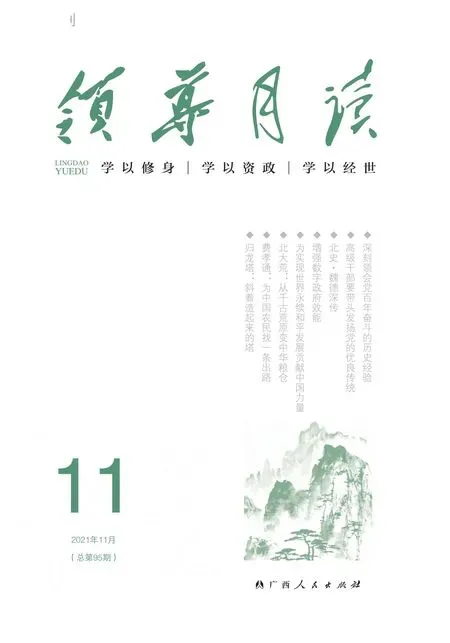管子·牧民第一
[春秋]管 仲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圣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唯有道者能備患于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于時而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后于事,吝于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原文據中華書局2004年版《管子校注》)
【譯文】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鄉,鄉不能治好。按照治鄉的要求治理國,國不能治好。按照治國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應該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鄉的要求治鄉,按照治國的要求治國,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因為不同姓,就不聽取外姓人的意見。不要因為不同鄉,就不采納外鄉人的辦法。諸侯國不要因為不同國,就不聽從別國人的主張。像天地對待萬物,不應有偏私偏愛。像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氣度。駕馭人民奔什么方向,看君主重視什么。引導人民走什么門路,看君主提倡什么。號召人民走什么途徑,看君主的好惡是什么。君主追求的東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愛吃的東西,臣下就想嘗試;君主喜歡的事情,臣下就想實行;君主厭惡的事情,臣下就想規避。因此,君主不要掩蔽自己的過錯,不要任意刪改國家的法度,否則,賢者將無法幫助你。在室內講話,要使全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講話,要使滿堂的人知道,這樣開誠布公,才稱得上圣明的君主。單靠城郭溝渠,不一定能固守疆土;僅有強大的武力和裝備,不一定能抵御敵人;地大物博,群眾不一定就擁護。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才可避免災禍的發生。天下不怕沒有能臣,怕的是沒有明君去使用他們。天下不怕沒有財貨,怕的是無人去管理它們。所以,通曉天時的人可以被任用為長官,沒有私心的人可以被安排為官吏。通曉天時、善于用財,而又能任用官吏的人就可以被奉為君主了。處事遲鈍的人總是落后于形勢,吝嗇財物的人總是無人親近,偏信小人的人總是容易失掉賢能的人才。
【簡析】
本文強調賢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應該注意幾個方面。首先應該具體分析全國各地不同的國情與民情,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建立制度與執行政令。尤其是“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的治國理念深得《道德經》“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這一名言的哲理精髓。《道德經》旨在強調大公無私,《管子》則旨在強調實事求是,看似有所不同,實則二者都是在強調治理民事要“順其自然”,盡可能避免主觀意見的干擾。所以接下來作者進一步闡述君主應該像天地對待萬物、日月普照一切那樣沒有什么偏私偏愛,雖然不能照搬其他地方的經驗,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忽視別處行之有效的辦法與主張而不予吸收學習。作者接下來將其落實到具體的為君之道上來,首先順著君主不能偏私偏愛的角度,立刻警醒君主的好惡會成為臣民的風向標,一旦整個國家都隨著君主的好惡來發展,就會非常危險。但是,由于君主也是人,不可避免地會有所好惡,作者馬上提出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即要求君主凡事都開誠布公地征求大家的意見,并且不要掩飾自己的過錯,這樣才能通過群策群力來避免君主的偏向。順著“言室滿室,言堂滿堂”這一邏輯,作者又進而從國家安全的層面,來高度警醒君主依靠堅固的城郭溝渠與強大武力裝備都不一定能夠維持國家的安穩,避免災禍的發生,只有全面地任用賢能來管理百姓、應對時勢,才能維持和諧穩定。由此可見,本文最終從理念回歸到現實,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與指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