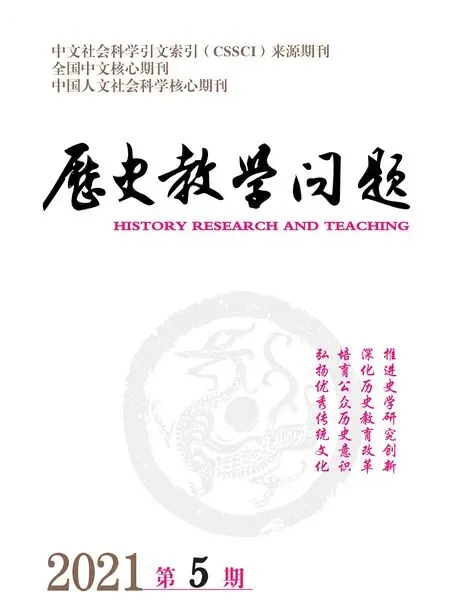“以思政帶學科”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
鄧 軍
新中國一經成立,思政課便成為高校必修課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思政課和專業課的關系詮釋了“紅”與“專”的關系在新中國70 年中的轉變。“又紅又專”是新中國成立頭30 年的特點,改革開放之后,思政課與專業課逐漸趨向于各守一方,在“紅”與“專”之間劃出一條界限。十八大召開之后,“課程思政”這一提法開始在高校當中逐漸明確,旨在打破思政課與專業課“紅”與“專”的畛域。2020 年5 月28日,教育部印發《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的通知,要求高校所有課程必須承擔起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專業課程“紅”的問題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如何將“紅”與“專”結合起來,成為高校課程思政是否成功的關鍵;對于一線的教師來說,挑戰在于如何將其落實。
絕大部分的高校專業課與思政課內容不一樣,其“課程思政”的突破口多在專業內部尋找“紅”的結合點。然而,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這門課卻與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門課程幾乎重合,這為我們思考“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切入口。
一、“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之歷史
當我們一想到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與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第一反應往往是兩者差異很大,而且理由大致不差,即前者是思政課的一部分,目標在于培養所有大學生“紅”的情懷;后者是中國通史課程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培養歷史系學生“專”的基礎。然而,一般人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門課何以成為思政課,卻不甚了解,而對其歷史的了解,將有助于我們去剖析“以思政帶學科”的可能性。
從名稱上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門課出現的時間并不長。2005 年2 月17 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教育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05”方案),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設置做出具體要求,“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成為高校本科生必修的四門思想政治理論課之一。它要求從歷史教育的角度承擔起思想政治理論的任務,幫助大學生認識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程及其內在的規律性,了解國史、國情,深刻領會歷史和人民是怎樣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①本書課題組編:《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1—2 頁。
然而,這并不意味此前的思政課便沒有歷史教育,而是以其它的名字出現在課程體系當中。在新中國成立伊始的1950 年初,高教部明確規定全國高等院校取消國民黨“黨義”課程,代之以“新民主主義論”(1953 年改為“中國革命史”)“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等三門課。其中,“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史”便是“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前身,“05”方案與其教學目標基本一致。此時,“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史”所講授的時間范圍是1919 年到1949 年,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主線,與黨史基本重合。
此后,隨著社會階段的變化,這門課又經過了幾次變動。②羅建平、胡繼冬:《建國以來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課程設置的歷史沿革》,《唐山師范學院學報》2007 年第3 期,第103—105 頁。1956 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高教部與教育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批示,開始在全國高等學校普遍開設“社會主義教育”課程,取代其它三門課程,“中國革命史”被取消。其后,由于中蘇論戰和國內的“四清”運動的開展,中共中央于1964 年下發關于高校政治理論課的意見,要求高校開設“中共黨史”代替“中國革命史”。文化大革命期間,該課基本停止。改革開放之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推出“85 方案”,重設“中國革命史”。其中,最大的變化在于前溯的時間,其起訖時間自1840 年至1956 年,而社會主義建設另設課程講授。自此,這門課的起始時間與中國近現代史重合,這表明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將自身的歷史及其領導的革命,放置于更宏大的近代中國與世界的沖突當中。
1998 年,因著“十五大”將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推出“98 方案”,以“毛澤東思想概論”代替“中國革命史”,重心在探討中國獨特的革命理論與實踐經驗,并建立其與新增的“鄧小平理論概論”之間的連續關系。2005 年,隨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發展,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推出“05 方案”,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形成一個獨立課程,而另設“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便要求“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超越中共黨史與中國革命史,在1840年至“十九大”這個歷史長時段里去尋求中國社會獨特的發展規律。
可以看到,“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門課的歷史與新中國的變化緊密相連,反映了新中國每一次重要的政治變動。在“05 方案”當中,思政課的重心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與實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過往所承擔的理論內容被劃出去,這使得其歷史性被凸顯出來。可以說,在新時期,沒有思政性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是不行的;同樣,沒有歷史性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也是不行的。
二、“以思政帶學科”的教學嘗試
在大學生當中,常常有這樣一種看法:他們喜歡歷史,但不喜歡“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句話背后的意思是“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不是歷史課,它缺少歷史細節,缺少真實的“人”。這門課設置的初衷是通過歷史教育讓大學生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困境與選擇,但是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所有的歷史結論都是在為政治做注腳,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被極度的簡化。這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現,認為歷史的細節和自身邏輯不足以支撐思想政治教育。它導致兩種結果,一種是學生不加反思、機械地接受各種結論,一種是學生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結論產生懷疑和反感,這兩者都與思政課的目標背道而馳。在某種意義上說,“以思政帶學科”,加強“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一課的歷史性,是完成思政目標的內在需求與最佳途徑。
具體來說,“以思政帶學科”首先需要的就是“論從史出”,其次是再現真實的“人”。我們以大家非常熟悉的論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例。大學生在中學里便學過的,并把它看成老生常談,但是讓大學生從歷史的角度去解釋的時候,又覺得沒什么好講。無非是傳統中國是封建社會,由于鴉片戰爭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一減一加,就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表面上看沒什么問題,卻極度簡化了其中的內涵,從而使這個結論看起來更像“口號”,而不是“歷史”。
就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來說,在教科書與過往的教學當中,更多強調的社會特征的變化,很少從“人”的思維特征去挖掘。當我們以思維方式切入時,詢問學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對“人”到底意味著什么?“人”在這種變遷當中世界觀如何被打破,又如何重建?當時人的命運如何與時代緊系在一起?學生將會重新思考他們熟悉的答案。
我們常說傳統中國是封建社會,然后展現它的繁榮與衰落,帶著傷逝之感進入中國近現代史的學習。實際上,揭示這一套政治與倫理體制背后的“天下體系”更為重要,因其塑造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們的思維方式。在“天下體系”之下,它認為中國居于世界的中心,根據文明的遠近來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二千年來中國大體上如此理解自己,中國人也大體如此理解自我。鴉片戰爭以后,西方人不僅帶來炮艦,而且帶來了不同的世界觀,即世界是由民族國家組成,世界如果存在中心,那么這個中心不再是中國。從這個意義上,中西沖突亦是兩種世界觀的沖突。從1840 年開始,清朝政府一直在維護著我們今天看起來很可笑的利益,然而究其根底在于“天下體系”所要維護的利益和民族國家所要維護的利益不一致。清朝士人承受近兩千年的遺產,他們負重面對新的世界觀。當不同的世界觀放在眼前時,他們只能調用過去的資源來理解和調適,步履維艱。當我們苛責鴉片戰爭之后20 年,才開始洋務運動;批評近代改革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總是變革不徹底。如果換個角度,不正說明近代中國變革是困難重重,而每前進一小步都是以撕裂自我的方式獲得的。歷史需要換位思考,當我們進一步讓學生假設自己處于那個時代,他們會如何選擇。這時,學生才能逐漸從感性與理性上去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既是中國屈辱的歷史,又是中國人一步一步變革和努力的歷史,更是近代中國人的“心靈史”,也是每一個大學生自己的“前史”,歷史與現實的延續性被建立起來。
不僅如此,“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更是個人安身立命崩塌的過程。如兩廣總督葉名琛(1807—1859),他常常被當做歷史的笑話,被稱為“六不總督”: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是我們看他的經歷,他少年得志,不到18 歲便考取貢生,38 歲任廣東巡撫,44歲任兩廣總督。他為人正直、為官清廉。可是他卻趕上了鴉片戰爭之后的廣東,政府要求他拒洋人于廣州城外,洋人按照條約要進城、要修約,他能如何?1859 年,他“不走”而被英國人俘虜至印度,他忍辱負重期望面見英國女王,勸她“弭兵”。在知道沒有希望后,便絕食而亡。①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年,第165—221 頁。在印度所寫的詩里,他自比宋國大夫向戌、漢代蘇武、北宋范仲淹、南宋文天祥。如果還在過去的“天下秩序”當中,也許他可以“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身前身后名”,完成其“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理想。然而,他碰到了這樣一個時代,生生變成了歷史的笑話。這何其可悲!我們要讓學生從中感知大時代之于個人的意義,理解比評價更重要。
這樣,從宏觀的社會、思維變遷到個人的生命歷程的呈現,“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再是一個空洞的結論。史料考證、歷史細節、邏輯嚴謹,這幾大史學元素的結合,讓當代大學生得以與1840 年代后的歷史時代與人物進行一場跨時空對話。“論從史出”與真實的歷史人物不但未抹殺政治思想教育的力度,反而能讓大學生更具反思性地理解國史、國情。
至此,我們仍不能說“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是一門歷史課,即使它充分借重了歷史學科的研究,然而其“論從史出”與呈現真實的歷史人物展現的主要是思想政治的維度,連接的是近現代中國的家國情懷與道路選擇。然而,歷史史料、方法與研究在“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運用,才使得這門思政課得以落地,并實現其思政價值。
三、“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互鑒的一點看法
如果未有“課程思政”的要求,這兩門課可以繼續持守“學術歸于學術、思政歸于思政”的理念。然而,在教育部的新要求之下,歷史學科中國近現代史的“課程思政”該如何進行,頗值得探討。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這門思政課已經歷了70 余年的探索,其性質、論域與界限已相對成熟。以其作為參照系來思考歷史學科中國近現代史的“課程思政”,不失為一個方法。
“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是要求中國所有的大學課程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這兩者似乎是越來越趨同。然而,基于歷史學科中國近現代史這門課,筆者認為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分別”,“課程思政”要把握好“限度”。如果將中國近現代史變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看似符合“課程思政”的要求,但最終取消的可能是中國近現代史存在的必要性。“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四個完全相同的字,但是并非完全要用思政取代學科。從某種程度上說,“思政課程”的教學目標與歷史結論是既定的,而“課程思政”仍然是基于其本學科的性質而存在,歷史學科的特點便在于其開放性。歷史學科可能不一定需要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有學者認為近代開始于宋代,有學者認為開始于1600 年前后,有學者認為開始于太平天國的覆滅),也不一定需要認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是把它們作為一種學術觀點予以探討,為學術留得爭鳴的空間。
如果思政結論只是歷史學科的一種學術觀點,那么“課程思政”體現在哪,這便是筆者說的第二點,即借鑒“思政課程”的家國情懷。說到底,歷史是一門人文學科,無論是否價值中立,它背后都存在著某種價值判斷。1840 年至今,無論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還是被淹沒在歷史中的微小事;無論是有著豐功偉績的大人物,還是籍籍無名的小人物,只要中國近現代史能夠為它們發聲,我們就一定能夠從中推出“個人—家—國—天下”,亦能推出“天下—國—家—個人”。如果中國近現代史能夠多方面、多層次發掘和解釋歷史與人,不是正好能與“思政課”形成互補,從而達成“課程思政”與“思政課程”設計的初衷。
以上,便是筆者所設想的“思政課程”與“課程思政”的分別與統一。
——評《新時代高校思政課的打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