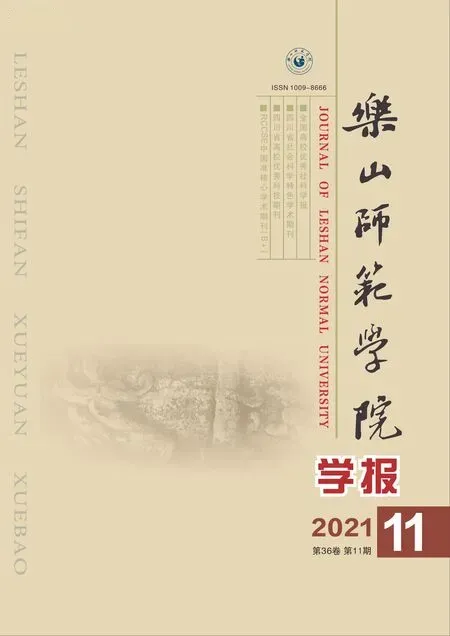別樣的“文軍西征”與“邊疆再造”
——評介《抗戰建國與邊疆學術: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邊疆研究》
封 磊
(延安大學 歷史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1986 年01 月28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視察浙江大學,贊譽浙大在抗戰期間跨越浙、贛、湘、粵、桂、黔六省的西遷是“一支文軍的長征”。2008 年,中央電視臺《見證》欄目組通過對歷史文獻、沿線遺跡以及親歷者口述等史料的挖掘與呈現,與浙大聯合攝制十集大型電視紀錄片,記述抗戰期間浙大西遷辦學的光榮歷程,片名即為《文軍西征》。“文軍西征”同樣適用于抗戰時期中國文化教育界整體的西遷辦學的核心樣態,以及這一壯舉所內蘊的現實意義與文化價值,最為人們熟知并享有盛譽的西南聯大即是明例。
學界對抗戰時期的“文軍西征”的史實及意義的研究指向多在三個層面:就西遷的主體構成而言,多指向國立大學(科研機構),間或有少量私立大學;就西遷方向性或目的性空間來說,均指向國土內部的邊緣空間;就辦學成就而論,多指向當時及后來在辦學規模、人才培養及科學研究等方面有著較高教育產出、豐厚歷史遺產、具有較高社會盛譽的高校(機構)。這意味著,私立大學往往被學界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盲視”;特別是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無論如何都不可缺席的教會大學,其在西遷的學術版圖中的存在樣態及相關學者的學術作為與生命歷程,多成學術史研究中易被遺忘的存在。
抗戰時期內遷高校的目的地,在時人眼中多被視為“邊疆”。在中國歷代政府對邊緣性疆域采取特殊的政策治理的歷程中,“核心—邊緣”的“邊疆”觀念已持續近兩千多年。[1]但在近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邊疆”是被重新發現并建構而成的,其動力來自近代民族主權國家的出現,進而在國與國之間產生明確的邊界,而邊疆即國境內鄰近邊界的區域。從既有的資料和研究來看,即便到抗戰時期,國人對處于核心區之外而特殊存在的“邊疆”的認知還相當模糊。而凝聚了全民意志并傾注全民力量的抗日戰爭,客觀上加速了學界對包括邊緣空間及其人群的疆土的重新認知與建構,從國家整體的角度進行調查研究,并將邊疆建設與國家重建關聯與共,以適應構建一個以中華民族為一體的現代主權國家的需要。大批學者履足邊疆,將各種文化資源、學科知識、理論方法帶入邊疆,并將所學廣泛、深入地運用到邊疆研究中。這種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指導下的科學化、學科化、專業化的研究實踐,并以發表學術論文或出版專著的呈現形式,與此前的輿地沿革考索、方志學或游記雜錄的學術傳統已經大相徑庭。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時期西遷高校的邊疆研究,無論是在研究對象的廣泛性、研究空間的整體性,還是研究成果的深刻性以及學術影響的深遠性,都無異于是對邊疆的“再造”。[2]
在對這一“文軍西征”與“邊疆再造”的學術史的深入研究上,學界多措意于對由北大、清華、南開遷至昆明組建的西南聯大與“魁閣學派”的學術遺產的研究,而對同期西遷的其他教育機構則較為零星;多投注于南京、北京、上海、重慶等地知名高校或機構,較少注意對同期西遷至如成都、西安、蘭州等西部城市高校。對民國時期邊疆學術史的研究成果,多矚目于少數知名學者,鮮少從高校史的角度切入;以教會大學的邊疆服務與民族研究為主旨的則更是稀有。這種有意或無意的遮蔽或回避,對于學術史研究本身來說是一個顯見的缺憾。
新近出版的汪洪亮著《抗戰建國與邊疆學術: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邊疆研究》(中華書局2019 年12 月,以下簡稱《抗戰建國與邊疆學術》),即是彌補這一學術現狀的精心之作。該著以抗戰軍先后分別從南京、濟南、北平等東部城市西遷至成都華西壩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齊魯大學、燕京大學,與東道主華西協合大學等聯合辦學,以及主要以藏羌彝走廊區域(藏邊社會)為研究特色的邊疆學術為主體內容,并對這一歷程中鮮為人知的邊疆學術理念及其在現代邊疆學科構建中的努力與成效,給予深入細致的探索。該著在宏觀性的結構透視、微觀性的聚焦考察等方面頗有特色。
一、宏觀性的結構透視
盡管以教會大學為研究內容并非首創,但作者立足于現代高等教育史與邊疆研究學術史視域,注重對華西壩邊疆學人與學術、學人與時局的交互關系的重點關懷,使其達到了宏觀勾勒與微觀細描的統一。
(一)華西壩教會五大學邊疆研究的淵源與發展脈絡
外地四所教會大學陸續集結至成都華西壩,在教學科研資源各方面都得到東道主華西大學大力支持,組成了一個和而不同的辦學聯合體。這個聯合體在教學行政管理上采取聯席會議制,秉持平等協商、主客一體的辦學原則,確保五大學教育教學活動的高效聯動;在人才培養上采取師資互聘、課程整合、自由選課、學分互認等舉措,確保師資、學生、專業、課程等的優勢互補;在學術研究上聯合舉辦學術講座、創辦研究機構、合作實驗研究,實現了現代學術團隊的組建與學術資源的聯動共享。一個最為明顯的例證,即是五大學聯合編輯、出版學術性刊物,共同發起、組織并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因此,該著認為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辦學模式為“西南聯合教會大學”(汪著第3 頁)。
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邊疆研究雖西遷而來,但殊途同歸,開始出現新的面相,即實現了此前以外國學者為主導到以中國籍學者為主體的研究格局的轉變,并在理論方法上實現本土化,最終形成華西壩邊疆研究學術共同體。如燕京大學,從以往注重對古代疆域沿革史的研究向注重研究當時的邊疆問題的轉變,金陵大學經歷了從傳統史地學到以民族學、社會學研究邊疆問題的學術轉向;齊魯大學、金陵女子大學西遷之前并無邊疆研究的學術傳統,但在西遷至華西壩后則迅速轉向融入到邊疆研究的學術潮流中,且表現相當不俗。這種轉變,不可謂不明顯,也更顯教會大學的學術關懷與戰時國家需要的共振(汪著第33-67 頁)。
(二)華西壩五教會大學邊疆研究的學術幽懷與核心特質
《抗戰建國與邊疆學術》的鮮明特色,即是對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邊疆研究的淵源與學術特征給予了深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實證性研究。正如作者指出的,該書更關注華西教會五大學學者的學術選擇及其學術論著,從中管窺學人的時局觀念、學術情懷及其對改良邊政與整合國族的洞見(汪著第13 頁)。他們的時局觀念,反映在學術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中,鮮明的例證即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史地學者,意識到抗戰建國與國家政治民族的同構關系,力圖從整體性上闡發具有抗日情感一體化的政治民族,呼吁構建現代國族以因應時局;再如民族學家馬長壽從歷史與內政的角度來區別近代已降的“邊疆”和“民族”問題,徐益棠從邊官、邊民與邊政的互動關系來闡釋當時邊疆工作存在的困境與可能的出路,體現出華西壩邊疆研究學人群以學術研究因應時局和國家需要的愛國精神。
此外,華西壩教會五大學另一鮮明的學術特質,即以邊疆研究來服務于“邊疆服務”,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與實踐風格。如實踐李安宅提出的研究、服務、訓練為一體的主張,實現了邊疆學者與邊疆工作者在邊疆社會建設中的密切互動,五大學師生以其專業性的學科知識與現代的學科理念與組織形式,經常赴藏羌彝走廊區域進行田野調查與實地服務;還以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和生計改良等具體舉措,在為邊民服務和增進民族融合方面都有實在而具體的收獲。汪洪亮利用教會大學的檔案、學人日記、存世報刊等多重史料,完整、清晰地揭示了華西五大學的邊疆社會服務的詳細情況,深刻而生動地揭示了華西邊疆研究的應用性特征。
(三)近代西學中國化潮流下華西壩邊疆研究的學科化努力
晚清以降,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出現了學術分科。20 世紀初以來在西方學術紛來之際,中國現代學術的學術分科趨勢與潮流更加明顯。[3]以分科為基準來認識和研究中國學問,成為學人所遵循的主流取向,而以分科為基準強調學術的學科化大約是20 世紀中國學術與此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4]但近年來在有關近代邊疆學產生及發展的研討中,學者們多認為是民國時期有著西學背景的學人積極參與將西方學術體系“中國化”的自身學科構建的嘗試,卻較少關切到20 世紀初以來在西學東涌之際,中國現代學術自身的分科化、科學化的整體趨勢。若將邊疆學術研究置于這一潮流來審視,從邊疆研究熱潮的迭次出現到學者們呼吁建立邊政學這一學術脈絡似也應當包含在這一學術理路之內。抗戰前夕即有學者指出:“我們研究科學往往分門別類,這種習慣本是為了便利工作而養成的。但就科學界近日一般趨勢看來,似乎有過分著重科學門類的區別而忽略它們共同性的危險……邊疆科學的發展特別困難是常常要遇及的。好比有時需要兩種訓練和習慣都不同的專家共同合作研究異同問題,進行的困難又非普通一般人所能預料及的。”正是中國學術自身也處于愈益強烈的分科治學之流中并以此來因應學科細化之后的學術格局,才有學者明確提出應將邊疆作為一門學科,科學地加以研究與整合,在獨立中與其他學科攜進研究,以及大學設立邊疆學的五點建議。[5]這一洞見與呼吁,其實在抗戰前即已被闡發。
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均系近代后由西方稗販而來。中國學者知識體系與學術實踐不可避免地參與到西方學科體系在跨文化空間中的傳播與建構。這一學術路徑的淵源,促使中國人類學者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多以對漢人等核心區或特定社區、偏遠地區或少數族群作為研究對象。這一點,費孝通先生晚年也曾指出,英國的功能學派(社會人類學)與美國的芝加哥學派(文化人類學)的相互靠近與互鑒,促成了中國人類學與社會學在1935 年的合流;而這兩個學派研究的共通之處即是在此前列強各自的殖民地的邊緣空間下的土著族群,而非本土的或本民族人群。[6]有學者指出,20 世紀30-40 年代早期中國功能主義人類學者從事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與其說關注的是中國,倒不如說是以西方視角觀察中國與解決西方問題。[7]然而抗日戰爭導致的中國學術版圖發生的自東向西的巨變,中斷了西學在核心區域的研究與應用。正如林耀華先生所言,日本侵華“中斷了中國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的正常進程,從而斷送了這些學科在那個時代取得應有成果的現實可能。我本人研究方向的改變就是一個例子。正是這場戰爭把我從一個研究漢人社會的社會人類學者變成了主要研究少數民族的民族學者。”[8]全面抗戰爆發后,東部文教界的西遷大軍西遷、集結于西部地區,邊緣地域及其人群順勢進入了社會科學家們的視野,眾學科、眾學人不約而同地轉向邊疆民族研究,實現了從中原到邊疆、從西北到西南、從官員到學者、從漢人到少數族群的時空性、學術性的轉型。而此時學者們的學術生活甚至學術事業或可概括為“學術與邊疆共進,足跡與邊疆同涉,文字與國族同書,學理與國族同構”。[9]
很顯然,作者汪洪亮洞悉并抓住了這一學術轉型的核心特質[10](汪著第53 頁),繼續在近代中國邊疆研究的學術轉型的課題研究中深耕寬拓,并延展至以高校、學者、學社等為中心的廣袤領域。而作者矚目于華西壩教會五大學這個特定群體,有利于填補過去邊疆學術史書寫中一直缺失的一環,讓很多相關學人與論著重新進入學界視野。難能可貴的是,從史料發掘與使用情況來看,作者還利用校史、校刊、檔案、報紙、雜志、論著、學人日記、書信等多種史料,對戰時教會五大學與學人的學術選擇、因應之舉與邊疆心曲均給予了細致、深入的發掘和述論,讓這一段鮮為人知的學術群體及其學術業績在塵封已久的史料中清晰、鮮活起來。
二、微觀性的聚焦考察
目前邊疆學界對學者、團體和相關刊物及其生命歷程、學術思想與學術實踐活動的研究相對滯后,需要對學人的集體群像、學術機制、學術生活乃至生命樣態進行細致挖掘與呈現。在《抗戰建國與邊疆學術》中,作者汪洪亮特別注意探究華西壩邊疆學人的“朋友圈”和“生活圈”。這一視角的轉向與努力,使該著在宏觀性的“骨架”搭建的基礎上,更顯“血肉豐滿”。
一是以專家、學會、團體、研究室等機構的組織化研究轉向學術化、學科化的路徑為例,具體到邊疆學術研究時,則體現在研究人員的專業化、研究水平的科學化、研究過程的規范化、研究領域的專門化、研究成果的理論化。一些高校設立與邊疆相關的專業,構建邊疆學術的學科體系,并培養邊疆研究的的專門人才。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為我們提供了明晰而完整的例證。
二是大學是現代學術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華西壩教會五大學成立了專事邊疆研究的機構與團體。諸如華西大學設立的邊疆研究學會、邊疆研究所、社會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金陵大學設立的社會學系邊疆研究室、中國文化研究所,齊魯大學下設的國學研究所、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邊疆服務部,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等。學者群體也因之而集結。諸如華西大學之葛維漢、鄭德坤、李安宅、聞宥、任乃強、于式玉、蔣旨昂等,齊魯大學之顧頡剛、張伯懷、侯寶璋、張維華等,金陵大學之徐益棠、柯象峰、馬長壽、衛惠林等,金陵女子大學之劉恩蘭,燕京大學之林耀華、李有義等諸多學者。這批學人多有留學歐美的經歷,見長于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理論與方法,多在民國學術界聲名鵲起或嶄露頭角,有的后來成為新中國相關學科的中堅和翹楚。
適逢國家處于危亡之秋,華西壩邊疆學者大多具有學術救國的積極性與社會責任感,有志于通過邊疆實地調查尋求邊疆社會問題的解決之策。他們在藏羌彝社會開創性的學術實踐以及留下的眾多著述,至今仍然是相關學科或專業領域難以繞過的經典之作。如任乃強先生對藏學的研究、李安宅于式玉夫婦對甘南藏族的研究,徐益棠、林耀華等先生對涼山彝族的研究等。這些學者雖然身處華西,但身后往往關聯著學緣、地緣因素,與各地學界保持著持續且緊密的聯系。正是在成都華西壩時期,這批學人群完成了在邊疆民族學術研究史上的集體亮相,并編制和演繹了一幅國家艱危時局下的民族生存史、群體生活史、學者生命史所交織的歷史畫卷。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汪洪亮并不滿足于對學人互動的考察與呈現,還努力嘗試挖掘和揭示學術互動背后的生活細節(即作者所稱的“生活圈”)。作者利用檔案詳細考察了由華西大學文學院院長羅忠恕發起成立的東西文化學社,為籌集經費而頻繁奔走于中央、地方的軍政大員與學人團體之間的曲折歷經;利用《顧頡剛日記》揭示顧先生籌備成立中國邊疆學會的經過與心境,還對顧先生在華西壩期間活動于學、政、商界的“朋友圈”給予細致耙梳和呈現。這種呈現不是宏觀勾勒,而是具體到了聚談、開會、宴請、互訪、講座、出游、看戲等日常性活動。作為以邊疆學術研究為志業的學人,日常性的活動幾乎無不圍繞學術視野開展。甚至可以說,這些日常活動已經成為學人學術生活不能超脫的部分。而這在以往的邊疆學術史研究視域中則多被忽視。該著可謂筆觸細膩、考證詳實,以生活史視域,將戰時華西壩學人的生活樣態給予挖掘和描述,使華西壩學人的日常形象與生活心曲得以靈動鮮活起來。
三是呈現教會五大學邊疆研究成果——刊物。近代已降,以學會、報刊/雜志為代表的團體、媒介全面參與了學術的發展過程,并充當學人、學術與政治、社會之間互動的橋梁。形式多樣和數量眾多的報刊雜志,成為學者宣達其社會關懷與學術思考的有力載體。而相對穩定的邊疆研究群體的形成與匯聚,以及研究社團和研究內容旨趣的相對一致,也促進了學術事業的發展,而專業性的刊物則為學者們提供了呈現其研究成果的動態機制。
近代邊疆研究成果的呈現,自然與刊物的創辦與維持密不可分。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創辦的英文刊物《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即成為國際性刊物;金陵大學衛惠林先生主持的《邊疆研究通訊》和徐益棠先生負責的《邊疆研究論叢》,成為華西壩邊疆學人的學術田園;齊魯大學顧頡剛先生編輯出版《齊魯學報》《國學季刊》《責善半月刊》等多種刊物。此外,如《邊政公論》等刊物也成為華西壩學人學術成果匯集之刊物。這些學術刊物主要以邊疆史地、民族文化、社會問題等為主要內容,既注重學科學理的介紹與闡發,也注重在實地調查基礎上的實證性、基礎性研究,其刊發的成果涉及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地理學等多個領域。這些刊物具有同人刊物的特征:有共同的學術志趣和治學風格、有基本固定的編輯群與作者群。這些刊物所構成的人脈網絡,也構成了當時邊疆研究和邊政學科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作者在著中所論:華西壩邊疆刊物“承載了研究時與校內外其他機構、刊物、人員之工作聯系的功能”,“成為抗戰時期邊疆研究的重要學術平臺”;這些刊物刊發的學術成果,“展示了五大學邊疆研究者的知識視野和思想境界,也體現了民族學和人類學等西學的本土化實踐以及多種學科在邊疆研究中的運用情況”(汪著第115 頁)。
綜上,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邊疆研究呈現明顯的專門化、學科化的趨勢,是華西壩學人及其機構自身建設、發展的日益成長壯大的體現。這反映了在蓉華西壩五所教會大學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以其學術事業承擔對國家民族的重新構建,為戰后現代中國國家、民族、社會、學術的重構提供了別樣的學術支撐和作為(典型代表即是以1950 年以李安宅為首的華西大學邊疆研究所同仁參加十八軍進藏)。
三、可能存在的些許不足
誠如作者所論,學術史研究不僅要關注學術思潮、學術機構與刊物,還要研究學者及其作品,關注其思想和行為(汪著第15 頁)。但可能是緣于該著側重于對華西壩教會五大學的邊疆研究的整體性研究,對學術機構(某種程度上來說,五教會大學本身即是學術機構)的發展脈絡,對學者個人的學術作品和學術思想的研究濃墨重筆,如對李安宅、顧頡剛等人的研究頗為厚實,而對學術機構本身的運作機制、經費使用、師資調配等情況,以及對展示邊疆學人的研究論著及其學術水準的刊物本身特征的揭示,則細致不足。如《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作為一份當時頗有國際影響力的專業刊物,如能以此為媒介,對其刊文情況、文章結構、學者群體及其地域分布等給予量化,可能更鮮明凸顯其學術特色。
也許是緣于要揭示成都華西壩邊疆學人致力于民族復興和國族構建的學術努力的研究主旨,即“五大學的邊疆研究反映了政、學兩界構建中華國族的努力和民族文化多元的事實”(第13-14 頁),故而在揭示華西壩邊疆學者運用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來研究邊地民族的學術自覺上用力頗深,但關于這批學人與政治,尤其是與戰時國民政府的互動,包括國民政府對這批學人的學術作為的回應,則是頗為薄弱甚至幾乎毫無揭橥的領域。作者在文末也指出這一明顯存在的問題。此外,還同樣缺乏對“教會大學學者與非教會大學學者,外籍學者與中國籍學者如何看待中國的時局與邊政”的比較研究,而使這一既定的研究目標似乎頗為稀薄。此外,還需指出另一缺憾,如若“華西學派”確如人類學的南北學兩派一般自成一派的話,那么華西學派在人類學與邊疆民族研究中到底在何種維度、何種程度及何種高度上能實現對自我的支撐與對他者的超越。這恐怕也是一個必須回答、佐證和論證的問題。
盡管作者立足社會史視角,盡力避免學術史研究中“人的隱去”的弊端,但相對來說,對華西壩邊疆學人的“學術圈”和“朋友圈”的揭示仍是較為薄弱的部分。若能從戰時華西壩學人的學術、政治、生活之間的多元交織及其選擇心曲這一方向深入挖掘和解釋,則該著不僅堪稱完整的邊疆學術史,還是一部融學術性、可讀性、趣味性于一體的力作。這或許是對筆者的苛責,但也著實寄托了邊疆學術史研究者對于這段時局、政治、邊疆、學術、學人交織激蕩的學術場域給予深入研究的熱切期待。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對抗戰時期邊疆研究學者群體、思潮、著作的學術史研究,真正引起學人的關注并取得進展還是近十余年的事情;可以說,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學界對這批學人及其著作的學術回顧與思想的再研究是欠缺的。[11]雖將其作為研究對象、抑或視為重要的學術文獻,但對其進行細致、量化、客觀的學理研究仍顯薄弱。而戰時華西邊疆研究作為民國時期邊疆學術研究場域中的一個特殊的存在尤顯珍貴。該著作者汪洪亮數十年來深耕于邊疆民族學術史研究,成果豐碩,多數成果已成學界被高引文獻,足見其用功之勤、用力之深。相信該著的出版,可與其另一部專著——《民國時期的邊政與邊政學(1931—1948)》(人民出版社,2014 年),構成一個完整的邊疆研究系列,助力這一研究領域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