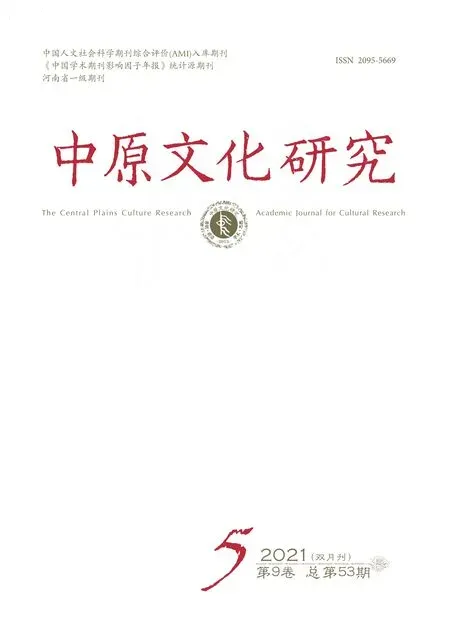論陜北漢畫像石中荊軻刺秦王故事的隱喻與象征
劉向斌 劉國偉
荊軻刺秦王故事或先流傳于民間,后載錄于《戰國策》《史記》等典籍中。西漢后期,該故事又以圖像的形式時時出現在漢畫像石中,甚至成為漢畫像石的表現主題之一。其實,漢代人在以文本或圖像的形式講述荊軻刺秦王故事時有著表達觀念的深層用意。因時代不同、載體有別、敘事方式變化,荊軻刺秦王故事的隱喻內涵也隨之發生變化。在《戰國策》《史記》等歷史文本中,其隱喻內涵便因時代不同而變化。當該故事以圖像形式出現于漢畫像石中時,其隱喻內涵也隨載體不同相應地再次發生了變化,對此學者提出了喜好歷史說、嘲笑秦王說、裝飾美化說等觀點。不過,通過考察陜北漢畫像石,荊軻刺秦王故事的隱喻內涵遠非上述諸說所能涵蓋,而具有頗為獨特的隱喻指向。
一、荊軻刺秦王故事的隱喻變化
在《戰國策·燕策三》中,秦即將滅掉六國、實現大一統是該故事的敘事背景[1]975。這其實是統一勢力與反統一勢力間的較量。按照《戰國策》的介紹,故事起因于燕太子丹入質秦國的“見陵之怨”。所以,太子丹返回燕國后決意抗秦,甚至收留了逃亡至燕的秦將樊於期,這讓太傅鞠武深為擔憂,認為其做法將使“秦王之暴積怨于燕”,無異于“委肉當餓虎之蹊”。為防不測,他向太子舉薦了“智深”“勇沉”的田光。而田光自感老弱無力,又舉薦了荊軻。于是,荊軻拜見了太子丹,才知其欲效曹沫劫桓公故事,“劫秦王”以使其“悉反諸侯之侵地”。如此看來,太子丹似乎并非為一己私利,而有維護各諸侯利益的救世愿望。
荊軻為報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決定冒險一搏。為了取信于秦王,落實“劫而不得便殺之”的刺殺方案,他也提前做了準備。他帶著一顆樊於期的頭顱、一張燕國的督亢地圖和一把淬了毒藥的匕首,與燕國勇士秦武陽結伴出使秦國。如果從道德層面來看,秦王是侵略者,太子丹等自然是反侵略者,因此荊軻刺秦王是用弱者的正義自衛反抗強者的非正義侵略。而結果是荊軻與太子丹被殺、薊城失陷、燕國滅亡。可以看出,《戰國策》中的荊軻具有講信義、重承諾的俠士精神和敢與強秦相抗、不惜犧牲自我的英雄氣概,但其悲劇結局則明顯蘊含著頹勢難挽、大廈將傾、非人力能為的時勢隱喻。
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可能采錄了《戰國策·燕策三》的相關材料,或許也吸納了民間傳說的部分內容,對故事進行了改造,其隱喻內涵發生了變化。在《史記》中,荊軻刺秦王故事被載錄于《秦始皇本紀》《燕召公世家》和《刺客列傳》。其中,《秦始皇本紀》《燕召公世家》敘事簡約而清晰,《刺客列傳》敘事詳備而豐贍。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2]233
可見,太史公明確了刺秦王的具體時間,使得可能源自民間的傳說有了信史的意味。在揭示刺殺原因時,司馬遷未采信《戰國策》的“見陵之怨”,而以“患秦兵至國”作為主要理由。由此,故事的寓意悄然發生了變化:凸顯了“荊軻刺秦王”乃為國著想的博大公心,相對弱化了太子丹報“見陵之怨”的狹隘私心。
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中,太史公也是簡筆勾勒了刺秦王故事發生前后十年間的歷史事件,對刺秦王過程的描寫亦很簡略:
二十三年,太子丹質于秦,亡歸燕……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于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2]1560-1562
在這個簡約的故事里,同樣凸顯了刺秦王的國家意義,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荊軻等被殺的悲劇色彩。司馬遷甚至認為,燕國外迫蠻貉入侵、內受齊晉擠壓,卻能延續社稷八、九百年之久,成為姬姓諸侯國中最后的滅亡者,應受惠于召公奭“甘棠且思之”的仁義精神。遺憾的是,仁義雖可垂范后世、綿延社稷、惠及子孫,卻無法抗力強秦、難免滅國失勢。就是說,仁義難與暴力相抗應是其隱含背后的隱喻指向。
在《史記·刺客列傳》中,司馬遷褒揚了“士固為知己者死”的報恩精神,采用欲揚先抑的手法,先依次介紹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等四位刺客,最后才讓荊軻緩步出場。接著,作者繼續采用欲揚先抑手法,介紹了荊軻的家世背景、傳奇經歷,寫他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而遭怒目、與魯句踐爭道而被叱時,皆采用“躲”“逃”等“懦夫”方式。來到燕國之后,他與高漸離相善,日日飲酒,或笑或哭,“旁若無人”。盡管如此,荊軻還是得到燕國處士田光的青睞。田光向燕太子姬丹舉薦了荊軻,于是才有刺秦王故事的發生。此后所載,內容與《戰國策》基本一致。作者敘寫了荊軻刺秦王的整個過程,并突出了荊軻飛刃刺秦王、擊中桐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等細節。在結尾處,作者不忘交代了一句,“秦王不怡者良久”[2]2531-2533。從而用秦王的驚嚇反襯荊軻的無畏。《史記》還盡量從真實、生動、合理的角度出發,重新設計了故事結局,并給讀者以合情合理的交代[2]2537。作者甚至自證其言:“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2]2536-2538這恰恰說明,司馬遷對神異而虛幻的民間傳說持謹慎的態度。
本項目電解工序主要溶液儲槽選用16臺Φ7 000 mm×10 000 mm玻璃鋼儲槽,造液、凈化工序為62臺Φ5 000×5 000 mm玻璃鋼儲槽,并對儲槽設計進行了優化改進:為防止罐底局部應力集中,儲罐基礎鋪墊50 mm厚的石英砂,出液口與鋼襯管連接部位增加了膨脹節;罐頂設置溢流孔、泄壓孔,以避免在使用過程中出現超設計范圍負壓或正壓;在罐頂進液口增加了導流裝置,以消除溶液對局部罐底的集中沖擊;在出液短接部位配置獨立支撐,要求使用壽命不低于20年。儲槽均采用MFE- 3乙烯基樹脂及輔料,玻璃纖維紗、無堿短切氈、玻璃纖維方格布、表面氈等材料現場纏繞制作,嚴格按標準檢查、驗收。
《史記·刺客列傳》中的五位刺客皆有重然諾、講信義、知恩圖報、敢于為義赴死的高潔品行,并在荊軻身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因此,《史記》用更多筆墨敘寫了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與《戰國策》的大勢所趨、非人力能為的時勢隱喻不同,《史記》中的荊軻刺秦王故事的隱喻內涵已悄然發生了變化。可以看出,荊軻是為信義、名節而赴死,也是為幫助弱者抵抗強者而死。因此,司馬遷對荊軻等人滿懷崇敬與贊美之情。在荊軻身上,既具有重然諾、崇信義、尚名節的時代精神,也有著“以暴制暴”的反抗意識,而這正是該故事的隱喻內涵。
二、關于故事隱喻內涵的不同觀點
從西漢后期開始,荊軻刺秦王故事經歷了由文本敘事向圖像敘事的轉換過程。在漢畫像石中,漢代人采用圖像敘事的方式來講述刺秦王故事,改變了文本敘事的模式與特點,很自然地實現了敘事方式的轉換。令人感興趣的是,這種轉換不僅僅是敘事方式的變化,也使該故事的隱喻內涵再次發生了變化。
研究者指出,漢畫像石的題材很廣泛,包括社會生活、歷史故事、神鬼祥瑞和花紋圖案等四大方面[3]11。其中,歷史故事包括古代的帝王、將相、圣賢、高士、刺客、孝子、列女等,荊軻刺秦王屬于歷史故事大類中的刺客類。漢畫像石跨越兩漢,“延續的時間從西漢初年的文景時期,一直到東漢末年”[4]97-99。不過,根據目前考古發掘所發現的畫像石來看,漢武帝以后可能才是畫像石大流行的時期,并在東漢中后期達到鼎盛,又在東漢末很快就走向了衰微。
那么,漢代人為何要將歷史故事刻在裝飾墓室的石板上?有學者強調:“墓主可能就屬于歷史故事的嗜好者,其生前喜歡這些歷史故事,并被故事中勇士的俠義、圣賢的事跡所感染,于是在安排死后世界的墓門裝飾時,有意選擇這些題材,以供其在冥界繼續欣賞。”[5]但是,這樣的說法是否符合實際?因為在這類歷史故事圖像石中,僅荊軻刺秦王畫像石的占比就不低。截至2004年,全國發現的“荊軻刺秦王”漢畫像石達18 幅,“成為歷史題材中已知數量最多的畫像”[6]115-122。事實上,2004年以后各地還有同題材的漢畫像石出土,其數量早已超出了這個數字。目前所知,刻有荊軻刺秦王故事的畫像石最早發現于西漢晚期墓[7]105-110,但絕大多數發現于東漢墓,并在河南南陽、山東嘉祥與沂南、浙江海寧、陜西綏德與神木、四川樂山等地皆有發現。這說明,“荊軻刺秦王”畫像石具有時間跨度大、分布地域廣、發現數量多的特點。
與史書中的文本敘事不同,漢畫像石中的歷史故事屬于圖像敘事。就敘事特點來說,文本敘事與圖像敘事有區別。前者可詳可略、伸縮自如,后者則受制于空間有限、鐫刻難度大等原因,須以簡約、突出重點為原則,以達到審美或教化效果為指歸,因此盡量展示核心道具、重點人物及主要矛盾。比如,在河南南陽針織廠西漢晚期墓出土的畫像石上,只刻畫了秦王、荊軻和秦舞陽三個人物,且個個身體瘦弱,衣服緊窄,似乎重在表現“刺殺情節”,“在極為簡潔的畫面上出現大與小、強與弱、重與輕、主與次,以及大義凜然與驚弓之鳥等不同狀態動勢的對比變化,形成了生動的荊軻刺秦王圖像早期圖式”[7]105-110。這種簡約而突出重點的早期圖式,很可能是后世效仿的“模板”。
關于荊軻刺秦王圖像故事的大流行時間,研究者認為,“大約至東漢中期經東漢晚期至三國時期”。其中,“較早者以山東6 幅和陜北2 幅為代表,較晚者則是山東沂南的1 幅、四川的8幅、浙江海寧的1 幅”[6]115-122。就構圖要素而言,荊軻、秦王、立柱、秦舞陽、夏無且、樊於期頭函是荊軻刺秦王圖像敘事的六大要素[8]318。因此,人物少不了秦王、荊軻和秦舞陽,道具則突出插在柱子上的匕首、打開來的樊於期頭函,而跪伏于地的秦舞陽、半截袖子、飄揚的衣裾、夏無且的藥囊等則為基本的過程要素。
關于漢代人將荊軻刺秦王故事刻在墓室中的原因,除了“喜好歷史”說而外,唐長壽先生作了如下解讀:
畫像選取荊軻最為卓厲、嬴政最為狼狽的那一刻,把荊軻置于險惡的眾敵之中,是在烘托孤膽英雄的大無畏。這種對荊軻進行的“高、大、全”式的藝術加工,實際上是在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來拔高荊軻,英雄化、美化、神化荊軻,丑化、鬼化、妖魔化秦始皇及其群臣。畫像這樣構思,是在明確無誤的傳遞一個重要信息——秦王是外強中干的,僅一個二流殺手(“不講于刺劍之術也”)孤獨的單挑(趴在地下“色變振恐”的秦舞陽作了反襯)就可以叫這位一國之尊(盡管身旁還有那么多執刀戈的衛士、侍從)如此狼狽不堪。[6]115-122
唐先生還根據已出土的“荊軻刺秦王”(18 幅)、“完璧歸趙”(13 幅)和“泗水撈鼎”(11 幅)等漢畫像石認為,“這些反秦王的眾多題材,還有一個共同的有趣特點,即笑話秦王”。而笑話權威蘊含著東漢士人的“不合作”思潮[6]115-122。這種說法看似不乏新意。可是,倘若這些畫像石不被埋入地下,而是公諸于眾,則這種“不合作”的態度與思潮還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問題是,漢代講究墓而墳,因此這些圖像故事被厚厚的封土所覆蓋,則如何讓統治者感受到這種“不合作”態度?如何讓后人理解這種“不合作”立場?也有學者指出,“荊軻刺秦王圖像完成在石祠壁面,具有社會的觀看審美功能”[7]105-110。就是說,圖像故事只有讓人看到,才具有“惡以誡世,善以示后”的教化作用,否則將無益于訓導或教化。
三、漢畫像石的構圖與位置問題
若從隱喻角度來衡量,西漢畫像石突出荊軻刺秦王的主題,可能確實含有指責暴秦無道、贊美“漢代正確”的政治隱喻與宣漢意識,因為西漢確有這種思潮,并在陸賈《新語》、賈誼《過秦論》等作品中有明顯的體現。而對前朝的批判或指責,既有“漢代正確”的宣漢意識,也有警示當下的隱喻用意。不過,東漢人崇儒而信讖緯,則該時期的荊軻刺秦王畫像石是否仍在講述著“漢代正確”的故事呢?若將該圖像故事置于陜北漢畫像石圖像敘事的整體序列中,或可發現,這并非是在講述“漢代正確”、具有“宣漢”意識,而是蘊含著新的隱喻意義。
比如,在陜北綏德出土的漢畫像石中,荊軻刺秦王圖像出現在墓門橫額上,時間比山東武梁祠漢畫像石要早,內容分為外、內兩欄:外欄為卷云圖和珍禽異獸,左為內刻金烏的日輪,右為內刻蟾蜍的月輪,以示宇宙世界圖景,是漢代人想象的神仙世界。內欄分為三部分,兩側皆為射獵圖(左為射虎圖、右為射熊圖),荊軻刺秦王圖置于中間,夾于射獵圖之間。若以斗拱式桐柱為界,在圖像左側,秦舞陽跪伏于地,前面是樊於期的頭函,再前面是受到驚嚇、身體后傾的秦王,舞陽頭頂有三只鳥飛向荊軻;在圖像右側,荊軻持匕首行刺,衣帶飄動,正繞柱追趕著秦王,旁邊可能是醫官夏無且。
可見,綏德漢畫像石的整個構圖,外欄顯然象征著神仙世界,諸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玉兔、麒麟等即可說明之。“荊軻刺秦王”居于內欄中間,與射虎、射熊等表示生活圖景的射獵圖組合在一起。而在陜北已發掘的漢畫像石墓中,“絕大多數有狩獵場面的畫像,只是表現場面大小不同”[9]101。游獵是漢代北方人的生活方式,但將神仙世界、歷史圖畫與狩獵生活組合一起,則給人的感受大為不同:生則高尚氣力、以勇敢為重,死則騰空升天、以成仙為宗。或許,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尚氣、尚勇乃是讓亡魂得以“復活”的生命力條件。所以,該漢畫像石中的荊軻刺秦王圖像,蘊含著追求勇敢無畏的生命激情的隱喻傾向,而這正與射熊、射虎等“高尚氣力”的漢代精神一脈相承。當然,這種生命激情也是墓主升天成仙的動力源泉。
再如,陜北神木大保當M16 墓門的橫額畫像石也分為內外兩欄:外欄為西王母、東王公及神禽異獸圖,在外側左上角和右上角分別有內刻金烏的日輪和內刻蟾蜍的月輪,象征著宇宙、神仙世界。而內欄則指向現實世界,又分為兩部分:右圖為竊符救趙,左圖為荊軻刺秦王。左圖又以立柱為界分為兩部分:從最左側開始,依次為驚慌拔劍的秦王、樊於期頭函、跪伏于地的舞陽、衣帶飄動的荊軻、驚倒在地的夏無且等。神木大保當畫像石突出了插在柱子上的匕首,沿襲了各地同類圖像“突出重點”的創作宗旨,而荊軻的衣帶飄動則意味著他發出的是揚手飛匕動作。
其實,在陜北漢畫像石中,完璧歸趙圖、竊符救趙圖也有類似的位置。比如,米脂官莊漢墓墓門橫額的圖像分為兩欄:上欄為車騎出行圖,浩浩蕩蕩向著西方世界前進。下欄左右為珍禽瑞獸祥瑞圖,包括羽人、玉兔、嘉禾等,說明這是神仙世界;中間為完璧歸趙圖,共有7 個人物,持璧的藺相如居中,倚柱而立。在綏德四十里鋪出土的墓門橫額上,完璧歸趙圖也分為內外兩欄:外欄為祥瑞珍禽異獸圖,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仙鶴、仙鹿等皆有,左右有日月,中間用二重閣樓將內外欄連接。內欄右側分為兩部分:最右側為拜謁圖,中間為完璧歸趙圖;左側為歌舞圖,閣樓中兩位主人面向歌舞方向而坐,旁邊有一侍者[9]170。
不難發現,完璧歸趙圖也置身于現實圖景的中間位置,而且與現實圖景一起,聯結著漢代人死后升天的想象世界——神仙世界。其實,這是將過去(歷史故事)、現在(狩獵或歌舞)和未來(神仙樂園)組合在前后相續的時間鏈條上,由此構成完滿的生命閉環,形成一種隱喻的世界——其間寄寓的恐怕不是政治觀,而應是從過去、現在走向未來的生命期待。而且,這一特點在竊符救趙漢畫像石中也有明顯體現。
竊符救趙圖在陜北神木、米脂、綏德等地都有出土。最典型的是綏德四十里鋪漢墓墓門橫額圖像,畫面分為兩欄:“外欄為祥云紋與羽人、青龍、仙鹿、吉羊、丹鳳、青鳥等珍禽異獸組成的紋飾,左右角刻日月輪,日輪內刻金烏,月輪內刻蟾蜍。內欄右部刻繪一組狩獵圖,左中部為竊符救趙故事圖畫。正中為一弓形楹柱上呈三層斗拱。楹柱左邊為趙惠文王,高冠闊袍,雙手平伸迎接抗秦救趙的信陵君。楹柱右邊為信陵君,高冠側身跪于地,右手握兵符,佩帶后揚,仰首呈昂奮狀態,似向趙王稟報自己利用魏安釐王寵妾如姬盜得魏王兵符,用義士朱亥擊殺魏將軍晉鄙奪得兵權,率魏軍破秦兵救趙國的艱辛過程。趙王身后有兩個持戟躬立者和兩個抱拳對語者”[9]173。和前述荊軻刺秦王圖、完璧歸趙圖類似,在陜北漢畫像石中,竊符救趙圖象征著過去,處于圖像敘事的核心位置,并與象征著現在生活的狩獵圖、象征著未來生活的神仙圖組合成時間鏈條,形成完整的生命循環。
四、圖像敘事的隱喻推論
由此可知,刻有“荊軻刺秦王”“完璧歸趙”和“竊符救趙”等圖像故事的陜北漢畫像石基本上分為內外兩欄:內欄為現實圖景或歷史故事,外欄為宇宙圖景或神仙故事。而米脂官莊出土的“完璧歸趙”漢畫像石,外欄似乎是反映現實的“出行圖”,內欄則將神仙世界與現實世界相結合,而把歷史故事完璧歸趙圖置于中間位置。其實,這“出行圖”不是現實世界的再現,而象征著從現實世界走向未來的神仙世界、宇宙圖景。當時的工匠很自然地將宇宙世界與現實世界勾連起來,使得借助于過去、現在與未來圖景所構建的圖像敘事網絡得以完成。
陜北漢畫像石中的“荊軻刺秦王”“完璧歸趙”和“竊符救趙”等故事基本上鐫刻于墓門橫額,且在整個圖像敘事中處于核心位置。這究竟是石刻工匠的隨意雕刻?還是遵從戶主吩咐的有意為之?或者是遵從了“應該”有的“模板”?從其頗具規律性的特點來看,工匠必然不能完全自由發揮,可排除第一種可能性。而戶主的吩咐可能也要遵從相關風俗約定,不會過分率性而為。因此,遵從“模板”的可能性很大。何況,墓門橫額是漢人觀念中的“陰宅”門面,若不是墓而墳的話,這門面的位置是可以示人的。所以,這些圖像敘事既然失去了現實的教化功能,也就不具有向現實世界宣示觀念的意義。
那么,鐫刻在墓葬石頭上的這些故事,究竟有何作用?我們知道,“荊軻刺秦王”圖像在陜北各地皆有發現,故事內容大體雷同,圖像篇幅也多有相似,刺殺場面永遠是圖像敘事表現的重點。因鐫刻者的水平和取舍視角不同,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變化,這“應是工匠用模板根據墓室結構、橫額豎石配置的不同拼繪而成的”[9]169。其實,“模板”是可以代代沿襲的,具有約定俗成性,這樣就會時刻告訴你,這樣做是“應該的”。因此,“模板”的原初意義可能早已被后世圖像敘事的隱喻意義所遮蔽。
其實,這種約定俗成性在當今陜北的喪葬活動中仍有體現。倘若仔細觀察當代陜北民間的喪葬活動,總有一束色彩斑斕的引魂幡立于靈堂前。這束引魂幡似乎在漢代卜千秋墓室壁畫里看到過,是引導亡者升天的指路航標。而在靈堂前擺置的“紙火”院落配件中,除了亭臺樓閣、大門院墻外,還有搖錢樹、金山、銀山、仙鶴、金童、玉女、羊、馬等。當然,院落擺件也會因時而變。比如,昔日的磨房、自行車、縫紉機等已被電視機、洗衣機、汽車、手機等所取代。而這座即將在新墓前焚化的院落外表繪飾,則幾乎永遠是恒定不變的。無論是云氣繚繞的神界花紋、攀龍附鳳的畫棟雕梁,還是寓意亡魂即將西游的坐騎仙鶴,仍保留著漢代圖像的古老印記。雖然不能以此為據,認為現代陜北人仍保留有漢代人的觀念。以此推論,“荊軻刺秦王”等圖像故事出現在祠堂壁畫時,可能也有啟迪后人、教人忠信的教化色彩。但是,東漢刻有“荊軻刺秦王”等圖像故事的畫像石被埋于地下,其教化寓意自然被弱化了,而作為美化未來生活“空間”、寄予墓主生命理想的意義得以凸顯。對亡者而言,墓室既是未來“生活”的自由空間,也是將來與子孫、家人聚會的活動場所,更是與人世隔絕的獨立世界。因此,圍繞著棺槨的圖像故事便是永恒的神仙世界(未來)、可時時“回味”的歷史故事(過去)和經歷過的游獵、觀舞、飲宴、庖廚、迎迓、拜謁、收獲等生活場景(現在),從而完成了一個生命循環。
總之,這些陜北漢畫像石實際上是將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統攝于圖像敘事的網絡中。歷史代表著過去,以史為鑒可使人清醒和智慧,故而與秦王、秦國相關的歷史故事便成為墓葬畫像石的重要主題。同時,由過去走向現在,自然使得反映現實生活的圖景絕不可少。對于生者而言,逝者并未“離開”,仍然“活著”,但不是“活”在現實中,而是“活”在仙界中。而這仙界,可能就是漢代人期盼的未來歸宿。漢代人認為,從過去到現在,再由現在走向未來,便完成了人的生命歷程。而人的未來歸宿,便是其更神秘、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這世界既是漢代人最為愜意的未來生活想象,也是他們最為持久的生命永恒期盼。若單獨看,“荊軻刺秦王”蘊含的隱喻內涵,可能有嘲笑秦王、褒揚忠信、贊美勇敢、寓意教化等原初意義。但是,若將該故事置于陜北漢畫像石的圖像敘事網絡中,則其間所蘊含的意義發生了變化。它與現在生活圖景、未來生活圖景組合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循環,具有渴望生命不息、長生永壽的隱喻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