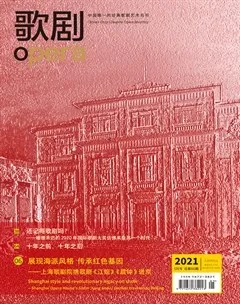驀然回首,卻在燈火闌珊處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兩位來自武漢的藝術家(周正中、徐洪)于2021年5月7日晚為上海的觀眾們獻上舒伯特的聲樂套曲《天鵝之歌》。當音樂的最后一個音符停止時,音樂廳響起綿延不絕的掌聲與喝彩。為何藝術歌曲會引起如此熱烈的反響?是兩位藝術家的氣質,還是舒伯特的魅力跨越數百年直擊國內聽眾的心靈?

觀眾對藝術歌曲的熱愛竟絲毫不遜于歌劇還是讓我有些欣喜——由于深受國內外經典歌劇的影響,觀眾們通常認為歌劇是代表聲樂藝術的最高水平,歌劇表演往往占據了觀眾們的主要視野。歌劇展現了歌者超高的技巧與戲劇舞臺魔力且富于戲劇性,人們癡迷于歌劇那天籟般的旋律與登峰造極的演唱技巧。與歌劇氣勢磅礴的戲劇張力相比,藝術歌曲則顯現出玲瓏剔透般的雕琢,二者恰似酒與茶,前者濃烈醉人,后者需耐心品味。雖然藝術歌曲在敘事性、戲劇張力上不如歌劇,但作為聲樂體裁,音樂與詩歌緊密結合,其豐富且細膩的情感變化不輸詠嘆調。
以浪漫主義時期德奧為代表的藝術歌曲往往凸顯該體裁獨特的魅力,舒伯特更是眾人中的佼佼者。相比他的聲樂套曲《美麗的磨坊女》《冬之旅》,《天鵝之歌》不是舒伯特集中構思創作的作品(舒伯特死后,由出版商整理出版)。無論音樂的連貫性與統一性,還是詩歌內容呈現出的情節聚合性都不如前兩部作品。但憑借作曲家精湛的創作技巧與獨特的音樂風格,加上作品標題引發的“話題性”為這部聲樂套曲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整場音樂會以聲樂套曲《天鵝之歌》為核心,共有十四首歌曲。當晚演出卻別出心裁,藝術家們并非一氣呵成地演繹十四首歌曲,而是將整部套曲分割為三個部分(以三位德國詩人的作品為界限),中間插入舒伯特的兩首鋼琴即興曲(作品號D899的第二首與第三首)。音樂會聲樂套曲插入鋼琴即興曲的結構恰巧是一個回旋曲式,有意地制造出精妙的音樂格局。鋼琴演奏家徐洪所演奏的即興曲宛如翩翩起舞的蝴蝶,縈繞在花叢間;又像叮咚的泉水噴涌出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珍珠。兩首即興曲成為藝術歌曲之間的“調味甜品”,不但為銜接三個部分的藝術歌曲,而且在三個部分的間隙中彌漫著一絲春意盎然,頗有瓊漿玉液之感。

古人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聲樂套曲《天鵝之歌》的前七首歌曲取自德國詩人萊爾施塔伯(Ludwing Rellstab)的詩歌,詩歌的主題內涵圍繞愛情展開,七首歌曲在情愫上呈現出對比變化的態勢(尤其是前四首),以此展現詩歌不同情境對愛情的渴望。
《愛的使者》(Liebesbotschaft)以托物言志方式來表達主人公對欽慕之人的濃烈愛意。歌曲的伴奏織體以十六分音符為主,勾勒出溪水汩汩潺潺,春日盎然的美妙景色。在我看來,周正中在演唱技巧、情感處理方面與音樂材料的起伏達成完美的統一。歌曲中有大量的上下行二度、三度音階,歌者細膩的氣息把握與聲線平穩地運轉,使每一個音符都具有清晰的顆粒感。聲樂與鋼琴的融合好似兩條不斷生長且纏繞在一起的蔓藤,平穩有序地前行。周正中處理歌曲的轉調時,并未過分地追求情緒、力度的對比性,而是細膩地同化并延長第二段的情緒表達(例如歌詞“她獨自默默在河邊徘徊”(Wenn sie am Ufer, in Tr?nme versenkt),為歌曲再現的統一性做足了鋪墊。

《戰士的預感》(Krigers Ahnung)具有雙重對比度。首先,與第一首《愛的使者》和第三首《春的憧憬》(Frühlingssehnsucht)在情感上形成鮮明的對比。其次,音樂本身也有強烈的對比性。徐洪在處理雙附點音符的強拍時有意加大力度,并且在延長音上留有更長的氣口,強化鋼琴織體的厚重感,凸顯周正中演唱中低音區時并未刻意追求力度,營造出唱詞中戰士所處的孤獨氛圍。在三段不同的音樂段落中,周正中的音色與力度變化像是嚴絲合縫的榫卯,絲毫感受不到音樂段落銜接時遺留的微弱轉換。《春的憧憬》回歸至開場的情緒,三首歌曲的情感變化考驗了演唱者對情感張力的駕馭程度。鋼琴以急促的分解和弦配合靈巧的旋律走句,你會發現兩位藝術家的演繹效果并不是你追我趕,而是相互引領前行。這首歌曲檢驗了歌者的氣息功底,連珠炮式的吐字發音并不影響他那穩如泰山般的氣息運轉,他似乎有獨門秘訣,對每個音符的氣息把握顯得細膩且勻稱。
如果將羅西尼喜歌劇《塞維利亞理發師》中伯爵的詠嘆調“看那明媚的天空”(Ecco,ridente in cielo)替換成舒伯特的《小夜曲》(St?ndchen),我相信羅西尼也會毫無異議。萊爾施塔伯的詩歌描繪一位小伙向心愛的姑娘傾吐衷腸,舒伯特運用帶變化的分節歌將音樂劃分成兩個部分。徐洪觸鍵的力度猶如在觸摸膚如凝脂的嬰兒,鋼琴仿佛瞬間變成奧菲歐手中的里拉琴,或是游吟詩人手中的維奧爾琴,通過小調的旋律引出細膩的情感線條。歌曲進行到尾聲,音樂從大調轉回小調,音樂的情緒與力度形成強烈的反差(前后兩句)。演唱者往往很難在細節上做到精準的把控,處理不當都會顯得矯揉造作,無法體現出音樂情緒變化上富有層次的收束感。周正中對這條情感線條的處理雖弱卻不虛,將每一個細微的技巧變化處理得恰到好處。
兩位藝術家對《天鵝之歌》藝術化處理宛如高超技藝的雕刻大師,對音樂的掌控力不局限于表演技巧與情感處理上。雖然兩者可以通過日積月累的訓練與舞臺經實戰經驗實現質的飛躍,但是表演時長時間維持那種極其自然的狀態,是具有敏銳嗅覺的藝術天賦。假如藝術的處理上顯露出毫厘之差,那都是裝模作樣的鄙陋。仿佛二人對音樂的敘述是娓娓道來,兼具細膩與深情。這種處理在舒伯特為海涅的六首詩而創作的作品中體現得尤為明晰。藝術歌曲《地神》(Der Atlas)與《離魂者》(Der Doppelg?nger)像兩根定海神針,作為第二部分的始末奠定了情緒的基調。音樂的情緒好似“莫比烏斯環”,循環反復,勾勒出一幅獨特的畫卷。《地神》是作者表達對地神阿特拉斯的同情,極具隱喻色彩。這首歌曲通過大量的減七和弦制造強勁的力量感,尤其出現音程的大跳(歌詞為“沉重大地背在肩上”(ich tragen, dieganze Welt mu? ich tragen”),周正中在演唱時專注于音樂力度的調節,但他并未借助強勁的力道撐破已有自然平衡狀態。他的這種狀態與徐洪形成默契,二人的演繹相得益彰,貫穿全曲,甚至這種默契度彌漫與發散在后六首歌曲中。

歌曲《離魂者》是套曲中演唱難度最大的藝術歌曲,對于演唱者來說挑戰巨大。首先,這部作品音域跨度大,對聲音與情緒的把握需要考究每一個細微的環節。其次,歌者在演唱前五首歌曲后,疲勞程度會影響演唱的質量,稍微不留神,就會失去其特有的節奏與律動,從而喪失情緒變化的層次感。《離魂者》是一首吟誦敘事性歌曲,其旋律宛如歌劇中的宣敘調,鋼琴的伴奏織體以附點二分音符的柱式和弦為主,恰似死神的腳步,刻畫深夜死寂般的氛圍,以此塑造情感上的割裂效果。音樂沒有復雜的旋律,從周正中的聲音狀態上可以感受到詩歌中彌漫著孤獨的氣息,它讓角色逐漸陷入凄涼與孤獨的境遇。
最后一首藝術歌曲《白鴿使者》(Die Taubenpost)選自賽德爾(Johann Gabridl Seidl)的詩歌。俗話說“解鈴還須系鈴人”,音樂會的第二部分(指海涅的六首詩歌)充斥著游離的凄涼感與迷離的孤獨感,而《白鴿使者》恰如春光,一掃《地神》《離魂者》制造的陰霾與傷感。《白鴿使者》與《愛的使者》首尾呼應,《天鵝之歌》再次回歸歡快情愫。詩歌中不斷強調“渴望”“希望”,雖有多段歌詞的反復,但周正中與徐洪的處理避免機械地重復而形成呆板的質感,這使得整首歌曲描繪出一條清晰的波浪式線條。令人感嘆的是,周正中在保持音樂快速的韻律時還注重清晰的吐字,歌詞之間形成豐富的色調,音樂猶如呼吸一般,張弛有力,富有詩意。

周正中與徐洪攜手演繹的聲樂套曲《天鵝之歌》,透露出兩位藝術家具有的中國式古典氣息——含蓄、包容、內斂、典雅、細膩。兩位音樂家之間的默契猶如山鳴谷應,音樂彌漫著淡雅氣息,內斂的情緒中包含暖暖的溫情。二人的表演萌發出的希冀,猶如撥云睹日,仿佛也流露出江城那固有的堅定和勇氣。
正如周正中演唱《白鴿使者》前向觀眾們解釋選擇聲樂套曲《天鵝之歌》進行演繹的兩方面緣由。首先,這部聲樂套曲使他追憶起學生時期初次接觸藝術歌曲的心理狀態變化。舒伯特的《天鵝之歌》充滿獨特的魅力改變了周正中對藝術歌曲淺顯的認識。其次,通過演藝聲樂套曲《天鵝之歌》,重新審視自我的人生閱歷,冥想《青玉案·元夕》中蘊含人生哲理及對他的重要意義。周正中強調與尋找的“驀然回首”不僅是歌唱藝術通過聲音建立的審美,也是自我哲理性的思索,以一名音樂家的身份向人們傳達音樂中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