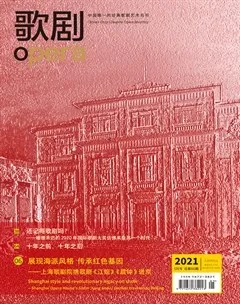敢夢敢當,有夢想才有希望

連續三天,天橋藝術中心中劇場成了這個京城音樂劇地標性建筑的風暴中心,五場演出幾乎每場都座無虛席,演出結束后掌聲喝彩聲不絕于耳,人們用難以抑制的激動之情為臺上的演員點贊,為這部熱血僨張的大戲點贊。“我是個報童,賣報的行家,穿大街過小巷,匆匆又忙忙……”這是原創音樂劇《新華報童》首演的燃情現場,一群追夢少年用激情用溫情用真情點燃了每一位觀眾的熱情,這個有關熱愛與成長的故事強烈地激蕩和震撼著人們的心。“好聽好看感動振奮人心”,這是眾多劇迷們看過之后的共同感受。在歷經了一次又一次熱血沸騰的戲劇沖擊之后,謝幕環節高潮再起。演員們用一曲全中國人人都會唱的《賣報歌》向經典致敬,向曾經點燃過無數有志青年的激情歲月致敬,向為我們今天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奉獻青春、熱血乃至生命的先輩們致敬。
經歷數月的精心打磨之后,《新華報童》終于迎來了首輪演出。令人興奮的是,所有的門票在演出前幾天就被搶購一空。顯然,這場人們期待中的燃情大戲尚未登臺啟幕,已經先期點燃了人們觀看的熱情。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看過舞臺版和電影版的《報童》,但是這個題材卻是首次被搬上音樂劇舞臺,用音樂舞蹈和戲劇來綜合講述當年山城重慶一群報童的故事。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這部原創音樂劇是由北京文化藝術基金、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支持,北京甲丁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慶文化產業投資集團聯合出品的獻禮之作。
音樂劇開始,一段熟悉的旋律刺激了觀眾的耳朵,那是曾經的《賣報歌》的旋律。不過,這段旋律只是過眼云煙式的閃現,之后立即進入嶄新的原創旋律中。這是作曲家何琪用自己的方式向我們熟悉的經典致敬。不過致敬只是情感或故事的引子,它讓我們隨著音樂穿越回大半個世紀前那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山城重慶。

《新華報童》取材于抗日戰爭時期重慶街頭的報童生活,通過講述新華日報社在1941年“皖南事變”前后的宣傳斗爭故事,展現了一群報童在中國共產黨的關懷與信念感召下,從迷茫的街頭少年成長為敢于與國民黨頑固派做斗爭、勇于與命運抗爭的愛國少年的過程,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開場的街斗引人入勝,餓肚子的少年們為了一個包子,與地痞無賴發生著爭執。有的撐不住撿起扔在地上的包子,更多的人為了尊嚴寧可挨餓也不受嗟來之食。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現實,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是如何更有意義地活著,則是少年們面臨的現實。與早年間的舞臺劇或者電影《報童》相比,音樂劇《新華報童》有著視覺的“年齡差”,原先兒藝老前輩們演的那個“報童”更符合人們對這個職業的想象,而音樂劇《新華報童》顯然是一群更能與當代青少年心意相通的熱血少年。李煒鵬、齊齊、曹小欠兒、王哲、湛嘉麗等一群當今音樂劇舞臺上頗具才華的青年后生堪稱本色出演,這些“90后”“00后”為主力的青年演員,將這群少年酣暢淋漓地展現在舞臺上,他們把一個個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角色,扎扎實實、活色生香地立在人們眼前,可謂滿臺生輝。
《新華報童》劇情緊湊曲折緊張,極具戲劇張力,用當今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全程無尿點”。年輕的編劇曹瑜展開自己的想象,使用了“老故事新講法”的方式將這個曾經的經典舞臺劇生發出不一樣的情景、不一樣的故事,除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與角逐,她還將“陰謀、諜戰、愛情”這些吸引當代觀眾的戲劇元素,完美融入這部音樂劇當中。國民黨特務李衡哲利用了帶著妹妹來重慶討生活的少年江陽,險些誤導單純想讓妹妹過上好日子的江陽破壞《新華日報》的印刷機。內心的良知讓江陽迷途知返,在報社編輯喬世寧和記者卓婭兩位共產黨員的引領下,最終與賣報少年九哥、平頭、眼鏡一眾小伙伴找到了人生的信仰,成長為革命的堅強力量。街頭面點攤,情報的接頭與傳送,是那個時代地下黨的工作日常,在這部戲中則成了貫穿全劇的線索,烘托了緊張的戲劇氛圍。當然,還有那對革命伉儷喬世寧跟卓婭,在共同的信仰天空下他們的愛情干凈而純粹,在面臨生死抉擇的關頭二人在歌聲中翩翩起舞,彌散著革命的浪漫激情,催人淚下撼動人心。

很多作曲家喜歡在作品中凸顯帶有標簽的個性符號,而該劇作曲何琪則表示,在《新華報童》中不需要個性張揚,最重要的是讓觀眾聽起來感覺好聽、走心,“用音樂的力量放大歌詞和劇本的文學張力,讓觀眾真切地在劇場里感受到音樂劇這種現代綜合藝術的魅力”,這是何琪的音樂主張。盡管這是一部主旋律的紅色大戲,但是創作者并沒有“板著面孔唱贊歌”,而是鋪陳了大量的情感積淀,進行火山爆發式的內心抒發,同時在舞蹈與音樂的呈現方式上又極具時代性。最重要的是,搖滾、說唱甚至街舞的律動,融入這個發生在1940年代山城重慶的故事中,竟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毫無違和感。出品人甲丁說:“重慶這座城市本身就有著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正是因為這種精神,才能使得這座城市在當時日本侵略者的‘戰略轟炸’中,‘炸不倒,炸不垮’。重慶人性格中的火辣與倔強,正是這一出《新華報童》人物的特定基調。”鋪陳全劇撼動人心的搖滾風格的音樂與演唱,與重慶人火爆的性子、賣報少年滾燙的激情和沸騰的熱血相得益彰,以至于人們看著看著不由覺得,只有搖滾才是最恰當的表達。劇中,賣報少年平頭的說唱是個亮點,特別是那段重慶方言的說唱更是讓聽得人大呼過癮。可能觀眾不知道,那段方言說唱就由平頭的扮演者、說唱歌手周子君親自創作的,他說創作動機就是被重慶的這種城市精神所打動。最燃情的演唱出現在上半場結束,重慶遭受日本大轟炸之后,聚光燈下幾乎所有的演員站在臺口齊聲高唱:“重慶人,中國魂,愈炸愈強……”那一刻,臺上歌聲陣陣,臺下熱血沸騰。

《新華報童》在音樂上最大的“聽點”就是燃情與溫情并存,與燃爆激情的搖滾與說唱相比,有時細膩的抒情更有力量更直擊人心,比如說那個走心的唱段《微微的爐火》。“微微的爐火,將夜色溫暖,聲聲的叫賣,像親人呼喚,夜歸的人啊,喝一碗粥吧,喝一口甜蜜,融化心里的寒……”溫暖抒情而又帶著一份淡淡憂傷的歌聲出自小女孩兒江雨之口,這美妙的童音像是在亂世中的一粒美好的種子,讓人們在殘酷的亂世中依稀感受到那份絕望中的希望。當然,還有那段喝臘八粥的橋段,幾位報童手捧著熱騰騰的臘八粥,唱著回憶著離別的親人以及因為戰爭失去的曾經的美好生活。殘酷的現實,殘暴的世道,那些美好得像花兒一樣綻放的歌聲,在如此強烈的反差之中更顯得動人動情。靜謐的夜空下,這音樂實在是太美好,在殘酷的空氣中聽起來令人發自內心的戰栗。
音樂劇是一門綜合藝術,一部優秀的音樂劇一定匯聚了一群優秀的藝術家通力攜手打造而成。除了在臺上接受鮮花和喝彩的演員,幕后的主創團隊更加值得尊重。如果說《新華報童》是一部奔跑在高速路上的跑車,那么導演美花、編劇兼制作人曹瑜、作曲家何琪就是其中最為強大的發動機,他們將文學、音樂、藝術等手段進行恰如其分的調動,最終讓這部戲近乎完美地呈現在舞臺上。而作為藝術總監的甲丁導演則是幕后團隊的核心,從創作之初他就與創作者們達成默契,他只負責把關和掌握方向,其余完全尊重主創的想法,給予幾位年輕藝術家極大的創作空間。有意思的是,最早甲丁并不看好這部戲,甚至也潑過冷水。在第一次聯排的時候,他為該劇的呈現僅僅打了低得可憐的20分。首演當天,甲丁釋然了,他連著看了5場,他對自己曾經折磨過的團隊表示滿意。他說:“每一部作品的創作過程都是艱難的,可能我的嚴苛更加劇了對這部劇所有主創的‘折磨’。但這所有,都將在得到觀眾掌聲的那一刻,得到釋懷。”不僅僅是對主創對演員苛刻,甲丁對最終的演出呈現也有著超高的要求。相對目前國內原創音樂劇的演出形式,現場樂隊與跟著錄音伴奏演唱有著質的區別。由于成本以及樂隊水準等原因,國產音樂劇大多采用“卡拉OK”式的演唱方式。而《新華報童》的首演,甲丁堅持使用現場樂隊,于是人們有幸看到作曲家何琪帶著由他率領的那支磨合了很久的樂隊出現在樂池里。此外,甲丁還不計成本地使用了聲音景觀沉浸聲系統,讓坐在劇場里任何一個角落里的每一位觀眾都能得到最佳的聲音效果。據說,這也是這套聲音系統首次出現在音樂劇的現場。

“我是個報童,賣報的行家,穿大街過小巷,匆匆又忙忙……”整個晚上,這首剛剛問世的新《賣報歌》因為朗朗上口、因為數次詠嘆,以至于觀眾看著看著已經可以跟著一起唱起來。“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就去賣報……”在謝幕環節,在藝術總監甲丁的建議下,劇組又放大招,與開場的引子致敬經典相呼應,所有演員們縱情唱起這首人人熟悉的經典《賣報歌》,瞬間點燃了全場觀眾的激昂情緒,喚起了人們記憶深處那些塵封許久的美好與純凈。音樂劇《新華報童》,無論是臺上的演員還是臺下的觀眾,每一場的演繹對于在場的每個人而言無疑都是一次火熱的洗禮。
我最早接觸這部戲是從一摞厚厚的劇本開始,沒有樂譜只有編劇曹瑜的文字,當時的音樂還只有幾段小樣。即便聽了,也沒有太多的感覺。看著字里行間間或夾雜著些許山城方言的唱詞,很難想象兩三個月后呈現在舞臺上的《新華報童》什么樣子。首場演出,坐在臺下的我感受著身旁觀眾的激動情緒,聽著他們發自內心的掌聲與喝彩,我感到很欣慰,為臺上付出數月辛苦的演員們,更感謝美花、曹瑜、何琪當然還有甲丁導演這個強大幕后團隊為京城舞臺為音樂劇市場奉獻了一部好聽好看感人走心而又滿滿正能量的好戲。
說到百老匯和西區動輒一部戲駐場演出一演就是十年二十年,靠市場賺得盆滿缽滿,這才是音樂劇最完美的生存方式。音樂劇首先是娛樂產品,它應當依靠市場去養活,直到把它養成經典。《新華報童》的創作與誕生的過程離不開北京文化藝術基金以及文投機構的大力支持,但當它立在舞臺上走向市場的時候,最終還得靠著自己的實力以及不錯的口碑。《新華報童》首輪5場演出,除極少部分工作票,其余門票提前四天全部售罄。而首演得到的市場反饋,幾乎都是一邊倒的叫好聲。對于一部音樂劇來說,這是一個好的開始,也為走向市場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在作曲家何琪的心中的有一個執念,他一直想做一部很成功的商業性劇目。他說,通過首演他看到自己距離目標很接近了,“我就是奔著這個目標去的,我希望我寫的每一個音符都值得大家付出的門票錢。我不想只花政府的錢創作,我想靠市場把那些投資賺回來。”我想,這是藝術家的信心、良心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