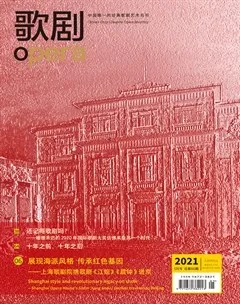四維觀《紅船》
1921年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勝利閉幕,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條游船因而獲得了一個永載中國革命史冊的名字——紅船。2005年6月21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弘揚“紅船精神” 走在時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闡釋了“紅船精神”,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源頭精神。百年前“紅船”上的會議見證了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百年將近,總書記提出的“紅船精神”成了中華民族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豐碑。

紅船劈波斬浪,揚帆鼓舞人心。紅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時代高度,是發展方向,是奮進明燈,是鑄就在中華兒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燈塔航標。在黨的百歲華誕即將來臨之際,全國各地文化工作者以繼承和弘揚紅船精神為己任,以優秀文藝作品為載體,不斷將紅船精神搬上舞臺,百花競妍,爭相怒放。
近日,歷時近4年之久、集結近400人之力打造而成的歌劇《紅船》,在浙江音樂學院大劇院正式首演。該劇由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廳、中共嘉興市委、嘉興市人民政府共同出品,浙江演藝集團(浙江歌舞劇院有限公司)、浙江交響樂團、浙江音樂學院、中共嘉興市委宣傳部、嘉興市文化廣電旅游局聯合演出制作。
歌劇《紅船》以中共“一大”為主會場,以相關重大而細膩的國史、家事為分會場,捻線串珠,為觀眾展開一幅宏闊激昂又細膩抒情的立體長卷,以深情的“歌”詠,綿密的“劇”構,深邃的“史”思,濃郁的“詩”情,在文本到音樂到整個舞臺呈現上,全方位地完成了一次頗為艱難而別致的創作。
洞見“史”思
寫歷史劇,大家較為肯定的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以及“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結合的原則,而對于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尤其是涉及重要黨史、國家重要領導人的作品,更加講求精準考證考究。編劇的“史”思,首先是“大事不虛”,重要的史實不能出現絲毫的偏差與訛誤。而每一處史實都要很慎重地對待,每一次改動都必須心懷虔誠敬畏之心。編劇在幾百萬字的閱讀基礎上,爬梳史序、分析史實,字斟句酌地力求表達歷史的真實。

如對于“中共一大”南湖會議的召開時間,編劇用了“八月初的一天”正是對歷史的尊重。關于這個時間,學界有很多說法,一直論而不定,于是編劇遵循“重證據,戒臆斷”的原則,在多方聽取黨史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如實標注了一個相對準確的時間。在描述李大釗迎接陳獨秀出獄時,編劇搬用了出自李之手的《歡迎仲甫出獄》詩,僅因歌詞格律稍做刪減。對于出獄之后李大釗送陳獨秀南下時李是否真的親自駕車等細節問題,也是幾經探討才最后酌定。至于紅船會議的最后一次明場表現過程中,關于不穩定因素“巡警”是否真的上船,也幾經爭論,舞臺呈現也在正式首演的版本中做了修改。
“大事不虛”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目的創作中固然是鐵定的法則,歷史當然容不得半分虛假,但藝術的真實同樣不容小覷,藝術精品的打磨有賴于“小事不拘”的精雕細琢。為解釋李大釗、陳獨秀兩位重要的建黨奠基人為何沒能參會的問題,編劇和導演在文本和舞臺表現上分別做了相對合理的集中虛構:李大釗布局在上場門區間,陳獨秀布局在下場門區間,一南一北,一左一右,區間分明地表現了“南陳北李”因事滯留又很關心會議的情形。兩者交錯而行,節奏緊張,事件清晰,二人沒參加會議是確證無誤的事實,為何沒參加則在時空上做了小的虛構與集中解釋。

史實浩繁,在如實再現歷史的基礎上達到兩個“真實”的統一,最要緊的還在于編劇基于廣度的摘選以及基于深度的剖析,在于編劇對歷史史實以及歷史人物給出的精準剖析與洞見,在浩繁的史料中挖掘出時代的必然與規律。正如紅船上的“一大”會議,編劇既重點表現了雖未與會卻是至為重要的奠基人李大釗、陳獨秀,還重點表現了黨的領袖毛澤東。舞臺上三線并行:第一條線即以毛澤東牽頭,明場表現一大會議;第二條線以李大釗、陳獨秀牽動,表現一大會議的早期奠基人的準備;第三條線也可以看成第一條線的副線,即毛澤東與楊開慧革命有情人的情感交織。三個主要人物牽動三條主要線索,鼎足而立,穩穩當當架構了“一大”的成功召開。事件深邃而細膩,人物剛硬而柔軟,這是編劇的結構,同時也在史實與人物的梳理與架構中給出的態度與選擇。
抒發“詩”情
一部作品的詩思詩情首先取決于題材,取決于題材中的人物的性格與氣質。從題材來分析,建黨無疑是史詩性事件;而從人物來看,毛澤東本人的革命浪漫詩人氣質早已為世人熟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早期思想巨擘與文學巨匠同樣是詩情濃郁的文人詩人,文本寫作中的詩思詩情只會與劇作本身要反映的內容更加相得益彰。從編劇方面來考量,王勇作品豐富,其文辭瀟灑雋永,風格典雅詩意,擅長以深刻的思想震撼力與人性的感染力打動人,多數作品正是以濃郁的劇詩品格獨步當代舞臺。《紅船》與“歌”結合,在文學氣質上則更進一步強化了詩意的抒情特征。
抒發“詩”情并不是只抒情不敘事,事實上,無論民風還是雅頌,無論宣敘調還是詠嘆調,淡妝濃抹,各具情態,為表達這個詩意的主題、表現這批詩意的群像,編劇將“賦”“比”“興”各種手法悉數運用。
開場“一大”開幕,各位代表“自報家門”:“張國燾、劉仁靜:‘我從古都北京來’;王盡美:‘我從趵突泉邊來’;毛澤東:‘我從岳麓山下來’;李達、李漢俊:‘我們在黃浦江畔期待’;董必武:‘我從黃鶴樓前來’;陳公博:‘我從珠江口岸來’;周佛海/馬林、尼克爾斯基:‘我從日本東京來/我從共產國際來’”,參會諸公直言不諱,文本“鋪陳其事直言之”,使得這種表明身份的介紹性的敘述同樣清新明了、詩意盎然。相類的賦法在《紅船》的寫作中屢見不鮮:如李大釗駕車送陳獨秀出京時,二人舉目遠眺,深情叩問蒼茫大地,編劇即以“黃河在嗚咽”“長江在呻吟”“黃山在凄慟”“長城在塌崩”等,來狀寫那鼓脹于胸的“偌大的家國卻無處安魂”的深重哀傷,并直言“生命不可承受之痛”,不鋪陳無以賦情,言雖淡而意味雋永。鋪陳浩浩蕩蕩,“比”“興”同步交融:前面舉證為表達家國悲傷而鋪陳之“黃河”“長江”“黃山”“長城”,同時也是心懷悲憫之“以彼物比此物”。直抒胸臆是詩情漫溢,“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物”更是詩思表達:時代風云變幻,形勢波詭云譎,而劇作在進場紗幕上營造的“黑云壓城”的態勢是一種“比”,明顯喻示了緊接其后的序幕“多少淚水無聲哭泣,多少魂靈無所歸依。苦難中華,我的父母之地;苦難中華,我的祖先之地”的情景。而后續的“一大”在南湖畫舫之前的那段“烏鎮姑嫂餅名不虛傳,嘉興肉粽滋味長,西塘八珍糕松脆可口,南湖紅菱透清香。還有那嘉興三塔觀興亡,更有那煙雨樓風云醞釀”,都是為了“興”起最后一句的“風云”二字,美好的民風民俗所要引起的“所詠之物”其實就是改變民族命運的決心與希望。最為人稱道的“我有一個夢”,入目的是沙漠、草原、滄海、桑田,“萬歲”輕聲呼喚的是“告訴天空”“告訴江山”“告訴時間”“告訴未來”,蕩氣回腸的形象打開了無限的時空,自然寄托了詩人深邃的詩思,劇詩的品格就來自這個被毛澤東、李大釗及眾人多次反復歌詠的“夢”與“萬歲”的祝福與希冀。文辭之形象、華美輔以詩歌樣式的回環復沓,經過歌劇音樂旋律的反復,全劇詩思詩情更加濃郁醇厚。
當然,劇中人時時口吐蓮花之際,“真理”“正義”“前進”“初心”“革命”“啟迪”“光明”“公平”等口號式高頻詞也是不時蹦涌,與陳獨秀、眾學生滿臺撒傳單,再經過多媒體渲染滿屏漫天的舞臺場景相輝映,此時此際那些直白的宣傳式標語,那些狂飆激進的鼓動言論,是當時當地先鋒前輩們最鮮明動人的本真,是時代思想啟蒙之必然,是從肌膚到骨髓連每一個毛孔都滲透著的特質。因此,我們在苛責劇作語言的些許概念化痕跡的同時,是否也認真考量過,摒棄了漫天飛舞的傳單,喑啞了慷慨激昂的口號,是不是也一并淹沒了某些直指時代與本真的標志與靈魂。
綜觀《紅船》劇作之歌詩吟詠,賦、比、興手法是多樣的,表達的風格是搖曳多姿的,表情之婉曲與直白雜糅,時代之沉郁與個人之流麗并進,全劇雖為歌為劇,更也不失為詩為文。
深情“歌”詠
接受“紅船”題材的舞臺劇創作本身就是挑戰,也是一份責任和一種擔當,歌劇“紅船”的最終舞臺呈現無疑推出了一部史詩級的成功之作。編劇王勇始終謙遜,他是時代需要的劇作家,在接受采訪時,對“時代需要什么樣的劇作家”卻是一帶而過。他毅然決然接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使命,像詩人一樣去完成生命之感悟,像思想者一樣去表達時代之考量,作為編劇站在了更高的時空維度上,更加精準而深情地噴發出來自內心深處對祖國、對黨、對英雄、對人民的謳歌。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王勇首先為“紅船”定位了一個最佳的藝術樣式——歌劇,噴薄之情發而為“歌”,“紅船”精神的表達方式是為恰到好處。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是人類壯麗航程的關鍵重要環節,而歌劇本身長于史詩題材的表現,當宏闊浪漫的史詩題材與長于表達壯麗篇章的藝術形式猝然相遇,瑰美的藝術火花自然噴涌而出。王勇筆名詠之,從業開始即執著于自我表達,至今初心不改,“紅船”如何“詠之”?
作為一位諳熟舞臺演出規律,文學理論功底深厚的劇作家,王勇創作并上演的劇作多達20余部,涉及話劇、兒童劇、歌劇、舞劇等諸多品類,創作涵蓋京劇、黃梅戲、上黨梆子、贛劇、瓊劇、呂劇、淮劇、河北梆子等多個劇種,可見其創作題材之繁復龐雜,內涵之豐厚蘊藉,樣式之廣泛多姿,尤其是近年來《呦呦鹿鳴》《天使日記》《星海》等數部民族歌劇的創作更是聲名鵲起。很顯然,作為《紅船》的編劇,王勇在多次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挑出了“歌劇”作為“紅船”精神的表達,既是“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使命使然,更是尊重藝術規律,爐火純青駕馭歌劇創作的高度自信使然。
歌劇之本體核心是音樂,此次掌舵《紅船》音樂創作的是倍受推崇的作曲家孟衛東。孟先生保持著通宵達旦的創作習慣,并且堅持每個音符出自本人之手筆,他與編劇也是合作多次,默契非常。全劇作曲風格端肅沉郁與清新流麗相輔,雅歌頌歌與民風民調相成,堪稱又一部西洋歌劇與民族歌劇結合的典范。紅色主題作品的創作,以風度以溫度完全俘獲了觀眾,音樂好聽入心,層出不窮的各種唱段很快建立了觀眾耳音。演出結束之后,熟悉的音樂旋律余音繞梁,很多觀眾甚至是一邊散場一邊哼唱。《萬歲》《我有一個夢》《一個幽靈》《你今出獄了》等重點唱段華麗優美,直擊人心;船娘的開船曲、細妹子的指天哭訴、毛(澤東)楊(開慧)相愛時的唱段等等又明顯加入了民歌民調元素,嘉興南湖的水鄉風情、湖南板倉的花鼓韻味以及遼遠時空處元雜劇竇娥式的指天發誓隨著音樂的旋律蕩漾,撩人情思,發人深省。

正是各個角色一段又一段既獨立又有機融合的深情“歌”詠,關聯了歷史,也立住了舞臺人物形象,史詩般的宏偉畫卷與性格各異的歷史人物因為音樂的豐厚多姿而生肌肉骨,靈動飽滿。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楊開慧、王會悟等人物形象,由男高音、男中音、女高音等角色分飾。他們以歌唱音樂賦予了人物靈魂與思想、性格與氣質:毛澤東在傾聽細妹子指天申訴血淚家史后,第一次深情詠歌《我有一個夢》,這是一個青年人面對滿目瘡痍的中華大地,面對百姓大眾流離失所的由衷哀歌,更是一個熱血青年壯懷激烈尋夢、追夢的破土萌芽,這是怎樣的“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是特別地指出來”,這個唱段讓我們看到了偉大領袖毛澤東在青年時代的悲憫與豪情;《萬歲》是紅船上的“一大”結束后毛澤東作為偉大事件參與者在當時當地發自內心的喜悅與歡欣的表達,這個唱段與《我有一個夢》遙相呼應,如果說《我有一個夢》是沉痛悲憫中的立志,那么《萬歲》是這個夢想的迎風啟航。對于毛澤東這個角色來說,這兩個唱段賦予了他革命詩人的浪漫氣質,又賦予了他偉大領袖的眼界胸懷;而穿插其中的,由他與楊開慧相逢又離別的若干唱段則既是毛、楊作為個體生命的赤誠“小我”的表達,更是以他們為代表的無數心有靈犀、生死相隨的革命青年群體的象征。作為核心人物之一,毛澤東的唱段并不是很多,但每段都很出彩,人物形象也因音樂的飽滿而鮮明生動。依此類推,陳獨秀、李大釗等角色也都各有各的精彩,即使是小個子劉仁靜在紅船會議中的一小段握拳扼腕的爭辯演唱也是那樣個性突出,動心動情。各個人物各美其美之余,更有那時代之疼痛以《一個幽靈》的唱段反復涌動,時代之理想以《我有一個夢》回環抒發,時代之頌歌以《萬歲》豪邁傾瀉,溢于言表的深情在反復回蕩的詠歌聲聲里淋漓盡致,激越昂揚。全劇音樂表現形式層出不窮,獨唱、對唱、齊唱、伴唱、合唱等等撲面而來,一部大體量的立體歌劇令人應接不暇。
綿密“劇”構
寫建黨偉業,必然要表達時代思想之風起云涌、核心事件之來龍去脈,相關人員之熙來攘往。史料堆疊如山,牽一發動全身,如何寫好紅船這個百年紅色起點之一,毫無疑問是塊硬骨頭。劇構的基礎首先考驗的是編劇,然后考驗的是導演的整體呈現。歌劇《紅船》的文本從2017年夏天開始構思,到2019年2月完成初稿,到2019年12月定稿,其間所經歷的切、磋、琢、磨和數易其稿已無法準確計算,只是對編劇王勇來說,這部作品是他至今創作的20多部舞臺劇當中,投入最深、付出最大的一次創作;而對于導演黃定山來說,歌劇《紅船》也是他最刻骨銘心的一次創作。
回眸百年歷史,謳歌瑰瑋黨業,“立主腦”“脫窠臼”“密針線”“減頭緒”依然是文本創作遵循的不二法門。《紅船》編劇以“寫人即寫人物關系”為框架,在紛至沓來的歷史事件和龐雜零亂的人物關系中突出了中心事件“紅船”上的“一大”會議和主要人物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楊開慧等,首先立住了主腦,精準定位的中心事件和核心人物及其相互關系是歌劇《紅船》這件舞臺藝術品揚帆走遠的奠基石。

《紅船》以“一大”開會會場的明面表現為主線索,沿著這一中心事件,以順時針線索為經線,將開會本身的來龍去脈尤其是會議的重點內容與主旨梳理得清楚明白,據統計,《紅船》明場表現的開會場景是5次,而每次會議又各有重點,各次會議之間更是層層推進。最關鍵的是關于“開會”問題,編導配合天衣無縫,每一次開會都表現得那樣的藝術生動、別開生面:第一次開會是在上海,一群有志青年以“自報家門”的方式介紹地域,來自五湖四海的異鄉人因著同一個目標圍桌而坐,很自然地完成了人物身份的交代。之后因特務搜查而氣氛陡轉,場景也隨之很快轉移。可以說主會場的第一次群體“亮相”猶如“鳳頭”,短而促,脆而勁。第二次“開會”從上海轉移到嘉興,開會場面由圍桌室內改為船泊水邊,與會代表歷經輾轉,顛簸勞頓,置身于濃郁的江南風情中依然鼓蕩起歡欣雀躍的情緒,在南來北往的叫賣與船娘軟語號歌聲中紅船漸入湖心,一次開天辟地的會議正式拉開序幕,此處舞臺重點在民風民韻,舞臺風格講求清新流暢。接下來的兩次開會及最后一次開會逐漸進入實質性的綱領討論與“中國共產黨”的最終定名,這是開會事件結構的“豬肚”部分,尤其最后的定名可謂整個核心事件的壓艙之石,幾次會議交相呼應,節奏更是幾經騰挪,跌宕不止:代表們既因意見相左而爭論而紅臉甚或劍拔弩張,也因最終意見統一而握手言和并相互擁抱。最值得一提的是會議本身是莊嚴神圣的,但劇作家、作曲家、導演等主創團隊也能于恰當處寓莊于諧,將會議開得活色生香,令人欲罷不能:舞臺呈現的最后一次會議場景甚至與麻將“攪和”在了一起。開會途中,遇人查船,會議不得不臨時暫停,代表們為躲避嫌疑,紛紛改扮身份,氣定神閑地打起麻將來,一連串的吟唱誦詩如“日出江花紅勝火,七對開杠餅萬筒”“春來江水綠如藍,單坎單吊一條龍”等,將緊張的氣氛巧妙化解在詼諧的唱詞與曲調中,莊、諧互動,舞臺效果反差強烈,觀眾忍俊不禁,編導對于劇目結構的把控如皮筋在手,松緊自如,妙趣橫生。
開會戲難寫,歌劇《紅船》在很好地完成開會明場戲的編織的同時,又以逆時針線索為緯線,反向貫穿自1919年5月4日到1921年8月之間改變中國命運進程的諸多史實事件:從“五四運動”的風起云涌,到營救陳獨秀的群情激憤;從李大釗迎接陳獨秀出獄到駕車送他喬裝出城;從毛澤東眼見得細妹子向天哭訴到驅張倒張運動;從青山祠毛、楊婚禮到轉瞬離別相送;從李大釗北京討薪到陳獨秀上海經營,人們或并肩作戰,或獨立前行,或親身參與,或幕后支持,每一個人,都在時代大潮中奮勇,每一顆心,都在為家為國為民沸騰跳動,開天辟地的那一刻在重重史實,渺渺人間升華定格。
編劇如椽巨筆,縱橫捭闔,形于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在時間上順敘、逆敘交叉而行,在空間上北京、上海、嘉興、長沙來回轉換,神思千載,視通萬里,由此也不得不佩服編、導的磨合與默契了,如此頻繁的時空轉換,對于舞臺劇來說,必然是新課題、新挑戰。近二十次的場景轉換還不是最終極致的看點,最可觀的是,在貌似散點式的各種場景變化的應接不暇中,那條紅船,那個“開會”的核心要點,以及圍繞在這次會議四圍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與事件,統統自覺進入了一個核心磁場,如同被吸入一個力道強勁的巨大漩渦。編、導共同營造了這個磁場,《紅船》的劇構在文本上力求“脫窠臼”,不落陳套,舞臺上同步求新,重視創意,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完成了“密針線”的環節。而相關的音樂、舞美、燈光等各種創作智慧的集中投入,又更進一步鑄牢了這部驚人的舞臺劇作的渾然一體,從而最終成就了文本在時空設定上的瞬息萬變,舞臺呈現上的流轉自如和出神入化,也從而最終完成了一次具有開拓性研究價值的新成果的整體“劇”構的展示。
一次開天辟地的會議,一群頂天立地的人物,一部史詩歌劇作品,《紅船》以藝術的手法,帶領觀眾洞見深邃而細膩的史事,感受沉郁而流利的詩思才情,共鳴于慷慨浪漫的歌詠,沉浸于宏大綿密的劇構。《紅船》的創作者們以這些獨具慧眼的自我解讀,照顧到了那么雄渾壯闊的宏大題材,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代人的金戈鐵馬、恢廓大度及其才情詩意、快意堅韌,甚或是幽微深沉的情感境界與彷徨求索的精神淬煉統統網羅,發揮出極致的舞臺劇作張力,從“小”處做出“大”來,從“淺”處見出“深”來,從“人人口頭有”做出“人人筆下無”來。嘉興試演,杭州首演,期待黨的百年華誕來臨之際,北京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