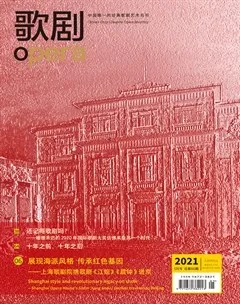十年之前,十年之后
中國音樂劇的黃金十年
文化廣場,作為上海文化地標,擁有太多故事和記憶。而今年,是它作為現當代劇場的十周年。
十年是大年份,同事讓我寫寫這十年來策劃與運作節目內容的感想。當初被調任文化廣場負責節目內容,對我來說實屬偶然。之前我在音樂劇圈算是業內人士,“爬”了很多“格子”(編者注:指寫了很多文章),說了很多話,說來慚愧,論專業建樹當年勝于如今,現在的空余時間畢竟太少了。
十年,不僅是文化廣場,中國的演藝行業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計劃趨向市場,團購趨向散票,從表現形式到內容方向,從代際差異到審美轉換,從科技變革到觀演關系……任何一面在戲劇歷史上都是獨特的。時代發展太快了,很多東西還來不及沉淀,又開始了新變化。
十年來,文化廣場一方面與國際接軌,持續開放、引進、合作了世界前沿和優質的音樂劇作品,推動了音樂劇在中國的全球視野與進程。另一方面,行業也在努力尋找、實踐與證明中國式的舞臺表達。此外,互聯網、全媒體與高科技的融合發展,可謂前所未有。這股力量超出了預期,對中國劇場演藝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
想談未來,不免想先談談歷史。
中國現代劇場的業態,是一百年前從西方傳入,近二十年集中發展起來的。在此之前,我們自己的“劇場業”是與戲曲對應的戲臺文化,一路綿延幾百年至今。說戲曲是中國傳統的音樂劇,是有道理的。戲曲的衰落,只因為當代社會的生活環境不能有效支撐傳統戲曲的劇場業態,并非戲曲自身出了什么問題。但既然換跑道,就免不了重新跑,再次做回“小學生”。其實,現代劇場業也不過是百余年來中國全方位西化的一個局部縮影。

看看亞洲近鄰,日韓在西方戲劇的跑道上比我們出發早得多,發展基礎也好得多。日韓的音樂劇產業起飛,分別是197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那時它們它們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消費能力和意愿都很強。如果把中國音樂劇放在東亞的視野去看,雖然我們已集中發展了20年,其實還一直處在補基礎的階段。
要注意,日韓起步時即是音樂劇本土化,因此它們培養的是自己的演員和制作隊伍。而我們的起步是引進,因此就行業資源的積累這一點,日韓與我們拉開了差距。
“拿來主義”是過去20年中國音樂劇發展進程中形成的主流,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全球化推動了更多海外劇目巡演的可能。另一方面,和文化心態有關。民眾心態,是會影響產業形態的,所謂“需求決定供給”。我們看到,從2002年音樂劇《悲慘世界》的上演到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18年來中國一直以海外經典音樂劇為主流,特別在上海,這座海派城市對于全國其他城市具有音樂劇示范意義。
18年,在快速發展的中國,可以算歷經兩代人了。
但這些年來,我們看到了新的趨勢,那就是年輕一代是更自信、更有個性、也更自由的。他們更在乎自己的感受,追求自己喜歡的作品和人。人有自信,才能自主。我們的上一代,骨子里還是不夠自信的,迫切需要吸收和學習,因此“拿來主義”盛行。而下一代富足了、自信了,創新也可能隨之而來。
因此我認為,中國人演戲給中國人自己看的音樂劇時代,就快到來了。
文化廣場的十年與三個時期
回到正題。
十年,回頭想來,文化廣場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時期,是“自覺直覺期”。自覺+直覺,是因為必須,也因為熱愛,有了熱愛,也會勇敢。記得我剛來到文化廣場的時候,老實說對是否能以音樂劇為品牌,按照自負盈虧的方式運營一家偌大的劇場,并沒有把握。
但新平臺的好處,是給人“海闊憑魚躍”的興奮。作為資深音樂劇愛好者,我的確有太多渴望親眼看見的戲了,那就先干起來吧!直覺告訴我,有些戲不會錯。直到今天,我還是依賴于自己對內容的直覺。在這個行當,很多道理都是“馬后炮”,決策的關鍵那一刻比的是綜合的思考力和感受力。
從2011年的開幕演出《極致百老匯》到當年的年末大戲法國音樂劇《巴黎圣母院》,我們的開篇很精彩,也走對了路。
年末大戲其實是檢驗音樂劇能否養活一個劇院的重要指標,做成了,就有戲。當時,大家其實都沒把握,但我倒有信心。那時我已知道,一個戲行不行,關鍵取決于品質與推廣,兩者缺一不可。不能簡單以成敗論英雄。
2002年,《巴黎圣母院》第一次訪滬只演了5場,票房不佳的原因不在品質,而是沒有大力推廣。后來我們的《巴黎圣母院》一炮而紅,連演24場,竟小有盈余,證明了選對了戲,把推廣做好,就能把劇場養起來。到了第二年,我心心念念的另一部法語音樂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也來了,成功連演20場。8年之后,重返上海的《巴黎圣母院》更不一樣了,2018年竟創下了兩天銷售2700萬的歷史佳績。
第二個階段,姑且稱為“理性成長期”,大約從2014年《劇院魅影》開始。在經歷了頭三年初創期之后,文化廣場已樹立起了音樂劇的品牌,有了比較垂直的觀眾,有實力和能力在一年中同時運作體量更為豐富的海外音樂劇了。

從2014年至2017年,文化廣場音樂劇演出體量開始持續上升。到2018年,甚至一年可以演出10-12部海外原版音樂劇,這是之前不可想象的。其中,有一半是我們自己主辦,另一半則來自社會上的民營演出公司,比如聚橙、七幕人生、華人夢想,等等。
文化廣場在這個階段實現了自負盈虧,財報在幾年內拉出了一根盈利的小陽線,直至今天。有了作為,就有地位。2016年,上汽集團對文化廣場的冠名,對于我們更是錦上添花。
因為市場慣性和供需關系,引進海外劇目依然是最有效、最快速的商業方式。有不少資本推動型的民營公司為了制造更快更大的現金流,體現市場活躍度,也會選擇引進國際大項目。而上汽·上海文化廣場作為中國音樂劇的標桿劇場,既是音樂劇大勢的推動者,亦受益于音樂劇大勢的發展。在2016至2018年,有大約25部海外經典音樂劇來到文化廣場的舞臺,每一年海外音樂劇的演出體量已穩穩站在200場以上。
如果不是疫情,引進海外演出的步伐可能不會減緩。但我判斷,因為政治經濟的全球變革,疫情后的海外演出恐怕也恢復不到之前的狀況了。
這對于本土原創音樂劇和中文版作品顯然是一個利好,也促使第三個階段——我稱之為“本土自制期”的快速到來。過去三年里,音樂劇中文版,特別是小型中文版作品活躍起來是一個重要現象。雖然體量無法與引進大戲相比,但音樂劇因為小戲而接地氣了。一批忠實的粉絲群體因為音樂劇小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而匯聚起來。
過去的20年,音樂劇的推廣過程中還難免有精英化的味道,口號也很“高大上”,令人仰視。而如今的音樂劇更屬于年輕一代,是愿意與作品和演員建立平等、親密關系的一代。因此,音樂劇由自己人創作與制作,由自己人演出,給自己人觀賞的行業基礎已經基本具備,可以參照日韓當年音樂劇蓬勃起飛的基礎時期了。

不算上疫情下的2020年,過去的四年,是文化廣場成長最快的四年,倒不僅是票房成績和音樂劇數量場次屢創新高,更是我們在原創孵化與中文版制作上,邁出的堅實一步。今年是文化廣場自制音樂劇的大年,共7臺自制音樂劇,其中4部為新戲。同時原創孵化也迎來了豐收年:3部2019年孵化的原創作品《生死簽》《南唐后主》《對不起,我忘了》將于今年首演;2020年孵化的2部原創作品《南墻計劃》《無法訪問》也已完成認標;而今年的孵化已經評選出了5部入圍作品。孵化是我們在度過生存期之后的行業回饋,也是一種行業前瞻。我們不僅孵化作品,也孵化人才。對此我們感到高興和驕傲。海外演出雖然可能有更好的收益,但最終,中國人演音樂劇給中國人看,才是真正有效的積累。
熱鬧之下的遠慮與近憂
樂觀之下,我也有擔心。疫情到底是中國自制音樂劇的催生劑,還是一種拔苗助長?去年和今年,我看到了一些現象——有著急上馬、催熟的戲,有主創主演同時接著幾部戲,有制作粗糙的戲,也有只顧流量的戲……而演員價格與制作資源明顯上漲過快。短期看,行業似乎很熱鬧,但卻隱含著破壞規范、敗壞人心的隱憂。
我們現在有一個不太好的戲劇現象,就是所謂觀眾的“非正常迭代”。在世界戲劇發達的國家,正常的“迭代”是各年齡段觀眾持續累計的,年歲增長,觀眾不是變少,而是更多。但中國不是累積,而是迭代,一代“滅了”一代。
結果就是商家總在為新一代的年輕人服務。
吸引年輕人看戲、為年輕人做戲當然無可厚非,但中年人、老年人,那些過去愛看戲的青年人,為什么漸漸就不太看戲了?這個結論我們是有數據支撐的。顯然這并不健康,但反過來也說明,劇場在中國不是必需品,而更像生活的調劑品。當生活壓力變大,可支配的收入和時間變少,戲劇生活是可以被放棄的。而在戲劇發達的國家,劇場是生活的必需品,不會因為歲月漸長而減少消費,相反,年紀增長反而容易成為穩定的觀眾。比如“FAMILLY SHOW”(家庭戲劇),是西方最主流的演出形式之一,為此《獅子王》《魔法壞女巫》《貓》等合家歡的音樂劇可以盛演幾十年不衰。

快速迭代的觀眾,追逐短期效益的制作人,單純迎合觀眾而不是引領,最終可能讓行業因為缺乏魅力而受到大眾冷落。這是我擔心的。
我還有一個擔心,就是技術革新與觀演的關系。如今,我們走在現場演藝的十字路口,西方2000多年的劇場傳統可能會“轉折”在我們手里,這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可能就是這么湊巧地遇到了歷史轉折點。大家這么忙,進劇場的決策這么重,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準備和符合時代的內容支撐,劇場是有可能被時代顛覆的。
而且,人類的體驗在科技之下獲得了幾何倍數的增長。AR、VR、沉浸式、全息……我們被信息包裹,輕而易舉可以獲得過去不可想象的體驗。那么,在劇場這樣安靜的面對面環境下,以什么拉住年輕觀眾?它的競爭力在哪里呢?
在沒有電影、電視、互聯網、手機的時代,舞臺藝術當然一枝獨秀。但如今有那么多娛樂的選擇,那么便捷,舞臺藝術的挑戰無疑增加了。對中國尤其如此,因為我們的舞臺藝術還沒有很強壯,就開始遭受新業態沖擊了。我認為,西方戲劇發達國家早年如果碰到與我們如今一樣的遭遇,他們現在的戲劇業態也會不一樣。

即便沒有太多科技含量,類似劇本殺、密室的體驗類游戲,有一定戲劇性,決策更輕、更便捷,門檻更低,更容易吸引年輕人。我看到在去年疫情期間,劇本殺和密室產業是逆勢大幅增長的。這又是新一代的演藝內容與消費群體了。
我們劇場行業起步得比較晚,有許多管理還比較滯后。當觀眾用腳投票的時代到來,當政府不會無限度貼補劇場,當以演出為中心成為必然之時,我們需要怎樣的劇場管理?我們需要怎樣的戲劇內容?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
十年之前,十年之后,一路挑戰無止境。這個時代,創新思維可能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精細化運營也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關鍵。“創新+精細化”,決定了我們的未來,我想這大概是下一個十年我們
持續努力的方向。(作者系資深音樂劇人,上海文化廣場劇院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