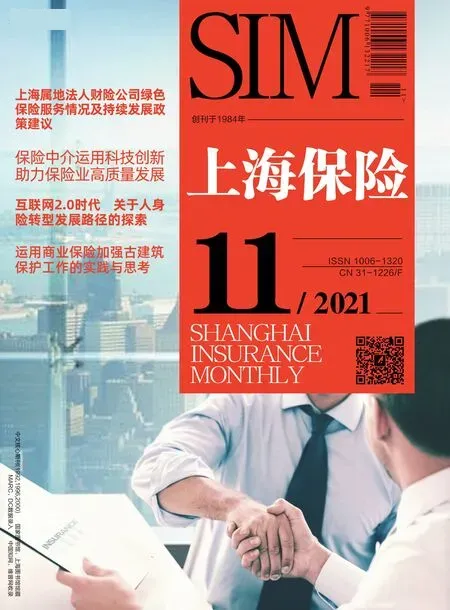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協同增信的機理與實現路徑
葉明華 陳 康 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

一、農業信貸狀況及違約風險分析
(一)我國農業信貸發展狀況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農業產業的發展、農村經濟的增長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均需要資金支持,農村金融機構通過資金供給方式擔負起我國農村經濟復興的重要使命。圖1顯示,截至2020年末,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發放涉農貸款余額38.95萬億元,是2007年涉農貸款余額(61151億元)的6.37倍,年均增長率為38.35%。與涉農貸款增速相對應的是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違約率處于相對較高水平。

圖1 涉農貸款余額及其年增長率(2007—2020年)
據圖2可知,自2009年至2018年,我國涉農貸款違約率經歷先平穩下降,后緩慢上升的態勢。盡管這期間我國金融機構全部涉農貸款違約率從5.94%下降至3.60%,但仍處于銀保監會所提出的普惠型涉農貸款不良容忍度3個百分點的臨界點,而作為農村地區涉農貸款發放主力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年均涉農貸款違約率為9.26%,最低為7.00%,最高達到15.48%,顯著高于我國其他類型銀行的涉農貸款違約率。

圖2 我國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違約率(2009—2018年,單位:%)
(二)我國涉農貸款高違約率的成因解析
1.自然災害風險的客觀性
我國幅員遼闊,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災害最頻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我國常見的自然災害有氣象災害,如干旱、洪澇、臺風、風暴潮等,地質災害如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等。而農業基本是靠天吃飯的弱質產業,易受客觀自然災害的沖擊。數據顯示,2002年至2019年間,包括干旱、洪澇、風暴、低溫冷凍和雪災等在內的自然災害造成農作物平均成災率達到29.82%,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農作物抵御自然風險能力相對較弱的狀況。
2.農產品價格的波動性
隨著我國農產品價格市場機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市場機制在農業資源配置中日益發揮主導性作用。市場機制的作用致使農產品市場價格發生波動,可能導致農業生產經營者必須以低于預期價格出售農產品,進而導致農戶正常收入受損,無法按期還本付息。據圖4可知,2002—2020年間的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均處于不斷波動態勢。同期,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均值和方差分別為105.96和49.32,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均值和方差分別為101.36和15.39,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業面臨著相對于工業更大的價格波動風險。

圖3 農作物受災狀況(2002—2019年)

圖4 農產品價格和工業品價格波動狀況(2002—2020年)
3.借貸雙方間的信息不對稱
由于農村交通條件較差、信息傳遞不便等原因,在農村金融市場中,金融機構對農戶的真實貸款意愿、還款能力、資金運用等信息難以準確獲得,農戶擁有貸款信息優勢而金融機構處于信息劣勢,由于這種信息不對稱,貸款前后可能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這是主觀因素所致的涉農貸款違約風險。
總之,相對較高的農戶違約率不僅影響了銀行績效,還損耗了農戶自身信用等級,造成金融機構在面對農戶申請貸款時,表現出“惜貸”現象,使得金融機構在支持“三農”發展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農業保險和農業擔保有助于提升農業生產經營者的抗風險能力,解決農戶缺乏抵押、擔保的問題,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助于提升農戶信用,增加其貸款可得性。
二、農業保險在農戶增信方面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問題
(一)農業保險在農戶增信方面取得的成效
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探索建立農村信貸與農業保險相結合的銀保互動機制”。2010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與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關于加強涉農信貸與涉農保險合作的意見》,正式把保險機制引入農業信貸市場。在政府相關政策指導下,我國保險機構和各類農村信貸機構(農信社、農商行、村鎮銀行等)陸續在河北、廣東、新疆、安徽等地開展試點,形成了以農業保險作為農戶申請貸款的條件和以農業保險保單作為抵(質)押品的替代或補充兩類農業保險増信模式,前者以安徽省政府聯合國元農險公司推行的“草莓保險+信貸”“茶葉保險+信貸”產品為代表;后者則以江蘇省財政廳、中國郵儲銀行江蘇分行以及人民保險江蘇分公司合作推出的“農業保險貸”為代表。
據圖5可知,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從2009年的134億元增長至2020年的815億元,年均增速18.26%,同期的涉農貸款余額從9.13萬億元增長至38.95萬億元,年均增速14.32%。兩者增速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農業保險基于農業風險損失補償、保單抵(質)押及農戶信用信息共享等優勢,為參保農戶進行間接“擔保”,進而為實現農戶増信、提升其貸款可得性提供了可能。

圖5 我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與涉農貸款余額狀況(2009-2020年)
(二)農業保險為農戶增信時存在的問題
盡管農業保險基于其風險管理優勢在提升農戶信用水平、緩解農戶“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農業保險在為農戶增信的過程中也存在如下問題:
1.農業保險覆蓋主體與涉農信貸資金需求主體不完全匹配
目前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主要覆蓋糧食作物和有限的畜禽產品,而從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成本看,農戶自我積累及農業生產資料供應商的隱形信貸基本上可滿足農戶糧食生產的資金需求。而信貸需求量較大、種植飼養經營風險較高的經濟作物種植、畜禽及水產養殖領域,則缺乏相應的保險產品提供風險保障,難以支撐農戶多種經營的信貸需求,導致保險保障的主體與涉農信貸資金需求主體之間存在不完全匹配的問題。
2.農業保險保障水平難以滿足信貸機構對抵押品的規定
我國農業保險總體的保障水平僅是美國的1/5、加拿大的1/3和日本的1/2。“低保障、廣覆蓋”是我國農業保險的主要特征。農業保險保障水平不足致使信貸機構對保險賠付的期望值偏低,使農業保險對信貸資金的抵(質)押作用受限,不能充分分散涉農金融機構所面臨的信貸風險狀況。另外,農業保險目前的定損方法和勘驗技術仍以人工現場定損為主,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問題,減弱了保險和風險之間的相關性。部分農業保險機構理賠時審批環節多、手續復雜,影響出險農戶向信貸機構按時還款。
3.農業保險作為農業信貸的前提條件受到制度約束
2019年發布的《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于開展銀行保險機構侵害消費者權益亂象整治工作的通知》認定,銀行在產品銷售過程中強制捆綁、搭售保險屬于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致使涉農金融機構在放貸時要求農戶投保保險,尤其是將銀行作為第一受益人的操作,被當作霸王條款而難以推行。在保單不作為抵(質)押品的情況下,農戶即使投保農業保險進行風險管理,也會因金融機構不是受益人,致使涉農金融機構仍然面臨農戶違約風險。
三、農業擔保在農戶增信方面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問題
(一)農業擔保在農戶增信方面取得的成效
2015年,財政部、農業部和原銀監會聯合發布《關于財政支持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指導意見》。2016年5月中央財政出資建立了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有限責任公司,隨后33家省級農擔公司相繼成立,基本形成了全國農業擔保機構網絡。截至2020年底,農業信貸擔保聯盟共設立專職分支機構924家,同時與地方政府或其他金融機構合作設立660家業務網點,對全國縣域業務覆蓋率達到94%以上。目前,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簡稱“農擔體系”)已初步建成并步入良性發展軌道,截至2020年底,全國農擔體系在保余額2117.98億元,放大倍數3.4倍,政策性職能逐步顯現。

農業擔保機構在農戶増信的實踐中主要實行的是“政銀擔”模式,即政府、農擔、銀行三方互相推薦項目,共同分擔風險,農擔實踐的典型模式主要有:(1)河南省農擔公司“政銀擔”模式。截至2021年2月底,河南省農擔公司已經與78家銀行建立合作關系,與102個縣按照4:2:4分擔風險的模式開展“政銀擔”合作,并到位風險補償金4.8億元,實現累計擔保業務規模對縣級風險金平均放大倍數16.47倍。(2)湖北省農擔公司“政銀擔”模式。截至2021年7月,湖北省農擔公司與全省97個縣(市、區)政府建立了政擔業務合作機制;與10家省級金融機構和93家地方銀行建立了銀擔業務合作機制,實現了全省4:4:2“政銀擔”合作風險分擔機制全覆蓋,實現累計擔保貸款20826筆,金額147.27億元,資本金放大倍數9.2倍。
具有專業信息甄別優勢的農業擔保機構不僅能夠發揮信號傳遞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而且承擔了為違約農戶進行代償、對擔保農戶進行監督的職能,能夠激勵農戶努力經營,降低違約風險,有利于提高農戶的信貸可得性。過去,商業性擔保在農村地區經營利潤較低且擔保門檻較高,服務深度不足。互助性擔保雖然能夠利用人緣、地緣優勢降低交易成本,但受到地域空間和資金規模的制約,其風險防范能力較弱。當前,政策性擔保公司的成立,成為政府介入農村信用擔保市場的一個嘗試,即通過政府介入緩解農戶、銀行以及擔保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二)農業擔保為農戶增信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農擔體系面臨的擔保風險較為集中
2015年《關于財政支持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指導意見》(第三條)、2017年《關于做好全國農業信貸擔保工作的通知》(第一、二、三條)及2020年《關于進一步做好全國農業信貸擔保工作的通知》(第三條)等政策文件均規定,農業擔保機構的政策性業務范圍限定在農業生產及與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產業融合項目之內。受以上政策限制,農業擔保機構無法通過多元化的擔保業務來分散經營風險。雖然農業擔保機構通過對農戶進行監督來介入農業生產經營風險管理,一定程度上規范了農業經營,但對外部存在的客觀風險管理有限,一旦遭遇較大范圍的農業重大災害損失,農擔體系就勢必面臨眾多農戶集體違約的情況。
2.政策性農擔體系運行的隱性制度成本較高
第一,農業信貸擔保經營風險補助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資金,這種政府兜底的風險補償措施加上農擔機構本身的政策性屬性,決定了即使其在面臨信息不對稱時,也會怠于對申請農業信貸主體的資格審核而同意擔保,出現“指令擔保”和“人情擔保”狀況,增加違約風險。第二,政策性農擔體系聚焦免擔保費、降費率、減手續“三項指標”,引導具有資金需求的農業經營主體進行債務融資,但是對于具有一定生產規模的農業經營主體,單獨依靠銀行貸款無法有效解決農業融資難題,政策性引導很可能導致其對政策性農擔貸款產生依賴,破壞其內源融資機制。第三,農擔體系目前仍處于建設初期,主要工作人員來源于政府部門和銀行等金融機構,缺乏信貸擔保專業人才。專業人才的缺乏會進一步加劇擔保信貸過程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增加農擔體系運行的制度成本。
四、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協同增信的機理與實現路徑
(一)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協同增信的機理
鑒于農業保險和農業擔保在農戶増信中具有各自的優勢和局限性,以下將探討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如何協同發展,共同服務于農戶信用提升。農業保險作為農業生產的“穩定器”,能夠分散農擔機構不能分散的外部客觀風險,提升農戶抗風險能力,一定程度上為農業擔保機構分擔了風險,可以作為農業擔保機構擔保的充分條件;另一方面,農業擔保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監督和代償責任,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農業保險的事中風險管理,彌補了農業保險保障水平相對較低的局限。總之,在政府引導下,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的協同發展有助于兩者功能優勢互補,進一步增強了對農戶生產過程的監督、信用甄別,完善了信貸風險補償機制。目前,國內相繼出現湘潭市“保險+擔保+信貸”模式、上海“銀行+擔保+保險”模式等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聯動増信的探索。
(二)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協同增信的實現路徑
農戶信用是農村普惠金融發展的基礎,唯有農戶信用提升,涉農貸款方可實現增量和增速的提升;而農戶信用的提升,既需要依靠農戶自身收入的逐步提高,也需要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的協同發展,共同助力農戶增信。
1.平衡政策機制與市場機制
農業具有顯著的外部性,而農業保險和農業擔保又具有準公共物品屬性,所以推動農業保險和農業擔保協同増信,離不開政府政策支持。一方面,政府需制定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聯動増信的指導意見,明確相關職責,從頂層制度政策層面加強引領,并注重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另一方面,在政府政策引導下,堅持實行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的市場化運作,承擔市場經營的相應風險,并構建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協同増信考核體系,以優化農業保險與農業擔保協同増信的運行程序,降低政策屬性隱形成本。

圖6 政府引導下農業保險、農業擔保與涉農銀行協同發展模式
2.聯合共建信息共享平臺
信息不對稱是阻礙農戶信用提升的重要因素,而信息共享平臺的建立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甄別農戶信用信息,提升農戶整體信用水平。為此,政府部門可基于其特有的公信力,發揮指導引領作用,協同農險公司、農擔機構及涉農金融機構建立特定涉農數據的收集、發布和共享,將各方所掌握的涉農信息通過共享平臺進行整合對接,并根據信息的變化及時更新,以降低各部門信息搜尋成本,提升涉農信貸效率。
3.注重提升農業保險保障水平
農業保險保障水平的提升關乎農業經營的抗風險能力,在提升農擔機構信息甄別能力和提高農戶抗風險能力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農業保險在為農戶増信時,需要把握自身風險管理屬性,不斷擴面、增品、提標,并搭建多層次的保險保障體系。一方面,農業保險機構要不斷創新保險產品,在提升農業保險產品風險敏感度的同時,積極與授信農戶所經營的農產品進行對接;另一方面,農業保險機構必須扎實做好保險理賠工作,可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提升定損、理賠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并注重簡化理賠過程,提升理賠效率。
4.不斷完善農擔體系風險補償機制
完善的風險補償機制是農擔機構持續健康運行的重要保障。農擔體系風險補償機制的完善需進一步優化風險保障基金投入,并在銀行、保險和農擔之間合理分配風險。一方面,改變財政資金作為風險補償基金唯一來源的現狀,探索吸收農業企業及其他社會資本,以減輕財政壓力,擴大基金規模;另一方面,優化風險分擔在農擔、農險和涉農銀行之間的合理比例,在保證農擔機構風險可承受的前提下,避免涉農銀行因有農擔“兜底”而產生疏忽管理道德風險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