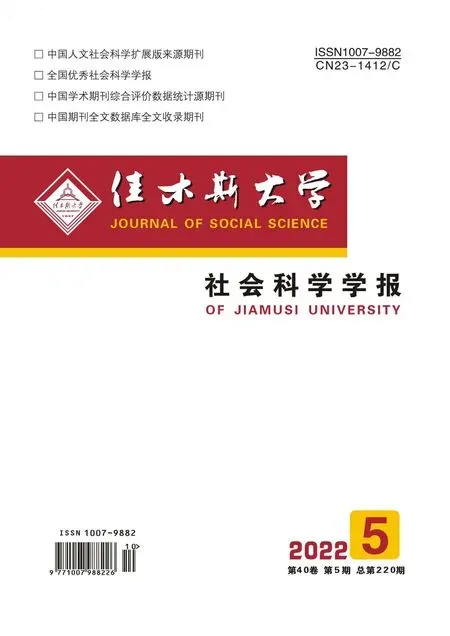《文心雕龍·樂府》發微
——淺論劉勰作《樂府》篇之原因
陳靜誼
(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海淀100084)
劉勰在《文心雕龍·樂府》篇開宗明義,將樂府解為“聲依永,律和聲”。劉勰在此明確了樂府為一種配樂之文體,也即合樂的歌詩。“聲依永,律和聲”六字又與《文心雕龍·明詩》篇的“詩言志,歌永言”相呼應,這表明了劉勰將樂府與詩相互區分的文體觀:樂府主聲主律,以聲律合詠誦;詩則主言主詠,以言詠表志心。在《樂府》篇的文末,劉勰表示“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自敘他效仿劉向《七略》以《六藝略》錄《詩經》類著作,以《詩賦略》錄“歌詩”的方式,將詩與歌作以區分。然而關于劉勰作此文的真正目的,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價值。
一、劉向之于劉勰:效仿還是借托
關于劉向的“詩與歌別”,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云:“此據《藝文志》為言,然《七略》既以詩賦文藝分略,故以歌詩與詩異類……此乃部居所拘,非子政果欲別歌于詩也。”[1]58然而,范文瀾則持有不同觀點,《文心雕龍注》中云:“《別錄》詩歌有別,《班志》獨錄歌詩,具有精義,似非止為部居所拘也。”[2]107
現將各家對于“詩賦”自成一略的說法總結如下:其一是認為漢人有意區分文學與經學,是一種文體認識的進步。郭紹虞認為,“《藝文志》本于劉向所定的七略, 以‘詩賦略’與‘六藝略’‘諸子略’等分列, 使文學類的創作, 和關于學術的書籍劃清鴻溝。”[3]59劉師培《論文雜記》云:“古人有韻之文,另為一體,不與他體相雜也。”[3]60相似地,顧易生、蔣凡認為,《漢書·藝文志》區別詩賦與六經諸子,是對文學和一般學術著作的區分觀念。[4]611-612
其二則是認為詩賦并非單獨成文體,而因為其體量過大而不得不單成一略。余嘉錫《古書通例》中表示詩賦因為“篇卷過多, 嫌于末大于本, 故不得已而析出”,類似于“《七略》史部附著于《春秋》”。[5]241程千帆、徐有富則認為:“后世史書出于《春秋》,詩賦出于三百篇, 然而《七略》卻將史書附在《春秋》之后, 而詩賦卻自成一略。源流雖同而處理各異的原因就在于篇卷多寡不同。史家之書, 自《世本》以下, 僅八家四百十一篇, 不足成略, 而詩賦自屈賦以下, 達百六家千三百十七篇, 非單獨自成一略不可。”[6]110
這兩種觀點,其一是從“文學自覺”的角度分析,其二則是從著書實際的角度考證,無論哪種說法,均不能作為劉向分別“詩”與“樂”的理由。根據《藝文志》“詩賦”分類下小序云:“不歌而誦謂之賦, 登高能賦, 可以為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由此觀之,賦既為“不歌而頌”,劉向將“歌詩”與“賦”列為一家,必不是出于能否合樂的考慮。而小序中多次征引《詩》,則可觀“詩賦”之源流本自《詩經》,也可從旁佐證第二種說法似更客觀。繼而推之,劉勰與劉向在分類問題上是存在明顯差異的。
黃侃在《札記》中評價道:“劉彥和謂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殆未詳考也。”[1]44應當如何看待這句話呢?根據《文心雕龍·序志》所言“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以及章學誠《文史通義》評“《文心》體大而慮周”,可謂“籠罩群言”,加之劉勰著書遍覽當時所能及,“積十余年,遂博通經論”(《梁書·劉勰傳》)的情況,遑論其“未詳考”,或顯武斷。筆者認為,劉勰倘若知自己與劉向學說之分別,仍借以為自己之學說之背書,必有其獨特的考慮。這便引向了下一個問題:劉勰作《樂府》篇的目的是什么?他所指的“以標區界”究竟為何?
《文心雕龍·樂府》為“樂府”文體的第一篇專論,劉勰意識到徒詩與歌詩的分別,把樂府作為一種文體與詩并列,對后世的樂府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作為《文心雕龍》文體論的第二篇,《樂府》緊繼《明詩》篇之后,劉勰注意到了詩的可歌與不可歌、合樂與不合樂的區別,他將樂府作為一種文體單列。然而劉勰是否是為了文體分類而作此篇呢?這需要我們對《樂府》的文意進行梳理。
劉勰《樂府》篇以時間順序行文,自上古的音樂之起源開始,簡述了先秦禮樂觀風俗知盛衰化動八風,漢魏設立樂府卻不得古法而詩聲俱鄭自此而生的情況。觀其所舉例子限于皇宮貴族與文人士族,忽略了作為漢樂府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民歌,對于這種樂府詩中具有極高文學價值的來源形式,劉勰自敘述先秦“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采言,樂胥被律”的采詩之風之后,居然在其對于后世樂府的敘述中被忽略掉了。劉勰在講漢樂府時,所舉例子為《桂華》《赤雁》,只字未提民間的樂府詩;述及魏,則講魏之三祖,宰割辭調,音靡節平,亦并未觸及魏朝樂府已不采民歌與漢樂府迥然不同之處;述及南朝時,也只舉傅玄、張華的作品,也未提及膾炙人口的民歌諸篇。周振甫評價為劉勰“對于樂府詩的選文定篇工作沒有做好”。[7]54張國慶《文心雕龍瑕疵辨析》中也認為,作為樂府詩主體的民歌,劉勰“只是表面上虛應故事,寥寥數語總體帶過,沒有進行任何稍微深入一點的考察和探究”。[8]68-75可以得知劉勰既沒有從分類的角度討論文體,也沒有給樂府以客觀合理的評價。《樂府》篇限于追溯歌詩之源流,并慨嘆“韶響難追,鄭聲易啟”,劉勰并沒有從文體分類的角度對后世的樂府研究給出太多有價值的啟發。故筆者認為,劉勰撰《樂府》,并非單純為了標舉樂府這一文體類別。
二、紀昀評“務塞淫濫四字,為一篇之綱領”析疑
關于此篇意旨的問題,除了“詩與歌別”,還有“務塞淫濫”一說。紀昀曾評“務塞淫濫四字,為一篇之綱領”。按說“務塞淫濫”其主語為“先王”,意為先王因樂化動人心的作用之強烈,故謹慎對待,務必止塞淫濫之樂的流傳。這句話的賓語落在了“樂”上,也即是說紀昀認為劉勰對于樂的態度應當是“務塞淫濫”,提倡“中和之響”的儒家音樂美學觀。關于這點,黃侃也謂“彥和此篇大旨,在于止節淫濫”。然而《樂府》篇是劉勰為了“正樂”而作這一觀點,仍然存疑。
劉勰在文中提到“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包含了“心”與“體”的層次關系,“詩”是核心,在內部圈層;而樂聲則是樂府詩的形態,在外部圈層。這種邏輯關系暗含了一種詩與樂的層次問題,顯然劉勰認為對于樂府詩,詩的重要程度是高于樂的。隨后,劉勰提出兩種辦法以正樂府:瞽師調其器與君子正其文。劉勰對于這兩種做法也是有所側重的,他說“淫辭在曲,正響焉生”,意味著文辭不當則遑論曲響;又云“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說明對文辭進行刪節以合雅正才是根本。而關于音樂方面的“務塞淫濫”措施則除了“瞽師務調其器”之外并未加以其他闡述。根據《樂府》篇的贊,“八音摛文,樹辭為體”,也可知劉勰雖以歌詩為一獨立文體,其論證的核心仍不出于“樹辭”。也即是說對于劉勰而言,樂府最終的落腳點仍然是“文”,故其旨意非為“樂心”而不出“文心”了。這就令人對“務塞淫濫”作為全篇綱領產生了一點疑問:既然劉勰對于詩與樂是有所側重的,詩重于樂, 而“務塞淫濫”是指向先王對“樂”的做法的,而彼時先秦,詩樂未分,樂府未立(或說秦時有前樂府,但依照本文武帝“始立樂府”認為未立),故以“務塞淫濫”泛泛指稱為本文主旨,就忽視了《樂府》篇的真正文意所在。
那么《樂府》篇的主旨為何呢?筆者以為簡言之是“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八個字,并且 “君子宜正其文”。此八個字既說明了劉勰對于樂府詩包含表意與表音的兩層,又包含了詩相比于聲,處于核心的地位,也即一表一里,“和樂無荒,故表里而相資”的關系,表現出《樂府》篇在“詩”與“聲”之間有所側重。黃叔琳在《文心雕龍輯注》中對“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上加了重點,并眉批作“二語透宗”,當為依據[9]69。“瞽師務調其器”不應作為文章旨意的原因是筆者分析認為劉勰對于“韶響難追,鄭音易起”的態度是比較消極的,他并未從音樂的角度提出解決方案,側重的仍是對于文辭的考量。另外一條黃叔琳的注也很值得一提,云“聲詩雖別,亦必無詩淫而聲雅者,固知鄭聲既淫則詩不待言矣”。[9]69-70這即是說聲雅而詩淫者不存,這句話是注“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的,固然深得《樂府》篇側重“節辭”而非“調律”的思想。
此外,在提及子建士衡時,劉勰認為“咸有佳篇,并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劉勰在此把不被絲管的詩也劃入樂府,似乎與其對樂府歌詩需要合樂的標準有所矛盾。黃侃認為這些詩“徒以蒙樂府之名,故亦從之入錄。”[1]44黃侃又言,“案彥和作《樂府》篇,意主于被管弦之作,然又引及子建士衡之擬作,則事謝絲管者亦附錄焉。故知詩樂界畫,漫汗難明,適與古初之義相合者已。”[1]45筆者以為此說甚是。大抵原因在于詩與樂分離為大勢所趨,因聲音不比文字,在傳承時受到諸多限制,文字可溯而聲響難追,出現徒以樂府為題卻不能被管弦者為常理之中。倘若因為這些作品徒有樂府之名而無聲,依照徒詩與樂府的分類方式,將其劃分入《明詩》篇,也頗為不妥。這也反映出劉勰分立《明詩》與《樂府》篇存在某種難以避免的困難。而郭茂倩《樂府詩集》的分類中有不入樂的“雜歌謠辭”與“新樂府辭”,后世也頗多以樂府命名詩集如白樂天《新樂府》者,正反映了詩與樂在傳承中存在差異的不可避免的趨勢。
三、余論:結合《明詩》與《樂府》討論劉勰的樂府觀
以上論證了劉勰作《樂府》篇最終落腳在于正其詩的旨意上,相比于“樂心”,更側重“文心” 。這樣的詩樂觀使我們認識到不應單獨論《樂府》一篇,而是應當結合《明詩》篇綜合來論。
雖然《明詩》與《樂府》篇開篇相互承應,一個為“詩言志,歌永言”,一個為“聲依永,律和聲”,并且也均對詩樂同源有所描述,但可以明顯看出劉勰對于詩與樂持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比較:
其一,“情”的角度。《明詩》篇認為情對于詩的影響較為正面, 比如“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劉勰認為人依據情感作詩吟志是出于自然,并且他對于《孤竹》篇評價為“古詩佳麗”,并曰“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可見劉勰不反對詩歌創作中切合情感。然而在《樂府》篇中,劉勰肯定了“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卻對于樂表達感情以“淫濫”而批評之。更具體而言,劉勰對于魏之三祖所作樂府,認為“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而對于不符合“中正”標準的“不離于哀思”之“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不置貶抑,對“張衡怨篇”評“清典可味”。具有矛盾的地方是,劉勰在《明詩》篇對于建安文學褒揚“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與在《樂府》篇的“音靡節平”“韶夏鄭曲”批判形成鮮明對比。由此可知,同樣是文辭,劉勰對于文學的詩和樂府的詩所限定的框架實為不同。
其二,“正”的角度。劉勰以詩之四言為正,以樂之韶響為正,但對于二者的容許度有較大差異。《明詩》篇中云“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可以看出劉勰對于四言與五言也具有正偏之分。綜觀篇內,劉勰使用大量筆墨描述五言,也對五言詩之佳作多有贊賞,說明劉勰對五言文體不持偏見。況且對于文思方面,又說“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雖然“鮮能通圓”“妙識所難”,可見劉勰對于詩文構思也并不加以過多限定。而在《樂府》篇中則沒有這樣寬容,劉勰對自“始立樂府”以來的樂府多加以批判,或曲調淫怨,或辭繁難節,自秦后禮崩樂壞之后,無論如何均是“中和之響,闃其不還”。當然,《明詩》篇中對于三六雜言詩則是一筆帶過,并且批評了“近世所竟”的爭奇斗妍的浮靡詩風,推重“風清骨峻,篇體光華”清麗佳篇,說明劉勰不管對于詩還是樂,都有“中正”的標準,只是對詩則時有佳評,對樂則多認為不合“中正”。
其三,“變”的角度。《明詩》篇對于文體流變持正面態度。劉勰認為“情變之數可監”,在《時序》中更是認識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關于樂的變遷,《時序》中也有言“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紋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可見劉勰對于反映“盛衰”“興廢”之樂的變遷不可避免這一點,也是有認知的。詩之流變“英華彌縟,萬代永瞻”,樂之流變則“韶響難追,鄭聲易啟”,說明劉勰在對待詩和對待樂的變遷觀點上出現了開放與保守的區別。
綜合以上三點,可以對劉勰的詩樂觀及其作《樂府》的用心進行如下的討論:
詩發與人心莫非自然,為何樂發于人心就需“務塞淫濫”呢?究其原因,仍是劉勰的音樂觀主要繼承于先秦儒家的禮樂思想。可以通過了解《樂記·樂本》中關于“聲”與“樂”的意義區分窺見其端倪。《樂記·樂本》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于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能知樂。”在《樂記》中,“聲”發乎情,但“樂”是經過禮與德節制后的產物,在“樂”的意義之中已然包含了統治者的倫理與政教,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性”,而那些不符合禮與德的政教準則的“流癖、邪散、狄成、滌濫”的聲響(《樂記·樂言》),都只叫做“音”,而非能稱之為“樂”。既然“樂”的含義包含了“正音”的層面,就不難理解劉勰為何要在對樂府的音與辭做出唯求“正聲”,務止“鄭曲”的苛刻要求。
在劉勰的時代,開始呈現文學自覺的風貌,詩開始脫離政治,也與樂產生分離,但是樂盡管在創作實際的層面上也逐漸開始脫離政教,在理論層面卻仍然未脫先秦禮樂觀的束縛。這也是劉勰的詩觀與樂觀之間產生不同步的重要原因。故而知劉勰將《樂府》單列一篇,并非單純為歌詩作傳,而是將詩從政教功能中抽離出來,使得樂府能夠繼續承載禮教的功用。在劉勰那里,文字藝術已經脫離了功利實用的層面,進入到審美的境界,但音樂大概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