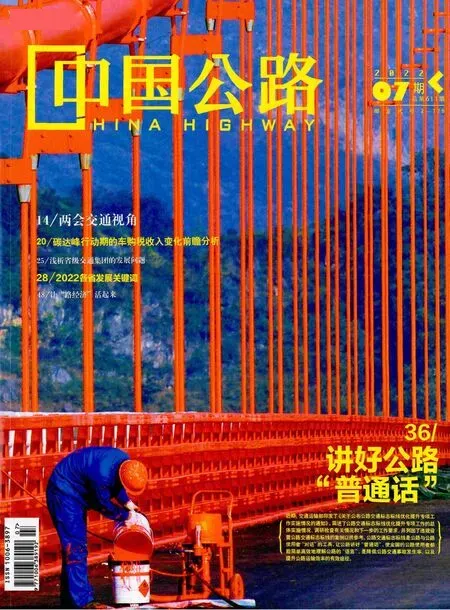改革設計 無法言說之痛
文|浮塵
此前談過建設領域借助補助資金和執法利劍,用韌性十足的管理手段,讓行業發展機構在與參建單位的博弈中進退自如、暫時安生的話題。其實,事物發展到一定階段,各方力量總會在不經意間達成某種默契,擴大既得利益,建設領域不過是其中一個縮影罷了。只是,當這種平衡以傷及第三方為代價,或者以出讓一方核心利益為前提時,追根朔源、調整重組的改革力量便已積蓄到位,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改革只待一個師出有名的時機。
“執法為民”作為一種理念推行后,“三轉”(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必須正面硬杠的首先就是轉職能。職能交叉、層級過多、機構重疊、多頭執法等問題首當其沖。給出的對策是“兩集中”(行政權力向行業主管部門集中、行政處罰向執法機構集中)。至此,“減少政出多門、重復執法”的出師之名已經到位,執法改革利劍順利出鞘。
成天一針見血,
自認快意恩仇。
苦心尋章摘句,
風雨中猶清醒。
所謂生民立命,
過眼便成浮塵。
文章若能濟世,
應問懸壺之人。
編辦負責 快字當頭
政府機構改革職能在編辦,行業要想在改革過程中消除積弊,必須在與編辦的博弈中取得主動。但是,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編辦的話語權都比行業高出不少,在強弱相差懸殊、甚至需要“仰視”的談判對象面前,行業表達自我訴求的底氣無疑會大打折扣。在改革參與者的實力比拼中,行業主管部門先失一城。
當然,政府在民生等問題上主動擔當履職盡責是毋庸置疑的,行業暴露出“阿喀琉斯之踵”的主要原因,在于壓力傳導過程中出現了偏差。本該考核下級政府和投資主體的進度和投資指標,最后卻變成了行業的任務!令人遺憾的是,改革對時間的要求,同樣被錯誤地傳導給了行業,不知不覺中,行業莫名其妙地變成了考核對象。畢竟在缺乏評判改革質量的有效標準,且職能型組織架構中改革“后半篇文章”由行業負責的情況下,從局部最優角度分析,承擔進度與質量雙重壓力的改革主持者編辦,將工作要求更多地向時間側重,似乎也無可厚非。
行業先是在強弱比拼中落了下風,又被時間節點倒逼,長期困擾自身發展、亟待解決的“治踵”問題只好在本輪改革中被迫擱置。至此,于編辦而言,改革的任務變成了堅守人員編制、身份和單位規格底線;于行業而言,改革的任務變成了內部的職能重構和人事調整。編辦作為改革的牽頭部門,因在政府部門中地位相對較高,掌握了工作主動權;行業因對自身更加了解,也更容易擺平內部事務,獲得了與改革主持者“坐下來談”的機會。但強弱對比早就注定了這是一次非對稱博弈,“退”是必然的,只是“退到什么地方”成為需要慎重考慮的課題。
接下來,改革正式進入謀劃、調研、構思、溝通、談判、妥協和綜合階段。這一切的前提是兼容并包、從善如流。需要專業的隊伍、足夠的時間、廣泛的摸底,以及一以貫之的思路和與之配套的制度。但是,從2018年底中辦方案印發,到2020年底改革基本到位,僅有兩年時間。其中,各省份僅是印發方案就花了大約1年。這似乎是一個可以充分論證的合理時間,但考慮到編辦要同時承擔5個類似改革的實際,情況就不那么樂觀了。因為即便排除一切干擾,一門心思放在改革方案上,加上節假日,留給每個行業的平均時間也只有70來天。而時間,恰恰是一個剛性考核指標。
閉門改革 質量堪憂
時間緊、任務重,說明改革者晝夜兼程,殊為不易。但是,在看到勞苦功高的同時也應看到,一些本該做實的工作可能被選擇性忽視了。也許是信息不對稱的原因,至少在筆者的朋友圈內,沒看到有誰參與過改革方案座談。甚至直到方案落地那一刻,連很多涉改對象的直接領導都不清楚隊伍的未來。對此,行業參與者的答復是:時間緊迫,來不及征求意見,而且征求意見可能會造成不良后果。較為統一的說辭有二:一是改革由編辦主持,在沒有定論前,行業越俎代庖、弄得滿城風雨,并不合適;二是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過早透露容易造成人心不穩,甚至影響當下工作。
面對難題求速度,是本輪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
改革參與者的話似乎有其合理成分,可擔心與現實之間畢竟還有差距。姑且不論“鴕鳥政策”能否換來天下太平,但用一個未經廣泛征求意見的方案,去決定一大群人的未來,至少在審慎性上是有缺失的。因此,社會完全有理由擔心方案在落地過程中遭遇挫折。
須知,改革看重的是重建,目的是通過高質量重建獲得較以前更“好”的效果。這需要十足的硬功夫,周全是必備的要素,科學論證是最基本的前提。在“隱秘”中推進的改革,有沒有經過科學論證,這里不便妄下定論,但至少在調研和征求意見方面推行“鴕鳥政策”有失周全。
一果多因 待留“來日”
改革的主持者難道就不怕因此造成機構運轉不靈,為后續埋下隱患嗎?不怕。職能型組織架構決定了編辦承擔的改革僅局限于前半部分,還有后續責任可以推諉。一果多因,無懼對證。反正改革全過程的考核指標并不明確,當前最為明確的目標就是按時完成。其他問題,大可歸結到改革“后半篇”去落實。
那么,行業的參與者就不怕留下罵名嗎?怕,但無奈。一是參與者對雙方的強弱對比心知肚明,談判中,實力是決定性因素,技巧只能往后排。二是參與者對行業內情未必完全知曉。對不知曉的部分,未必有底氣談判,更別說硬杠;對知曉的部分,未必有談判技巧或擔當,談不下來。三是在“強權”和時間的雙重擠壓下,留給行業“討價還價”的空間和時間未必充分。三因疊加,與前述的“一果多因”“后半篇期許”相結合,可求得暫時心安。
簡而言之,改革主持者在職能型組織架構設計中,只負責改革前半段,不用考慮有人接盤的后半段怎么辦。在剛性考核僅限于時間、職責僅限于“上半場”的情況下,所有質疑都可以靠“一果多因”的說辭順利過關。在這場非對稱博弈中,雙方只要各退一步便能盡快完成任務。所以,在顯示出足夠的“誠意”后,“對方案嚴格保密”很容達成共識,成就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這就是職能型組織架構的硬傷——只負責流水線上某一時間段的工作,在沒有明確的判別標準時,按時完成成了唯一的追求。這種物化思維用在涉及未來的改革上,負面效應便被逐漸放大。
“三個不變”馬太效應
講回改革方案,絕大多數改革落地方案是將行業視為一個整體,在維持既有人員身份,機構級別、數量和單位編制總量“三個不變”的基礎上,由行業部門與編辦商定職能調整內容。但一些涉改對象在信息不對稱時,部分參與了對職能職責的重新分配,由于缺乏系統性統籌,對原本處于“模糊地帶”的職能,以“領導交辦的其他任務”方式完成的工作,便被選擇性忽視,形成改革后的職能真空。
“人隨事走、事隨編走”是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部分地方為保證人員的平穩過渡,在滿足“三個不變”的前提下,采用了“自主選擇去向”的分流思路。這導致當單位級別不一致時,在級別相對較低的單位,由于對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人崗匹配成為難以實現的現實問題。這一問題進一步拉大了后期博弈的非對稱性。一些在崗“挑大梁”的執法人員,卻因身份問題被阻擋在執法大門之外,執法隊伍跛腳隱患至此埋下。
“三個不變”引起的馬太效應,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單位分家時,許多工作基本保障都被劃到了更強勢的一方。例如,一些人帶著編制離開行業,使得單位后續發展被釜底抽薪;又如,一些地方以執法為主體推進改革,海事車(船)被一并帶走,“岸巡”在行業便應運而生;再如,一些地方最大限度地保持行業的完整性,執法人員并未“隨事”到執法機構去,后續履職還需依托在職責劃分上存在零和博弈的行業。而徹底將單位撤散、符合條件者都可自主挑選心儀單位的情況,更讓改革亂成了一鍋粥。
最要命的是,如果模式相對單一,還能集中精力打打“補丁”,但上述模式往往是相互交織、廣泛存在的。所以即便分家,行業管理和綜合執法依然在一起糾纏不清,無時無刻不在敲打著管理者脆弱的神經,考驗著上級管理者尋找對應部門的智慧。
總而言之,在強弱對比中落下風的行業,在壓力傳導出現偏差后,即便勉強與只對“改革上半場”負責的主持者坐到了一起,多數精力也只能白白消耗在與時間賽跑的過程中。為規避“三個不變”可能帶來的爭議,“鴕鳥政策”引發馬太效應,推倒了多米諾骨牌……仔細分析,這些現象不但與改革維持在既有框架下“隱秘”進行有關,也與改革面臨的外部環境密不可分,更多問題,留待后續進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