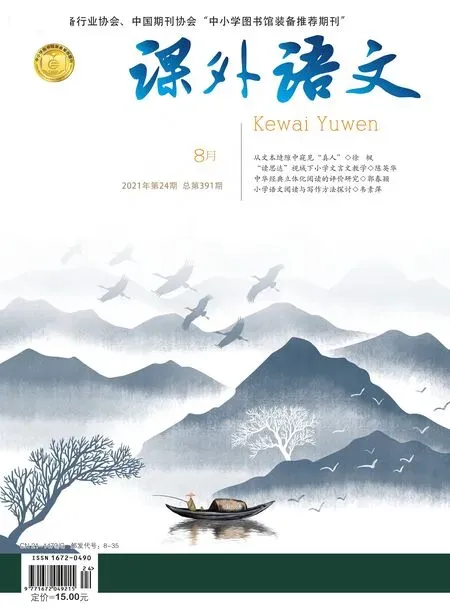基于學科融合的高中古詩文教學策略探究
伍美璇
(廈門市第三中學,福建 廈門 361006)
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在改變著人們的交流方式、思維方式,影響著人的情感化育過程。在現代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使用著現代漢語的孩子們對于古詩文難免有隔閡感。如何創設情境,搭建古文與今文之間的橋梁,使學生更容易進入文言語境,一直是高中語文教學的重點和難點。
傳統的教學方法是通過大量的背誦和練習來積累字詞和文學文化常識,以期提升古詩文閱讀能力。但往往事倍功半,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學生的古詩文閱讀能力依然原地踏步,更談不上靈活運用。究其原因,只重視知識的積累和考點應對,而缺少基于文史背景的系統梳理以及閱讀語境、運用語境的構建,是高中古詩文教學格外費力的關鍵所在。
如何在現有資源條件下構建更適合學生學習古詩文、傳承優良文化傳統的教學環境是本文探究的要點。
一、“基于學科融合的古詩文教學”之學理支撐
(一)中國古代教育一直是“文史哲不分家”
中國傳統思想重視聯系,很少孤立地去看待事物,中國學術向來文史哲不分家,主張不同學科的交融貫通。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教育史上,以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為核心的教材不僅承載著思想教育功能,還承載著史學教育功能和文學教育功能。學科草創期的國文教科書更是融合各種生活知識和處事道理,“清末民初的小學國文教科書如《最新初等國文教科書》等就基本上是由說明文以及用以介紹各種知識和便于傳授各種道理的記敘文組成”。
(二)新課標明確語文學科“綜合性”的特點
現代語文獨立設科之后突出了學科工具性的特點,對于讀寫能力的演練長期是教學重點,而對人文性的關注則較為不足。《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提出“語文課程是一門學習祖國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不僅語文教材的選文涉及各科內容,而且語文能力的養成也需要各學科知識的支撐。語文核心素養的四個方面“語言建構與運用”“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都或多或少關涉其他學科的學養。新教材“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研習”“當代文化參與”“科學與論著研習”“思辨性閱讀與表達”等學習任務群的設置更明確提出了學科融合的要求。
(三)教材中的古詩文文本關聯了諸多學科
從文本內容考量,古詩文文本內容關聯了諸多學科。如《琵琶行》和《李憑箜篌引》關聯音樂學科,《蜀道難》關聯地理學科,《采薇》《離騷》關聯生物學科,更不用說《馬嵬》《念奴嬌·赤壁懷古》等懷古詠史詩和《燭之武退秦師》等歷史散文不可脫離當時的歷史、地理、政治。
從寫作技巧考量,古詩文的創作技巧汲取了其他學科的經驗。例如文學作品中大量的技巧來自繪畫藝術,如烘托、渲染、白描、濃墨重彩、勾勒等。“唐詩、宋詞、元曲、《水滸傳》和《紅樓夢》等明清優秀小說,都在藝術手法、藝術精神等方面深受繪畫影響,都表現出一種繪畫美”。古詩文中的音韻、節奏等要求則與音樂學科緊密關聯,如《尚書·舜典》所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四)學科融合是對現代社會復雜問題的回應
現代社會面臨的復雜問題,無法只靠單個人或者單個科目的知識來解決。“跨界”成為潮流,而教學層面的學科融合要求也迫在眉睫。“依靠多學科協作關系形成的資源稟賦,學科壁壘和知識界限被打破”,學科知識的利用效率更高。不管是教師對課堂教學情境的優化,還是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都需要學科知識的關聯。或者說關聯各學科的能力,是評價學生內化、運用學科知識的重要指標。語言作為思維的工具,在關聯能力的培養上有重要的作用。學科融合有助于激活發現和創造的火花,避免思維模式的單一、僵化。
二、“基于學科融合的古詩文教學”之教學實踐
(一)基于人文史觀梳理古代文化常識,將碎片知識系統化
古代文化常識是準確理解古詩文的基礎,但在教學中,對于古代文化常識的學習和積累往往成碎片化狀態,一般是在課文學習時教師介紹或學生自主查閱相關常識。在對單篇課文的學習上,這種做法是行之有效且效度極高的。但不足之處是知識過于零碎,不利于深入理解掌握和進一步遷移運用。
2020年“停課不停學”的網課期間,常規授課方式被打破,而學生擁有更多自主學習的時間,筆者借機指導學生對高中古代文化常識進行梳理。教學設計理念基于傳統文化史觀,以《文心雕龍》的“象征”觀為核心理念,以“天、地、人”為軸線,貫穿“星象”“時序”“山川”“風物”“人事”等篇章,基本涵蓋高中課文涉及的古代文化常識。同時,時空坐標的確立、歷史源流的追溯也有助于學生更系統地理解古代文化,構建相應的思維體系,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為高中階段的古代文學文化經典著作的學習奠定基礎。
(二)融合相關學科知識優化教學情境,將文本認知結構化
在漫長的以四書五經為主要教材的封建社會里,學科的劃分并沒有現代社會那么精細,相應的,此種教學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讀書人也以“通五經”“貫六藝”為高標,體現在作品中就是素材豐富龐雜、思想博大精深、技巧豐富多彩。現實的教學中如果以狹隘的文學觀去看待必然會出現理解上的疏漏和偏差。所以跨學科的知識儲備成為正解語文教材的必備基礎。
以“芙蓉”這一意象的教學為例。高中教材中涉及“芙蓉”意象的篇目有《涉江采芙蓉》《荷塘月色》《望海潮》《離騷》《一剪梅》《蘇慕遮》《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長恨歌》等。出現頻率之高足見其在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教學時如果只抓住事物的外在特點顯然不足以認知其豐富的內涵,也難以充分把握作者情感意旨。基于此,本人設計了以“芙蓉”為學習主題的學科融合課程,包含以下幾個環節:
第一,融合生物學科。選擇班級向陽處在合適的季節種植蓮花,并要求學生寫作觀察日記,從選盆、擇地、擇時、選土、育苗等環節開始觀察荷花的生長習性。
第二,融合歷史、美術、音樂學科。運用文獻梳理的方法,了解荷花的栽種史,象征意味以及相關文物中出現的蓮花圖案、器型、紋飾,與蓮花有關的音樂等。
第三,融合地理學科。了解蓮花在世界范圍內的分布,繪制相關地圖,從中發現地理與人文之間的關系,探究相互影響的因子。
第四,回歸語文學科。在前期學科融合的基礎上深入品析探究,從語言技巧的角度品讀“芙蓉”的諧音意味,從意象解讀的角度理解作品內涵,從梳理探究的角度完成對“芙蓉”意象的整體認知,從創造性運用的角度賦予荷花新的內涵,開發新的適用性場景。
如此四個環節,立足于“語言建構與運用”,融合了“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實現語文核心素養的提升。古人云“格物致知”,基于學科融合的課程設置通過對“物”的觀察分析進一步體會“物性”,察知“物理”,再進一步關聯“人文”,躍升為對“精神品質”的抽象把握,明了“形象”與“抽象”之間的密切關系,切實掌握古詩文中常見的“借物喻人”“寓情于景”等手法,理解古人含蓄蘊藉的表達方式,體認世間萬物在古人眼里呈現的盎然詩意,實現對文化的理解與傳承。
(三)基于真實情境合理設計學習任務,將學習目的真實化
王寧先生說:“真實的情境是指向學生語文生活的真實需要。”新課標對語文學科素養進行了具體說明,它是“學生在積極的語言實踐活動中積累與構建起來,并在真實的語言運用情境中表現出來的語言能力及其品質;是學生中語文學習中獲得的語言知識與語言能力,思維方法與思維品質,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綜合體現”。只有基于真實情境合理設計學習任務,學生的學習才會更有效度。古詩文教學尤其如此,如果只以應試為目的,只會導致學生厭學,老師厭教。如果能將學習目的真實化,亦即指向學生的真實需要,那么效果則截然不同。
例如教授《廉頗藺相如列傳》一課時,筆者設計了創造性運用課文素材的一道題目:參考以下兩座雕像(鼓浪嶼鄭成功雕像和西湖秦檜跪像),說說如果你要為廉頗塑像要采取什么姿勢哪種材質,理由是什么。通過問題引導,加深學生對人物形象的認識和把握,同時在古文學習與現實生活運用之間建立聯系,學以致用,以用促學,進一步激發學習興趣,培養多方面能力。
再如教授《歸去來兮辭》一課時,設計“請你為陶淵明寫一封辭職信”的學習任務,引導學生更深切地體會陶淵明辭官歸隱的心情,把握人物形象,理解人物精神品質。教授《氓》時,指導學生用課本劇的形式呈現詩歌人物形象和矛盾沖突,引導學生在具體的語文活動中理解超越時空的人類共同情感,并體會不同文體的特點,創造性運用課本素材。
類似的活動融合了美術、音樂等學科知識,也需要歷史、地理的學科知識及對相關風物、人文背景的了解,在此基礎上創設的情境才更有真實感,既貼近作品的原質也適切學生語文生活的真實需要。學生的“學”更富有積極性,老師的“教”也更具有針對性。
三、“基于學科融合的古詩文教學”之教學反思
相較于常見的以背誦默寫、題海戰術為主的古詩文教學方式,基于學科融合的古詩文教學策略由扁平、單調轉向立體、豐富,由孤立、碎片轉向聯結、系統,更符合新課標精神。但也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學科融合的前提是立足“語文本位”
融合課最終是為提高語文核心素養服務的。這一根本認知在融合課的設計意圖、課時安排和教學內容上都要有鮮明的體現。例如前文所舉“芙蓉”為主題的課程。教學目的是為了認知“芙蓉”意象的情感內涵、文化意蘊,課時安排上應以第四個環節為主,切勿喧賓奪主變成種植課或繪圖課,進行相關文獻梳理時也應圍繞核心目標展開,不可過于枝蔓。
(二)情境活動應圍繞語文基本能力展開
真實情境下的語文活動應圍繞“聽、說、讀、寫”四項基本能力展開,尤其是“讀”和“寫”。例如前文所舉“為廉頗塑像”一例,要培養的并不是學生的繪畫或雕塑能力,而是學生理解文本,描述形象和闡述理由的能力。再如《氓》課本劇,要培養的并不是學生的表演能力,而是通過劇本寫作和劇情表演激發學生的創造力,提高共情能力和表達能力。
總之,只有抓住語文的核心素養,明確課程目標,才能靈活自如地把學生學習、生活中的素材都變成語文學習的素材,跨越學科界限,拉近時空距離,搭建古今橋梁,提高古詩文教學的效度,更好地實現語文學科“立德樹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