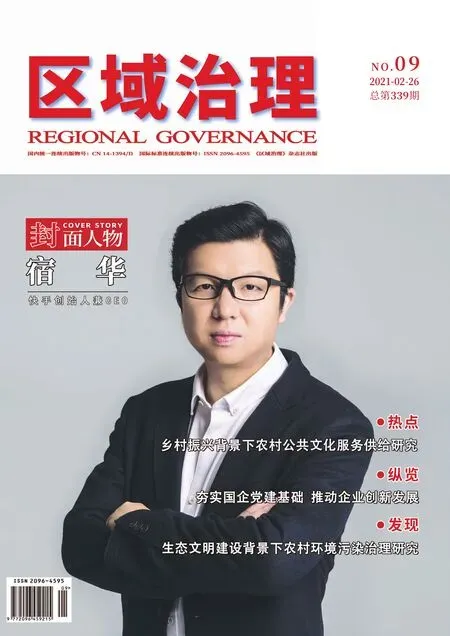鄉鎮社會協同治理中倚重非制度化方式的社會文化邏輯——以廣東省D市H鎮為例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李明月
伴隨著全民共同建設、共同治理、共享格局的提出,我國社會治理步入了新階段。近年來提出的以多元主體互動合作、協同治理為特點的社會協同治理模式,在我國部分城鎮試點取得了矚目成就。然而鄉鎮在推進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仍存在著諸多問題與挑戰,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較城市而言,鄉鎮更倚重非制度化方式治理。對于這一現象,本文將結合蘇力老師的《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下文簡稱《送法下鄉》),從社會文化邏輯進行分析討論。
一、鄉鎮倚重非制度化方式
H鎮在社會協同治理的實踐探索,可以說是當前中國鄉鎮社會治理的一個縮影,體現著諸多鄉鎮社會協同治理的共同特點,例如黨建統領促民生、政府統籌穩發展、多元主體共發力等。但在推進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鄉鎮與城市有一個明顯的區別——鄉鎮倚重非制度化方式治理。
在社會治理的制度供給方面,鄉鎮政府主要依賴于上級政府的文件,本身沒有立法權。“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地對社會行為確定的規范,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一旦確立就會形成制度剛性對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我國是中央集權國家,要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高質、高效,國家層面的頂層立法設計必不可缺,但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制定統一的《社會協同治理法》以及社會治理的具體配套條例。雖然一些地方政府也進行了社會治理立法,但是存在立法質量不高、操作性不強、權威性不夠、約束力不強的問題,因此鄉鎮在具體推進過程中常常因“無法可依”而轉向非制度化方式治理。
同時,近年來社會發展不平衡情況日趨明顯,H鎮外來人口與當地人口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高發,在處理這些社會矛盾時,鄉鎮政府往往習慣于使用“專項治理”和“集中整治”方式,即政府領導自上而下進行垂直命令,然后進行大規模群眾動員,集中配置治理資源以解決社會沖突。例如,在出租屋整治問題上,上級政府并未對此做出詳細批示,H鎮政府一般采取特定時期摸查,前期先宣傳、安排好相關的人員以及所需調配的物資,然后各片區網格員對問題租戶、戶主進行協調,采取口頭教育、判處罰金等方式,這就導致該時期內“沒有人頂風作案”,成效顯著,而由于耗費成本較大,這種效果往往只能持續一段時期,“風頭”一過出租屋問題便又再次出現。這種非制度化方式對于快速解決某種社會問題具有一定效果,但因其與法治的不兼容而為官員的權力尋租和越軌提供了契機。
二、背后的社會文化邏輯
如果從制度體系層面進行分析,在社會協同治理中,鄉鎮倚重非制度化方式也許與制度建設不完善、鄉鎮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官僚體制運作中上下級政府關系等有關,但考慮到鄉鎮所處的場域與省、市有較大不同,鎮政府其實是與農村接觸最密切的基層政府,結合《送法下鄉》,本文打算換個角度來分析這一現象,即從社會文化邏輯來分析鄉鎮倚重非制度化方式的原因。
(一)宗法傳統觀念
政府(包括鎮政府以及上級政府,但在鄉鎮社會協同治理的實際運作中上級政府的張力較弱)、村社、群眾、企業等構成了H鎮社會協同治理的多元主體,在共同參與治理的過程中,宗法傳統觀念對治理方式有著重要影響。
H鎮下轄16個村和1個社區,這使得村社在H鎮的社會協同治理中占據重要地位。同時,每個村的村干部大都由本村的宗族成員組成,比如B村是Z姓宗族、G村是W姓宗族等,而社區則傾向于現代化社區,外來人口居多,但擔當要職的大多是“當地人”,這為宗法傳統觀念在鄉鎮社會協同治理中的滲透打下了現實基礎。
在傳統中國,宗族依靠首領在宗族中的權威以及族人依照血緣遠近和輩分高低所形成的等級排列次序來運作,這些宗族首領在族中同樣權勢至高無上,本族的大小事務幾乎都是在其主持下進行的。管理宗族遵循的是族規祖訓,宗法色彩濃厚。而進入現代社會后,廣大村民由于長期受宗族文化的影響和熏陶,法制觀念和法治意識往往比較差,更加重視禮俗、倫理的作用,血緣、宗親、人情等關系比法律等制度體系更為優先,加之農村社會又是一個熟人社會,本著“有人好辦事”的原則,村民習慣于用倫理與道德來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對于通過法律來處理和協調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的做法并不適應。且宗族具有政府所不具備的權威和凝聚力——在H鎮,你問村民們鎮長是誰、鎮黨委書記是誰,不一定能得到準確答案,但問村長是誰、村支書是誰,每位村民都能答上(不僅局限于村民,大部分H鎮居民都如此),這就導致了村干部在鄉鎮社會協同治理中具有特殊地位。同時,鄉鎮社會治理覆蓋了醫療、衛生、治安、社保等復雜的民生問題,加之鎮政府各部門內也存在著各宗族的成員,這就使得在推進某項社會治理項目時脫離不了農村。長此以往,鄉鎮在推進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就算是有相關的法律規章制度,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對于民眾而言也是權威性不夠、約束力不強,而非制度化方式在此時則顯得更為“因地制宜”。
(二)“自己人”邏輯
正如《送法下鄉》中所說,人文空間同樣影響權力的運作方式。在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中,國家只是一種概念的存在,國家的權力沒有太多的根基,被視為是外來力量,“胳膊肘向里拐”是一個普遍現象。而本文更傾向于把這種“胳膊肘向里拐”稱為鄉鎮的“自己人”邏輯。“自己人”相較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言,其實透露更多的是一種“妥協與讓步”,而在鄉鎮推進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自己人”邏輯貫穿始終。
“自己人”邏輯遵循人情取向,講究吃虧讓步,法律則要求鐵面無私、追求公平公正。相較于“自己人”而言,法律意義上的權利觀念也許更現代、更能與世界接軌,卻可能破壞村社原本的社會互助網絡。在村落社會,“自己人”共同體是輿論和道義上的社會支持網絡,在此共同體中,人們榮辱與共、困難相扶,在一些利益沖突發生時,會較“外人”而言多一些內部協商的余地。由于鄉鎮社會協同治理涉及的主體較為多元,包括政府、村社、群眾、企業等,其中政府雖然是國家公權力的代表,但是由于權力存在著流動,難免會出現“強龍不壓地頭蛇”的現象,這與上文提到的宗法傳統觀念有著聯系。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是“自己人”往往影響著治理的實施進程。
在社會協同治理過程中,多元主體間難免會存在利益沖突,彼此之間往往未能很好地尊重其他主體的利益和意愿,不能很好地聽取、接受其他主體的訴求。而鎮政府由于自身也處在這一利益關系中,在特定情況下無法完全公正、公平、有效地化解利益沖突,這就導致了治理主體間“各謀其利”。如果僅憑制度化方式把利益界限“一刀切”劃分明確,雖然能夠暫時解決前期的沖突問題,但這些治理主體私下將很難達成共識,多方不愿自己吃虧,會就一個問題斡旋很長時期,最后導致治理無法順利推進。例如H鎮2018年以社區營造試點村為契機,構建的“朱子文化村落”建設項目,其中涉及改造B村舊農場、升級B公園、整合以“朱氏宗祠”為中心的古建筑群等,前期鎮政府依據上級政府的相關條例順利進行定點規劃,但由于改造期間鎮政府、B村村干部、村民間始終無法達成共識,如資金問題,按照相關條例,村和鎮政府在社區營造項目中的出資配比是明確的,村子會出一部分資金用于村建,而鎮政府則支付另一部分,但在這個過程中村干部會認為我們借了場地給“外人”(鎮政府),因此我們應少出資,然后以各種理由推諉,再如村民的房屋改造問題等,這導致該項目只能被暫時擱置。后來2019年鎮政府通過委派“當地人”官員聯系村干部,經過多次商討會、下村走訪,讓B村村干部和村民逐漸意識到政府是“自己人”,消除了“外人占自己便宜”的顧慮后,預留出來更多“妥協與讓步”的協商空間,該社區營造項目才有所推進。因此,鄉鎮在推進社會協同治理時,僅依靠法律規章等制度化方式未必能達到效果,而是需要治理主體間相互認同對方為“自己人”,在這一共同體邏輯下,多方才能有更多的協商余地。
總之,鄉鎮在推進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往往需借助“自己人”邏輯下的共同體力量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法律規章制度才能真正貫徹。在此過程中,制度成為了行事底線,而非制度化方式則更具操作性,也更可實現。
三、總結
總體而言,鄉鎮在社會協同治理過程中采取非制度化方式并沒有錯,但是隨著國家法治化程度的不斷深入,正式的制度才是社會協同治理真正的保障,倚重非制度化方式則顯得不合時宜了。然而,當前的中國鄉鎮社會,如果一味地摒棄非制度化方式、強硬地執行制度化治理也不合適,甚至是無法實現的。因此,本文認為目前在推進鄉鎮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較適應中國國情的是尊重、遵循、善用中國鄉土的社會文化邏輯,正確發揮治理主體的積極作用,不斷完善制度化體系的建設,使制度化與非制度化方式雙管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