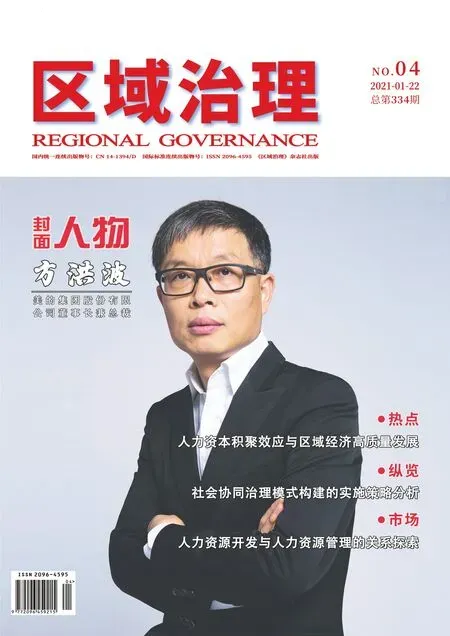分析預約合同違約責任
廣東財經大學 何茜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法釋[2012]8號)(以下簡稱《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2條確立了我國預約合同制度的基本結構。
目前,《民法典》合同編第495條對上述司法解釋條文進行了吸收改造,將預約合同的適用范圍進行了擴大,由原來的買賣預約擴大至不限于買賣上的預約,并對預約合同作出了更為清晰的表述,但同時可以發現其并未規定違反預約合同要承擔的違約責任形式。面對實務中很多預約合同糾紛,有必要進一步研究違反預約合同的責任承擔方式。本文在查閱大量文獻并結合司法實踐的基礎上,分析探討在《民法典》現有制度下的預約合同違約責任承擔方式,以期為進一步明確違約責任形式提供參考。
一、關于預約合同的概述
預約合同指的是雙方當事人所訂立的、約定在之后一定時間內兩方簽署本約合同的一種合同形式。預約合同的內涵包括:首先,預約合同給雙方施加了締結本約的義務;[1]其次,雙方被預約合同所約束,不得訂立與本約具有相同屬性的任何其他合同。預約合同的組成要素包含了明確訂立本約合同的承諾和明確的預約內容。[2]
依條文規定,如果當事人違反預約合同,則須承擔相應違約責任,但關鍵問題在于如何承擔違約責任。然而不管是現在的《民法典》還是之前的《買賣合同司法解釋》,均未回答實踐中存有較大爭論的兩個問題——當出現違反預約合同的情形時,守約方主張繼續履行的請求能否得到支持?當主張解除預約合同時,守約方能否要求違約方賠償本約履行利益?下文將通過實證研究,對這兩大問題展開討論。
二、預約合同違約責任的實踐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繼續履行
兩方簽訂預約合同的目的是為了簽署本約。因此,如果一方違約,大多數守約方希望違約方繼續履行預約合同,直到本約簽署。可以說,繼續履行這一方式能不能得到適用,是預約合同違約責任存在的最大分歧。
大多數法院認為這一方式干預了當事人意思自治,不支持繼續履行的適用,如仲崇清案[3]、寶蓮城公司案[4]等;但許多判決則采取了相反的判決,如在郭志堅案[5]、山東菱重機電設備公司案[6]中,法院認為預約的目的是為了達成本約。如果不能保證本約的簽署,則預訂合同制度將失去其價值,并可能帶來額外的道德風險。
(二)損害賠償
司法判決中關于損害賠償的主要爭議點在于守約方能否要求違約方賠償本約履行利益。如在呂青案中,法院認為預約和本約有明顯差別,預約合同違約的損害賠償范圍不能完全等同于本約的賠償,故賠償范圍僅包括信賴利益損失,而不包括本約履行利益;[7]但在陳榮根案中法院的觀點截然相反,為了合理保護守約方的利益,應讓其達到猶如合同全部履行的狀態。[8]
三、預約合同違約責任的認定適用
由于缺少制度供給,導致圍繞上述關于預約合同糾紛的爭議一直存在,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的案件比比皆是。因此,對于違反預約合同,建立明確的救濟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若預約合同約定的具體義務是磋商,一方拒絕磋商即可成立違約;若約定的具體義務是簽訂本約,一方拒絕簽署本約才成立違約。所以關于違反合同的一般責任規則并不能直接適用于預約合同,需要從預約合同的效力出發,區分類型加以分析。
(一)繼續履行
能否將繼續履行看作違反預約合同的違約責任之一,在理論界極富爭議性,有否定論、肯定論和內容決定論之分。第一,否定論。這一學說認為預約合同的守約方不能主張繼續履行,只能要求違約方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我國實務界大多采納這一學說,[9]其法理基礎是當事人意思自治以及人身不可強制。實際上,這種觀點有待商榷。這一方式并沒有造成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違背,若把繼續履行排除在違約責任外,則會大大降低預約合同制度的功能價值,這與建立預約合同的目的背道而馳。第二,肯定論。這一學說認可繼續履行的適用,背后的支撐理論是意思自治、期待可能性和信賴利益保護理論。然而,這種觀點的缺陷在于,如果不加區別地將其應用于一切預約合同,很有可能會造成雙方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平衡。[10]第三,內容決定論。這一觀點認為違約方能否承擔繼續履行責任要分情況討論。根據《合同法》第12條合同主要條款,一些學者把預約劃分為簡單預約、典型預約以及完整預約。前兩種類型不能適用繼續履行,最后一類則能夠采用。[11]
筆者認為,繼續履行是否可以成為違反預約合同的一種責任承擔形式,關鍵是看適用于什么情況下:(1)當在預約合同中雙方約定了必要條款并達成最終合意時,此時預約合同具備強制締約效力,可以采用繼續履行規則。原因是:首先,繼續履行的功能在于維持合同的約束力,契約嚴守原則是其價值基礎,所以,其與這類合同的訂立目的非常吻合;其次,在這一類預約合同中,當事人之間具有較強的信賴度,反映了他們之間訂立本約合同的合意,所以守約方可以采取強制締結本約的方式進行救濟;再次,依合同法一體適用的要求,一般而言,預約和本約合同須受到合同法中違約責任制度的統一調整。但是,應當指出的是,預約合同中的繼續履行責任也同樣要受《民法典》第580條的限制。(2)當兩方簽訂預約合同時并沒有達成完全的合意,約定的具體內容僅為繼續磋商時,此時的預約合同僅具備善意磋商效力,則不宜適用繼續履行這一違約責任形式。因為針對這類合同而言,由于其與上述那類具有強制締約效力的預約合同相比,雙方之間的信任度較低,因此,違反預約合同不應具有強制締結本約合同的法律后果,不應把繼續履行作為其違約責任形式之一。
(二)損害賠償
應將什么利益用作計算預約合同違約損害賠償的基礎?是簽署本約合同的信賴利益,還是含本約合同的履行利益在內,學界對此觀點不一致,主要的學說有“信賴利益論”“履行利益論”以及“內容決定論”。第一,信賴利益論。這一觀點認為損失賠償額只包含直接損失,不含機會利益的損失。在機會利益損失得以賠付的情形下,信賴利益的范圍已經無限接近履行利益。[12]第二,履行利益論。這一觀點認為應按本約的履行利益確定賠償數額。第三,內容決定論。這一學說認為預約合同的損害賠償范圍須根據不同階段區別認定,并非完全賠償本約合同的履行利益,和信賴利益也有一定的差異,但對于損失賠償數額,可以依據完全賠償原則進行計算。[13]
筆者認為,同樣有必要從預約合同的效力開始討論:(1)如果雙方約定好了合同的必要條款并在預約合同中達成了將來簽署本約的明確合意,在損害賠償責任的范圍原則上應該采用履行利益論。主要原因是這類合同的效果讓雙方有強制締約的義務,雙方的信賴度很高。其保護的對象超越狹義信賴利益的范圍,逐漸接近履行利益。所以,由于這類合同成熟度高,其損害賠償金額可參照本約合同違約責任的損害賠償加以確定。[14]支持“信賴利益論”的學者反對“履行利益論”的主要觀點在于,若其損害賠償范圍擴大到履行利益,那此時預約和本約合同又有何不一樣呢?此時討論預約合同違約責任的意義何在?這種觀點似乎是合理的,但實則是站不住腳的,這是因為:首先,根據本約合同的損害賠償制度計算違反這類預約合同的損害賠償范圍,是建立在我國合同法上對于信賴利益和履行利益的二元區分較完善的基礎上的,但絕非把預約合同的違約責任與本約的違約責任劃等號;其次,與本約合同的損害賠償不同,預約合同在計算損害賠償金額時雖然可以參照本約的履行利益,但是賠償范圍不應超過本約合同的損害賠償范圍。(2)如果雙方僅約定繼續磋商,雙方對于是否訂立本約處于不明確的狀態,此時信賴度較低,所以其保護的對象實則為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責任的范圍以信賴利益論為限;此外,可將締約過失責任的損害賠償計算方法作為計算損害賠償范圍的參照。[15]但不意味著將此處的違約責任等同于締約過失責任,因為兩者存在許多差異,諸如歸責原則、具體的責任形式以及舉證責任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