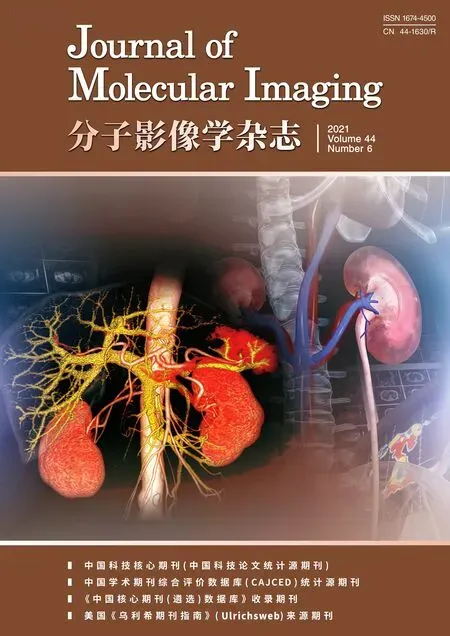磁共振動態對比增強掃描定量參數與原發性肝癌患者病理特征及缺氧誘導因子
--1α水平的關系
何承峻,楊小丁,陳海洋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資陽醫院//資陽市第一人民醫院普外科,四川 資陽641300
原發性肝癌包括肝細胞癌和肝內膽管癌,近年來發病率不斷增加,是全球癌癥相關死亡率的重要病因[1]。原發性肝癌是高發病率高死亡率的惡性腫瘤,手術切除是其最主要的根治性治療,但術后5 年生存率僅約50%,5年復發率達60%~70%[2]。對未出現肝功能受損的患者,由于主訴模糊和無特異性癥狀,原發性肝癌早期診斷通常較為困難。影像學檢查和實驗室檢查是原發性肝癌診斷的主要方法,用于原發性肝癌診斷、制定治療計劃、管理和隨訪的影像學研究包括超聲檢查、CT和MRI[3]。有研究顯示,與CT相比,MRI在原發性肝癌診斷中與病理檢查一致性更好[4]。了解肝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是評估患者狀況,制定治療計劃和預測患者預后的重要步驟。動態對比增強磁共振成像(DCE-MRI)已在臨床廣泛應用,其基于三維體積薄層掃描梯度回波T1WI序列,在靜脈注射造影劑后快速多相重復掃描獲得內臟器官的血流灌注信息,然后通過后處理軟件進行分析得到不同的灌注參數[5]。有研究顯示,原發性肝癌患者經DCE-MRI技術檢測后,多種灌注參數與病灶微血管密度(MVD)、病理分級明顯相關[6]。但該研究僅對DCE-MRI定量參數與肝癌病理分析的關系進行分析,未關注患者其他臨床病理特征和實驗室指標與DCEMRI定量參數的關系,仍需進一步研究。本研究選取94例原發性肝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以探討DCE-MRI定量參數與原發性肝癌患者病理特征及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水平的關系,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1月~2020年12月收治的94例原發性肝癌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符合原發性肝癌診斷標準[7]者;年齡>18歲者;初診;入組前未接受其他任何抗癌治療;均接受DCE-MRI檢查。排除標準:合并其他惡性腫瘤;有任何DCE-MRI禁忌證;合并其他原發性肝臟疾病;妊娠期婦女。40例肝臟良性結節患者中男性28例,女性12例,年齡26~71(49.09±11.01)歲;血管瘤32例,肝硬化不典型增生6例,肝吸蟲2例。94例肝癌患者中,男性71例、女性23例,年齡32~77(49.78±11.16)歲。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已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
1.2 檢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使用Discovery MR750型MRI掃描儀(GE)進行檢查,所有患者均于受檢前1 d禁食禁水4 h以上。患者取仰臥位,頭先進,體部線圈置于受檢者劍突,確保肝臟位于磁體中心;先行平面掃描,T1WI序列:TR 4000 ms、TE 47.5 ms、FOV 42×42,矩陣384×256、層厚6.0 mm、層間距1.8 mm;T2WI序列:TR 4000 ms、TE 47.5 ms、FOV 36×36,矩陣384×256、層厚6.0 mm、層間距1.0 mm。DCE-MRI檢查:使用釓噴酸葡胺作為對比劑,經肘正中靜脈注入0.2 mmol/kg釓噴酸葡胺,速率2 mL/s,注射完成后靜脈注射20 mL生理鹽水沖管;行橫斷面或矢狀面DCE-MRI檢查,肝臟加速容積采集LAVA-XV序列,參數:TR 5.1 ms、TE 1.7 ms、FOV 380×380、層厚3 mm,連續掃描35個相位,成像時間325 s。圖像處理:將掃描圖像傳輸至掃描儀自帶工作站,手動勾畫病灶感興趣區,測定血管內至血管外細胞間隙的轉運系數(Ktrans)、血管外細胞外間隙轉運至血管內的速率常數(Kep)、血管外細胞外間隙體積百分比(Ve)。由2名影像學醫師在低倍鏡下選定MVD最高處,調至高倍鏡下雙盲計數并計算平均值作為MVD計數。
1.3 實驗室檢查
所有受試者均采集清晨空腹外周靜脈血,3500 r/min離心5 min后收集上清液,-80 ℃保存待測。采用酶聯免疫法測定患者HIF-1α水平,試劑盒購自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檢測步驟嚴格遵照試劑盒說明書。
1.4 觀察指標
評估兩組MVD、Ktrans、Kep、Ve及HIF-1α。分析肝癌患者中不同腫瘤分期、不同分化程度、是否有轉移、不同HIF-1α水平者DCE-MRI定量參數的差異。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9.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性別等計數資料以n(%)表示,組間比較行χ2檢驗,兩變量相關關系分析采用Spearman和Pearson相關分析法。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MVD、Ktrans、Kep、Ve及HIF-1α水平
肝癌患者MVD、Ktrans、Kep、Ve及HIF-1α水平均高于對照組(P<0.05,表1)。典型病例(圖1)。

圖1 肝癌患者,男性,58歲,Ⅲ期,低分化Fig. 1 A58-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liver cancer,stage III,poorly differentiated.

表1 兩組MVD、Ktrans、Kep、Ve及HIF-1α水平Tab.1 Levels of MVD,Ktrans,Kep,Ve and HIF-1α in the two groups(Mean±SD)
2.2 不同腫瘤分期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比較
肝癌患者Ⅲ/Ⅳ期者MVD、Ktrans、Kep、Ve水平均高于Ⅰ/Ⅱ期者(P<0.001,表2)。

表2 不同腫瘤分期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比較Tab.2 Comparison of DCE-MR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liver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umor stages(Mean±SD)
2.3 不同分化程度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比較
肝癌低分化患者MVD、Ktrans、Kep、Ve水平均高于中高分化者(P<0.001,表3)。

表3 不同分化程度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比較Tab.3 Comparison of DCE-MR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liver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erentiation(Mean±SD)
2.4 有無淋巴結轉移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比較
有淋巴結轉移的肝癌患者MVD、Ktrans、Kep、Ve水平均高于無淋巴結轉移者(P<0.05,表4)。

表4 有無淋巴結轉移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比較Tab.4 Comparison of DCE-MR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liver cancer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Mean±SD)
2.5 不同HIF-1α水平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比較
以肝癌患者HIF-1α中位數(162.96 ng/L)作為界限對其進行分組。HIF-1α≥162.96 ng/L的肝癌患者MVD、Ktrans、Kep、Ve水平均高于HIF-1α<162.96 ng/L 者(P<0.05,表5)。

表5 不同HIF-1α水平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比較Tab.5 Comparison of DCE-MR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of liver canc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IF-1α levels(n=47,Mean±SD)
2.6 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與臨床病理特征及HIF-1α的關系
Spearman 相關分析法顯示:肝癌臨床分期與MVD、Ve呈正相關關系(P<0.05),肝癌淋巴結轉移與Ktrans、Ve呈正相關關系(P<0.05)。Pearson相關分析法顯示:HIF-1α與MVD、Ktrans、Kep、Ve呈正相關關系(P<0.05,表6)。

表6 肝癌患者DCE-MRI定量參數與臨床病理特征及HIF-1α的關系Tab.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CE-MRI quantitative parameter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HIF-1α in HCC patients
3 討論
DCE-MRI定量參數分析可以反映組織的血流灌注、微血管通透性等信息,能客觀地評價病變內部的病理生理特征[8],在肝癌診斷、分期及預后方面有重要作用。有研究顯示,DCE-MRI對宮頸癌患者的臨床病理學特性具有一定的評估價值[9]。但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中,DCE-MRI多應用于肝癌鑒別診斷中。動物實驗顯示,DCE-MRI定量參數Ktrans和MVD相關,可無創評估肝癌的腫瘤血管生成狀況[10]。而相關研究顯示,DCEMRI定量參數與腫瘤增殖狀態、組織學分級或MVD,存在弱但顯著相關性的關系,這說明DCE-MRI評估肝癌臨床病理特征方面是可行的,也為肝癌鑒別診斷提供一個新的途徑[11]。肝癌多為富血供腫瘤,是一種以新生血管形成和血管侵犯為特征的腫瘤,微血管形成也是腫瘤增殖、復發和轉移的主要機制之一[12]。HIF-1α是具有較強的誘導血管生成能力的血管生成因子,其表達情況與肝癌腫瘤分期、包膜完整性、腫瘤轉移均存在相關性,是影響患者預后的重要指標[13]。本研究分析DCE-MRI定量參數與原發性肝癌患者病理特征及HIF-1α的關系,也發現各指標存在關聯。
本研究結果顯示,肝癌患者各DCE-MRI定量參數及HIF-1α水平均高于對照組,與相似研究結果一致[14-15]。肝臟有血管內間隙、血管外細胞外間隙和細胞內間隙3個間隙,Ktrans是指對比劑分子從血液進入血管外細胞外間隙的速率,Kep是指對比劑分子由血管外細胞外間隙回到血管內的速率,Ve指血管外細胞外間隙內對比劑的容積分數[16]。DCE-MRI定量參數與腫瘤病灶組織內血管灌注情況、血流情況和血管通透性等均相關。肝癌作為惡性腫瘤,其血供主要是肝動脈,血供豐富,故MVD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同時,由于肝癌組織富含新生血管,血流量和血管通透性增高,造影劑更易在血管內間隙、血管外細胞外間隙和細胞內間隙活動,故Ktrans、Kep、Ve水平更高。而正常肝組織血液主要來自門靜脈,細胞結構密集,血流量或血管通透性不如肝癌[17]。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臨床病理特征方面,不同腫瘤分期、不同分化程度、有無淋巴結轉移肝癌患者MVD、Ktrans、Kep、Ve水平各DCE-MRI定量參數水平差異顯著,這提示應用DCE-MRI定量參數了解肝癌患者臨床病理特征是可行的。實體瘤的發生、生長和轉移依賴于血管生成,腫瘤血管生成不僅是血管數量的增多,血管壁結構也發生異常,內皮細胞間隙增大、基底膜增厚或變細等[18],均是腫瘤血供變化的原因。腫瘤血供變化與其發生進展相互影響,因此腫瘤病灶異常的血管結構,會導致其灌注情況、通透性變化,使腫瘤組織獲得更豐富的血供,繼而支持肝癌發生進展,故腫瘤分期越晚,DCE-MRI灌注參數越高。同時,低分化肝癌患者腫瘤細胞惡性程度高、侵襲性強,所需營養物質就越多。有研究顯示,高分化肝癌進展為中分化,其腫瘤組織動脈供血表現出增加趨勢[19]。在這種情況下,腫瘤組織發生惡性侵襲性行為,致使新生血管增加,改變組織血管結構,也會導致DCE-MRI檢查時低分化腫瘤組織表現出更高的灌注參數水平。但本研究數據顯示,腫瘤分化程度與DCE-MRI灌注參數線性相關關系不顯著。有文獻指出,腫瘤在中、高分化時,有氧代謝突出,尤其是低分化時,伴有大量無氧酵解,促使低分化時血供下降[20]。故部分低分化肝癌患者血供可能相對豐富,但不足以與灌注參數呈現線性相關關系。本研究還顯示,肝癌臨床分期與MVD、Ve呈正相關關系,肝癌淋巴結轉移與Ktrans、Ve呈正相關關系,HIF-1α與各灌注參數均呈正相關關系。HIF-1α在肝癌組織中高表達,能通過激活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轉錄,促進血管生成及腫瘤的侵襲和轉移,并維持著腫瘤細胞的代謝,是肝癌發生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調控蛋白之一[21]。因此,HIF-1α表達水平與腫瘤組織血管生成、血供和血流動力學密切關聯。臨床可綜合應用HIF-1α水平與DCE-MRI灌注參數評估肝癌患者病情進展程度及預后情況。
綜上所述,肝癌患者DCE-MRI灌注參數及HIF-1α水平顯著升高,且各灌注參數水平與患者臨床分期、有無淋巴結轉移和HIF-1α水平存在關聯性,DCE-MRI灌注參數具有實際應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