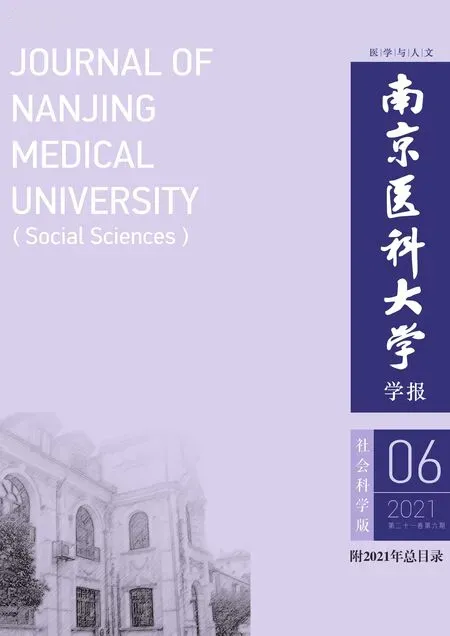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概念模型、現(xiàn)實困境與驅(qū)動因素
許興龍,周綠林
江蘇大學管理學院,江蘇 鎮(zhèn)江 212013
傳染性疾病、慢性病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主要醫(yī)學難題,更是社會學難題,由此衍生出社會環(huán)境中健康風險增加、健康管理難度提升等一系列顯著特征。2019年7月,國務院發(fā)布《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國發(fā)〔2019〕13 號),提出“健康第一責任人”理念,首次從戰(zhàn)略層面強調(diào)需方主動參與對于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的重要意義。這對于促進全民共建健康中國、人人共享健康中國戰(zhàn)略成果、落實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小處方”和社會整體聯(lián)動“大處方”相結合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基于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改革的實踐,探索性提出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的概念,并結合理論分析構建概念模型,分析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的現(xiàn)實困境和驅(qū)動因素。
一、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概念模型
價值共創(chuàng)的思想最早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學領域,有學者在研究服務業(yè)對經(jīng)濟貢獻時指出,“服務過程需要生產(chǎn)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合作”,由此開啟了價值共創(chuàng)由生產(chǎn)者和消費者共同參與創(chuàng)造的思想[1],并指出服務業(yè)的生產(chǎn)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消費者的知識、經(jīng)驗、動機和誠實程度[2]。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改革是分級診療目標實現(xiàn)的重要抓手,也是健康中國戰(zhàn)略實施的主陣地。根據(jù)價值共創(chuàng)理論可知,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即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提供者和使用者能夠在價值創(chuàng)造過程中進行合作。合作理論認為,個體或組織間的合作源自彼此對對方資源的需要,而相關資源只有通過供需雙方分工協(xié)作才能獲取并加以利用[3]。
在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改革過程中,各級政府為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工作開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而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提供方需要得到基層居民的認可、信任和主動利用,從而體現(xiàn)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在此過程中基層居民需支付相應費用,并對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效果做出直觀反應,由此倒逼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供給產(chǎn)品、供給方式優(yōu)化;同理,基層居民作為理性經(jīng)濟人,渴望獲取優(yōu)質(zhì)可及的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這就需要政府部門不斷強化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資源投入,引導優(yōu)質(zhì)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下沉,同時提升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人員服務動力。這構成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的基礎。
在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過程中,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供需雙方分別遵循供方邏輯和需方邏輯。基于供方邏輯的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是以社會整體健康價值為出發(fā)點,供方在價值創(chuàng)造過程中得到需方的響應和互動,努力獲取為基層居民共創(chuàng)價值的機會,并根據(jù)國家和地方政府相關制度安排和居民信息反饋來優(yōu)化價值共創(chuàng)過程。基于需方邏輯的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是以基層居民個體健康價值為出發(fā)點,需方在價值創(chuàng)造過程中主動利用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由此獲取優(yōu)質(zhì)、高效、可及的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在此過程中對供方的產(chǎn)品質(zhì)量、行為態(tài)度、服務效果等方面表達價值訴求。
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融合供需雙方,促使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供需雙方積極互動、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目標是建立價值共創(chuàng)支持系統(tǒng),從而使得供需價值產(chǎn)出最大化。其中,供方價值產(chǎn)出主要體現(xiàn)在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分級診療制度初步形成,健康社區(qū)戰(zhàn)略得以落地。需方價值產(chǎn)出主要體現(xiàn)在基層居民健康素養(yǎng)和健康狀況改善,就醫(yī)可及性和便捷程度提升,就醫(yī)經(jīng)濟負擔得到有效降低。據(jù)此,本文提出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概念模型見圖1。

圖1 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概念模型
二、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現(xiàn)實困境:基于家庭醫(yī)生簽約視角
2016年5月,國務院聯(lián)合七部委出臺《關于推進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的指導意見》(國醫(yī)改辦發(fā)〔2016〕1 號),標志著我國開始全面推進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工作,并將其作為新時期深化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2018年10月,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國家中醫(yī)藥管理局印發(fā)《關于規(guī)范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管理的指導意見》(國衛(wèi)基層發(fā)〔2018〕35號),進一步提出要提升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規(guī)范化管理水平,促進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提質(zhì)增效。現(xiàn)階段家庭醫(yī)生團隊成員主要包括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注冊全科醫(yī)生和具備能力的鄉(xiāng)鎮(zhèn)衛(wèi)生院醫(yī)師和鄉(xiāng)村醫(yī)生等。為提升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動力,政府要求各地方在編制、人員聘用、職稱晉升、在職培訓、評獎推優(yōu)等方面重點向家庭醫(yī)生傾斜,從而增強家庭醫(yī)生職業(yè)吸引力和簽約服務動力。在服務內(nèi)容方面,家庭醫(yī)生主要為轄區(qū)居民提供基本醫(yī)療、公共衛(wèi)生和相關健康管理服務,居民可根據(jù)自愿原則與家庭醫(yī)生團隊簽訂服務協(xié)議,并交納一定簽約服務費(部分地區(qū)免費)。簽約后,家庭醫(yī)生須免費為居民提供協(xié)議范圍內(nèi)項目,對于協(xié)議范圍外的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項目,家庭醫(yī)生團隊可根據(jù)規(guī)定另行收取費用。在服務方式方面,各地紛紛采取全程服務、上門服務、錯時服務、預約服務等多種服務形式,保障簽約居民優(yōu)先轉(zhuǎn)診和住院,同時實行差異化的醫(yī)保支付政策,以期實現(xiàn)居民基層首診目標。
然而,在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實踐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以下突出問題,一是簽約居民被動履約現(xiàn)狀明顯。2017年,新華社一則《我國超過5億人有了自己的家庭醫(yī)生》的報道引發(fā)社會廣泛熱議[4],“簽而不約”“為簽而簽”等話題迅速走進公眾視野。筆者通過實地調(diào)研了解到,政府對于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的相關要求和考核指標,忽視了部分地區(qū)家庭醫(yī)生團隊的實際工作承擔能力,造成家庭醫(yī)生團隊出現(xiàn)人浮于事的現(xiàn)實案例,因而導致部分居民并不知曉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的相關政策。部分居民享受了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項目,但卻不知道這類項目屬于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協(xié)議范疇,對簽約后擁有的保障權利并不知曉,造成了簽約居民被動履約狀況頻發(fā)。二是簽約居民主動利用服務的動力不足。盡管各級政府不斷致力于規(guī)范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管理制度、提升家庭醫(yī)生團隊服務功能,但由于部分基層居民對于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項目的內(nèi)容和功能定位并不十分了解,因而制約了居民的主動利用服務。此外,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居民對于高質(zhì)量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需求持續(xù)攀升,這也造成部分簽約居民仍會選擇忽略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而直接前往城市大醫(yī)院就診。三是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模式有待優(yōu)化。2020年8月,課題組實地走訪了江蘇省江陰市、高郵市、鎮(zhèn)江市丹徒區(qū)等部分社區(qū),通過對家庭醫(yī)生團隊負責人訪談得知,某社區(qū)通過注重簽約服務的“儀式感”,提升居民對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認知程度。如居民簽約家庭醫(yī)生時需繳納50 元簽約費,同時家庭醫(yī)生承諾社區(qū)(村)將在一段時間內(nèi)將50 元全額返還給簽約居民,這使得居民對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有了更加深刻的認知;也有社區(qū)設計了一系列個性化簽約服務包(協(xié)議期內(nèi)免費服務項目),如單部位一次CT 半價、市級醫(yī)療機構專家門診等,因此轄區(qū)居民對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的主動利用率較高,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取得了顯著成效。
綜上可知,政府部門圍繞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工作進行了不斷探索與嘗試,旨在強化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網(wǎng)絡功能、保障基層居民獲得感和幸福感。但居民對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相關政策的知曉程度偏低,對家庭醫(yī)生團隊服務能力信任度仍然欠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價值的體現(xiàn)。此外,簽約居民主動參與度不足也反向影響了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團隊的工作積極性和服務效果。
三、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驅(qū)動因素
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的首要條件是參與主體達成觀念共識。在本文中,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雖然作為一個新的概念被提出,但相關的理論基礎已基本形成。價值共創(chuàng)理論指出,價值產(chǎn)生過程需要生產(chǎn)者和消費者之間共同合作,共同創(chuàng)造服務價值,這改變了過去學者認為的生產(chǎn)者是唯一的價值創(chuàng)造者,而消費者是純粹的價值消耗者的傳統(tǒng)觀點[5]。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對健康的定義為,健康不是沒有疾病或者不虛弱,而是生理上、心理上和社會關系上都處于良好狀態(tài)。這反映了健康不僅僅意味著身體患病后被動接受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而且鼓勵居民擁有主動健康意識。現(xiàn)階段,全球醫(yī)學技術水平不斷進步,人類戰(zhàn)勝重大疾病和疑難雜癥的典型事例不勝枚舉,然而傳染性疾病、慢性病仍然占據(jù)全球疾病經(jīng)濟負擔前兩位[6],這就需要醫(yī)療衛(wèi)生改革戰(zhàn)略由過去的“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轉(zhuǎn)變,從依靠衛(wèi)生健康系統(tǒng)向社會整體聯(lián)動轉(zhuǎn)變,倡導全民參與、人人行動。因此,政府和學界都愈發(fā)強調(diào)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項目優(yōu)化和居民主動健康觀念在健康中國戰(zhàn)略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的關鍵需要參與主體追求價值共生。當前,我國居民能夠選擇并堅持主動健康行為的人數(shù)甚少,多數(shù)居民思想仍然停留在“治已病”層面[7],這類居民往往被動接受健康信息,缺乏科學健康素養(yǎng)和健康規(guī)劃,對自身健康管理重要性的認知度明顯不足。事實上,自2009年“新醫(yī)改”啟動以來,我國業(yè)已在全國范圍內(nèi),向全體社區(qū)居民免費提供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并于2016年全面開展家庭醫(yī)生簽約服務,旨在幫助社區(qū)居民預防傳染性疾病、重大疾病和做好慢性病健康管理工作,實現(xiàn)居民主動健康目標。然而實踐發(fā)現(xiàn),社區(qū)居民大多是被動接受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主動利用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的現(xiàn)象并不多見,個體主動健康意識并不明顯,這造成了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的浪費,制約了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供給的效果。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公共服務利用是一項涉及政府主導、服務供給和需方認可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復雜過程。結合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而言,其供給效果受政府相關政策實施(服務項目、服務經(jīng)費等)、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機構服務供給(服務意識、服務態(tài)度、項目落實程度等)和社區(qū)居民認可(服務知曉、服務接受、主動參與等)多方面影響,加上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具備顯著的外部性特征,不同主體在參與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過程中,均會對服務效果產(chǎn)生重要關聯(lián)。因此,追求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長效目標就不能僅僅依賴于政策激勵,還需要服務供給主體功能的發(fā)揮和獲得社區(qū)居民參與、認同、信任等外在支撐。
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的最終目標是形成健康共贏。一直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發(fā)展衛(wèi)生和健康事業(yè)。據(jù)統(tǒng)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我國居民健康水平持續(xù)改善,人均預期壽命從35 歲提高到77 歲,嬰兒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孕產(chǎn)婦死亡率由1 500/10萬下降到18.3/10萬,主要健康指標優(yōu)于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8]。眾所周知,人口健康有助于降低疾病經(jīng)濟負擔,并帶來社會各項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紅利[9]。2021年7月,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財政部及國家中醫(yī)藥局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做好2021年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項目工作的通知》(國衛(wèi)基層發(fā)〔2021〕23 號),明確要求進一步加大人均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經(jīng)費補助標準、統(tǒng)籌推進常態(tài)化疫情防控、提升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質(zhì)量等系列工作任務和目標,再次體現(xiàn)黨和政府始終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的戰(zhàn)略地位,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這一系列有益舉措使我國重大慢性病過早死亡率逐年下降,因慢性病導致的勞動力損失明顯減少。截至2021年9月,全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經(jīng)濟社會秩序加快恢復[10]。國家繁榮昌盛是人民健康的根本保障,人民健康也是國家經(jīng)濟社會健康發(fā)展的重要基石。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本文將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的驅(qū)動因素歸納為改革過程中供需雙方達成觀念共識,形成價值共生,追求目標共贏三類主要因素,其示意圖如圖2所示。

圖2 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共創(chuàng)驅(qū)動因素圖
四、結 論
結合上述分析可知,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需要供需雙方主動參與并積極反饋,當前各級政府不斷致力于深化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供給側(cè)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改革過程中也發(fā)現(xiàn)基層居民認識度、參與度、主動利用程度不足等突出問題。因此,未來需進一步強化需求側(cè)改革,激勵和引導基層居民主動參與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事業(yè)改革過程中,從而共創(chuàng)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
(一)發(fā)揮社會資本嵌入作用
居民對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功能定位、服務項目、服務方式、服務價格等情況了解不全面仍然是制約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識別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情境中不同類別的社會資本,挖掘不同類別社會資本嵌入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作用機制,從而提升居民對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功能的認知程度,引導其主動利用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
(二)強化需方主動參與行為
近年來,政府不斷致力于優(yōu)化和完善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供給體系,這為提升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網(wǎng)絡功能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現(xiàn)階段居民主動選擇和利用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行為并不多見,這導致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資源閑置,影響了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也制約了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價值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因此,可制定相應的激勵機制和引導政策,強化需方主動參與行為,由此倒逼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項目優(yōu)化、服務能力提升。
(三)優(yōu)化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項目內(nèi)容
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催生了居民多元化、個性化的健康需求,而目前基層地區(qū)多以基本醫(yī)療、基本公共衛(wèi)生和健康管理類服務項目供給為主,制約了居民選擇和利用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動力。因此,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機構可以通過開展個性化服務、為居民提供靈活點單式服務等形式開展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工作,不僅能夠滿足基層居民多樣化、個性化的健康需求,同時也有助于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價值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