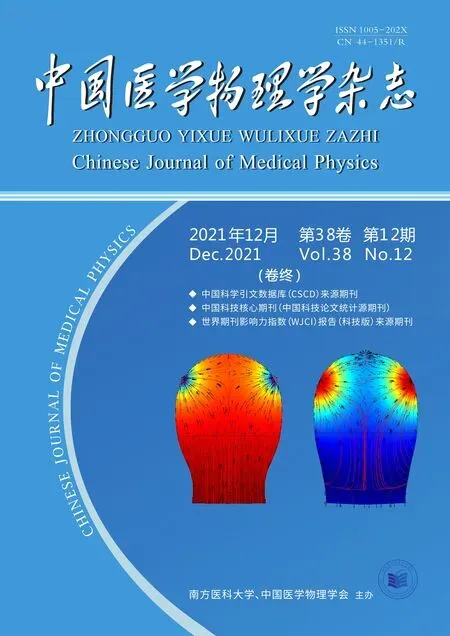利用放射生物學模型比較周圍型肺癌立體定向放射治療中的3種劑量方案
黃寶添,林佩賢,羅利梅,王影
1.汕頭大學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放療科,廣東汕頭515041;2.汕頭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醫院感染管理科,廣東汕頭515041
前言
原發性肺癌是我國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國家癌癥中心2019年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新發肺癌病例約為78.7 萬例,發病率為57.26/10 萬,位居我國惡性腫瘤發病首位[1]。但是因年齡及其它原因(如心肺功能差、嚴重糖尿病等)部分早期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不能耐受和拒絕手術,立體定向放射治療(SBRT)是首選的治療手段[2-4]。對于早期NSCLC 患者,采用SBRT 技術能獲得不亞于手術的治療效果,且放射治療毒性較低[5-6]。盡管目前使用SBRT 技術治療早期NSCLC 能取得令人鼓舞的治療效果,但是對于周圍型肺癌患者目前國際上尚未有統一的劑量分割方案。ESTRO ACROP 組織于2017年首次嘗試統一早期周圍型肺癌的劑量分割方案。根據該組織問卷調查結果,對于周圍型早期NSCLC 患者,建議采用3×15 Gy 的劑量分割方案,而對于毗鄰胸壁的腫瘤,ESTRO ACROP 則建議采用4×12 Gy 的劑量分割方案[計劃靶區(PTV)D95~D99,最高處方劑量為125%~150%],對于發生嚴重合并癥概率較低且預期可獲得長期生存的患者可以考慮使用3×18 Gy 的劑量方案[7]。放射性肺炎是肺癌SBRT治療中常見的放療毒副反應,ESTRO ACROP組織在推薦的劑量方案中只考慮到腫瘤毗鄰胸壁的情況,而對于靶區與肺組織體積比較大的病例其放射性肺炎的發生概率較高[8],對于這些病例該采取何種劑量方案文中并無提及。本文將分別設計3 種劑量分割方案的放射治療計劃,利用放射生物學模型探討3種劑量方案對腫瘤局部控制率和對肺、胸壁和肋骨放療毒性的影響,以期根據腫瘤與危及器官的毗鄰關系實現個體化SBRT治療。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資料
選取20 例病理確診的Ⅰ期周圍型NSCLC 患者的CT圖像資料,所有患者已在本院行SBRT治療。
1.2 四維計算機斷層掃描(4DCT)模擬定位
患者使用頭頸肩固定面罩或真空袋(廣州科萊瑞迪醫療器材有限公司)進行體位固定后,使用飛利浦公司(Brilliance Big Bore)放療專用大孔徑4DCT在自由呼吸狀態下掃描分別得到一套自由呼吸3D圖像和一套4DCT 圖像,3D 和4D 均采用相同的掃描范圍,掃描時層厚與層間距均設定為3 mm。4DCT 的10 個呼吸時相圖像(0%~90%時相)、最大密度投影(MIP)和平均密度投影圖像(AIP)均由計算機重建獲得后再通過DICOM 端口傳送到Eclipse 計劃系統(美國Varian公司,10.0版本)進行靶區勾畫和計劃設計。
1.3 靶區的勾畫
實體腫瘤(GTV)在自由呼吸圖像上使用肺窗勾畫;內靶區(ITV)由在肺窗下分別勾畫4DCT上0%~90%呼吸時相上的腫瘤再合并生成;考慮到擺位誤差,PTV由ITV在三維方向外擴5 mm生成。
1.4 危及器官的勾畫
正常肺組織、胸壁和肋骨等危及器官的勾畫在3D 平靜呼吸圖像上進行,肺和胸壁的勾畫按照腫瘤放射治療組(RTOG)0915 號報告[9]和Kong 等[10]的標準進行,肋骨按照Stam等[11]的方法進行勾畫。
1.5 放射治療計劃設計
采用TrueBeam 直線加速器去均整器模式(6XFFF,1 400 MU/min劑量率)射束能量進行計劃設計,劑量計算采用各向異性算法(AAA,版本10.0.28)。分別使用3×15 Gy、4×12 Gy 和3×18 Gy 共3 種處方劑量分割方案設計放射治療計劃。按照RTOG 0915 號[9]和TG-101 號[12]報告對肺癌SBRT 治療計劃劑量的要求,分別從靶區劑量、靶區外劑量下降梯度和危及器官劑量等方面分別進行限制。計劃設計時通過調整優化參數保證靶區內最高劑量約為處方劑量的120%且最高劑量點落在GTV內,使用處方劑量包含95%PTV體積進行劑量歸一。
1.6 生物效應評價
放射生物學模型計算流程按照本課題組之前發表過的研究進行[13]。采用Liu模型計算腫瘤的3年局部控制率(TCP)[14],采用Wennberg 模型計算放射性肺炎發生概率(RIP)[15],采用Din 模型計算胸壁疼痛發生概率(CWP)[16],采用Stam 模型計算肋骨骨折發生概率(RIRF)[11],具體計算參數見文獻。將以上4種放射生物學模型編譯成MATLAB(MATLAB 2012)代碼進行批量計算。
1.7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25.0 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不同劑量分割方案計算得到的概率數值比較采用配對秩和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3 種劑量方案的TCP、RIP、CWP 和RIRF 的概率值以散點圖表示,為了更直觀地顯示,把RIP、CWP和RIRF 發生概率較高(RIP 發生概率≥8.8%,CWP 發生概率≥17.2%,RIRF 發生概率≥3.6%)的患者劃分為高風險組,其它患者劃分為低風險組。低風險患者組3種劑量方案的TCP、RIP、CWP 和RIRF 的發生概率如圖1 所示,高風險患者組數據如圖2 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到:(1)無論是對于高風險患者還是低風險患者,3 種劑量方案對TCP 數值沒有顯著影響。雖然3×18 Gy 劑量方案的TCP 數值在CWP 和RIRF 發生概率較高組患者、RIP 和RIRF 發生概率較低組患者對比3×15 Gy 和4×12 Gy 劑量方案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差別僅為0.1%,可忽略;(2)放療毒性方面,4×12 Gy劑量方案的放療毒性最低,3×15 Gy放療毒性稍有增高,而3×18 Gy的毒性最高。不同劑量方案的RIP、CWP 和RIRF 概率數值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3)無論是對于高風險患者還是低風險患者,使用3×18 Gy 劑量方案的RIP、CWP 和RIRF的中位發生概率均明顯高于其它兩種劑量方案,特別是對于高風險患者,其差別更加明顯。盡管高風險患者病例數較少,但差異仍然有統計學意義(P<0.05)。

圖1 低風險患者組3種劑量方案的TCP、RIP、CWP和RIRF的概率數值Fig.1 TCP and the probabilities of occurrence of RIP,CWP and RIRF in 3 dose schedules for the low-risk cohort
通過數據統計分析,對于低風險患者,3×15 Gy、4×12 Gy 和3×18 Gy 劑量方案RIP 的中位發生概率分別為6.3%、5.4%和9.7%;CWP 的中位發生概率分別為13.4%、12.8%和14.6%;RIRF的中位發生概率則分別為2.9%、2.2%和7.1%。而對于高風險患者,3×15 Gy、4×12 Gy 和3×18 Gy 劑量方案的RIP 中位發生概率分別為16.3%、13.0%和28.4%;CWP的中位發生概率分別為20.4%、18.3%和33.0%;RIRF的中位發生概率則分別為5.4%、4.0%和13.0%。
3 討論
目前臨床肺癌SBRT 治療并沒有統一的劑量方案,因此不同中心的治療效果難以比較。如何根據腫瘤的大小、位置及與危及器官的毗鄰關系等特點給予肺癌患者個體化的劑量治療方案,是肺癌SBRT治療中亟待解決的難題。3×15 Gy、4×12 Gy 和3×18 Gy 等3 種劑量方案是肺癌SBRT 治療中常見的幾種劑量分割方案,通過比較它們之間的劑量效應差異,可為臨床治療提供劑量學上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通過放射生物學模型比較3 種劑量方案在TCP、RIP、CWP 和RIRF 方面的差異,發現3 種劑量方案對TCP 沒有顯著影響。而在放療毒副作用方面,4×12 Gy劑量方案的放療毒性最低,3×15 Gy放療毒性稍有增高,而使用3×18 Gy 劑量方案的RIP、CWP 和RIRF 發生概率則明顯高于其它兩種劑量方案。本研究結果是對ESTRO ACROP 問卷調查結果的補充。基于本研究數據分析結果可以認為,對于腫瘤遠離胸壁和放射性肺炎發生概率較低(如PTV和肺組織體積比較小)的患者,可采用3×15 Gy 的劑量方案,因為該劑量方案可在沒有明顯增加放療毒性的情況下減少放療的次數,在可減少病人經濟負擔的同時為病人帶來方便;對于腫瘤毗鄰胸壁和放射性肺炎發生概率較高(如PTV 和肺組織體積比較大)的患者,建議采用4×12 Gy的劑量方案,因為該方案可在保證腫瘤局部控制的情況下降低放療毒性;在肺癌SBRT 治療中不推薦使用3×18 Gy 的劑量方案,因為該劑量方案在沒有提高腫瘤局部控制的情況下反而顯著增加放療毒性,尤其是對于RIP、CWP和RIRF 發生概率較高的高風險患者,建議慎用該劑量方案。
近年來國外多篇文獻已證實在肺癌SBRT 治療中,腫瘤的局部控制率與靶區內最高劑量緊密相關[14,17-20],而不是與處方劑量相關。但是文獻資料擬合出來的劑量效應曲線卻有所不同,爭論的焦點在于該曲線在多高的生物等效劑量(BED)將到達劑量坪區。Guckenberger 等[17]和Santiago 等[18]分別通過LQ 模型擬合了13 個中心的395 例患者和23 篇文獻資料的1 975 例病人的治療數據,曲線擬合結果顯示當BED超過200 Gy10時,繼續提高劑量還有助于改善腫瘤局部控制率;Tateishi 等[20]最新研究報道結果也表明,腫瘤靶區的最高劑量≥200 Gy10與<200 Gy10相比,能提高腫瘤的局部控制率;但是Liu 等[14]通過腫瘤再生長模型擬合46 篇文獻資料的3 479 例病人的治療數據后發現,當BED超過90 Gy20時,劑量效應曲線即到達坪區,即局部控制率將不隨劑量的增加而增加,并且該研究對比了該模型與其它的另外5種模型LQ、USC、LQL、mLQ和mLQL,發現腫瘤再生長模型的擬合效果最優。以上文獻報道的結果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究竟哪種模型更加符合臨床治療結果,這還需要更多的文獻資料對此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由于Liu 模型納入分析的樣本量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且已證明該模型優于另外5種預測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是Liu 模型計算腫瘤局部控制率。本文發現,3×15 Gy、4×12Gy和3×18 Gy 劑量方案對TCP 并沒有顯著影響,由于3×15 Gy、4×12 Gy 和3×18 Gy 等3 種劑量方案中心點的BED 分別為151.2、140.5 和204.8 Gy10,這說明3 種劑量方案最高劑量點為處方劑量的120%時,已經到達劑量效應曲線的劑量坪區,再提高劑量并不能改善腫瘤的局部控制。
本研究中用到的幾種計算模型都是經臨床治療數據擬合而成。使用Liu 模型計算TCP 概率數值的原因上面已進行討論;本研究使用Wennberg 模型計算RIP 發生概率,正常肺組織定義為雙肺扣除GTV,而使用這種肺組織定義作為劑量評價已得到越來越多研究的支持[21-23];Din 和Stam 模型是目前經文獻報道唯一可用來計算胸壁疼痛發生概率和肋骨骨折發生概率的模型[11,16]。本研究是基于放射生物學模型對3種劑量方案的優劣進行綜合分析和評價,由于使用不同的模型和模型參數的不確定性會對本研究結果產生影響,因此在今后臨床實踐中應納入更多臨床病例來驗證本研究結論。
綜上所述,3 種劑量方案對腫瘤TCP 數值沒有顯著影響,4×12 Gy 劑量方案的放療毒性最低,采用3×18 Gy 劑量方案會顯著增加RIP、CWP 和RIRF 的發生概率。建議臨床治療前應根據腫瘤與危及器官的毗鄰關系選擇合適的劑量分割方案,以平衡腫瘤局部控制和放療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