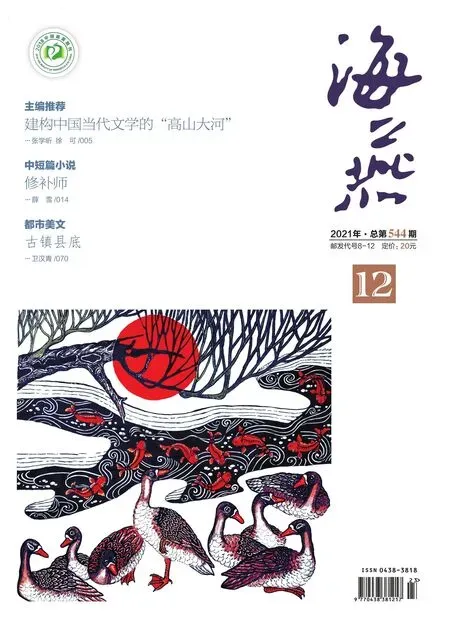漂亮女生
伊爾根
“老師,安寧決定和寧遠復婚,這回我徹底沒戲了。”
“你說他倆要復婚?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安寧親口說的,這事不能有假。”
“那張健怎么辦?安寧不管了?”
“張健被判死緩,你讓安寧怎么管?”
“你真的死心了?”
“不死心又能怎樣呢?老師,我真是太傻了,白等了她25年!”說完,沒等我接話,高飛舉杯一飲而盡。
高飛是我的學生,臨下班的時候,他打電話請我喝酒,我高興地答應了。我是在同事們羨慕的目光中離開辦公室的,難怪他們羨慕,已經畢業(yè)25年的學生請老師喝酒,怎么想都是一件讓人驕傲的事。沒想到高飛找我訴苦來了。這么說吧,安寧、張健、高飛是我的學生,至于他們三人還有寧遠之間到底發(fā)生了怎樣的故事,一兩句話說不清楚。
故事是從1994年開始的。
那年,我擔任高三班主任,開學不久,安寧轉進我?guī)У陌嗉墶PiL告訴我,安寧之前在私立高中念書,班級有兩個男生追求她,并因此發(fā)生了流血事件,她不得已才轉過來的。又叮囑,安寧長得漂亮,人也活潑,可能成為班級的不穩(wěn)定因素,你作為班主任必須要重點關注才是。我一邊答應一邊想,到底什么樣的女生,值得男生為她兵戎相見?
見到安寧,答案便有了。她近1.70米的身高,體形勻稱,五官精致,皮膚光潔,即便穿著松松垮垮的運動裝,也難掩天生麗質。最惹眼的是她的五號頭,頭發(fā)天生卷曲,五指隨意一攏,便散發(fā)出一種濃郁的、與年齡不相稱的女人味。這在清心素面的高中女生中,確有一枝獨秀的驚艷。很快我班里轉來一位漂亮女生的事就在學校傳開了。課間,我班門口經常聚集一幫男生,他們來不為別的,就為一睹新校花的芳容。到了后來,女生也三一群、倆一伙地過來了。一個未婚男老師開玩笑說:“趙哥,安寧有沒有男朋友?要是沒男朋友,你把她介紹給我,我可以一直供她到大學畢業(yè)。”就連退休返聘、白發(fā)蒼蒼的組長老太太也生了好奇之心,她笑咪咪地說:“小趙老師啊,你以取作業(yè)為名,把那個安寧喊到物理組來讓我瞧瞧。”


插圖:李雨薇
很快我便發(fā)現,安寧的性格和她的姓名截然相反,她天生是“自來熟”,興之所至更是“人來瘋”,進班級沒用幾天時間,便和幾個活躍的男生混得滾瓜爛熟。和女生關系也不錯,但到底沒有和男生那么熟絡。到食堂吃飯,她不介意和男生同桌。課間休息,她喜歡扎進男生堆里。一次課間,居然和男生掰起了手腕,教室里山呼海嘯,引起眾多外班學生前來圍觀。體育課上,女同學聚在一起打排球,她偏去和一幫男生打籃球,看她帶著籃球橫沖直撞,男生一個個嚇得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次周六打完籃球,她竟然請幾個男生到飯店喝酒,在她的循循善誘下,幾個男生吐得翻江倒海,她卻面不改色。女生和男生交往如此沒有界限,要么是“假小子”,要么是舉止輕浮,可發(fā)生在貌美如花的安寧身上,就格外顯得伶俐可愛了。當然女生是不會這么認為的,她的招搖不可避免引起了一些女生的反感,其中不乏嫉妒之心。
安寧求學的那所私立高中,盡管頂著某國際名校的光環(huán),但教學質量委實不怎么樣。她原來在班級里名列前茅,到了我們這所重點高中,經過幾次小考就原形畢露了。安寧骨子里有種不服輸的勁頭,奈何她的學習基礎太薄弱了,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趟兒,沒辦法只好跟同座不恥下問。時間長了,同座難免心生厭煩,安寧感覺到了。一日,她找我請求串座,說想和高飛同座。我問原因,她說高飛講題明白還有耐心。高飛成績穩(wěn)坐年級第一,是學校重點培養(yǎng)的清華北大苗子。排座位歷來是班主任的一道難題,為了坐在前排中間,為了和學習好的同學同桌,家長找關系托人情甚至砸錢收買老師。學生到你面前哭哭啼啼的,一想這些事腦袋就會大一圈,至于學期中間串座更是沒半點可能性。那天安寧哭眼抹淚地說:“老師不麻煩您,我自己串,您只要同意就行。”這個要求不過分,我在答應的同時心中暗想,安寧座位靠后,想調到高飛的前排座位殊為不易,連老師辦起來都非常頭疼的事,她一個初來乍到的學生能辦到?
始料不及的是,安寧真把座位串成了。
后來我才知道,是張健幫的忙。張健是班長,為人少年老成,學習成績一般,組織能力超強。為幫助安寧達成心愿,張健先做通了高飛和他同座的工作,然后犧牲自己向后坐到安寧的座位上,高飛同座坐到他的座位上,如此繞了一圈,安寧便和高飛同座了。班里學生都看出來了,張健這是在向安寧獻殷勤。我了解情況后十分擔憂,一方面害怕張健分心,他是班長,一旦他帶頭談戀愛,班級風氣有可能被帶壞;另一方面,更害怕安寧影響高飛學習。安寧太撩人了,這樣一個撩人的女生坐在身邊,在荷爾蒙洶涌澎湃的年紀,哪個男生會心如止水?
我的擔憂在寒假前變成了現實。
元旦,班級召開聯(lián)歡會,張健和安寧擔綱主持人。聯(lián)歡會中間,安寧和高飛合唱了一首《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合唱結束后,學生提議兩位主持人合唱一首,一個男生跟著起哄,說不唱拉倒,要唱就唱《夫妻雙雙把家還》。安寧和張健小聲商議了一小會兒,最后合唱了一首《戀曲1990》。之前就有學生私底下嘀咕張健追求安寧,聯(lián)歡會結束后,風言風語便公開化了。班長帶頭談戀愛,班主任不能聽之任之,我找張健談話,他振振有辭地說:“老師,您太敏感了,我和安寧只是正常的同學交往。”找安寧談話,她一臉莫名驚詫,“老師,您憑什么說我倆談戀愛呢?”
憑什么?這話一下子把我問住了。憑學生的背后議論?憑他倆合唱愛情歌曲?憑他倆課間并排站在走廊里聊天?憑他倆給彼此買冰激凌吃?說服力不強啊!曾經,一個女生公然在走廊里摟摟抱抱,我批評她,她不承認,我臭她:“難道非得懷孕了才算談戀愛?”那是一個沒皮沒臉的女生,她嬉笑著回應:“老師,你說我要是真有孩子,他是喊您姥爺?還是喊您舅舅?”氣得我差點一巴掌掄過去。安寧卻截然不同,特別是她的目光,像山泉水一樣清澈見底,有那么一瞬間,我的確懷疑自己神經過敏了。我板起臉來故作惱火地教訓她:“什么也不憑,就憑我是你的老師,所以有必要提醒你,一定要把精力用在學習上,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安寧一臉陽光燦爛地笑了,“謝謝老師,我絕對銘記在心。”走不遠,又轉身回來深鞠一躬,“老師您放心吧,我倆從來沒有約會過,沒有約會哪能算談戀愛呢?”語氣特別真誠,我不由得信了。不信也不能深說,多年的班主任經驗告訴我,學生談戀愛就像彈簧,你越想壓制,反彈力越大,只要在班級里沒有親密行為,班主任還是該干嘛就干嘛去吧!
我的警告多少還是起了作用,安寧消沉了幾天,但她很快又活躍起來。沒有辦法,她天生就是外向性格,不是誰一兩句話就能改變得了的。和張健的交往倒是收斂了許多,應該合乎“發(fā)乎情止乎禮”吧。對于兩人走得過近,班級同學早就見怪不怪了。那會兒,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學生都是“只要不學死,就往死里學”,誰有閑心管別人的事呢?安寧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緊迫感更強,加上高飛的輔導起了作用,她終于沖到了班級中間位置。讓我頗感意外的是,高飛的成績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相反學習勁頭更足了。張健的成績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事實證明我多慮了。有時坐在教室里,我不免感嘆自己落伍了,眼前這幫小毛孩子,在處理復雜的感情問題時,比成年人還能拿得起、放得下。
校長到班級聽課,看到高飛和安寧同座,如臨大敵,他喊我到校長室,呵斥我道:“趙老師,你怎么能讓安寧和高飛同座?真是荒唐!胡鬧!”難怪校長生氣,學校好幾年沒出清華北大生了,社會上對此議論紛紛,他壓力很大。我小心翼翼地分辨:“校長,您大可不用擔心,自從他倆坐在一位,高飛的成績比原來更好了。”我說的是事實,校長不好再說什么,但黑風罩臉地給我打預防針:“趙老師,你聽清楚了,高飛要是考不上清華,我唯你是問!”我嘴上唯唯諾諾,但其實內心壓力不小,現在所有的課任老師如眾星捧月一樣捧著高飛,無非眼巴巴盼著他考上清華好揚眉吐氣。如果被安寧扯了后腿,那我在學校不會有好果子吃。
離開校長辦公室,我把高飛喊到教研室,拐彎抹角問他學習情況,他聽明白了我的意思,說:“老師,您放心吧,我給安寧講題不但沒耽誤學習,相反對題目的理解比原來更深刻了。”看我懷疑,他又哀求:“老師,這眼見快高考了,你千萬不要把我倆分開,你要是把我倆分開,那對誰都不好。”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便默許了。
終于熬到報高考志愿了,當時高考是先報志愿后考試,大學分為重點大學和普通大學。張健第二批錄取第一志愿報考本省一所農業(yè)大學,按照他三次模擬考試成績,算得上中規(guī)中矩。安寧第二批錄取第一志愿報考我念書的雙海師范大學,專業(yè)選擇物理學系,她征求我的意見,我問:“你這么喜歡當老師?”她回答:“喜歡。”“那為什么選擇物理學系呢?”
“這個……”安寧羞澀地笑了,“我要說喜歡物理,那是騙您呢,主要是物理難學,報考的學生可能少些,要是報別的系,我有點沒有把握。”安寧的成績考不上重點大學,女孩子選擇教師職業(yè)確實不錯,我同意了。高飛第一批錄取只報一個志愿:清華大學,第二批錄取也只報一個志愿:雙海財經大學。這個報法太離經叛道了,我問:“你已經決定了,一本院校只填一個志愿?”高飛說:“決定了,要是考不上清華,只能考三流重點大學,沒意思。”我問:“二本為什么只報一個志愿呢?”高飛說:“一本我冒險往上沖一下,如果沖不上去,二本我就得保險一點,我們家經濟條件不好,復不起課。”我說:“也可以考慮報別的財經大學,好男兒志在四方嘛。”高飛說:“老師,在外地念書來來往往,光交通費就得花不少錢,我想節(jié)省一點是一點。”說得挺有道理,我答應了。清華確實太難考了,高飛的父母是普通工人,要是他落榜了,他父母斷然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擊,按照他平常的學習成績,我本想建議他二本志愿報得再高一點,可考慮到他的家庭條件,就忍住沒說。
高考成績終于出來了,讓我大跌眼鏡的是,高飛成績雖然名列全校第一,但比預估低了20分!指望通過他露臉的肥皂泡破滅了,我一個人坐在教研室里黯然神傷。
高飛向我道歉:“老師,對不起,讓你失望了。”
高考是真刀真槍,成績比照平時差上差下很正常,我不好過分責怪他。沉默了一會兒,我問:“數學才答了110分,怎么搞的?”數學是高飛的強項,按照那年的高考成績,他考130分以上才算正常。“數學我估136分,現在看來可能答題卡涂串行了。”我信了他的話,正常情況下,像他這樣的高才生,單科估分和考分上下不會超過5分。
“后悔沒有用,反正已經這樣了。”我安慰他,“雙海財經大學也是全國知名大學,要是你愿意,畢業(yè)后還可以考清華的研究生。”
高飛、安寧和張健都考上了第二批錄取第一志愿。安寧如愿以償,她開玩笑:“老師,過去我是您的學生,現在可變成你的師妹了,也許將來有一天,我沒準會成為你的同事呢。”張健到學校取入學通知書,我問他高飛情緒如何,張健說:“心想事成,比考上清華還高興。”我不解,問為什么,張健說:“老師,雙海師范大學是您的母校,您肯定知道,雙海財經大學和雙海師范大學中間只隔了一條馬路。”我還是沒聽明白,張健進一步解釋:“老師,高飛喜歡安寧,您一點沒看出來?也難怪,您把注意力全放在我這兒了,要是您再稍微分分神,就會看出來高飛喜歡安寧。”我沉默了,直覺告訴我他說的是真的,雖然我確實沒看出來。
那年寒假,高飛和安寧一起到學校來看望我。兩人離開后,同事閑聊,都說看來我們的校花有主了。我聽了替高飛高興,那時我雖然經歷了一些人生滄桑,但仍沒擺脫年少輕狂,特別是胸中充盈著無限的浪漫情懷。我想高飛雖沒考上理想大學,但若能和喜歡的女人走到一起,未嘗不是一件人生幸事。哪知過了幾天,安寧又和張鍵一起過來了,我心中便隱隱有些不安。在感情的天平上,我希望安寧能接受高飛,可是在內心深處,又隱約覺得安寧和張健更合適。男人天生喜歡美女,可喜歡是一回事,和她風風雨雨一起過日子卻是另一回事。經驗告訴我,美女大多如烈馬,不是優(yōu)秀的騎手根本駕馭不了。高飛固然情深意重,但對男人來說,癡情往往是致命的缺點。相比之下,張健卻成熟穩(wěn)重,并且張健的父母都是單位主要領導,家境比高飛不知要好多少倍。
第二年寒假,安寧和高飛、張健一起到學校來看我,三人離開后,同事好奇地問:“趙老師,你說那兩個男生,安寧最后會選擇哪個?”我回答不上來。一次大學同學聚會,我問一個留校的同學安寧在校表現,同學告訴我,安寧是物理學系的系花,在系里非常活躍,是學生會文藝部部長,但專業(yè)課成績一般,好像還掛科了。我問她交沒交男朋友,同學說追她的男生有很多,系學生會主席正對她窮追猛打,但她和他若即若離,因此具體什么情況說不清楚。同學最后笑著補充:“我們念大學那會兒,男生追女生叫‘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你的這位美女學生可不然,人家是‘全面培養(yǎng),重點選擇’!”
第三年寒假,安寧和張健一起來看我,我以為這下兩人的事可以定下來了,誰知張健告訴我:“老師,安寧心中有人,我沒戲,高飛也沒戲。”這太意外了,我問:“安寧有男朋友了?”張健回答:“是,一個初中同學對她死纏爛打了多年,現在終于修成正果了。”初中同學?我聽了感到匪夷所思,“他什么大學畢業(yè)?”“什么大學也沒念,就是中專畢業(yè),目前在一個化工廠當會計。”“你能確定?”我無論如何不相信貌美如花、大學畢業(yè)的安寧會找一個普通工人。“我和那個男生面對面談過,這事還能有假?”“高飛知道嗎?”“當然,可憐他到現在還不死心,傻乎乎等著安寧回心轉意。”“我聽我的大學同學說,物理系學生會主席正在追求她,好像機會蠻大的。”“追不上的,安寧我太了解她了,等她畢業(yè)了,他們之間的交往就結束了。”
張健走后,我立馬喊來高飛,問他到底怎么回事,高飛告訴我,張健說的是真的,那個男生叫寧遠,是安寧的初中同學,兩人早就交往了,只不過安寧閉口不說而已。高飛說得言之鑿鑿,可我還是不相信,“你真的能確定?”“那當然能,這事我能胡說嗎?”原來寧遠背著安寧偷偷找過高飛,說他和安寧的關系已經明確了,求他以后不要再去打擾安寧。為了讓高飛相信,寧遠拿出了他倆到各地旅游的照片,照片有在北京故宮拍的,有在上海外灘拍的,有在安徽黃山拍的,反正中國的風景名勝區(qū)基本讓他倆走遍了。我一聽就明白了,別看高飛是大學生,人家是中專生,可他的經濟實力,和人家相比根本不在一個級別。沉默片刻,我問:“高飛,你這么喜歡安寧,和她攤過牌嗎?”高飛憋了好一會兒,說:“攤過一次,安寧說她暫時不想考慮個人問題。”我激勵他:“不管怎樣,好歹再攤一次,以免今后后悔。”高飛猶豫了幾秒鐘,說:“老師,真的不能再攤了,要是再攤,話就得說死,那以后一點機會也沒有了。”我勸高飛把目光放長遠一點,為一個女人犧牲前途不值得,高飛重重嘆了口氣,說:“老師,我早就做出犧牲了,那年高考,我故意答錯了五道選擇題,現在說什么也沒有用了……”
想不到一年半后,我和安寧竟然成了同事。
雙海師范大學下面有一所附屬中學,是省內著名的重點高中。由于我在高中物理教學方面成績突出,附中便向我伸出了橄欖枝,調我到附中任物理組組長,人往高處走嘛,我答應了。報到那天,我聽說安寧被附中留用了,母校畢業(yè)的學生中,能被附中留用的幾近鳳毛麟角,聽其他老師說,安寧學習成績一般,但實習時在課堂上和學生互動好,加上母校物理學系竭力推薦,附中才決定留用的。
四年大學過去,安寧早擺脫了高中時的青澀,愈發(fā)出落得楚楚動人了,只是言談舉止矜持了許多。見到我,安寧嫣然一笑,說:“老師,你記不記得高中畢業(yè)時,我說我倆有可能成為同事,當時你還不信,現在你看是不是變成真的了?”“是啊,這么說你還真有先見之明呢。”我笑著打哈哈。說不清什么原因,我對我教的這個漂亮女生起了戒備之心。
新老師要拜師,安寧自然拜我為師,她問我新老師要注意什么,想起她之前的個性,我說要先行為世范,再學為人師,她說老師你放心吧,我保證不給你丟臉。安寧教學很用功,悟性也好,業(yè)務上手很快,和別的老師相比,她的課堂氣氛特別活躍,不可否認,她的容貌起了作用,雖然并非決定性的,但肯定也是至關重要的——學生喜歡美女老師,說起來真是一件讓人無可奈何的事。安寧也會別出心裁抖小激靈,比如批閱學生作業(yè),其他老師只批對錯,紅叉打得張牙舞爪,她卻在學生作業(yè)上畫臉部表情,比如笑臉、哭臉、怒臉,或者寫一兩句搞笑的話:聰明,姐喜歡你;再錯,姐要發(fā)火了,諸如此類。她的創(chuàng)意很成功,學生對此既見所未見,亦聞所未聞,看到批語無不歡呼雀躍,這樣過了半年,安寧講課受到了學生的普遍歡迎。
美女總會引人注目,一個未婚男老師聽說我是安寧的老師,就托我?guī)兔榻B,我初來乍到不好拒絕,便私下問安寧有沒有男朋友,安寧矢口否認,但她委婉地說不想找同行,這等于間接回絕了。男老師聽后撇了撇嘴,那么漂亮沒有男朋友,誰信?人家是在看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呢!
高飛被雙海財經大學保送研究生,張健在父母的運作下,被分配到雙海市財政局,兩人聽說我被調到附中來了,給我設宴接風,并請安寧作陪。那天喝了不少酒,后來還出去唱了一會兒歌。在歌廳,張健借著酒勁兒說:“安寧,我倆再合唱一曲《戀曲1990》,可以嗎?”安寧咬緊嘴唇,說:“那年元旦聯(lián)歡會唱歌是你提前安排好的,你別以為我不知道。”張健微微一笑,說:“老師,確實是我提前安排好的,本來要唱《夫妻雙雙把家還》,因為你在場,才臨時改成了《戀曲1990》。”安寧大呼小叫:“沒想到你這么狡猾,害得我被全班同學指指點點好多天!”張健繃起臉來,說:“再狡猾也沒有你狡猾啊,你早有男朋友了,我和高飛卻傻呵呵的一點也不知情。”安寧花容失色了幾秒鐘,但笑容立刻又如出水芙蓉一樣綻放開來,“誰有男朋友了?高飛,我倆大學緊挨著,你說我有男朋友嗎?”高飛甕聲甕氣地說:“有沒有男朋友你心里知道。”安寧轉而向我求救:“老師,兩個男生欺負我,你管不管?”我沒法接言,只能笑著打圓場:“你們誰要是有朋友就快點結婚,老師等著喝你們的喜酒呢!”
半年后的一天,安寧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老師,有個事兒向你匯報。我確實有男朋友,他叫寧遠。他追我好多年了,我不想辜負他。他是中專畢業(yè),我以前怕你笑話,沒敢講實話。”本來因為高飛,我對安寧持有偏見,卻沒想到她是一個重情重義的女孩子,雖然我認為一個中專生配不上她,但仍然給予鼓勵:“只要兩人相愛,學歷不應該成為婚姻的障礙。”安寧高興地說:“老師,你這么說我就放心了。之前我有顧慮,總怕拿不出手。這樣吧,明天我把寧遠帶來,請老師給把把關。”
翌日,寧遠請我吃飯。握手寒暄時,我仔細打量寧遠,一米八左右的身高,體格健壯,面目有型,衣著講究,上下里外透出一股精銳之氣。兩個挺拔、俊朗的青年男女站在一起,活脫脫一對金童玉女。寧遠是開一輛桑塔納過來的,我無話找話地說:“車不錯。”寧遠口氣平淡地說:“剛買的,新車買不起,就買了臺二手車裝門面,有車出去談生意會方便一些。”
之前沒說到哪兒吃飯,落座后我才省悟過來,原來是本市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頂層的旋轉餐廳,我從來沒有到過這么高檔的地方,便竭力做出司空見慣的神情,但那里餐廳的裝修,大堂的音樂,以及服務員的神情,都在精致中露出傲慢霸道之色,就連空氣分子也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你是一個窮人!安寧卻像回家一樣自然,她看出了我的窘迫,嗔怪寧遠:“我說不到這里吧,你非要來,看把我老師弄不舒服了。”寧遠漫不經心地把磚頭般大小的“大哥大”立在餐臺上,說:“這地方誰能老來呢?就是來一次見見世面,也好知道這個社會是怎么回事。”又對我說:“您是安寧的恩師,就是我的恩師,請恩師吃飯,不來這里不足以表示誠意。”
寧遠太會說話了,每句話都能觸到人心深處最柔弱的部分,怪不得安寧喜歡他,女為悅己者容嘛。中間安寧上衛(wèi)生間的時候,寧遠說:“老師,安寧漂亮,追她的學生肯定不少,你知道她為什么會選擇我嗎?”我問:“為什么?”寧遠說:“她的姓和我的姓連起來恰好是她的名字,她的名和我的名連起來恰好是我的名字。她說這是命運的安排,所以她才選擇我。”我認真想了想,還真是那么回事。快結束的時候,寧遠問我用不用再加點什么,我說不用了,他隨意從皮夾子里抽出一沓錢,對服務員說不用找了,多余的錢算小費,服務員樂呵呵地接過錢走了。結束的時候,寧遠舉杯說:“老師,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雖說你只比我們大幾歲,但你對安寧的恩情,我倆一輩子都不會忘懷。我有一個不情之請,就是我和安寧結婚的時候,想請你當證婚人,不知可不可以?”由于酒精的作用,也可能是寧遠的話把我捧得迷迷糊糊的,我痛快地答應了。第二天安寧問我對寧遠的印象,我回答說小伙子挺不錯的,安寧說既然老師許可了,那我可就把終生托付給他了。
幾天后我和張健、高飛聚會,中間談到了寧遠,我說他好像生意做得挺大的,張健撇撇嘴說:“他能做什么生意?還不是和廠長聯(lián)手,把廠子掏空了。”高飛附和:“張健說得沒錯,我做過專題調查,窮廟富方丈,是我們這兒很多國有和集體企業(yè)的常態(tài)。”我開玩笑:“你們倆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吧?”張健冷笑一聲,說:“老師,說出來你可能不信,企業(yè)破產是眼下最快的發(fā)財路徑,情形如果照此發(fā)展,我相信用不了幾年,我市的大部分國有和集體企業(yè)就會化為烏有,不信等著瞧!”
三個月后,安寧和寧遠結婚了。婚禮就是在那家豪華的五星級酒店舉辦,本市電視臺綜藝節(jié)目王牌主持人主持婚禮,婚禮現場氣氛喜慶熱烈,我的證婚詞也足夠精彩,婚禮結束后舉辦了一場小型音樂會,由本市出爐的某當紅歌星現場獻歌三曲,這在當時簡直是翻天覆地的事。婚后,兩人遠赴歐洲旅游了一圈,我給安寧代的課。一年后,安寧生了一個女兒,小家伙天生一個美人胚子,可愛得很。美中不足的是寧遠所在的工廠不久破產了,好在兩人家底殷實,加上寧遠頭腦靈活搞建筑,兩口子小日子過得紅紅火火、甜甜蜜蜜。
兩年后張健也結婚了,妻子是銀行職員,兩人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五年后,張健被下派到一個區(qū)任財政局局長,仕途走得風生水起。高飛讀完碩士讀博士,博士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并評上副教授,學術成果在經濟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但他始終沒有結婚。我因為教學成績突出,被評為省級物理學科教學帶頭人,校長找我談話,準備提我當學校主管教學副校長,我不愿意離開三尺講臺,就堅決地拒絕了。
安寧對我不當副校長很有看法,她勸我:“老師,副校長占有的資源是你當組長比不了的,比如你要是當上副校長,想評特級教師就容易多了。”我清楚她的心思,我要是當上副校長,她就能順理成章當上物理組組長。為實現她的愿望,她把張健搬了出來,張健特意單獨請我喝酒,酒至半酣,他問:“老師,有什么關口不好過嗎?要是有,讓學生替老師擺平好了。”“沒有,我就是不想干。”“老師,能有機會替老師出頭,是學生的幸運,你千萬不要怕給學生添麻煩,我向老師保證,絕對小事一樁。”“老師領情了,就是真心不想干。”“老師,我知道你向來淡泊名利,可你要是當副校長,上哪兒辦事肯定會方便得多,你不為自己考慮,也要為家里人考慮才是。”張健最后這幾句話讓我動心,我其實沒那么迂腐,我明白一個老師的社會地位,遠不能和副校長相比,可人生有一得必有一失,當老師我可以活得云淡風輕,當副校長卻不能意氣用事,很多時候甚至得委曲求全,而我天生不是愿意接受拘束的人。于是我說:“還是讓給那些有志向的人大展宏圖吧,我覺得當老師就挺知足的。”張健看我說得斬釘截鐵,只好作罷了。
三個學生中,張健發(fā)展得最好,能量更是大得無邊無際。那年安寧評高級教師,學校只有兩個名額,安寧排名第三,她找張健幫忙,張健雖然在另一個區(qū)工作,卻硬是從區(qū)教育局多給安寧爭取了一個名額。學校的規(guī)矩是,高級教師開支有名額限制,安寧排名靠后,盡管評上了高級教師,卻只能掙一級教師的工資,這事難不倒張健,他給區(qū)財政局局長打了一個電話,問題便迎刃而解了,連帶著排名在安寧前面的一個老師也跟著沾了光。
日子如流水一般,10年就這樣波瀾不驚地過去了。
那天下午,寧遠給我發(fā)短信,說請我喝茶,又叮囑說千萬不要讓安寧知道。合上手機,我想寧遠搞什么名堂,喝茶弄得像特務接頭似的。待到見面時,寧遠卻說出了一個超出我想象力的事:安寧出軌了,對方竟然是張健!
剛會面時,我就發(fā)現寧遠不對勁,他頭發(fā)蓬亂,臉腮瘦削,胡子拉碴,我原以為他是生意太忙累的,卻沒想到受到了如此重創(chuàng)。努力收斂起凌亂的思緒,我問:“這事不好瞎說,你能確定嗎?”寧遠埋下頭,沉默了一會兒,說:“安寧承認了。”“安寧承認也不見得是真的,這種事……”我想說這種事如果不抓現形,就不能確定,可當事人是我的學生,我說不出口。寧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他苦笑一聲,說:“老師,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他并沒有說具體細節(jié),可憐的寧遠,他到現在還想維護安寧。
我不知道該怎樣安慰寧遠。頓了一會兒,他艱難地抬起頭,說:“老師,安寧想離婚,可孩子還小,我不想孩子這么小就父母分離,你是我倆結婚時的證婚人,我想求你幫我勸勸安寧,只要她回頭,我就當什么事都沒發(fā)生。”我知道寧遠如果不是走投無路,斷然不會來找我,男人誰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戴綠帽子呢?但“清官難斷家務事”,何況又是出軌,叫我這個當老師的怎么啟齒,但是看寧遠傷心欲絕的神情和滿懷期待的眼光,我不忍心當場拒絕,只好含含糊糊說:“讓我試試看。”
寧遠走后,我把高飛喊過來,問安寧和張健到底怎么回事。張健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是在高飛的學校讀的,這些年兩人好得像一個人。高飛說:“老師,自從寧遠的工廠破產后,安寧和寧遠一直打冷戰(zhàn)。”“為什么?就因為寧遠沒有以前那么風光了?”“也不全是,主要是寧遠不服氣,今天想干這,明天想干那,錢折騰出去不少,事卻一個沒干成,安寧為此身心俱疲,兩人為此經常吵架。”“那也不能成為出軌的理由啊?”“老師,對夫妻來說,家如果不能成為愛情的港灣,就會在外面尋找感情寄托,這再正常不過了,何況這些年來,張健幫了安寧不少忙。”“舉幾個例子聽聽。”“例子可多了,別的不說,就說寧遠干建筑工程,活兒干了錢要不回來,安寧就去找張健,張健是財政局長,寧遠跑斷腿也辦不了的事,張健一個電話就解決了。”“你是說安寧找張健幫忙,寧遠一直蒙在鼓里?”“這事安寧敢告訴寧遠嗎?站在寧遠的立場,他寧肯錢要不回來,也不會去求張健幫忙。”
聽高飛的話,基本就還原了事情的過程。“高飛,你實事求是跟老師說,這么多年過去了,你是不是還對安寧不死心?”問得特別殘忍,我知道安寧出軌張鍵,高飛的難受程度并不會比寧遠差,可我不能不問,因為如果繼續(xù)放任他在感情問題上走死胡同,那受到的傷害會更大。“也是也不是。”高飛說:“我之前確實對安寧存有幻想,可是我現在想明白了,我喜歡的是昨天的安寧,或者說,與其說我喜歡安寧,倒不如說我喜歡我們純情的青春,可我知道青春回不去了,就像我們的年齡回不去了一樣。”
高飛說得很理智,我放心了。“那你知不知道,張健下一步怎么打算?”“張健不想離婚,可他妻子知道了,他擔心婚姻維持不下去。安寧倒是態(tài)度明確,說和寧遠過不下去了,堅決離婚,她的想法好理解,因為她不想一輩子在寧遠面前抬不起頭。”
我一直沒找安寧談,不是不想談,就是覺得實在沒法談。寧遠也沒有再來找我。大約三個月后,我和安寧一起準備物理試驗,安寧失手把試管打碎了,她瞅著滿地的玻璃碎片,失神了好一會兒,問:“老師,你說玻璃碎了能復原嗎?”她問得很鎮(zhèn)定。我說:“碎了就碎了,想恢復原樣沒有可能,與其這樣,還不如換一只新的。”她沉思了一會兒,說:“我想也是這樣。”
半年后,安寧和張健走到了一起。
光陰似箭,一晃又一個10年過去了。此間發(fā)生了如下變化:我如愿以償評上了特級教師;高飛評上了正教授,并被提拔為經管學院院長,其間他閃電結婚又閃電離婚,我問他離婚的原因,他說他的情感被安寧掏空了,除了安寧,他對別人失去愛的能力了;張健先后被提拔為市財政局副局長、局長,成了本市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校長知道張健是我的學生,讓我?guī)椭鷮W校和財政要錢,我推脫說張健是安寧的丈夫,這事找安寧辦才合適,校長說找過安寧,她說張健家教很嚴,絕不允許家屬參與政務。校長連續(xù)找了我?guī)状危覍嵲诓缓镁芙^,就委婉地向張健轉達了校長的意思,張健回答說老師正常事正常辦即可,沒有必要這樣拐彎抹角。后來學校的圖書館、體育館都被推倒重建了,學生教室和老師辦公室也煥然一新,老師們私下議論,說學校能有今天的變化,全是借了安寧的光,安寧聽了鄭重其事地解釋:“不是你們說的那樣,是咱們校長力度大,我只是在家稍微吹了一點小風而已。”
安寧借助高飛的人脈,在教育系統(tǒng)雜志發(fā)表了幾篇很有分量的論文,因此積攢了一定名望,她先到一所高中任副校長,兩年后,又回到我們這所學校任黨委書記,也就是說,她成為我的領導了。一次在公開場合,我喊她安書記,她聽后臉色大變,她找機會把我喊到辦公室,生氣地說:“老師,你這是打學生臉呢,從今往后你必須喊我名字,你要是再喊我書記,我就沒法在學校待下去了。”她說得情真意切,我照辦了。
變化最大的當屬寧遠,經過幾年艱苦卓絕地打拼,他坐上了市內房地產業(yè)頭把交椅,頭上頂著市工商聯(lián)主席、省勞動模范、某大學客座教授等諸多光環(huán),在本市政商兩界左右逢源,揮灑自如。寧遠是本市有名的鉆石王老五,關于他沒有再婚的原因,一直是各界人士津津樂道的八卦話題,有人說他為情所傷,有人說他心有所屬,有人說他風流成性,有人說他看破紅塵,傳聞真真假假,莫衷一是。因為孩子,他和安寧一直保持聯(lián)系,兩人還多次請我吃過飯,讓我不由感嘆,如今的世道,真是讓人看不懂了。
和同齡人相比,張健算得上平步青云。財政局在市直部門中舉足輕重,按照勢頭,他再上一步指日可待。然而高處不勝寒,就在張健仕途走得順風順水的時候,危機毫無征兆地來了。那天在市財政系統(tǒng)反腐敗工作會議上,他正慷慨激昂地講話,紀委的人進來把他帶走了。過程太戲劇化了,以致傳聞滿天飛,領導干部因為貪腐被抓,總能刺中吃瓜群眾的興奮點,以至由此掀起的風波,遮蔽了事件本身蘊含的意義。
聽說張健出事了,我第一時間喊來高飛,問他到底什么情況,高飛說:“具體情況不清楚,但聽財政系統(tǒng)的人說好像不樂觀。”“你知道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事了嗎?”“這個倒是知道一些。”高飛告訴我,財政的錢存哪家銀行是有說道的,一家銀行出現內訌,連帶著把張健供了出來。我不曉得其中的奧秒,問:“如果單這一件事,問題應該不會太大吧?”高飛擰緊眉頭,說:“老師,我是研究經濟的,對銀行內部的貓兒膩清楚得很,老師我和你說,單單存款回扣這件事就絕對過不去,現在的關鍵是,張健不見得知道為什么事留置他,他當了那么多年財政一把手,每年經手的資金過百億,常在河邊走,還能不濕鞋?要是他胡咧咧出別的事,那肯定萬劫不復了。”
看來張健遭遇人生滑鐵盧了。我說:“張鍵就是升得太快了。”高飛說:“老師說得對,這幾年他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所以特別膨脹,什么黨紀國法,早就被他拋在腦后了。”我說:“張健出事,安寧肯定很難受。”高飛沉默了一會兒,說:“老師,說出來你不相信,安寧和張健已離婚3年多了。”我聽了大吃一驚,“半月前我們兩家還聚過一次,我看他倆夫唱妻隨、恩恩愛愛的,你說離婚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一方面張健可能嗅到了風險,他想保護安寧,另一方面張健在外面到處拈花惹草,安寧管不了也不想管,你別看兩人住在一起,其實早就分居了。”“安寧跟你說的?”我警惕地問。“是的,她有時心里苦悶,就找我倒倒苦水。”高飛抬頭瞅我一眼,說:“老師你不要想多了,我們倆之間沒有別的事。”
半月后,張健轉為刑拘。安寧盡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妝容和衣著打扮依然一絲不茍,若非仔細觀察,看不出她眉宇間緊鎖的哀愁。多年的養(yǎng)尊處優(yōu)加上精心保養(yǎng),歲月的刻刀并未在她身上留下明顯的雕琢痕跡,相反卻散發(fā)著一種中年女人特有的風韻。在學校師生眼中,她總是那么精明強干,那么端莊嫵媚,那么威嚴大氣,不管她在哪里出現,周身總是籠罩著一道尊貴的氣場。我問她打算怎么辦,她說自從張健出事,關系網立刻土崩瓦解,現在誰都怕和張健沾上關系,除了寧遠,她找不到可以依賴的人。
“你說寧遠?”我懷疑自己耳朵聽錯了——寧遠會有那么大度?當年可是張健搶了他的女人,按照常理,他不落井下石就謝天謝地了。
“不錯,只有寧遠可以依賴。”安寧遲疑著說,“寧遠起家的時候,張健幫過很多忙,4年前,張健還在幕后支持他開發(fā)過一個地產項目,所以說張健出事了,寧遠不能不管。”
“你和寧遠說過嗎?”我仍然感到匪夷所思。
“說過了,寧遠也答應了。”安寧眼神里現出了少有的茫然和虛空,“盡人事看天命吧。”
半年后,張健鋃鐺入獄。我探望過張健一次,他跟我檢討:“老師,我想得到的太多了,結果連手中現有的也失去了。我對不起兒子,讓他小小年紀就蒙受屈辱,更對不起父母,沒能給他們一個幸福的晚年。”奇怪的是,他并沒有說對不起安寧。
兩杯酒下去,我和高飛都有些醉意了。我問:“你一直對安寧念念不忘,告訴老師,這些年來總共和她表白過幾次?”
“總共四次,大二時一次,她說暫時不想交男朋友;和寧遠鬧冷戰(zhàn)時一次,她說不想離婚,誰知后來她和張健走到了一起;和張健離婚后一次,她說怕影響張健前途,不能和他分開;張健入獄后一次,她哭著說配不上我,如果有來生,一定會選擇和我在一起。老師,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備胎呢,可現在看來,我什么都不是。”
“和寧遠復婚,她又是怎么說的?”
“她說反正已經丟臉了,就把臉丟到底吧,好歹孩子結婚時身邊父母雙全。老師,我現在要地位有地位,要名望有名望,錢雖然沒有寧遠多,可也足夠花了,我不明白,為什么安寧總不給我機會呢?”
我沒法回答他。感情的問題誰能說得清楚呢?就像眼前的高飛,一個著名的經濟學家,能把復雜的經濟學現象闡釋得條分縷析、入木三分,可在處理起個人感情問題時卻弄得一塌糊涂。憑窗遠眺,夜幕已經沉下來了,街道上車水馬龍,遠處高樓林立,各種燈五光十色,輝映著一個撲朔迷離的世界。
我回身,舉起酒杯,說:“忘記過去吧,讓我們?yōu)橥赂杀 ?/p>
高飛舉起酒杯,說:“我聽老師的,為往事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