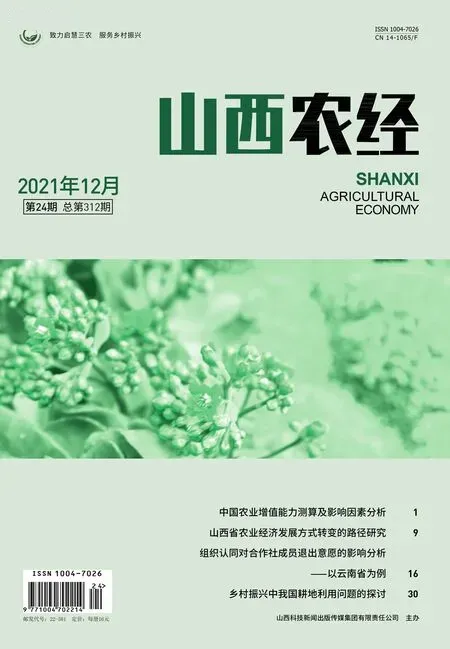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中新鄉賢主體類型和功能實踐實證研究
——以云南省P 市M縣L村和Y村為個案
□段妍智
(玉溪師范學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實現需要各類人才的參與,然而目前云南邊疆民族地區農村出現了“空心化”、人才流失等現象。
新鄉賢是推動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重要人才之一。探討該地區新鄉賢群體的類型、特質及其功能實踐,具有特殊意義。結合在云南省P 市M縣L 村和Y 村的調研實踐,對該地區新鄉賢的類型及其在鄉村振興中價值和作用進行實證研究,以助推當地鄉村振興實踐。
1 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中新鄉賢的內涵及主體類型
一般而言,在新時代背景下,有資產、有知識、有道德、有情懷,能影響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態并愿意為之作出貢獻的賢能人士[1],都可稱作新鄉賢。具體而言,新鄉賢應具備4 個基本要素。
一是場域要素。在鄉性即生活在農村,是新鄉賢重要的身份要素。其中,駐村干部和大學生村官屬于新鄉賢主體范圍,而短期居住于農村的外聘專業顧問等不屬于新鄉賢。
二是品德要素。新鄉賢應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弘揚者和踐行者,能夠以自身的嘉言懿行垂范鄉里,涵育文明鄉風,助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扎根鄉村[2],同時愿意為鄉村振興作出貢獻。
三是才能要素。新鄉賢大多事業有成,或有資本,或善管理,或懂市場,或有一技之能,或有豐富的知識。新鄉賢既包括扎根于鄉土社會文化德行高尚、對鄉村公共事務有所貢獻的本土鄉賢,也包括反哺家鄉且具有奉獻精神的離土鄉賢[3]。
四是聲望要素。新鄉賢不僅要得到村民的認可,同時要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新時代下,新鄉賢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引領者,不是“新鄉霸”或資本代理人。
根據新鄉賢是否在場、是否具有較高的身份地位,可以將其分為以下幾個類型:在場精英新鄉賢,如返鄉的富人、企業家、退休公職干部等;不在場精英新鄉賢,如在外富人及企業家、當官居城人士、專家、教授、學者、文化名人及媒體人等;在場平民新鄉賢,如身邊好人、道德楷模、老黨員及積極分子、退休教師、退休村組干部、家庭領袖等;不在場平民新鄉賢,如外出務工優秀的青壯年等[4]。
新鄉賢具有地域性、先進性、內生性和非正式的特點[5],主要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依靠自身道德、文化、技能、資源等綜合能力而獲得村民的信任與地方政府的認可。面對云南邊疆民族地區農村“空心化”的現實而言,新鄉賢來源主體應為居住在鄉村的“賢能型”人才或復合型精英。因此,云南邊疆民族地區新鄉賢主體應界定為生活在農村的賢達之士,既包括非體制內的生長并生活于農村的鄉村能人、道德模范、返場投資富人、企業家等,也包括體制內的駐村干部、大學生村官等。
2 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中新鄉賢主體類型的功能實踐分析
結合實際,對于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中的新鄉賢,以“是否與鄉村有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是否是精英”作為劃分標準,將新鄉賢在場主體劃分為“內生型”精英新鄉賢、“內生型”平民新鄉賢、“嵌入型”精英新鄉賢、“嵌入型”新鄉賢平民4 種類型,如圖1所示,并對新鄉賢主體類型的角色認定和效能進行深入分析。
不同類型新鄉賢的角色認定、參與路徑、功能實踐是不同的,助力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方式和效能也是不同的。因此在探討新鄉賢助力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時,不僅要認清不同新鄉賢的作用和價值,還要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剖析該地區新鄉賢群體的類型,類別化、針對性地探索新鄉賢助力鄉村振興的作用和參與路徑。
2.1 “內生型”新鄉賢的功能實踐
這一類新鄉賢是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基礎的關系網絡中內生的新鄉賢,主要包括鄉村致富能人、“土著”村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老黨員、“返場”(即返鄉并在場)能人(如退休公職干部、退休教師、退休村干部)等。這類新鄉賢主體與鄉村有著深厚的情感聯結,有著濃厚的鄉親觀念、故土觀念、鄉愁情結,多是自發助力鄉村振興。其中,鄉村致富能人、“返場”退休公職干部、道德模范屬于內嵌型精英新鄉賢;身邊好人、“返場”退休教師、“返場”退休村干部、老黨員、“土著”村干部屬于內生型平民新鄉賢。
具體來看,在鄉的鄉村種養殖大戶、合作社負責人等新鄉賢,可以通過技術培訓、經驗分享、項目承包等,助力鄉村經濟發展、產業振興。在鄉的在職村干部、退休公職干部、退休教師、退休村干部和民族文化傳承人等新鄉賢,具有較強的號召力,是推動鄉村組織振興的重要力量。道德模范、身邊好人、民族文化傳承人、老黨員等德賢,可以涵養文明家風、淳樸民風、和諧鄉風、傳承傳統技藝、傳承創新民族傳統文化,助力鄉村文化振興。“返場”退休公職干部、“返場”退休教師、“返場”退休村干部等新鄉賢,有著濃厚的鄉愁情結和故土觀念,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具備的政治、知識、品德的作用,為家鄉建設貢獻力量。
鄉村致富能人、“土著”村干部、民族文化傳承人、道德模范、身邊好人、老黨員等,他們的生產生活主要在鄉村內部開展,鄉村的發展直接關系他們的生產、生活。因此,他們有較強的動機參與鄉村振興,對實現鄉村振興有著強烈的愿望。“返場”退休公職干部、“返場”退休教師、“返場”退休村干部有濃厚的鄉愁情結,愿意為鄉村發展出謀劃策,但由于年齡和身體原因,精力有限。
2.2 “嵌入型”新鄉賢的功能實踐
這一類新鄉賢與鄉村、村民沒有血緣、親緣和地緣的情感聯系,大多是行政介入或者其他因素“下鄉”的嵌入型人才,主要包括市場-盈利導向的投資者、駐村干部、大學生村官等。
市場-盈利導向的投資者屬于“嵌入型”精英新鄉賢,他們以資本下鄉的趨利性嵌入到鄉村振興中,通過項目投資等推動鄉村產業振興。這一類新鄉賢只有當鄉村具有足夠經濟條件和吸引力的情況下才會涌現,常出現在經濟資源優越、民族傳統文化資源豐富的地區。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無論是經濟資源還是文化資源都比較匱乏,“嵌入型”精英新鄉賢比較稀缺。
駐村干部、大學生村官屬于“嵌入型”平民新鄉賢,他們多源于工作需要或政治訴求,以行政介入方式嵌入到鄉村振興中[6],通過理論知識、組織協調溝通能力等,與“土著”村干部一起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出策出力。他們個人雖然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資源,但可以全身心投入鄉村治理和生態文明中。更關鍵的作用在于他們可以通過動員群眾的方式,切實解決鄉村振興中產生的實際困難。
3 實證考察云南省P 市M 縣L 村和Y 村新鄉賢的主體類型及功能實踐
2021 年1 月深入云南省P 市M 縣L 村和Y 村進行實地調研和訪談,為探討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振興中新鄉賢的類型界定和功能實踐提供一手資料。
L 村位于縣城東南部,在縣城與鎮政府駐地之間,距縣城17 km,距鎮政府駐地12 km,全村國土面積28.83 km2,為哈尼族和漢族雜居。該村新鄉賢主體類型和效能情況見表1。

表1 L村新鄉賢主體類型和效能情況
Y 村地處縣城北部,距離鎮政府所在地40 km,全村國土面積23.59 km2,有15 個村民小組,常住人口為1 426 人。該村新鄉賢主體類型和效能情況見表2。

表2 Y村新鄉賢主體類型和效能情況
L 村和Y 村兩個村雖然都有規模養殖的種植養殖大戶,但規模不大,并不能形成產業規模、帶動鄉村產業發展,更不能帶動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種植養殖大戶在助力L 村和Y 村鄉村振興過程中主要是分享種植養殖經驗和技術,因而屬于內生型平民新鄉賢。L 村引進1 家蔬菜訂單農業公司,種植辣椒(野山椒)科技示范地1.33 hm2,帶動群眾發展辣椒(野山椒)產業10.67 hm2,但種植規模不大、產業基礎設施薄弱、產業發展層次偏低。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目前L 村和Y 村的新鄉賢主體類型主要是平民型新鄉賢,主要效能是分享種植、養殖經驗和技術,參與鄉村治理,弘揚傳統美德,培育文明鄉風,樹立良好家風。可見,云南省P 市M 縣L村和Y 村新鄉賢主體類型比較單一、功能實踐有限。
4 結論和建議
云南邊疆民族地區鄉村也存在區域差異性。經濟、交通和民族傳統文化資源較為豐富的鄉村能夠吸引各種類型的新鄉賢,因此新鄉賢主體類型多樣化。例如特色小鎮旅游景區、普洱茶產區等,既可以吸引嵌入型精英新鄉賢,如投資企業家、富人等,也有內生型精英新鄉賢,如鄉村致富產業戶、民族文化傳承工作室等。這些地區引導新鄉賢助力鄉村振興,應圍繞“新鄉賢怎么用”展開。需要構建各類型新鄉賢合力機制,共同推動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組織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全面發展,同時要注意對新鄉賢進行制約和監督,依法助力鄉村振興。
經濟、交通和民族文化資源匱乏地區的鄉村,缺乏吸引新鄉賢的資源和物質基礎,新鄉賢主體類型比較單一。這些地區對人才和人力資源的需求更加迫切,可以吸納一些“內生型”平民新鄉賢助力鄉村振興。通過對鄉賢文化的挖掘、宣傳,將新鄉賢組織化,為新鄉賢助力鄉村振興提供制度、場所等條件,激活“內生型”平民新鄉賢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