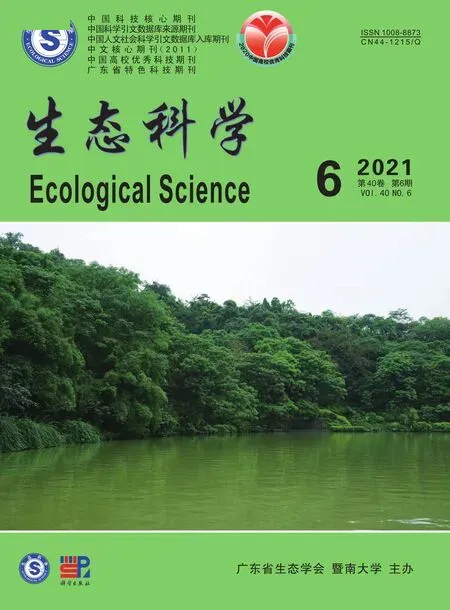基于土壤生物工程的小流域侵蝕溝治理研究進展
冷瑜, 曹麗娜, 張振興, , *, 孫偉, 楊海軍, 林晨鷺, 高玉福
基于土壤生物工程的小流域侵蝕溝治理研究進展
冷瑜1, 曹麗娜2, 張振興1, 2, *, 孫偉1, 楊海軍3, 林晨鷺1, 高玉福1
1. 東北師范大學植被生態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長春 130024 2. 東北師范大學國家環境保護濕地生態與植被恢復重點實驗室, 長春 130024 3. 云南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 昆明 650000
水土保持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國家重點資助應用基礎研究, 是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治理理念的經濟發展領域。當前我國水土流失問題依然嚴峻, 仍有超過國土四分之一水土流失面積, 且分布廣、治理難度大, 給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 亟待加快推進小流域侵蝕溝治理。基于土壤生物工程技術的小流域侵蝕溝治理已受到國內外學者高度關注, 國內相關研究理論儲備較充分, 但理論結合實踐方面距世界先進水平仍有較大差距。為進一步推動該技術在我國的應用和發展, 文章綜述了土壤生物工程的需求背景、概念和發展; 其次, 從生態視角梳理其地上-地下生態功能, 論述其優缺點, 探討影響工程建設與實施的主要因素; 最后, 做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土壤生物工程研究展望。結果表明土壤生物工程技術不僅是高效的小流域侵蝕溝生態治理方法, 還兼具經濟與景觀功效。建議在系統開展基于土壤生物工程技術的小流域侵蝕溝治理的同時, 進一步加強其理論和技術研究, 以期提供更完善的理論支撐和因地制宜的技術方法, 進而為科學推進我國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工作奠定堅實基礎。
侵蝕溝; 水土流失; 生態修復; 土壤生物工程
0 前言
減少土壤侵蝕是世界范圍不同國家學者和組織所共同面臨的環境挑戰和科學熱點難題[1]。眾所周知, 土壤侵蝕是指外營力(水力、風力、凍融、重力等)對土壤及其母質破壞、剝蝕、搬運和沉積[2]。根據外營力源的不同, 將土壤侵蝕類型劃分為水力侵蝕、風力侵蝕和凍融侵蝕。其中水力侵蝕最為常見, 也是小流域水土流失的主因[3]。現階段, 小流域侵蝕溝的水土流失約占總侵蝕土地面積的55%[4], 因此侵蝕溝的治理至關重要。據西班牙科爾多瓦大學的Castillo在2016年Earth Science Review文章中所述, 近一百多年來, 具有應用推廣價值的侵蝕溝治理研究只占侵蝕溝總研究的4.2%[5], 這表明侵蝕溝治理雖長期位列科學研究熱點榜單, 但實踐研究在量上的缺失, 進一步加劇了有效的治理方案難以在實踐層面有所突破。自上個世紀中葉產生生態危機, 進入新世紀以來, 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尤為理性, 更加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并對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價值有了新的認知和理論發展。土壤生物工程不僅有效結合系統生態學原理, 融合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6], 修復退化土地, 提高土壤、空氣和水的質量[7-8], 控制水土流失減少災害[9], 還在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上具有多樣性和適宜性, 兼具經濟與景觀效益, 對人類日益減少的土地資源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 近年來土壤生物工程治理侵蝕溝的研究逐漸受到更多關注, 并有望成為侵蝕溝治理的重要技術。
本研究綜述了土壤生物工程技術的概念與發展, 從生態環境角度分析其地上與地下部分的功能作用, 將其與傳統侵蝕溝的治理工作方式相比較, 總結土壤生物工程治理侵蝕溝的優缺點, 指出植物與工程兩部分相輔相成的重要性, 最后根據我國土壤生物工程的研究現狀指出當前研究的不足之處, 從生態修復的角度提出科學合理的建議, 以期為今后侵蝕溝治理提供可借鑒的理論參考和技術支撐。
1 概念、發展概述
土壤生物工程(soil bioengineering)概念的雛形、變化和發展, 歷經波折。從中國古代黃河流域的治水到歐洲羅馬時期水利工程, 再到歐洲工業文明興起及近代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重塑, 土壤生物工程經歷了從雛形階段、發展階段、確立階段到興起階段, 并最終伴隨人類社會發展日趨完善、逐步成熟。當前, 在充分借鑒國內外現有研究成果和科學共識的基礎上, 及基于作者多年實踐中的理解和感悟, 土壤生物工程概念可總結為, 土壤生物工程是一種以活體植物(或部分植物體)為主體、天然土石、人工鐵絲和混凝土等為輔助材料, 配以適宜的工程結構和參數, 一方面充分利用植物地下發達根系及其適應性生長特性, 固土保水、維持工程整體結構穩定、減少水土流失[10], 另一方面構建地上生態群落演替早期的植物先鋒種群。土壤生物工程可作用于邊坡、河岸、道路等區域, 是一系列以減少侵蝕和改善生境為目的生態工程技術集[11-13], 是真正意義的固土保水技術, 而非一般的植被綠化和恢復工程[14]。

注: 圖a, 經典土壤生物工程示意圖[15]; 圖b—f均加工自文獻[16], 其中, 圖a是侵蝕溝現狀; 圖b是生態修復前; 圖c是施工中; 圖d是剛竣工; 圖e是修復5個月后; 圖f是修復15個月后。
Figure 1 Sketch map of soil bioengineering
土壤生物工程主要發展階段論述如下(見表1): (1)雛形階段。幾千年前, 類似土壤生物工程的技術就已經出現。中國古代便有“榆、柳盤根最固, 取材最宜, 既可御水, 兼可衛堤, 實為河工要需”的相關記載[17]。公元前歐洲凱爾特和伊利里亞村民發展了將柳樹枝條編織在一起以創造柵欄和墻壁的技術, 同時羅馬人也將捆成束狀的柳樹枝用于水利工程[18-19]。(2)發展階段。工業革命時期, 歐洲國家生產力大發展, 但普遍缺乏生態環保意識, 面對山地、坡道、河道侵蝕問題, 片面地采用土壤生物工程施工材料, 通過植被和自然材料單一組合, 暫時延緩了侵蝕加劇。這一時期實踐研究在法語國家被稱為“山地恢復”(RTM), 在德語國家被稱為“山澗建筑”(WLB), 在意大利語國家被稱為“林地水力系統”(SIF)[20]。當時RTM-WLB-SIF的研究常被誤認為是土壤生物工程的發展, 然而RTM-WLB-SIF并沒有從環境和生態景觀的角度考慮, 僅僅是套用土壤生物工程方法, 忽視了土壤生物工程控制侵蝕、恢復生態、改善生境的核心思想。因此土壤生物工程在這一時期并沒有得到健全發展[21]。(3)確立階段。土壤生物工程技術的正式確立是在19世紀下半葉, 學界普遍認為是從V.Kruedener在1951年寫的一書開始。工業革命促使以硬質混凝土鋼筋為代表的傳統工程被過度使用, 歐洲的山區景觀坡道和河道區域出現大面積侵蝕最終, 對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破壞日趨嚴重, 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嚴重受損, 爆發不可逆的生態危機, 人們對于這種嚴重的侵蝕退化現象感到擔憂, 迫切需要新技術解決這類環境問題[21]。為此, 人們嘗試重新發掘將“活”的植物和“死”的工程材料結合起來的土壤生物工程技術, 并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在山坡、陡坡和河岸中使用, 實現力學穩定的同時最大程度降低對環境和景觀的負影響[22]。(4)興起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 土壤生物工程師開始傳播這種技術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土壤生物工程技術從歐洲傳至世界各地,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提倡使用基于自然手段的方法來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性, 并將土壤生物工程技術列為一種有效的防御自然災害的技術工法[23]。
雖然土壤生物工程在我國歷史悠久, 人們一直使用樹木、林秸、塊石捆扎穩定河岸[24], 但理論研究處于停滯狀態。近年, 國內學者在該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和啟發性探究, 相應研究成果為該領域的不斷發展提供了寶貴借鑒和參考。如夏繼紅和嚴忠民歸納生態型護岸為單純植物護岸和植物與工程結合護岸[18]。2006年, 李小平等論述了土壤生物工程在我國的發展潛力[25]。高甲榮等(甲榮集團)對土壤生物工程開展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施工技術、植物材料、植物生長、根系固土及環境影響), 為土壤生物工程在北方地區廣泛應用提供理論支撐和技術參考[26]。張振興等2006-2008年間, 在長春市郊修建了長2.4km的土壤生物工程護岸, 并對其修復效果和后期管理做了必要探討[27-28]。近些年, 湖北工業大學的劉瑛團隊在不同土壤生物工程技術固坡效果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 并極大推動該領域發展[29]。
2 生態功能
在生態角度看, 地上-地下兩部分是土壤生物工程的核心構件, 只有這兩部分的協同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其生態功能。目前, 較為常見的基于土壤生物工程的侵蝕溝治理方式是利用植被快速覆蓋土壤, 即: 將活的插條和活莖埋在土壤中作為加固材料, 并設置排水溝及阻礙泥土移動的工程措施。如在用植物和土木材料穩定加固侵蝕溝邊坡土壤、在侵蝕溝的溝頭設置防護林等防護措施改善上游的徑流條件等。在功能需求和解決方案方面, 土壤生物工程與傳統的恢復、修復和再生技術有相似之處[30], 但不同的是, 傳統治理措施都是對侵蝕溝地表和植被的治理恢復, 往往只將植物對水蝕控制的適宜性歸因于地上植被能夠降低侵蝕率的作用[31]。研究發現, 侵蝕溝的發育不僅與地表徑流有關, 還與地下徑流侵蝕密切相關, 而傳統治理措施往往忽略了地下根系的固土保水作用[32]。

表1 土壤生物工程發展史
2.1 地下—固土保水
國內外許多研究表明, 土壤生物工程的固土保水功能主要體現在降低土壤侵蝕速率、減小徑流能量、截留降雨、持續地發揮固土作用方面[33]。土壤生物工程的植物通過復雜的根系網絡結合土壤顆粒, 固定溝道邊坡土壤, 提高整體穩定性[7]; 在墨西哥馬德雷德爾蘇爾山脈侵蝕溝水土流失控制項目中, 研究人員用土壤生物工程抬高石壩, 設置侵蝕溝植物屏障, 最終該地區平均土壤侵蝕速率有效降低了38.7%[34]; 另有研究表明, 土壤生物工程對傳統河岸到高地過渡區的防護作用極為顯著, 可有效降低徑流能量、截留降雨, 防止徑流造成侵蝕破壞[35]; 最終土壤生物工程的固土保水效果還是依賴于植物選取和工程構建參數的搭配, Simon在埃塞俄比亞高原西北部半濕潤地區, 利用根系加固模型分析植物根系和土壤附加剪切阻力, 比較本土和外來植物根系固土效果, 量化保水能力, 結果表明不同種植物根系對侵蝕控制具有較大差異性[36]。此外, 土壤生物工程能夠實現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35], 其地下根系形成了低速和低剪切阻力帶, 在抵抗侵蝕時, 根系的生長往往會隨侵蝕的發生而進行移動, 一旦被徑流沖斷或被連根拔起沖刷至下游地區, 它們也能從新的土壤基質中吸收養分, 持續生長以達到固持水土的目的[37]。
2.2 地上—構建生境
土壤生物工程除了地下根系所具有的強大生態-力學固土功能之外, 地上植株和土木工程結構復合體所起到的固土保水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地上生境的構建為溝道提供了一定的粗糙度從而形成侵蝕緩沖帶, 可以有效降低徑流流速并攔截沉積物, 從生態功能的角度上改善土壤地質條件、凈化水質, 并為昆蟲、兩棲類和鳥類等小型哺乳動物提供優質棲息地。在地上生境的構建方面, 優選本土植物種是國際共識的植株選用原則, 本土植物種相對容易獲得, 并且在長期的競爭中適應了當地的氣候和土壤條件并具有一定的水生和陸地生境價值; 在地上工程結構的建立方面, 土木工程材料均為當地能夠收集到的材料, 通過人工運輸可以便捷高效地移至項目地。
據多年監測表明, 土壤生物工程具有較高的初始強度, 隨著植被的建立生長以及時間的推移, 土壤生物工程的強度會不斷增強。從科學角度分析, 土壤生物工程的技術優勢在于依靠前期土木工程穩固地上地下的土壤, 優先保證先鋒植物能夠得以迅速生長, 隨著植被演替, 土木結構逐漸腐爛、喪失其工程力學功能之后, 植株最終依靠其強大的地下根系和地上生物量實現生態系統的恢復[38]。地上植被(莖, 枝和葉)能夠增加流動阻力, 降低局部流速, 將動能耗損在發生形變的植物上[8], 侵蝕溝中生長的植被與土壤生物工程措施相互作用, 有利于其他植物的定殖和演替, 進而提升植被總體覆蓋率[39]。
當植物發育完整后, 根系會加固土壤, 并從土壤剖面去除多余的水分, 這也是土壤能夠長久穩定的關鍵, 并為工程區提供優質的景觀和適宜的棲息地[40]。即使植物死亡, 根和表面的枝干及有機廢物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為其它植物體的構建提供平臺。
3 較傳統措施的優缺點
傳統的侵蝕溝預防、治理的傳統措施主要分為(1)工程措施、(2)生物措施、和(3)農業措施。其概述如下: (1)工程措施方面, 通過各種尺寸和材料的工程結構來控制侵蝕溝是世界范圍內的一種普遍治理方式。首先侵蝕控制措施通常是直接建在溝道上或跨越侵蝕溝溝谷的大型土壩、大型石壩、石籠, 其次是建立在侵蝕溝外, 以防止水進入侵蝕溝溝道造成溝頭削減。而對于常見的溝頭侵蝕, 按照侵蝕溝流量大小以及地形條件需要采取不同的工程措施: 當溝頭流量較小時, 一般沿著溝邊修建土埂、石擋墻攔水, 形成攔蓄式建筑; 而當溝頭流量較大、徑流較為集中時, 在攔蓄式建筑的基礎上修建溝頭跌水或溝頭挑水建筑, 利用工程結構消減水流侵蝕能力[41]。(2)生物措施方面, 侵蝕溝治理的生物措施主要利用植物替代巖石、混凝土等工程結構材料, 通過這類柔性屏障控制徑流, 減少水土流失, 以達到穩定侵蝕溝的目的[42]。樹籬和草籬都是有效的篩網結構, 將樹枝木樁安置在溝坡溝底之中, 作為侵蝕溝的多孔植物水壩, 從而將徑流中的泥沙通過植物之間的天然孔隙過濾掉, 并且可以將一些植物栽植在木樁上, 使得他們可以發芽生長, 形成活的篩子, 在熱帶地區, 種植香根草作為篩網并且應用于水土保持的生物治理措施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43]。(3)農業措施方面, 治理侵蝕溝的農業措施主要依靠當地的土地管理制度。一般政府部門提倡在坡耕地采取深耕地、輪作、間作套作等耕作制度, 并配合深松犁耕以及農業機械共同作用, 而在其他類型的土地上則采用禁牧、圍欄封育等措施, 以此增加土壤抗蝕能力以及地表植物覆蓋度, 減少侵蝕溝徑流, 提高土地蓄水能力, 從而起到控制侵蝕溝發生發展的作用, 并且改善當地生態環境[44]。
由上述分析可知, 傳統措施都是針對侵蝕溝地表和植被的治理恢復, 忽視了地下生物量的作用。而土壤生物工程不同于傳統侵蝕溝治理措施, 它通過聯系地上地下的特殊性, 將工程結構與植被相結合, 在滿足恢復治理需求的前提下, 秉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竭力尋求景觀的美化以及生態系統的有序演替, 是解決侵蝕問題的新興方法。
該研究中選取2012年7月—2013年7月在該單位接受口腔種植骨結合治療的糖尿病患者與非糖尿病患者各50例,并對這些患者進行隨訪5年,對接受治療的兩組患者的牙齒成活情況進行分析比較,對所得的糖尿病患者與非糖尿病患者種植體修復牙齒的3個月、1年以及5年失敗率的數據進行對比,進行統計學計算得出,數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通過得出的數據結構發現糖尿病的種植體修復牙齒失敗率略高于非糖尿病患者,所以糖尿病是可以對種植體骨結合有所影響的。
3.1 可持續性和富有生命力
目前傳統上對于侵蝕溝的控制方法主要依賴于固體屏障的建立, 在受侵蝕區域搭建石墻、石籠, 注入混凝土以此形成剛性的屏障結構。雖然這一系列的措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捕獲沉積物并且抵消侵蝕運動, 但是長期暴露在野外環境之下, 環境因素嚴重影響了土木結構的穩定性, 降雨會將巖石沖刷至下游, 而徑流會導致混凝土的破裂, 承載土木結構的土壤隨時間的流逝逐漸瓦解直至坍塌, 所以通常情況下傳統措施多以失敗而告終[45]。
區別于傳統工程, 土壤生物工程的獨特之處在于它通過植物根系的生長賦予巖石、土塊以“生命”。Cavaille等研究發現根系的空間結構、抗拉強度、粘附特性可以有效地加固土壤[46], 垂直于土體表面的根系通過增加剪切強度加固土體, 而平行于土壤表面生長的根系則通過增加平面張力來加固土壤[47], 縱橫交錯的根系網絡作為聯結土壤、土木材料、巖石的紐帶, 給土壤生物工程提供了良好的初始強度, 在設立之初就能夠承受較強的雨水沖刷, 并且隨著植被的成長, 植物根系網絡更加發達, 土壤生物工程的強度隨著根系的生長逐漸增強, 即使栽植的植被不幸死亡, 殘留的植物根系和枝葉也會在重建過程中充當緩沖材料, 并作為營養成分的提供者繼續完成其固土保水的使命。

表2 侵蝕溝治理傳統措施
3.2 高生態效益/低環境破壞
土壤生物工程技術通常與其他系統結合, 并運用在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 尤其是在防治侵蝕和穩定邊坡與河岸時, 防護系統和生活系統結合起來的護坡系統是近自然治理措施的重點, 它往往比單獨處理植被或植被結構的解決方案更經濟有效, 而且這種結合有助于維持長期穩定, 減少對生物和環境沉積物的影響, 有利于該地區生態環境的優化, 并能創造多樣化的棲息地, 提供一種健全的管理方式。土壤生物工程提高了植物的保留率, 利用較少的投資成本建立、發展更多的植被, 明顯改善人類與動植物的生境, 為當地創造了和諧的生活環境[48]。在生態功能上, 土壤生物工程或減少或避免了侵蝕災害造成的損失, 提高生物棲息地的多樣性, 維持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和相對穩定。土壤生物工程運用恢復生態學原理, 基于群落構建的生態位理論與中性理論, 根據植被科學中的演替理論, 通過人工與天然相結合, 創建一系列植被恢復技術, 能夠在恢復當地生態功能、創造良好的景觀環境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創造經濟價值[49]。
3.3 后續養護要求低
通過建造各種尺寸和材料的土木工程結構控制侵蝕溝時幾乎不需要進行后續的工程養護, 但是這種單一的剛性措施初始成本極高, 并會對當地生態環境與生物結構造成一定的影響, 土木材料在外營力的侵蝕作用下最終需要更替重建。不同于土木工程結構, 土壤生物工程是一種柔性結構, 工程建立后植被通常能夠在一個生長期內通過再生演替和生長對侵蝕溝的土壤進行加固, 減少水土流失率, 后續養護要求低, 只需要重復監測和少量維護費用。為了確保能夠建立可持續、有生命力的工程, 土壤生物工程建立之前就需要進行仔細的檢查, 并且定期進行監控和維護, 主要包括清除碎屑物質, 清除侵入性或不良物種以及重新種植, 管理植被的生長、修剪, 防止蟲害和野生動物啃食以及人為破壞等。
3.4 局限
迄今為止, 植物根系對邊坡穩定性和土壤侵蝕控制的積極作用已得到廣泛的認可, 也提出了一些關于根系加固土壤的量化方法[50]。然而在土壤生物工程中, 具體哪些植物根系特征在這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對于根系結構在工程應用中的重要性尚不明確[51], 土壤生物工程的小流域侵蝕溝治理所產生的具體生態效益和工程效果研究較少, 量化評價結果尚不統一, 值得后續進一步深入研究。一般來說, 土壤生物工程措施不是有效解決小流域侵蝕溝治理問題的唯一方法, 它并不適用于所有的環境條件。首先, 土壤生物工程的植被建立易受限: (1)易受水分和氣候的影響的植物種無法順利生存和成長; (2)土壤養分和陽光的缺乏可能會影響營養成分的建立和生長; (3)植物可能會受到野生生物和人類的破壞。其次, 土壤生物工程受環境限制, 現實情況中理想的自然條件并不存在, 惡劣天氣難免會對土壤生物工程造成威脅, 因此土壤生物工程具有更高的失敗風險, 需要詳盡的調查以及風險地預估, 因地制宜設計考慮具體措施。最后, 土壤生物工程受勞動成本限制, 為確保工程兼具經濟與景觀價值, 工程設備一般要求盡可能減少與勞動者的接觸, 并且對作業區域產生較小的擾動, 土壤生物會工程在勞動密集型區域具有較高的成本效益, 但在勞動力稀缺區域產生過高的成本投入。
4 影響因素
4.1 植物的選取
植物是土壤生物工程的靈魂, 植被的地上部分通過截留降水、增加水分來減少水引起的侵蝕, 植物的地下根系增加土壤顆粒的分離難度, 阻滯水土流動, 使土壤保持穩定, 甚至能夠再增加土壤肥力[52]。正是由于土壤生物工程將植物作為聯系地上地下生境的特殊紐帶, 使其得以發揮強大的生態復合功能進而保護土壤免受侵蝕, 達到固土保水、重建生境的目的[53-54]。通常來講, 土壤生物工程小流域侵蝕溝治理的最佳備選植物是本土植物與臨近區域根系深且密的植物種, 因為這些植物種類已經適應了當地的生態環境, 種植成活率高, 取材便捷、易收集, 不會對原有生態系統造成過多的干擾。當條件適宜時, 草和灌木可以迅速發芽, 根系可以形成較好的初期分布, 并且種植成活率較高, 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減少退化土壤上的水流侵蝕[51]。為實現土壤生物工程的可持續治理目標, 減少維護成本, 永續地提高土壤肥力, 可以選擇如二月蘭、沙棘、紫花苜蓿等與細菌和真菌共生的固氮植物[55], 在關注生態環境效益、維護生態系統動態平衡的同時力求治理區域的相對穩定。
4.2 植物的生長和維護
無論選擇何種植物, 優先考慮限制植物生長的首要元素——水的可利用性, 水量和季節性供應對于植物的生存周期和分布范圍有著深遠影響, 良好的水分條件是土壤生物工程植物建立的關鍵[56-57]。Clewell和Aronson研究指出[58], 土壤生物工程項目前期以及完成后的監管尤為重要, 良好的維護可以確保營養成分的建立和生長, 例如在氣候干燥降水稀少的地區需要輔以人工灌溉; 而在受生物災害嚴重的情況下, 還需要適當使用滅蟲劑并且驅趕野生動物; 在極端天氣造成大面積破壞后, 需要人工及時補種植物以防止營養成分的流失, 定期篩查土壤生物工程項目的實施對諸如此類的意外情況做出及時補救。
4.3 國內土壤生物工程的設計與選擇
目前, 我國關于土壤生物工程在侵蝕溝侵蝕治理中的應用起步較晚、研究較少, 而且我國土地幅員遼闊, 氣候、地貌、水文、土壤等條件特殊, 很難在土壤生物工程應用中形成統一的設計標準, 需要因地制宜地根據現場生態環境條件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 逐步探索實踐[56]。近年來我國學者在原有工程措施之上結合了土壤生物工程的治理研究, 進行了一系列土壤生物工程設計施工的探索嘗試: 劉瑛首次將土壤生物工程技術使用到北京地區河岸生態系統的修復之中, 通過植物適宜性、根系特征、固土機理以及植物枝條柔韌性這些方面評價其環境效益, 比較分析了扦插、梢捆、灌叢墊、籬墻以及埋根等不同土壤生物工程施工方式的適合度[59]; 李小平等評估了我國首個采用土壤生物工程修復河道坡岸的上海浦東新區機場河道工程, 從植物根系加固穩定作用與棲息地改善情況兩個方面評價了工程的設計與完成效果[56]; 高甲榮等針對北京市河流生態系統的岸坡侵蝕問題, 為穩固坡岸采用了不同土壤生物工程措施, 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受侵蝕區域的抗侵蝕問題, 并且從不同方面改善了河岸地生態環境[60];王芳等研究柳溝小流域灌木根系形態以及可塑性, 為西北黃土高原的土壤生物工程的設計施工提供了理論基礎[53]; 陳瓊等分析了烏海市公路邊坡工程的保水能力、植物生長情況與水土保持能力, 利用土壤生物工程技術, 根據公路邊坡的特殊情況, 選用將護坡植物與現澆網格生態護坡技術相結合的措施, 解決了目前我國護坡工程生態效果不佳的問題[61]。
由此可見, 相比于傳統侵蝕治理方式, 土壤生物工程尤為關注生態環境效益, 在維護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的同時力求治理區域的相對穩定, 土壤生物工程需要根據不同的侵蝕狀況和現場條件, 針對水流沖刷強度、邊坡穩定性程度、泥沙輸移堆積狀況選擇具有適宜的設計方案[62]。
5 展望
綜上所述, 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 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背景之下, 土壤侵蝕災害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水土流失問題, 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侵蝕溝的發生發展破壞了土地資源, 影響社會經濟發展, 導致生態環境惡化, 因此侵蝕溝的修復治理問題迫在眉睫, 而土壤生物工程具有科學治理侵蝕溝的潛力, 是解決土壤侵蝕問題的有效方式。目前基于土壤生物工程技術的小流域侵蝕溝治理受到了國內外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雖然國內相關理論研究儲備較為充分, 但是國內研究多集中于侵蝕溝發生發展及其分類方面, 對于侵蝕溝的預防以及修復治理的相關研究較少, 理論結合實踐方面距世界先進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土壤生物工程的相關研究亟待開展, 為進一步推動該技術在我國的應用和發展, 未來更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索研究:
(1)首先缺少對于侵蝕溝治理研究的完善資料體系, 應建立一個侵蝕溝的研究網, 以評估大尺度范圍的溝侵蝕狀況, 選定并長期監測作為基準地點的溝侵蝕情況;
(2)關于土壤生物工程使用植物材料進行治理時, 很少有人嘗試測量植物對控制侵蝕溝侵蝕的所有特性, 地下根系的固土力學和根系力學方面容易被忽視, 目前缺乏統一的標準來評估包括根在內的整個植物的侵蝕控制策略;
(3)目前有多種可用于治理侵蝕溝的土壤生物工程處理方法, 但這些方法用于應對處理的情況各不相同, 重要的是要了解治理背后的方法原理及其安裝方式, 以確保將合適的方法放置在適當的位置。在相關措施施工完畢后, 還存在監測管理和維護問題, 對于治理后的效果評價體系也尚不完整。
(4)最后, 需要呼吁管理人員和普通群眾提高關于侵蝕溝的生態問題, 提高對生態系統的保護意識, 普及土壤侵蝕危害的相關知識, 認識到水土流失的危害, 理解并積極配合相關治理措施的實施, 不破壞侵蝕溝治理工程材料。
[1] MONDAL A, KHARE D, KUNDU S, et 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future soil erosion in different slope, land use, and soil-type conditions in a part of the Narmada River Basin, India[J]. Journal of Hydrologic Engineering, 2015, 20(6): 1–12.
[2] 王禮先, 朱金兆. 水土保持學[M]. 北京: 中國林業出版社, 2005.
[3] 李志飛. 東北黑土區侵蝕溝發展現狀及研究方向[J]. 水土保持應用技術, 2014(5): 26–27.
[4] BRIDGES E M, OLDEMAN L R. Global assessment of human-induced soil degradation[J]. Arid Soil Research and Rehabilitation, 1999, 13(4): 319–325.
[5] CASTILLO C, GóMEZ J A. A century of gully erosion research: urgency, complexity and study approaches[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16, 160(9): 300–319.
[6] MITSCH W J. When will ecologists learn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s learn ecology? [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4, 65(4): 9–14.
[7] PRETTY J L, HARRISON S S C, Shepherd D J, et al. River rehabilitation and fish populations: assessing the benefit of instream structures[J].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03, 40(2): 251–265.
[8] WEBER C, WOOLSEY S, PETER A. A strategy to assess river restoration success[J]. Archives Des Sciences Journal, 2006, 59(2): 251–256.
[9] YAM P D, Tang Qiuhong. Soil bioengineering application for flood hazard minimization in the foothills of Siwaliks, Nepal[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5, 74(1): 458–462.
[10] MITSCH W J, JORGENSEN S E.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 field whose time has come[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03, 20(5): 363–377.
[11] SCHIECHTL H M. Bioengineering for land reclamation and conservation[M]. 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1980.
[12] TEREZINHA C D B G, ALOISIO R P, MARIA G P, et al.Bioengineering techniques associated with soil nailing applied to slope stabilization and erosion control[J]. Natural Hazards Review, 2010, 11(2): 43–48.
[13] STOKES A, SPANOS I, NORRIS J E, et al. Eco- and ground bio-engineering: the use of vegetation to improve slope stability[J]. Developments in Plant and Soil Sciences, 2007, 103(8): 1990–1993.
[14] EHRENFELD J G.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science and strategies for restoring the earth[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990, 1(1): 74–75.
[15] POLSTER D F. Soil bioengineering techniques for riparian restoration[C]//26th annual British Columbia mina reclamation symposium in Dawson Creek. British: BC TRCR, 2002: 230–239.
[16] MAFFRA C R B, SUTILI F J. The use of soil bioengineering to overcome erosion problems in a pipeline river crossing in South America[J]. Innovative Infrastructure Solutions, 2020, 5 (24): 1–8.
[17]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編校,再續行水金鑒[M]. 湖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18] 夏繼紅, 嚴忠民. 國內外城市河道生態型護岸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J]. 中國水土保持, 2004(3): 24–25.
[19] BISCHETTI G B, DIO D F M, FLORINETH F. On the origin of soil bioengineering[J]. Landscape Research, 2014, 39(5): 583–595.
[20] BISCHETTI G B, CHIARADIA E A, AGOSTINO V D, et al. Quantifying the effect of brush layering on slope stability[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0, 36(3): 258–264.
[21] EVETTE A, LABONNE S, REY F, et al. History of bioengineering techniques for erosion control in rivers in western europe[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9, 43(6): 972–984.
[22] STERN R. Water bioengineering techniques: for water-course, bank and shoreline protection[M]. London: Black-well Science Inc., 1997.
[23] MONTY F, MURTI R, FURUTA N. Helping nature help us: transforming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through ecosystem management[M]. Gland: IUCN, 2016.
[24] 趙潤江, 師衛華, 趙輝. 城市護岸的發展歷程和趨勢[J].現代園藝, 2008(9): 46–47.
[25] LI Xiaoping, Zhang Quanli, Zhang Zheng. Soil bioengine-ering and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riverbanks at the Airport Town, Shanghai, China[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06, 26(3): 304–314.
[26] 劉瑛, 高甲榮, 顧嵐. 基于植物柔韌性的土壤生物工程護岸材料選擇[J]. 北京林業大學學報, 35(6): 74–79.
[27] Li Kun, ZHANG Zhenxing, YANG Haijun, et al. Effects of instream restoration measures on the physical habitats and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s in an agricultural headwater stream[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8, 122(10): 252–262.
[28] ZHANG Zhenxing, CAO Lina, ZHU Ziyu, et al. Evaluation on soil bioengineering measures in agricultural areas: poorer durability of wooden structures and better aboveground habitat improvements [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9, 129(4): 1–10.
[29] 陳鵬, 劉煜, 吳耕華, 等. 不同土壤生物工程措施根系附加黏聚力研究[J]. 安徽農業科學, 2018, 46(23): 168–171.
[30] MARTIN D. Bioengineering techniques for streambank restoration a review of central European practices [M]. Washingt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Lands and Parks and Ministry of Forests, 1995.
[31] BOCHET E, POESEN J, RUBIO J L. Runoff and soil loss under individual plants of a semi-arid Mediterranean shrubland[J].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2006, 31(5): 536–549.
[32] GYSSELS G, POESEN J, BOCHET E, et al. Impact of plant roots on the resistance of soils to erosion by water: a review[J].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2005, 29(2): 189–217.
[33] BOCHET E, GARCíA-FAYOS P. Factors Controlling Vegetation establishment and water erosion on motorway slopes in Valencia, Spain[J]. Restoration Ecology, 2010, 12(2): 166–174.
[34] LIRA-CABALLERO V G, MAR-TíNEZ-MENEZ M R, ROMERO-MANZANARES A, et al. Initial floristic composition of rehabilitated gullies through bioengineering in the Mixteca Region, Sierra Madre del Sur, Mexico[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8, 15(10): 2120–2135.
[35] STEPHEN D M.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inciples, values, and structure of an emerging profession[J]. Restoration ecology, 2013, 21(5): 658–658.
[36] SIMON A, CURINI A, DARBY S E, et al. Bank and near-bank processes in an incised channel[J]. Geomor-phology, 2000, 35(3): 193–217.
[37] ALEJANDRO G, MICKOVSKI S. Plant-soil reinforcement response under different soil hydrological regimes[J]. Geoderma, 2017, 285(1): 141–150.
[38] Wang Jianhua, Lu Xiaoguo, Tian Jingha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riparian wetland[J]. Wetland Science, 2008, 6(2): 97–104.
[39] REY F, BURYLO M. Can bioengineering structures made of willow cuttings trap sediment in eroded marly gullies in a Mediterranean mountainous climate? [J]. Geomorphology, 2014, 204(1): 564–572.
[40] LEWIS L. Curbing roadside erosion soil bioengineering as an alternative to concrete and steel[J]. Conservation, 2010, 3(2): 39–43.
[41] VALENTIN C, POESEN J, LI YONG. Gully erosion: Impacts, factors and control[J]. Catena, 2005, 63(2): 132–153.
[42] SCHUMM S A. Evolution of drainage systems and slopes in badlands at Perth Amboy, New Jersey[J].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56, 67(5): 597–646.
[43] 景可. 黃土高原溝谷侵蝕研究[J]. 地理科學, 1986, 6(4) : 340–347.
[44] 張信寶, 白曉永, 周萍. 監測土壤流失的標線法及其測定犁耕運移土壤的嘗試[J]. 中國水土保持, 2011(7): 44–46.
[45] MEHRETIE B, WOLDEAMLAK B. Assessment of gully erosion and practices for its control in north-western highlands of Ethiopia[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12, 69(5): 714–728.
[46] CAVAILLé P D L. Functional and taxonomic plant diversity for riverbank protection works: bioengineering techniques close to natural banks and beyond hard engineer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5, 151(55): 65–75.
[47] Yue Zhou, DAVID W, Li Yuhui, et al. A case study of effect of lateral roots of Pinus yunnanensis on shallow soil reinforcement[J]. Forest Ecology & Management, 1998, 103(2): 107–120.
[48] REY F, ISSELIN-NONDEDEU F A B. Vegetation dynamics on sediment deposits upstream of bioengineering works in mountainous marly gullies in a Mediterranean climate (Southern Alps, France) [J]. Plant and Soil, 2005, 278(1/2): 149–158.
[49] DE CESARE G. Soil Bio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ype manual[M]. Switzerland, vdf Hochschul-verlag AG der ETH Zürich, 2007.
[50] MCHENRY J R, RITCHIE J 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arameters affecting transport of 137Cs in arid water-sheds[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1977, 13(6): 923–927.
[51] GENTR M K L V. Accretion and canal impacts in a rapidly subsiding wetland. III. A new soil horizon marker method for measuring recent accretion[J]. Estuaries, 1989, 12(4): 269–283.
[52] MORGAN R P C. Soil erosion and conservation[J]. Earth Science Reviews, 1985, 24(1): 68–69.
[53] 王芳. 六種灌木根系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在土壤生物工程中的應用[D].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2006: 86.
[54] BAETS S D, POESEN J, GYSSELS G, et al. Effects of grass roots on the erodibility of topsoils during concen-trated flow[J]. Geomorphology, 2006, 76(1): 54–67.
[55] 婁會品. 土壤生物工程在北京郊區生態護岸應用效果研究[D].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2011: 57.
[56] 李小平, 張利權. 土壤生物工程在河道坡岸生態修復中應用與效果[J]. 應用生態學報, 2006,17(9): 1705–1710.
[57] RAUCH H P, SUTILI F, STEPHAN H. Installation of a riparian forest by means of soil bio engineering techniques—monitoring results from a river restoration work in Southern Brazil[J]. Open Journal of Forestry, 2014, 4(2): 161–169.
[58] ANDRE C, JAMES A. The SER primer and climate change[J].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Restoration, 2013, 14(3): 182–186.
[59] 劉瑛. 土壤生物工程技術在河岸生態修復中應用效果的研究[D].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2011: 145.
[60] 高甲榮, 劉瑛. 土壤生物工程在北京河流生態恢復中的應用研究[J]. 水土保持學報, 2008,22(3): 152–157.
[61] 陳瓊. 基于土壤生物工程技術的現澆網格生態護坡應用研究[D]. 北京: 北京林業大學, 2014: 68.
[62] REUBENS B, POESEN J, FRéDéRIC D, et al. The role of fine and coarse roots in shallow slope stability and soil erosion control with a focus on root system architecture: a review[J]. Trees, 2007, 21(4): 385–402.
Research progress on erosion gully control in small watershed based on soil bioengineering
LENG Yu1, CAO Lina2, ZHANG Zhenxing1, 2,*, SUN Wei1, YANG Haijun3,LIN Chenlu1, GAO Yufu1
1. Key Laboratory of Vegetation Ec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Wetland Ecology and Vegetation Restoration, School of Environ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7, Jilin Province, China 3.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a national key funded application of basic research. It is a field of development to practice the governance concept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China is still serious. There is more than one quarter of the soil and water loss area, which is widely distributed and difficult to manage, causing serious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Erosion gully management in small watersheds based on soil biotechnolog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oil bioengineering technology;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main methods of erosion gully management based on soil bio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il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heir ecological func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il bio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not only an effici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thod for the management of erosional gullies in small watersheds, but also has both economic and landscape effects. It is suggested that while systematically conducting erosion control of small watersheds based on soil bio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eir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technical method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for erosion channel management, and it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ally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China.
erosion gully; soil eros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oil bioengineering
10.14108/j.cnki.1008-8873.2021.06.028
S157
A
1008-8873(2021)06-225-08
冷瑜, 曹麗娜, 張振興,等. 基于土壤生物工程的小流域侵蝕溝治理研究進展[J]. 生態科學, 2021, 40(6): 225–232.
LENG Yu, CAO Lina, ZHANG Zhenxi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erosion gully control in small watershed based on soil bioengineering[J]. Ecological Science, 2021, 40(6): 225–232.
2020-05-19;
2020-06-2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32071587, 41501566); 留學基金委項目(202006625001);國家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2017ZX07101003); 吉林省教育廳項目 (JJKH20211293KJ )
冷瑜(1995—), 男, 江蘇溧陽人, 碩士, 研究方向: 河流生態修復, E-mail: lengy151@nenu.edu.cn
通信作者:張振興, 男, 博士, 副教授, 主要從事: 恢復生態學、流域生態學研究, E-mail: zhangzx725@ne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