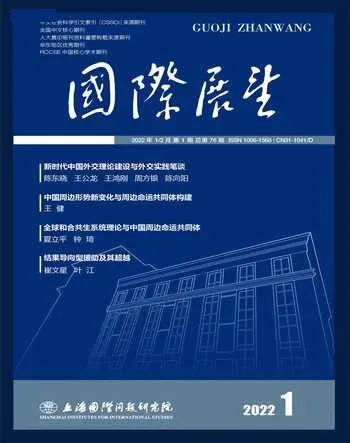結果導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崔文星 葉江
【關鍵詞】??國際發展合作??聯合國2030年議程??全球發展倡議??話語權
【中圖分類號】?D8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2)01-0074-21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201005
二戰結束后,以美國和蘇聯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在冷戰背景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成為兩個超級大國為自己爭取盟友的重要手段。對于援助國來說,其合法性依據主要在于通過援助使某個受援國成功留在己方陣營,而較少關注援助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促進了受援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隨著冷戰的結束,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不復存在,但援助國政府在制定援助預算時面臨著新的合法性危機,議會和民眾對本國進行的大量援助并未有效改善受援國狀況提出更多批評。援助有效性(aid?effectiveness)的討論正是在此背景下興起,而對可衡量的結果的重視是討論的主要內容。
進入21世紀以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成為援助有效性辯論的重要參照,全球多邊和雙邊援助機構亦開始了結果導向型援助新實踐。中國高度重視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可持續發展議程與中國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進行了有機結合。目前,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各項落實工作已經在中國全面展開。?2021年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強調中國不僅要通過自身發展,而且要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推動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落實。2021年8月,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了《對外援助管理辦法》,以加強援外工作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76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2021年10月30日,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六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的講話中強調,通過全球發展倡議加快聯合國2030年議程的落實,這標志著中國國際發展合作與全球發展議程的對接進入新階段。
援助有效性是發展援助在實現經濟或人類發展方面的效力。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方援助國的政府和援助機構開始意識到,它們在提供發展援助時所采取的不同援助方式和對受援國提出的不同要求給受援國帶來巨大的成本壓力,導致援助的效力降低。因此,它們開始尋求通過相互間以及與發展中國家的協調與合作來提高援助的有效性。2000年9月,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世界各國領導人就消除貧困、饑餓、疾病、文盲、環境惡化和對婦女的歧視,商定了一套有時限的目標,即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MDGs),實現這些目標的主要手段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這一目標體系為援助者之間的政策協調提供了重要參照,援助有效性評價的國際進程也由此開始。
2002年3月,聯合國發展融資峰會在墨西哥蒙特雷舉行,雙邊與多邊援助機構同意擴大援助規模并提高援助有效性。?2003年2月,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的援助協調高層會議上通過了《關于援助協調性的羅馬宣言》(Rome?Declaration?on?Harmonization),強調援助重點要與受援國發展的優先領域保持一致并加強援助國之間的協調。?2005年3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援助有效性高層論壇上簽署的《關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Paris?Declaration?on?Aid?Effectiveness)提出了國家自主決策(ownership)、一致性(alignment)、協調性(harmonization)、成效管理(management?for?results)和相互問責(mutual?accountability)五項援助原則。?其中第四項原則強調需要加強對援助實效與成果的測量,使援助能夠切實促進受援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2008年,第三屆援助高層論壇在加納首都阿克拉舉行,會議通過的《阿克拉行動議程》(Accra?Agenda?for?Action)在認可南南發展合作價值的同時也更加關注發展結果。?2011年11月,在韓國釜山舉辦的第四屆援助有效性高層論壇上通過的《釜山宣言》(Busan?Partnership?for?Effective?Development?Cooperation)正式提出國際援助政策的關注點應從援助有效性轉向發展有效性。結果導向型援助(results-based?aid)模式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在一些西方國家和多邊援助機構中發展起來,并日益受到中國學界的關注。
“聚焦于結果”(results-focus)曾是圍繞援助所進行的辯論的重要維度。例如,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分析框架就將援助直接與績效和結果相聯系,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Easterly)在《白人的負擔》(The?White?Man’s?Burden)一書中就有相關分析。還有一些理論、概念和方法也與“結果”相關。例如,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關于國家選擇(country?selectivity)的討論也隱含著聚焦“結果”,其背后的理念是對那些表現良好的國家予以獎勵,并激勵它們表現得更好。?此外,為援助附加條件也直接涉及對政策實施與改革結果的激勵。
對援助結果的重視雖然由來已久,但對結果導向型援助這一新援助方式的深入研究則主要是在2011年釜山援助有效性高級別論壇之后,在國際發展話語從援助有效性向發展有效性轉變的背景下逐漸興盛起來。在這次論壇之后,德國發展研究所(Deutsches?Institut?für?Entwicklungspolitik,?DIE)的一批研究人員開始對結果導向型援助進行專門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國際組織在非洲國家的相關項目,重點關注教育、衛生與治理。斯蒂芬·克林格貝爾(Stephan?Klingebiel)對結果導向型援助方式的局限性進行了分析。?阿曼達·梅麗娜·格里特納(Amanda?Melina?Grittner)對衛生部門結果導向型融資進行了研究。?莎拉·霍爾扎普菲(Sarah?Holzapfel)與海納·賈納斯(Heiner?Janus)對教育部門中結果導向方式的指標進行了歸納。?海納·賈納斯和莎拉·霍爾扎普菲對農業部門中結果導向方式所面臨的挑戰與教訓進行了總結。?海納·賈納斯和尼爾斯·凱澤(Niels?Keijzer)對坦桑尼亞結果導向型援助項目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分析。?除了德國發展研究所,英國、荷蘭以及一些國際組織的研究人員也對結果導向型援助進行了研究。馬克·皮爾森(Mark?Pearson)對結果導向型援助概念進行了分析,并探討了其是否促進了結果的實現。?朱里安·圖嫩(Jurrien?Toonen)等以馬里和加納作為案例,對衛生領域中結果導向型融資進行了研究。?美洲開發銀行則通過來自薩爾瓦多衛生部門的證據對結果導向型援助是否比傳統援助更有效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世界銀行對教育領域中結果導向型融資進行了研究,并對這種融資方式對加強世界銀行系統所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分析。
隨著中國日益深度參與全球發展治理,國內學者在對援助有效性和發展有效性的討論中也更聚焦結果。李小云對西方援助有效性戰略為何走向無效進行了分析,認為援助主體、對象、機構和領域的碎片化是影響援助效果的重要原因。?張海冰認為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是一種發展引導型援助,以發展的有效性作為衡量援助是否有效的關鍵標準,這一點不同于巴黎俱樂部所推崇的援助有效性概念。?黃梅波構建了援助有效性和發展有效性相結合的國際發展援助質量評價框架,利用該框架對中國對外援助效果進行評估。
總體而言,國內學者在關于發展有效性的討論中加強了對援助效果和結果的研究,西方學界和政策界則對結果導向型援助的概念、原因、效果等基本問題從不同的領域和視角并結合不同的國家案例進行了初步探討。
與結果導向型援助相對應的是過程導向型援助。過程導向型援助是以投入(如提供了多少資金)和進展(如建成了多少所學校)為導向。與此相對應,對援助效果的衡量也通常是根據投入或進展指標來進行,例如,受援國是否增加了教育預算,是否出臺了教育改革政策。這種援助評估方法主要關注的是受援國的活動,但并不確定預期結果是否能夠實現。例如,預算增加和教育改革政策的出臺是否實際促進了入學人數的上升和教育質量的提升。如果結果得以實現,其與援助活動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這些都是過程導向型援助難以回答的問題。結果導向型援助力圖彌補傳統援助方式的不足。
結果導向型援助致力于在援助活動開始之前確定可以衡量和量化的與發展援助活動直接相關的結果目標,援助國與受援國在合同中確定促使結果目標實現的激勵措施,即援助的實施與結果目標的實現情況相掛鉤。?援助國與受援國事先就結果的“單價”(Unit?Price)達成一致,例如,受援國每有一名學生通過期末考試,援助方將會提供多少援助,但援助方并不參與援助項目的具體實施。結果導向型援助在援助支付和發展結果的實現之間建立了聯系,旨在消除以投入為導向的援助方式的弊端,如沒有明確的結果證據、援助交易成本高、大量使用援助方的執行能力而繞過受援國國家系統等。
結果導向型援助主要基于三個假設。第一,由于強有力的激勵措施,結果導向型援助可以促進受援國在主要結果目標方面取得進展。第二,結果導向型援助降低了援助的交易成本,因為它需要的報告流程較少,而且受援國的國內系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更好的利用。第三,受援國對結果導向型援助的計劃制定和政策實施有很強的自主權,而且援助國和受援國之間的責任分工也更加明確。
結果導向型援助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主要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步是援助國與受援國簽訂發展合作合同。第二步是開展實現結果目標所需的活動(受援國負責整個實施過程)。第三步是對結果目標的進展情況進行評估(通常由第三方完成)。
“結果”通常被定義為“投入”(input)和“活動”(activity)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可以劃分為不同的層級。“產出”(output)通常是技術層面的結果,如新建的學校;“產出”可能會導致下一層級的結果是“成果”(outcome),如因有了新的學校設施而使兒童入學率提高;最具雄心的結果層級是“影響”(impact),如因教育成果改善而帶來的減貧效應。
對目標結果的實現情況進行衡量需要使用指標。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Assistance?Committee,?DAC)將指標定義為“定量或定性因素或變量,提供衡量成就的簡單可靠手段,反映與干預有關的變化或幫助評估發展行動者的表現”。在所有類型的發展計劃中都會使用指標對實施過程進行管理并對實施結果進行報告。
在結果導向型援助中,指標被專門用于決定所支付資金的數額。雖然所有發展干預都需要某種形式的證據,如資金支出的文件證據來確定援助的支付,但結果導向型援助通過與支付掛鉤的指標(Disbursement-Linked?Indicators,?DLIs)將資金撥付與預先確定的目標或結果直接相聯。與支付掛鉤的指標有三種分類方法。
第一種分類是“進程指標”與“結果指標”。與支付掛鉤的指標可以根據結果的不同層級來進行界定。結果導向型援助的影響鏈條始于“投入”,然后是為實現預期目標所開展的“活動”,“投入”和“活動”有助于“結果”的實現。?“結果”又有三個層級:直接的“產出”、短期和中期的“成果”以及長期的“影響”。“投入”指標用來衡量所使用的財務、人力和物力資源,如分配給教育計劃的預算。“活動”指標衡量所采取的行動或所開展的工作,如舉辦教師培訓研討會的數量。“產出”指標用來衡量發展干預所產生的產品、資本品和服務,如接受過培訓的教師人數。“成果”指標用來衡量干預的短期和中期效果,如學生學習成績的改善。“影響”指標用來衡量干預的長期效果,如青年就業率的增加。
第二種分類是“直接指標”和“間接指標”。“直接指標”指發展的主體,?如接種疫苗的兒童人數是兒童疫苗接種計劃“產出”層面的直接衡量指標。“間接指標”衡量與結果本身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很好地描述結果的實現程度,?如家庭資產和住房情況通常用作家庭生活水平的間接衡量標準。當收集“直接指標”的數據困難、成本高昂或不可行時,就會更多使用“間接指標”。在發展中國家,如果收入、支出和消費等生活水平的直接衡量標準難以收集或收集成本高昂,“間接指標”就特別有用。
第三種分類是“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定量指標”是通過客觀或可獨立驗證的數值(如絕對值、百分比、比率等)對結果進行衡量,如接受培訓的教師人數、受益于衛生條件改善的人數、每日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例、每一千名活產嬰兒中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等。然而,并非所有現象和結果都可以量化,如促進民主、善治或機構能力建設的干預措施其結果往往是定性的,因此通常可以通過定性指標來衡量,如法律是否已獲通過或是否已建立機構,受益人對服務的評價是優秀、滿意還是不滿意。
對與支付掛鉤指標的適用性進行評估通常采用“聚焦于結果”“與受援方努力相關”“需財政激勵”“可衡量驗證”“考慮意想不到的后果”等有關標準。一是更加注重結果是結果導向型援助的主要目標之一,與支付掛鉤的指標應聚焦于對三個層級上結果目標的衡量。二是當援助撥付與指標掛鉤時,這些指標應衡量那些因受援方努力而產生的變化。三是在財政激勵方面必須為在指標方面取得的進展進行定價,以及確定是否為額外的單位進展進行增量撥款。四是當支付與結果掛鉤時,這些結果必須是可衡量和可獨立驗證的,這樣才能確保其可信度。五是指標的設定要考慮意想不到的后果并注意避免激勵扭曲。例如,當及格率指標被用于確定援助撥付時,受援方有強烈的動機把精力放在幫助那些最接近及格門檻的學生,而忽視那些距離及格線較遠的學生。
世界銀行資助的坦桑尼亞“教育中的重大成果計劃”(Big?Results?Now?in?Education?Program,?BRNEd),是教育部門中第一個結果導向型援助的試點計劃。該計劃始于2014年,其目標是提高坦桑尼亞中小學的教育質量,其衡量指標包括:全國二年級學生的閱讀平均成績、全國二年級學生的平均算術成績、中小學暗訪期間在教室里發現的老師百分比等。?這一項目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與坦桑尼亞國家改革議程中“立即實現重大成果”(Big?Results?Now,?BRN)倡議緊密聯系并保持一致。
該倡議聚焦于包括教育部門在內的六個優先領域,致力于在規定的時間內實現可衡量的目標,表現出較強的結果導向特點。世界銀行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并在五年內(2014—2018年)出資1.22億美元,共設立了16個與支付掛鉤的指標對進展進行監測與評估(見表1)。

資料來源:Sarah Holzapfel and Heiner Janus, “Improving Education Outcomes by Linking Payments to Results: An Assessment of Disbursement-linked Indicators in five Results-based Approaches,”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5, 2015。
從“聚焦于結果”標準看,與支付掛鉤的指標分布在結果鏈條中的投入、活動、產出和成果四個層級。大多數指標對制定預算、生成報告等活動進行獎勵,唯一的成果指標對閱讀、寫作和算術方面的改進進行獎勵。從“與受援方努力相關”標準看,這些指標的改善與政府部門控制范圍內的活動密切相關,因此,11個指標針對中央政府部門的行動進行獎勵,5個指標針對向學校提供資金和教師的地方政府的行動進行獎勵。從“財政激勵”標準看,支付要么基于達到某些閾值,要么基于規模上的單位。在16個指標中,9個被確定為閾值,主要用于衡量是否已制定預算、計劃或測量工具。這些指標的支付大多在第一年進行一次,指標是以二元術語表示的定性指標。因此資金要么全部發放,要么完全不發放。其余7個指標基于不同的尺度,對目標進展情況按比例進行獎勵。從“可衡量驗證”標準看,大多數指標都是直接和定性的,并評估政府實體的績效。雖然這些指標在針對特定活動的意義上是直接的,但它們只是總體目標的間接衡量標準。從“意想不到的后果”標準看,許多潛在的意外后果和各自的緩解策略已經被提前考慮并包含在計劃設計之中,主要風險包括2015年的國家選舉結果、管理薄弱、執行部門的監督能力欠缺等。
結果導向型援助可以在如下幾個方面促進受援國的發展。一是激勵受援國,因為資金撥付與可量化的結果相聯系,這可以激勵受援國努力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二是在受援國產生溢出效應,受援國在某一個部門所形成的發展成果會對其他部門的發展產生推動作用,如教育水平的提高會增加民眾的衛生知識,從而進一步促進健康目標的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就吸取了千年發展目標“筒倉”結構的教訓,?致力于提高各目標之間的協同效應。三是加強受援國政府的自主權,2030年可持續發展子目標17.15強調要尊重每個國家制定和執行消除貧困和可持續發展政策的政策空間和領導作用,?實現目標的任務在于受援國政府,這加強了受援國的政治和行政系統。四是援助更具可見性,發展成果和援助激勵之間的因果關系更為明晰,這可以幫助援助國展示援助帶來的具體成果。
然而,結果導向型援助也存在著劣勢。一是造成援助“寵兒”與“孤兒”,即結果導向型援助僅適用于那些表現良好的國家,對于低收入和高度依賴援助的國家而言,這些激勵條件不存在或效果不佳。二是對受援國執行能力要求高,該方法意味著受援國需要有能力取得成果。如果它們的能力不足、公共財務管理系統不完善,這種方法并不現實。三是容易導致整體政策缺乏系統性,對某些特定結果的關注往往會導致整體政策缺乏系統性,實現特定目標的壓力可能會導致對同一部門其他重要問題的忽視。四是部門限制,結果導向型援助無法在所有部門得到同等實施。教育、衛生等社會部門以及容易衡量的基礎設施服務部門(交通、公共供水等)更適合此種方法。其他部門可能較難衡量這些結果或與受援國達成協議,例如,關于良好治理的復雜協議。五是預融資能力不足。在這種方法的設計中,受援國需要自己預先出資,然而一些低收入國家的預算非常緊張,這可能是一個主要障礙。六是時間范圍。結果導向型援助往往具有短期視角傾向,因為它可能只考慮那些可以快速實現的目標,對于那些只能在中期或長期實現的目標可能會與短期政治目標(如贏得選舉)發生沖突,?因此,結果導向型援助并非靈丹妙藥,過于強調結果也會造成政策的短視。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國際社會為全球發展建立的一個結果框架。這一框架包含17個大目標、169個子目標以及230個指標,大部分目標的截止期限為2030年。?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體系并不是為發展合作本身(包括官方發展援助)或單個發展合作提供方設置的框架,但它為結果導向型援助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發展合作提供方(援助方)與合作伙伴(受援方)都可以通過將其結果框架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聯系而獲益。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于2015年通過后,西方國際發展學界及政策界就開始加大對結果導向型援助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其指標的相關性進行研究。2017年9月,OECD-DAC發布了題為《通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子目標和指標加強援助方的結果框架》(Strengthening?Providers’?Results?Frameworks?through?Targets?&?Indicators?of?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列舉了由53個穩健指標(robust?indicators)支持的42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成果”(outcome)子目標和涵蓋實施手段(means?of?implementation)的18個可持續發展子目標及其指標,并建議發展合作提供方以此菜單作為制定自身發展合作結果框架的參照。
以教育目標為例,聯合國2030年議程的目標4為“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與目標1—16中的其他大目標相同,該目標下設的子目標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到2030年要實現的目標(主要聚焦于結果鏈條中的“成果”層面),第二部分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主要聚焦于結果鏈條中的“活動”層面)。例如,子目標1為“到2030年,確保所有男女童完成免費、公平和優質的中小學教育,并取得相關和有效的學習成果”。衡量目標進展的指標則包括:在二年級或三年級、小學結束時、初中結束時獲得基本的閱讀和數學能力的兒童和青年的比例,按性別分列;初等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的完成率。實施手段則包括建立和改善教育設施與增加合格教師人數等。此外,為了確保可持續發展目標1—16的如期實現,目標17“加強執行手段,重振可持續發展全球伙伴關系”,則專門強調了發展合作的作用,通過發達國家全面履行官方發展援助承諾以及加強南南合作與三方合作等促進發展中國家在可持續發展目標1—16方面取得進展。2030年議程中與結果導向型援助密切相關的子目標和指標為援助方與受援方在發展合作中確定責任歸屬、進行溝通交流、明確合作方向和總結經驗教訓提供了重要基礎,?這是發展政策一致性努力的重要里程碑。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致力于自身發展的同時,始終堅持向經濟困難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擔相應國際義務。2011、2014、2021年,中國發布了三份白皮書,對中國對外援助的發展歷程與成就、對外援助管理體系、國際發展合作趨勢與特點等進行全面介紹。2011年白皮書將中國對外援助歸納為八種方式:成套項目、一般物資、技術合作、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援外醫療隊、緊急人道主義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債務減免。?總體來看,2011年白皮書對中國援助情況的總結主要是集中在結果鏈條中的“活動”與“產出”層面(如提供了多少價值的藥品、援建了多少所學校和醫院等),而對中國的援助在受援國產生的“成果”及“影響”基本上沒有提及。2014年白皮書在2011年白皮書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進,更加注重對援助所產生的結果的強調,這顯然與結果導向型援助的國際發展合作潮流是相契合的。2014年白皮書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別對中國援助在推動受援國民生改善和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的作用進行了總結,但所提供的支撐材料的“成果性”并不突出,如中國在2010—2012年期間援建了156個經濟基礎設施項目,舉辦了1?579期官員研修班等。
2015年聯合國2030年議程通過后,中國對外援助及國際發展合作開始與聯合國2030年議程對接。2021年1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將國際發展合作定義為“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國通過對外援助等方式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包括人道主義援助方面開展的多雙邊國際合作”。這份白皮書除了將“援助”擴展為“發展合作”之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內容是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和推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列為白皮書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這說明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向結果導向又邁進了一步,表明了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國際發展合作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貢獻力量的意愿與決心。在此基礎上,2021年9月1日,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新的《對外援助管理辦法》,將《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的基本精神體現在具體的對外援助管理之中。總之,2021年中國發布的與國際發展合作及對外援助相關的文件都對結果導向型援助有所強調,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國際社會對結果導向型援助的討論是基本同步的,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與全球發展治理話語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更顯示出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具有相通之處。
“對外援助”(foreign?aid)、“發展援助”(development?assistance)、“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ODA)和“發展合作”(development?cooperation)是相近的概念,但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對這些術語有著不同的使用偏好。美國多使用“對外援助”,且往往不對發展援助和軍事援助進行區分。“發展援助”和“官方發展援助”在一些歐洲國家和國際組織使用較多,強調援助是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而非出于軍事或其他目的。?經合組織和歐盟的文獻中則較多使用“發展合作”,以表明其致力于提高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平等性。長期以來,中國的官方文件中更多使用“對外援助”一詞。例如,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總理宣布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又如,2011年4月和2014年7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第一份和第二份《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然而,2021年1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則將“對外援助”升級為“國際發展合作”,這一表述的變化是中國國際發展政策與時俱進的體現,且與結果導向型援助及聯合國2030年議程相互關聯。
二戰后的國際援助體制是以1947年“馬歇爾計劃”的啟動為標志而展開,?在此后的4個財政年度,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1.5億美元。?“馬歇爾計劃”促進了西歐經濟的復蘇與發展,這使西方國家認識到對外援助的積極作用,此后西方國家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援助逐漸展開。然而,在接受援助的幾十年中,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并未成功走上發展之路,即使在進入21世紀之后仍然在為擺脫極端貧困而努力。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Human?Development?Report)中對援助效果不佳的原因作了系統分析。首先,援助金額受到援助國經濟發展情況及對外戰略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其直接表現是援助承諾出現無法完全兌現的問題。其次,大多數西方援助國都將提供援助與苛刻的條件掛鉤,這降低了援助資金的有效額度、加劇了援助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再次,不同的援助方對受援國關于援助資源使用的報告和援助效果的評估有不同的要求,援助機構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調,給受援國帶來了沉重的人力和物力壓力。?2009年,贊比亞學者丹比薩·莫約(Dambisa?Moyo)甚至提出了“援助死亡”(Dead?Aid)的觀點,認為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對非洲援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均已走入絕境,此種由外部力量主導的援助造成非洲對外部的嚴重依賴,埋葬了非洲自主、獨立發展的機會與意愿。?而結果導向型援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與西方傳統援助國的對外援助不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始終堅持以自力更生作為立足點,在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也注重受援國自主發展能力的提高,?將“輸血”與“造血”相結合。?因此,將“對外援助”轉化為“國際發展合作”更能體現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平等互惠性質,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中國的發展援助理念與結果導向型援助理念相契合。
二戰結束后,在美蘇冷戰的國際格局下,國際發展合作實踐至少存在著三條主線:第一條是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第二條是蘇聯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援助;第三條是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南南合作。中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始終是在南南合作框架下進行,強調合作的互利性。然而,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以來,各國對危機和疫情的不同應對導致國際權力格局東升西降的趨勢進一步加速,中國進一步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此背景下,國際上出現了許多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質疑的聲音,如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2019年7月指責中國通過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在貿易中獲得更多利益,?英國國際貿易大臣伊麗莎白·特拉斯(Elizabeth?Truss)在2021年4月也表示英國將會重新審視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對此,中國在2021年《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中重申南南合作是中國開展國際發展合作的基本定位,強調中國開展國際發展合作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幫助,與南北合作有著本質的區別。?正是由于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具有南南合作的特性,使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能夠避免結果導向型援助的某些負面因素,比如能夠避免援助中出現“寵兒”和“棄兒”的現象。隨著中國更為強調國際發展合作,中國的對外援助在關注援助結果的同時,也十分關注均衡地對發展中國家實施以結果為導向的援助。
鑒于西方發達國家在歷史上對殖民地的掠奪,它們在道義上有援助發展中國家的責任,而南南合作則沒有這一歷史包袱。另外,也同樣由于殖民思想的影響,今天的南北合作依然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性,這種不平等突出體現在發展道路的一元性與合作模式的垂直性。一元路徑觀的哲學基礎是堅持西方社會的“先進性”和所有民族都要經歷相同發展道路的社會進化論。?受此理論的影響,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來,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發展,只能沿著西方國家走過的路前行。這一思想在國際發展實踐中的體現是垂直型的南北合作,即西方發達國家以“教師爺”自居,通過附加條件的援助為發展中國家開出種種發展“藥方”,如結構調整、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人權、善治等。與南北合作不同,南南合作倡導發展道路的多元性與發展合作的水平性。中國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展南南合作時始終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則,尊重其他國家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這顯然有助于在保持結果導向型援助優勢的同時克服其劣勢。
在2013年10月24—25日舉行的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2014年7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國會發表演講時強調,“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在援助話語中,援助方(donor)和受援方(recipient)的表述一方面具有居高臨下和施舍的不平等意味,另外也體現出雙方關系中資源單向流動的不均衡性。而“國際發展合作”顯然更具平等性與均衡性,體現著資源雙向流動與共同發展的內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更為契合。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國國際發展合作以“一帶一路”為重要平臺,以推動聯合國2030年議程的落實為重要方向,毫無疑問這是對結果導向型援助的劃時代超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利用好“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2030年議程對接所帶來的機遇,同時有效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圍堵,需要在借鑒的同時解構甚至超越西方的國際發展話語,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中國的全球發展理論。這樣才能增強中國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的話語權,并且更好地把握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的未來發展方向。
1949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就職演說中宣布了“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計劃”,他在為國際發展時代揭開序幕的同時,也在提倡一種構想國際關系的新方式。?這種“新方式”用全球經濟中貿易伙伴之間的看似平等的關系取代了原來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等級制度。在新的國際關系中,一批“欠發達”國家落在后面,需要“發達”國家的慷慨援助才能趕上去。通過這種新話語,對自己和他人的一種新認知被創造出來,20億人被貼上了“欠發達”的標簽,?他們不再是原來具有豐富多樣性的群體,而成為反映他人現實的鏡子,這面鏡子對他們進行貶低并將他們送至隊列的末尾。人們在談論他們時首先不再是其文化多樣性,而是他們統統都是欠發達地區的人。?世界上存在著“發達”和“欠發達”的社會,前者在北方而后者在南方,后者問題的解決受益于前者的知識。這一思維方式類似于臨床觀察,其特征是將注意力放在他人的缺陷上,將有關治愈的知識歸于自我,而忽略他人的知識。在這一視角下,北方沒有成為發展干預的對象。因此,根據發展學派的觀點,“發展”的不變特征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對“欠發達”社會進行干預的合法性,基于“發達的自我”(developed?Self)的歐洲中心視角以及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知識的歸因,基于可以對不同社會進行比較的普遍標準。?由此,結果導向型援助雖然克服了過程導向型援助的種種不足,但是卻依然難以超越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中的以北方為中心的西方發展觀。
從某種程度上看,聯合國框架下的四個發展十年和千年發展目標體系都應該屬于國際發展議程,議程中所設定的目標主要是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則主要是援助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單向流動。盡管結果導向型援助這一修正過去西方發展援助負面影響的理念對上述聯合國的國際發展議程有明顯的積極影響,但是卻并沒能改變國際發展中的這種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單向流動。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一批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和環境議題在發展議程中的進一步凸顯,這一狀況正在發生變化。由于發達國家也面臨著環境等發展可持續性問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具有普遍適用性,適用于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在促進目標實現的資源和知識方面,作為執行手段的千年發展目標8(建立促進發展的全球伙伴關系)并未提到南南合作的作用。與此不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作為執行手段的目標17則明確將南南合作、三方合作與南北合作并列,強調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也是發展資源與知識的來源。因此,從目標適用范圍和發展知識來源的視角看,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屬于真正的全球發展議程。更重要的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國際發展合作和全球伙伴關系方面既吸收了結果導向型援助的積極因素,也為超越該理念奠定了基礎。
通過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找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中國的發展成就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之路確立了信心,中國也開始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開展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平臺,也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是中國在全球發展話語建構方面邁出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該倡議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織影響下的全球發展指明了方向,對“要不要發展”“要何種發展”“如何發展”等根本性問題進行了回答。全球發展倡議將發展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堅持發展優先;致力于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普惠包容性發展;堅持創新驅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全球發展倡議是在充分借鑒全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的,蘊含了西方文明中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中的“公平”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等要素。全球發展倡議與“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生態文明思想共同構成了中國全球發展話語權建構的重要基礎,并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超越了結果導向型援助,為全球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指明了方向。
多年來,中國國際發展合作受到眾多發展中國家政府與民眾的歡迎與好評,但也遭到一些西方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學者與官員的質疑與詬病,“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缺乏透明度”等指責也一度甚囂塵上。要增強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的話語權,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的效果需要更多可量化的結果證據來支撐。中國需要吸收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在結果導向型援助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合作實踐中結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指標,對國際發展合作的實踐進行改進與完善。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既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也是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圍堵的重要突破口。
在中國為全球發展提供的方案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解決的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問題,而生態文明則致力于解決人類與自然以及人類與自己的關系。生態文明不僅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對傳統的由西方主導的發展話語的超越,它既包含了替代性發展,也包含了發展的替代。這些理念為中國全球發展理論的構建提供了重要啟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發展理論,超越結果導向型援助,以增強中國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的話語權,既與全面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相關,也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責任編輯:石晨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