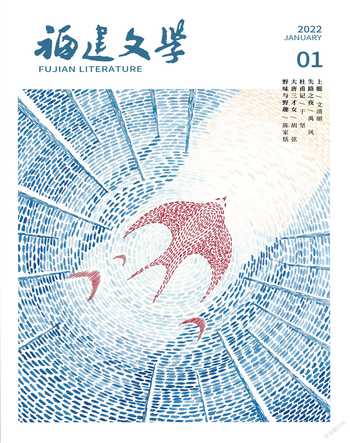舊時月色
文河
舊 時 月 色
月亮升起的時候,人間就靜了。
舊時,樹多,草茂。樹多成林,一片一片的樹林,月亮照著,一攤一攤樹影汪汪如潑墨,遠看有生動變化的輪廓曲線。舊時,水也多,池沼,溪流,湖泊,很多地方,都亮閃閃的。月亮照著水面,每個水面都有一個月亮,舊時的月色也就更多了。以前,人們稱月亮為月婆、月姊,人和月亮是一種世俗的關(guān)系。
在中國的抒情傳統(tǒng)中,月色也是中國人心靈的底色,像宣紙一樣,無邊無際地鋪著,鋪遠了,就看不清了,人的心靈和天地渾然一體。月色是一種調(diào)和,也是一種撫慰,那種朦朧,似夢境,又不是夢境。這種底色,也正是老子所說的“光而不耀”,由此產(chǎn)生了渺若煙云又空靈含蓄的水墨藝術(shù)。
多年前,受一個出版社朋友約稿,曾打算寫一部李清照的傳記。寫了一個開頭,從一個月夜開始的,月色里還有一叢綠竹,微風(fēng)里竹影婆娑。后來卻缺乏足夠的熱情,遂作罷。李清照,這個名字里,鑲嵌著一輪月亮。
明月照積雪,又冷,又亮。明月照大漠,空曠,渾茫。月色也有凜然的時候,不過,這并不是主要的。蘇東坡的詞句,“我欲乘風(fēng)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這應(yīng)該是我們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我們的精神境界,追求的是溫潤,而非高寒。積雪很快就會融化的,變成檐前的滴水聲,而大漠只是一種情調(diào),一種境界,是人世的邊塞,塞外荒寒正是為了映襯關(guān)內(nèi)的繁華。中國傳統(tǒng)的美學(xué)意象,主要還是“春江花月夜”。月色中有情感的傳遞和恒久的牽掛,“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日光是愛,月色是思。思,是一種濃而不烈的感情,唯其如此,才更能綿綿無盡,悠悠不斷。
中國人追求清涼之境,卻又能止于幽寂,與整個世界無間然,千江有水千江月,月色與流水,明亮而不刺眼,寧靜而不沉寂。清涼之境,也是佛教中國化之后的心境,禪宗之境。禪宗的靜,是靜謐,而不是靜寂,充滿了寧靜的生機。楊萬里的詩,“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禪宗就是那只長著透明翅膀的紅蜻蜓,渾身透著靜謐,但又隨時會輕盈地飛起來。生命和意識若是長久地靜在一處,便會失去靈動之氣,變呆。
在樂府民歌里,小兒女情思婉轉(zhuǎn)涌動,月色保持著應(yīng)有的明亮和安靜。這種情思脈脈不斷,盈盈似水,一直涌流進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里。
想到細雨,會想到柳色覆蓋的金陵。想到月色呢,則會想到秋風(fēng)吹拂的長安。月落長安,雨濕金陵。那風(fēng)中折柳送別的人在哪兒呢?那燈下拈針縫衣的人在哪兒呢?那月下舉杵搗衣的人在哪兒呢?一代一代的人,在急速流逝的歲月中老去,消失,泯滅無蹤,而月色依然。
月色中的桃花源,桃花滿枝,一朵朵紅著。露水落下來,連花朵中的枯枝都變潮濕了。犬吠,燈火,房屋里隱隱透出人的說話聲,還應(yīng)該有嬰兒的啼哭。真正的仙意隱藏在煙火紅塵之中,正如真正的佛境即是人境。桃花源里的月色,也是王摩詰輞川山中的月色。也許可以這樣說,東籬采菊的陶淵明如果被禪宗的露水浸潤,就會變成坐看云起的王摩詰。
唐詩宋詞里的月色,《老殘游記》里的月色,《紅樓夢》里的月色,《聊齋志異》里的月色,張愛玲小說里的月色。長河悠悠,月華如練。
《水滸傳》里可以不必有月色。但如果《西廂記》里沒有月色,張生和崔鶯鶯被禁止的感情,仍會一如既往地向前發(fā)展,只是,這種感情的底色,將會失去詩性的明麗純凈,變得昏暗渾濁。男女之間的艷情,在朦朧如幻的月色里生發(fā)進展,才能濃烈而不失含蓄,旖旎而不顯狎邪。《花間詞》里的作者,尤其明白這個道理。
月色中的虎嘯,有幾分神秘感。黑暗中的虎嘯,則只有冷冰冰的恐怖了。月黑殺人夜,風(fēng)高放火天。這是對人世界限的突破和毀滅。月色從中國人心靈中消失的時候,一片晦暗,往往天下就亂了。
路邊的槐花開了一陣子,開始落了。淡白隱綠的花朵,簌簌往下掉,地上已是厚厚的一層。國槐花小,堆積多了,就成陣勢了。槐葉稠密,密不透風(fēng),也不容易透雨。晚上偶爾落下一陣疏雨,并不影響散步。回來的時候,走在樹下,密葉間突然一縷蟬鳴,聲如裂帛,破空而來,倒讓人一驚。抬頭一看,云彩早已散去,一輪明月,靜靜懸在天空。
草 色
韋應(yīng)物有好句,“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
天地自然中,時刻有美好的事物發(fā)生和出現(xiàn),雖然我們沒有看見,但這一切卻依然與我們有關(guān),因為我們始終在,并沒有缺席。這里有一種人與萬物的交融和律動。在與不在,知或不知,這種萬物交融的感覺卻并沒有隔絕。古人的生命感覺向來是虛實相生的,遼闊而充實,具體而空茫。如今,我們已經(jīng)喪失了這種對于天地自然的感覺,所以,人生的幅度也變得狹小了。
清晨,微雨后的空氣多么清新,春草之色多么新鮮。川原悠悠無盡,草色綿綿無盡,那遠行的人,漸行漸遠,慢慢變成一個虛影,一個墨點,然后,消失在天際。而歸來的人呢,踏著青青草色,越來越近,身影清晰,由虛相變成了現(xiàn)實。仿佛這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無論你看見還是看不見,都是真實的,篤定的,不可懷疑的。
佛經(jīng)里的諸佛之所,寶相莊嚴,香花遍滿,七寶琉璃鋪地,然而,我卻更喜歡人間的青青草色、阡陌縱橫。我想,我終究是一個世俗之人,有塵俗之想。
讀《古詩十九首》,好像在讀整個悠遠的人世。這些詩里有一個廣大深遠的空間感,也有千年萬年的光陰徘徊。風(fēng)吹嘉樹,風(fēng)吹人世,古國那跌宕的心靈,對憂樂愛恨生死,由于過于執(zhí)著,還沒有想到超脫。即便對自己的人生想開了,也帶著一種自我安慰的調(diào)子。古國蒼蒼,川原茫茫,草色綿綿,相思不斷。盛夏,幾場大雨過后,北方的草色漲天,浩浩長風(fēng)中,綠得蕩氣回腸。
對我而言,江南是一種文化情結(jié),而不是一個地理概念。在我的文化想象中,古典的江南淡綠淺青,正是春草初生的顏色,哪怕冬天也是如此。這種情結(jié),也是一種文化鄉(xiāng)愁,但只適合懷想。它是由眾多的史書筆記和古典詩詞所塑造培育的。所以,當我說到江南,更多時候,只是一個文字里的江南,詩性的江南,逸筆草草的江南。南朝的江南芳草萋萋,煙雨迷離;唐宋的江南笙歌悠揚,月光如水;明清的江南呢,繁花似錦中,又似乎總是莫名其妙地透出一縷揮之不去的故國之思、遺民之恨。那夕陽芳草波光瀲滟的江南,時光陳舊,王孫未歸——也永遠不會再歸了……
我們這兒常見的草有蕭、艾、蒿、茅、薊、斷骨草、芨芨草、狗尾巴草、豬耳朵棵等。還有一種草,生命力和繁殖力極強,叫莎草。有一個詞牌名,就叫“踏莎行”。如果雨后赤足踩在莎草上,涼涼的,感覺尤好。樂府詩里有“蒿里”之詩,蒿草味道濃烈,有荒蠻之感。殘秋,草葉落盡,蒿草的梗株變紅,棵棵錚錚挺立,那種紅色極艷。
晨讀杜詩。杜甫流落秦州之時,生活極其困頓,當?shù)赜形挥讶耍娃鸥橹畬懺娨皇祝f此薤“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箸頭”。玉箸頭,是說薤根之白。薤有圓錐狀鱗莖,可食。自古衣食艱難,至今依然。一個偉大的詩人,其生活也只是尋常。或者說,尋常生活,更能成就一個詩人的偉大。陶淵明的生活,更是如此。生活的豐富,在于心靈的感受,而不僅僅在于肉體的經(jīng)歷。強烈的印象,可能會對心靈產(chǎn)生刺激,卻不一定能被心靈攝取和回味。而薤是菜,不是草。記得讀樂府詩《薤露》,“薤上露,何易晞”,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為這是一種北方地區(qū)密密叢生的野草。朝陽初升,葉上露珠滾滾,晶瑩閃爍,讓人想到惠特曼的詩集名——《草葉集》。
還是杜甫的詩句,“萬國兵前草木風(fēng)”,亂世的草,好高啊。
有一種命運遭遇叫花落溷藩,就是花瓣落到了廁所里,似乎比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更為不堪,而有一種文學(xué)之美則叫落花依草,娟然自媚。先秦諸子著作,《莊子》里有盛夏草木的氣息。春秋戰(zhàn)國,楚國給人一種草木莽莽的感覺。
深秋初冬,郊外漫步,我喜歡看那些荒草,有時也在上面坐一坐,躺一躺,看那藍得發(fā)硬的天空。幾場苦霜,天氣肅殺,荒草就變枯了。枯黃的草色,干凈而清爽,風(fēng)吹過來,草葉搖曳,這種色彩,也不再顯得跳脫。黃昏,天地靜悄悄的。殘陽濃紅,茅草長長的密葉靜靜伏著,沒有風(fēng),然而,草叢的傾伏狀態(tài),仍保存著某場大風(fēng)的“風(fēng)姿”和“風(fēng)勢”,仿佛這場風(fēng)還沒有刮遠,隨時就會回來。寂澀的草色,鉛華盡洗,最能讓人省思。
梅 意
吳偉業(yè)應(yīng)清廷之召,無奈出山,風(fēng)雪途中,寫詩寄意:“辜負故園梅樹好,南枝開放北枝寒。”此句意在言外,是象征,也是寫實。此時的梅樹,開的就是向南的枝條。即使是同一樹花,也有不同命運。吳偉業(yè),號梅村,詩稱“梅村體”,果然和梅有緣。他比錢謙益更有品節(jié)上的愧疚感。北宋滅亡,先失去半壁江山,衣冠猶存,南宋又延續(xù)了一百五十多年。南宋滅亡,雖是夷族入侵,但還是有一個緩沖的集體心理定式。明朝則是呼啦啦大廈傾,很快就倒了,南明沒支撐起來,文人的幻滅感和哀痛感更強烈深沉,江山易主,同體大悲。
這種悲,包含著絕望,整個人生存在的絕望,廣漠的九曲回腸的絕望。連頹廢都不是,頹廢還可以是精美的,是情感多于情緒的,是情感的有余而非不足。頹廢只能是感受性的。當頹廢超越于生活態(tài)度時,其實是可以變成一種細膩的美學(xué),一種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的。大悲痛,大絕望,便削發(fā)為僧。明亡后那些出家人,陳寅恪指出有政治意義在。他們不是放下這個世界才出家的,而是走投無路才出家的。像詩人陳子龍,拋不下九十老母,遁為僧。后欲結(jié)兵舉事,事泄被獲,便乘間投水而死。
梅花在南宋被賦予人格和情操上的新意,如繪畫里的折枝梅,折枝是江山的隱喻。在北宋則是審美上的歌詠,一種個人化的自我投射,比如那個梅妻鶴子的隱士林和靖。北宋惆悵,只有敏感而多情的人才會惆悵,比如晏小山、秦少游。惆悵是女性化的。惆悵是對人生的意猶未盡,其中有愛和不舍。而古典式的惆悵不是頹廢。現(xiàn)代的頹廢則情緒多于情感,是精神的局促不安。這樣自我世界便狹小了,容不下相反的事物。在一個大的格局中,相反的事物,并非矛盾和沖突,而是相互補充。在心靈的空間,同體而相反的兩翼更能扶搖直上九千里。
南宋則顯得冷瑟,有身世之感,比如姜白石,其詠梅詞,《暗香》《疏影》,我讀起來,美則美矣,但總感覺有一種隔,用張愛玲的比喻來說,就是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白手套上。好的作品應(yīng)該有肌膚之親般的實在和確鑿。范成大晚年于蘇州石湖玉雪坡植梅數(shù)百本,且修梅譜,稱梅為“天下尤物”,可謂推崇備至。范雖有宰輔之才,但其生命的幅度和北宋歐陽修諸人相比,畢竟小了許多,故而風(fēng)流不逮。就連辛棄疾這等豪健的雄杰,慷慨悲歌中也處處只見積郁難舒,當然不可能有蘇東坡的曠達。蘇東坡的曠達是對整個人生的超脫,所以是大的。
當生活的意義和目的,是索取而不是給予的時候,現(xiàn)在,我們能給我們生活中的事物賦予什么新意呢?山河大地,我們置身其中,既不能使其增色,又不能靜觀風(fēng)景。我們?nèi)狈κ挛锏睦斫饬ΑUf到底理解力也是一種生命力,它的深刻緣于生命的蓬勃和寬宏。理解力甚至是一種熱愛,但真正的熱愛不是一種占有,而是真誠的奉獻和給予。
而梅樹也真是一種神奇的樹。梅花開時,便只有花朵。梅花落了,才長出綠葉來。梅花的葉子很厚密、很粗澀。仿佛葉子是怕遮掩了花朵之美,故意謙遜地退避,讓花朵獨領(lǐng)風(fēng)騷的。
責任編輯 陳美者
- 福建文學(xué)的其它文章
- 江 水(外二首)
- 重溫經(jīng)典
- “將光明與歡樂帶到世上”
- 接骨
- 一灣江水流
- 野味與野趣